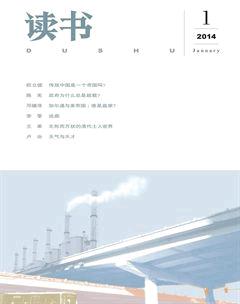王蒙的“中段”
赵一凡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王蒙飞抵乌鲁木齐,签售新书《这边风景》。次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又在伊宁市巴彦岱镇,举行“王蒙书屋”揭牌式,老王亲临致谢,维族乡亲也纷纷赶来道喜。我读这段新闻,正在考察途中。那天我驾车横穿巴丹吉林沙漠,当晚下榻额济纳宾馆。搜看新闻时,得知老王又回伊犁了。
查看新疆网,发现一则笑话。原来新书出版后,媒体揣测它尘封四十年的隐情。王蒙笑称:他在小说中找到了自己,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中段!回京后,老王寄来《这边风景》(以下简称《风景》) ,令我恍然:原来老王的中段落在这里!
二零一零年我发表《从鲁迅到王蒙》,试图说明:鲁王首尾相连,构成一个 “及远而反”的思想循环。而此一循环,早在鲁迅 《文化偏至论》(一九零九)中已被描述为一个“中西化合”之梦。鲁迅预测说:未来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大势,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而中国现代化功成之际,自当“外不后世界之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
我的评论有缺憾。首先我从青年王蒙说起,中间跳过二十四年,径直讨论他的《蝴蝶》。此处麻烦是:缺了二十四年,王蒙还是王蒙么?此人偏又一生多事,其狡黠思想轨迹,忽隐忽现。在我看来,老王特殊性有三:一、他在巴金去世后,已成为中国文学的最大存在,即声望最高,作品最多,经历最曲折。二、老王与诺奖无缘,窃以为与其红色履历有关:生为少共作家、文化部长,他与中共血肉相连,关系密切到登堂入室、名列中枢。我预测老王领奖之日,不仅打破陈规,也是中国终被西方承认的标记。届时,鲁迅的中西化合梦,就算大功告成了。三、澳门大学汪应果教授称:王蒙创作主题,即“反思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其反思强势来自其“革命主体身份,所以他最有资格,也最具深度”。此说中肯。二零零七年,老王在上海介绍《王蒙自传》,说他将完成“一个人的国家日记”!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过此人上千万字的作品,近八十年复杂经历,岂不构成一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其间老王左摇右摆,东倒西歪,却一直痴心不改,苦中作乐,丝丝入扣地记录下他的生命历程。所以,缺了王蒙的新疆记录,我将无法交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折。老王的中段,因而很重要,也很棘手。
《风景》开篇,就讲一九六二年“伊塔事件”。事件爆发背景,即中苏论战,两国交恶。那年中国遭遇天灾,苏联领事馆乘乱造谣。四月底,伊宁、塔城五万多人,蜂拥逃去苏联。一九六二年在北京,亦是多事之秋。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承认国民经济困难重重,诸如粮食紧张,供应短缺,财政亏空。中央被迫调整如下:精简城市人口三千万,压缩基建八十亿元,工业总产值减半。调整至六月,彭德怀递交八万言书,庐山上的政治钟摆,骤然从反左变成了反右。
王蒙的中段,竟有这般山呼海啸的时代背景!若要追根溯源,只怕要从《史记》、《汉书》说起。而我搜罗的史料,不仅残破,而且断裂。西域文献自古稀缺,原因在于中原人去西域,素以军士、刑徒、垦丁为主,伴随少许商贾、犯官、随军幕僚,其文化水平有限。当然有例外,如隋尚书裴矩、唐高僧玄奘、清大学士纪昀。其中深入西域,又写出长篇巨制者,王蒙堪为古今第一。
老王成为第一,实属造化弄人。身为右派,他自请下放新疆。《风景》记录下一幅“刻骨铭心的地图”:下放干部尹中信,乘火车走京汉线,从华北平原,到黄土高原。汽笛长鸣,烟尘滚滚,伴他走过西安古塔、兰州铁桥。其后改走兰新线,穿越乌鞘岭的盘山路,嘉峪关的古长城。戈壁黑风,祁连白雪,护送他来到乌鲁木齐。偏偏小尹不愿留省城,于是又搭长途车,逶迤走过昌吉、石河子,乌苏、奎屯。三天后抵达终点,即王蒙下放的伊宁县。
二零一零年我驾车走遍新疆。当时最大遗憾,即国人对于西域,迄今一知半解。途中我携带两本王蒙文集,其中有散文、诗歌、短篇。应该说,老王写起新疆来,情感充沛,题材丰富,无人能比。可在我目中,新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一向缺少与之匹配的弘大文体。而这种文体,只能是史诗。
所谓史诗,首先是指荷马《奥德赛》、弥尔顿《失乐园》。依照亚里士多德定义,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创世记”故事:它源自神话,又突破神话;它以英雄为中心,描述艰苦旅程,异域风情;它以长篇叙事,面向民众,口口相传。
“五四”前后,中国学者一片惊呼:吾国无史诗!梁启超指“泰西诗动辄数万言, 中国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不过二三千言”。王国维悲叹中国没有荷马那样“代表国民精神”的文豪。胡适沉吟道:“史诗在中国来的迟,世界文学史上少见。它的产生不在文人阶级,而在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民间。”
怅然若失中,王蒙寄来《风景》,让我大喜过望:老王还有七十万字的新疆长篇!书中说古道今,排山倒海,无奇不有。请看老王自诩:“小说中有生活、有真情、有细节,有各种人性的集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写到了;国际国内斗争,我写到了;吃喝拉撒睡我写到了,就连洞房,我也钻进去写了。”
我在书中看见啥?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民俗画卷,一卷王洛宾的《西部情歌集》,一部穿越时空国界的边疆史话。其中最大难点,是作者“以右派身份,写左派小说”。据王蒙自述,一九七四年他从新疆文联去“五七干校”,荣任炊事班班副。突然间蠢蠢欲动,要写长篇了!此际王蒙人到中年,满腹经纶,灰头土脸。他在妻子鼓励下,发誓要写长篇,惹祸也要写!岂知一九七九年脱稿后,世风大变,他被迫藏匿书稿,直到二零一二年,才又被家人发现。
看来“吾国无史诗”说,命题沉重。王蒙执意写史诗,险险乎成了废纸。
中国到底有无史诗?看来关键首在文体,次在哲理。所以我由文体入手,步步设问如下。
问题一:老王落难新疆,何以如此多产?他坦言:“新疆是我的乐园,即使在苦难岁月里也罢。新疆是我的亲人,即使人际关系受到扭曲也罢。新疆是一幅最绚烂最悠长的画卷,新疆是一个充满幻想和野性的地方。”依照汉人俗见,老王这是天目开张了。所以他写了短篇,又写长篇,死活要完成一幅“最绚烂最悠长的画卷”!王蒙的新疆朋友维族作家阿拉提表示:“老王在困难日子里也没放弃自己,他学习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新疆人民选择了他,让他变成一个普通活命人。”老天有眼,安拉圣明,王蒙在伊犁乡下,变回普通人啦!他若不开心,朋友就劝他喝酒:“老王啊你是作家,真主会支持你。一个国家没有皇帝不行,没有诗人作家更不行。”王蒙于是明白:“聚餐是一所学校,说笑是教养男人的方式。”
问题二:史诗展示辽阔地域,炫耀异域风情。老王走运,一头扎进新疆的后花园:那里雪山森林环绕,激流奔腾而下。天山脚下,牛羊满坡。果子沟里,香气袭人。唯独气候无常:一时大雪纷飞,一时风和日丽,让人领悟唐诗里的惊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伊犁绿洲上,住着十几个民族。对于王蒙,这又是天赐良机!他说新疆的民族分布丰富多彩、闹热红火!《风景》写了十个民族,即汉、回、维、蒙古、锡伯、塔塔尔、哈萨克、俄罗斯、乌兹别克。他们个个有名有姓,还有一个五代词人李珣,老王说他祖上来自波斯。
西域歌舞,妙曼轻柔。唐代诗人岑参,当年初识胡旋女,不由得神魂颠倒:“凉州七里十万家,胡儿半解弹琵琶。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未之见。”可在王蒙小说中,漂亮女孩随处可见,她们巧笑倩会,美目顾盼。塔塔尔族美妇人莱依拉,更是国色天香!老王加注曰:莱依拉与英语同,是百合花之意。
纪晓岚在迪化,一度垂青西域民妇:“蓝帐青裙乌角簪,半操北语半南音,秋来多少流人妇,侨住城南小巷深。”楚楚动人开了头,却没有下文。又写乌鲁木齐某同知查案,“破门而入,见俩情侣,裸体拥抱而死”,接着是一段酸词:鸳鸯毕竟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
王蒙不然:他写边疆人的恋爱婚姻,有头有尾,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小说第十一章描述维族美女乌尔汗,在俱乐部里翩翩起舞,如痴如醉:“这个十五岁的姑娘,出挑得明光耀眼。她在跳《迎春舞》,舞曲出自《十二木卡姆》:它让乌尔汗轻盈起舞,越来越激扬,流露解放后的春色满怀,又在欢乐中表现感恩和祈求。”再往下看,这妮子会让你牵肠挂肚!
问题三:史诗作者擅长说唱。王蒙呢?不但维语说得好,羊肉吃得香,还喜欢赶着马车,领略伊犁人的夜半歌声。朋友们确认:老王酷爱维族情歌《黑眼睛》:“麦西莱甫晚会热闹非凡。乐手沙依提江大叔为他演唱时,王蒙静静地听着,双眼噙满泪水。”中国西域史上,何曾有过善解风情至此的中原文人?李白出生碎叶,可他不会像王蒙那样,“一讲维语就春风得意”。王蒙写《风景》,是先用维语构思,再译成汉语!可见他的情感思维,与百姓水乳交融。老王踏歌而行,如诉如泣,讲述各民族悲喜故事,这难道不是史诗么?
史诗旧案,曾经陈寅恪一招点破,学生我斗胆议论了。以我拙见,《风景》虽有西洋史诗皮相,也混杂苏联小说血脉。其中《静静的顿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作为二十世纪革命史诗,无疑让王蒙刻骨铭心:对于这位少共作家,“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远离莫斯科》大开大合,上下两卷,《风景》与之前呼后应、旗鼓相当。阿扎耶夫描述一群首都青年高唱战歌,前去开发远东。王蒙豪情满怀,奔赴新疆,几乎如出一辙。再看肖洛霍夫少年得志,二十岁写完《顿河》第一部。面对奔腾的伊犁河(比顿河不差) ,剽悍的哈萨克(哥萨克又如何) ,王蒙岂肯低人一头?
自鲁迅起,中国作家对于舶来洋货,顺手拿来,见怪不怪。所以王蒙尝试写一部原汁原味的革命史诗,本是好事。无奈中国革命大浪迭起,冲波逆折,几度跌入深渊,令人不堪回首。小说中一系列事件,前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后有大跃进、人民公社、社教运动。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值得大动干戈么?可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目中,它们谱写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王蒙追忆工作队文化,悚然动容:自鸦片战争以来,能将偌大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改变一盘散沙状况的,正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风景》 ,454页) ,他加按语说:“工作队下乡,这是一个本事,一个成功经验。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国民政府一旦离开城市,就失去影响力、控制力。历朝历代,能像共产党这样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贯彻到村村户户的,再无先例。”
王蒙好学,无书不读。他曾邀我去开会,商讨中国作家学者化,又请 我修改英文稿,以便他赶去欧洲作家大会发言。这让我刮目相看,视他为一架先进观测仪:从中我可以把握中国改革的温度、速度,及其中西化合的程度、限度。近来老王学问大进,开始涉猎美国汉学,让我有些手忙脚乱。
费正清与中国有缘。他是我的研究重点,也与《风景》密切相关。早在抗战中,费氏已结识中共领袖周恩来,参观过八路军根据地。其时他在重庆分析战况,一再向华盛顿发报,称“中共不是苏联傀儡,中国革命极富本土性,具备强大内生动力”。抗战胜利,国共相争,他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共终将胜出。原因在于中共一大法宝:群众路线。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
费正清历时半个世纪,写成《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至晚年,他又调集欧美大腕,编撰《新中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费氏有一评语,可注释王蒙小说的复杂性:“中国人依据他们承袭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造就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其中中外因素彼此交织,达成共识。但千万别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
至于《风景》中的极左政治,费氏亦有冷静分析:“中国文化优越,中国人因此获得一种深藏不露的优越感。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化也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改变更多,这是由于它停滞得太久了。结果便有一股惰性遏制力,让中国革命带有痉挛性,时而从内部抑制,时而迸发出破坏性。”
费教授一九九一年去世,未能读到《风景》。王蒙满头华发,仍在《苏联祭》中痛说家史:“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在这块广袤土地上进行的实验,个中的经验教训,爱恨情仇,都会长久地留在史册上。”
至于新中国文学,王蒙赞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称许孙犁的《白洋淀》,说它们充满乡土气息,反映深刻变革。可它们能否经受历史考验?老王分析:中国自古推崇文以载道,视文章为经国大业,把小说当成政治工具,结果养成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倾向”。
“五四”学者痛批传统文学,指其迂腐陈旧,缺少反思启迪。荷马史诗里,能有多少哲理思辨?请看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奥德赛》讲述俄底修斯率部返乡的经历。阿多诺说:俄氏为了返乡,不断与命运搏斗,最终否定了自我。途经塞壬岛时,他命水手用蜜蜡封耳。女妖歌声令人欲仙欲死,可是众水手听不见,齐心划船远去。塞壬的神秘世界就此崩溃,西方英雄昂首步入文明!这说明俄氏通过自控,获得主体意识。身为启蒙英雄,他又彰显了工具理性。
难道中国文学,一无反思批判?纪昀皮里阳秋、装神弄鬼,鲁迅却道“他是不信狐鬼的,不过对愚民,不得不以神道设教”。又说老纪在乾隆法纪最严时,竟敢攻击礼法,“以当时眼光看,算得很有魄力”。再看陈寅恪。先生中年饱学,“于弹词复有所心会。衰年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遂草成此文”。
我辈愚钝,不明白先生偌大学问,干吗看重陈端生、柳如是?后读冯友兰、周一良纪念文,始有觉悟,陈寅恪革新近代中国史,掌握百科全书式的丰富资料,远超古人。先生又长于贯通,巧于补缀,因能化腐朽为神奇。
一九五七年,先生在中大讲课,偶尔透露心迹:“我之所以用唐诗证唐史,实因唐自武宗后,历史记录多有错误,复杂难辨。但唐诗中保留了大量实录,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此一将诗补史、史诗合一的新方法,让先生在乱麻一团的明清诗词笔记堆里,赫然发现地火穿行的近代史诗!其文言格式,掩不住风流放诞的靓丽人生,其冗长叙事,饱含着毫无拘牵的自由梦想。
中国文化优越性,造就一个傲慢保守的自闭系统:它内有缜密抑制手段(毁禁图书,修编国典) ,外有狂躁冲击破坏(农民起义、政治运动)。费正清为此扼腕道:中国革命自有一种痉挛性,它反复发作,伤及国体。老王苦等四十年,直到今年才推出“考古文本”。这说明什么?痉挛过去了。王蒙的侥幸,让我如释重负:中国文化系统,终于开始宽容了!再看纪昀与王蒙,他俩同为当朝一品,都以犯官身份流放新疆。老纪忧谗畏讥一生,硬是没有老王的运气!
如何让荒诞年月再现,于后世有所交代?老王在《风景》每章之后,补写小说人语,自称是模仿司马迁“太史公曰”、蒲松龄“异史氏曰”。窃以为,他以七十九岁的老辣眼光,反思三十九岁的创作,恰是一种史诗对话!其中有白头宫女的唠叨,也暗藏“作家变学者”的欲望。吊诡之处,在于他能否借力司马迁,将《风景》变回一部史诗?对此我不敢妄断,笔录几段如下,敬请行家过目。
关于革命浪漫:第三十五章写三个女人一台戏。雪林古丽是村里的美人儿,可她婚姻不幸,郁郁寡欢。队长妻子米琪尔婉,时常宽慰这个苦命姑娘。她俩共有一个闺蜜,那是来自湖南的女农技员杨辉。听说工作队要进村,三人一边做晚饭,一边商议如何迎接工作队,又憧憬今后的好日子。小说人语:那时共和国多么年轻,那时年轻人更浪漫,更会发烧,更容易上当(454页) 。
关于阶级斗争:小说中除了地主恶霸,还有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叛逃未遂的科长麦素木,暗藏的特务赖提甫。小说人语: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如能倾听生活,而不执著于基本教义(原教旨),人们就会生活得舒服一些。要求干净彻底地消灭对手,这样的思路略显修辞化了。共产党重视文学,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习惯于以诗治国(443页) 。
关于极左思潮:第四十一章写工作队员章洋,与七队队长伊力哈穆发生冲突。小说人语:章洋的执拗,是重要小说元素,奥赛罗、项羽、李自成都有这种性格,传统文化包含一种自毁潜程序。章洋具备阶级斗争的理论与激情,追求斗争的修辞化、表演化,结果是没事找事,恶性循环,越来越左(521页) 。
《伟大的中国革命》结尾,费正清出示历史X光片:其一,西方人梦想改变中国,给它套上洋马鞍。他们两次对中国文化发起冲击,自由主义一次,马克思主义一次,但中国迄今保持大一统的文化连续性!其二,解放后出现两轮激烈循环:大跃进与“文革”,费氏戏称是“民粹派痉挛”。每次痉挛后,都会进行系统修复,重提经济建设。这就造成中国的革命两极化:左右摇摆,新旧激荡,复古与西化争执不下。费氏仰天长啸:不知何时消停,不再循环?
呼应老费,老王在《风景》后记中表示:“许多事情都改变了,但生活依旧,人性依旧,拉面条和奶茶仍然甘美,亭亭玉立的后人仍然亭亭玉立。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而是生活,是人性,是鲜活的生命。”
二零零八年老王蒙做客凤凰卫视。面对尖锐提问,他理直气壮道:我若写诗,就是“我告诉你,我们相信”!面对新一轮左右相争,老王主张渐进变革。其理由是:“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太多激进主义的亏。现在又有急切情绪,这与以往的激进一脉相承,很危险!”
王蒙早年是右派,中段他形左实右,如今孰左孰右?铁凝说她认识两个王蒙,一个是退休高官,一个是讲维语的老王。毕淑敏读王蒙小说,发现他一直厕身于政治与生活之间,搅和稀泥。查建英进而推断:王蒙是主流温和派,他体现中庸之道。我的说法更传统一些:王顾左右而执中。
当年陈寅恪写完《钱柳姻缘诗释证稿》,留下一首《稿竟说偈》: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得成此书,乃天所赐……今逢老王八十大寿,谨以此诗庆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