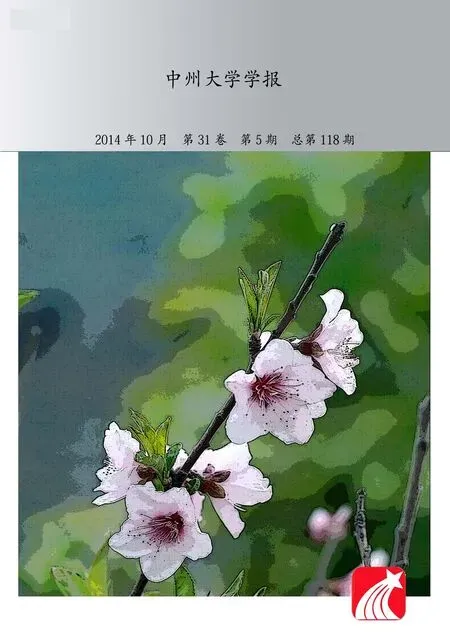论清王朝涉藏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
——以青海藏区为范围的分析
冯志伟,闫文博
(1.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法学系,天津 300382;2.河北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 300000)
青海藏区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地处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清王朝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统治是由间接到直接,并逐渐增强的,即随着清王朝政权的稳定和国力的增强,对藏区的控制力也不断得到加强。在既有成果中,学界对藏族内部的刑事案件多有涉及,但却极少关注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刑事案件处理,更无对涉藏刑事案件司法管辖的细致分析。涉藏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需要首先明确“涉藏”“刑事案件”的含义,并进一步结合清代司法行政合一的特点,把握清王朝青海藏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才能围绕青海藏区的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因素,分析其司法管辖方面的自身特点。
一、涉藏刑事案件
涉藏刑事案件,主要指藏民与汉民、蒙民、满民以及其他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刑事案件。在研究司法管辖权之前,“涉藏”的含义必须加以明确,否则无法进一步展开探讨。
从广义上看,“涉藏”的概念,与藏区、藏族密切相关。从地理区域角度看,既包括西藏地区,也包括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藏族聚居区。清代中国境内的藏族多分布于青藏高原上,从现代角度看,主要是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一行政区划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有其地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元代以来历代王朝对藏族地区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结果。[1]
从行政区划角度看,涉藏必是涉及这些藏族地区。但从狭义的角度看,“涉”指“牵涉、涉及、关联”等意思,也可以用来分析此问题。如同“涉外”是指在公务上涉及外国,及与外国有关系的涉外单位。若以这层意思来谈“涉藏”,则应该是公务上涉及藏族,及与藏族有关系的涉藏部门。具体到“涉藏刑事案件”,则应该是涉及藏族及与刑事案件处理有关系的部门,而从“涉藏”的角度来分析清王朝涉及藏族刑事案件的处置过程,应该能够成立。其理由如下:
从民族的角度看,藏族不仅仅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及藏族聚集区,在全国各地或多或少都有居住,而其他民族在西藏自治区及藏族聚集区也有居住。“从清王朝涉及藏族的刑事案件来看,有的发生在京师,也有的发生在内地,还有的发生在民族杂处而交往贸易地区,而更多的是在各民族交界的地方。至于发生在西藏地区腹地的案件,一般的刑事案件,清王朝原则上不予审理,只有事涉重大,理藩院和驻藏大臣才参与审理。基于此,涉藏刑事案件从民族的角度,不牵扯藏族本民族内部的刑事案件,只有涉及到其他民族的刑事案件,才能够称为涉藏刑事案件。”[2]137-138
既然涉藏刑事案件是指涉及藏族与其他民族间发生的刑事案件,则涉藏刑事案件研究就应该审视发生在藏民与汉民、藏民与蒙民、藏民与满民、藏民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刑事案件。可以说,“清代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既牵涉到藏区的习惯法、清代的藏区立法和司法审判制度,又包括清代对涉藏刑事、反叛、宗教等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
此外,刑事案件的定性及案例选择的标准,也应该予以明确。《大清律例》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为7律,分为30门436条,除了名例律46条为总则之外,涉及的罪名有390种,均为刑事罪名。人们习惯称的户婚、田土、钱债等细事,实际上也是刑事案件,只不过这类罪行,在州县官自理的范围内,有学者将之目为民事案件,实际上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引用律例裁断的案件,都是刑事案件。
具体到涉藏刑事案件而言,390种罪名都有可能出现,若是以案发率来看,除了户婚、田土、钱债等细事之外,当属人命、贼盗、斗殴、诈伪、犯奸等为多。其中贼盗28条,涉及谋反大逆、谋叛、造妖书妖言、强盗、劫囚、白昼抢夺等恶性犯罪。基于涉藏刑事案件的处理特点,案例选择以人命、贼盗、斗殴以及户婚、田土、钱债等为主,同时也关注谋反、大逆、谋叛案件。同时,由于藏区政教合一制度根深蒂固,因此,也会选择涉及宗教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析。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将“涉藏刑事案件”定位为:以分析藏民与汉民、藏民与蒙民、藏民与满民、藏民与其他民族之间发生的刑事案件为重点,关注藏族与汉、满、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员之间的冲突解决,分析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以清王朝官方处置的案件为主,从法律和政治层面解析案件处理背后的政治理念,以期对现代民族关系的和谐提供历史的启示。[2]138
二、涉藏刑事案件处理的司法行政体制
由于清代的司法行政是一个整体,青海地方的司法行政体制必然会受到中央的影响和制约。《圣武记》中说:“本朝开国初,首抚固始汗,以通西藏,兼捍甘、凉、湟、洮诸边。故虽以准夷之猖獗终不敢越西陲而犯青海。”[3]在王朝施政的影响下,青海、蒙古实现了由外藩到近藩的转变。在与清王朝关系上,也由羁縻变为臣属。然而,清王朝对于青海内部事务的管理,却仍然严重依赖各蒙古贵族。可以说,从清王朝入主中原到康熙末年,清王朝对青海的统治形式,基本上是依赖于青海八台吉的间接统治。而就青海地区本身来看,各台吉统治过程中,建立起各自的世袭领地,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并依此维持对封地的管理①,其在领地上的统治,更接近于“自治”。
经过多年的发展,清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断加强,并一直谋求对藏区的直接、全面和有效的施政。雍正初年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后,清王朝找到了推行青海地区改革的契机,意在实现全面建政施治。年羹尧的《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奏折,得到清廷核准,遂成为治理以青海为中心的广大藏区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两个法律文件涉及蒙、藏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多个方面,其批准生效拉开了清王朝在青海全面施政的序幕。
青海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农牧分治,二制并行”上,即根据农牧区的不同情况分别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和“西宁府”为主的管理机构。对青海乃至甘肃、四川部分地区统治和管理均依托这一体制,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重点分析。
答:我理解一个女儿的心情,你妈妈64岁,身体多病,尤其是尿中有隐血、双肾结石,应当去医院检查,对应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从补养的角度,我认为,睡觉不好,会影响疾病的治疗和身体康复,应当服用补氧胶丸和绞股蓝调节睡眠。关于她的皮肤问题,系由过敏反应引起,建议服用矿元素和麦绿素,矿元素也可外涂于皮肤患处,可止痒。
1.西宁办事大臣及其体制
青海地区存在广大牧区且人烟稀少,蒙藏民族多逐水草而居,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内地。考虑到这种情况,清王朝在施政时专门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将纯牧业区作为特殊行政区域,进行特别管理。西宁办事大臣,全称为“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最初是清廷为了完成平叛后的善后工作而设立的专门人员。雍正二年(1724),清廷委派鄂赖赴西宁,“办理蒙古事务”[4]。雍正三年(1725),正式任命副都统达鼐为“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宜,这一职官遂成为定制(乾隆元年后也称为“西宁办事大臣”)②。最初,西宁办事大臣的辖区主要是青海蒙古三十旗和玉树四十族的游牧之地。乾隆五十六年(1791),循化及贵德两厅所属的76个“熟户”部落和77个“生番”部落也归由西宁办事大臣调遣[5]14。嘉庆十一年(1806),西宁镇、道以下官员也归入西宁办事大臣兼辖节制[5]21。上述蒙藏部落辖区的一切政教事务均由西宁办事大臣总管。具体而言,主要包括蒙古王公及札萨克的封爵承袭,藏族千百户头人的任免,各大寺院活佛转世事宜;管理、控制蒙藏各旗、部落的茶粮贸易;稽查各旗、部落的田亩、牲畜、户口;会同驻藏办事大臣、四川督抚及陕甘总督协调处置有关青藏、青川和甘青之间的有关事宜;管理蒙藏两族之间的各种纠纷和命盗案件;统帅军队,定期督查和主持会盟等。
为了加强对蒙古的统治,达到“众建以分其势”的目的,清王朝以满族原有的八旗组织为形式,依托“鄂托克”“爱马克”等蒙古社会组织,通过封爵、封地等手段,在蒙古地区推行具有经济和政治等多种属性的盟旗制度。雍正三年(1725),清廷在青海适用盟旗制度,将青海蒙古五部编为29旗。这些札萨克“或远或近,皆在青海之四面联络住牧”[6],旗长称为扎萨克,由清廷在有功蒙古王公中任命,综揽旗内的军民司法诸权。札萨克以下设管旗章京一人,承札萨克之命,统管一旗之事。在对青海牧区藏族的管理体制上,则采用了千百户制度这一延续几百年的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千百户制度的实质与土司制度类似,是以千户、百户等官吏为主体的一种藏族基层管理制度。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之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强对青海藏族的管理,结合青海藏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情况,将牧区藏族社会存在了数百年的千百户制度予以借鉴并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了一种在青海牧区藏族社会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雍正三年(1725),就如何“设立条目,酌定额赋,安集番民等事”这一问题,川陕总督岳钟琪细加筹划,将方案上奏朝廷,主要内容是添设千百户,清查户口及额定赋税。岳钟琪认为:“其不产五谷,无可耕种者”,“此种部落与切近内地者不同,自应就其原有番目给予土千、百户职衔,颁发号纸,令其管束。至于纳粮贡马,近州县卫所者归州县卫所,近营汛者归营汛”[7]。清王朝采纳此建议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生番”“熟番”和“野番”的不同概念及相异的管理方法:熟番以农业生产为主,清廷的管理方式与汉、回族接近,要求缴纳贡粮,但田赋量较轻;生番主要从事畜牧业,清廷设置千百户进行管理,主要缴纳贡马银;野番由于游牧无固定地域,清廷对其管理程度不高。
2.西宁府及其体制
对于纯牧区以外,青海东部广大的农业和半农半牧地区,清王朝采取的是与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体系,将该地行政事务分别交给府、州、县(厅)等各级官府管理。清初在青海东部地区“画土分疆,多沿用明朝”[8],因此,明朝的卫所制度得到了沿用,在以上地区最初主要由西宁卫统辖。清王朝在定鼎中原之初于此地继续实行卫所制度,主要出于稳定边疆,提供兵员,确保王朝疆域等军事方面的考虑。随着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统治能力的加强,原来的卫所制度也逐渐被统一的行政体制所取代。罗布藏丹津叛乱为清王朝在青海的施政提供了有利时机。
雍正初年,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之后,针对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生产方式等特点,清王朝结合内地行政体制,对青海地区行政建制进行了变革。雍正三年(1725),青海和甘肃的行政机构出现了较大调整:升改西宁卫为西宁府(治今西宁),下辖西宁县(治今西宁市)和碾伯县(治今青海乐都碾伯镇,由所改置);添置大通卫(治今青海门源),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大通卫为大通县(治今青海大通城关镇);添置贵德所(治今贵德,原名归德所,先后隶河州卫、临洮府,乾隆三年改隶西宁府),乾隆五十七年(1761),改为贵德厅,设抚番同知;仍设西宁抚治道,并迁西宁通判常驻盐池(治今青海湖西南盐池);乾隆九年(1744),又增设巴燕戎格厅(治今青海化隆),置通判;乾隆二十七年(1762),移河州同知于循化营,设循化厅(治今甘肃循化),隶兰州府,道光三年(1823)又改属西宁府;道光九年(1829),特设丹噶尔厅,将原西宁县派驻丹噶尔主簿,升格为抚边同知,隶属西宁府。经过行政建制的调整完善,西宁府最终辖三县四厅,辖境包括东部农业区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大部分藏区。
三、涉藏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划分
清王朝在对青海藏区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建制改革和职官设置充分体现了“从俗而治,从宜而治”的政治理念。清代统治者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治理藏区只有在尊重藏族地区原有的行政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社会组织形式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统治措施,建立统治机构,才能实现中央政权的一统天下。与行政建制的划分一样,清王朝在司法管辖方面,并未一味套用内地的司法行政体制,也按照“农牧分治”的原则进行了区分。具体而言,清王朝将藏族称为“番子”“番众”③,而根据藏族的汉化程度以及与官府之间的关系,又将其分为“生番”“熟番”。这种划分便利了管理,但“生番”“熟番”的概念,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诠释:“熟番”,确切地说,应当是聚居于城镇、营汛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生番”,则是指聚居区远离城镇、营汛,主要以游牧为生的藏族部落。由于“生番”“熟番”的社会组织和结构的不同,清王朝的行政管理方式也不同,使司法管辖权的行使部门、行使方式等产生了地域上的差异。因此,结合青海藏区的行政建制,按照掌握司法管辖方式和权限的不同,在此将司法管辖类型划分为两种:对“熟番”司法管辖、对“生番”司法管辖。
1.对“熟番”司法管辖权
“熟番”主要聚居于城镇、营汛或附近,清王朝一般将他们纳入到地方政权的统治和管理范围。他们的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特点,能够符合清王朝地方政权统一管理的要求:第一,这些地区的藏族群体主要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生产,并与蒙、汉、回、撒拉等民族杂居,其原有部落的血缘关系逐渐为地缘关系所取代。不仅许多族(部落)、堡寨的名称发生了变化,而且其原有部落结构以及部落具有的生产、军事、行政三位一体的职能也不复存在。经过此番转变,藏族部落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地方政权下的“编户”,能够同其他民族一样向官府纳税,接受官府的管理。第二,有些藏族部落,虽然保留了“土流参治”的行政体制,设有土司、土千等各级土官,但清朝地方流官、营汛力量的增强,削弱了土官的职权,打破了土官“统领部落”的绝对权力。最终,土官也融入地方官之中,统一听从朝廷的调遣。第三,在民族融合的社会变迁中,其意识形态、文化也多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虽然他们仍然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但有逐渐融入汉族的趋势。[9]这些因素的单独或共同作用,保证了清王朝沿用内地治理经验治理青海藏区的有效性。
从青海藏区的行政建制来看,实施地方政权管辖的主要是西宁府及所辖三县四厅。这些地方政权对案件的受理和审判与内地一致,即均依据《大清律例》和有关法律进行审判。显然,清王朝对这些藏族的司法管辖也适用内地法律的司法管辖的规定,即县、府、司、院分别具有一定的管辖权。在这种行政体制之下,青海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发生的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刑事案件,也均须受到清王朝统一律法的约束。各级官府必须严格按照清王朝统一律法规定的内容执行。例如,“一般人到官府投诉,称之为‘告’‘控告’‘首告’‘举告’。而重大刑事案件还需要呈报,即相关的责任人必须协同当事人,或直接到官府报案,称为‘报’‘呈报’‘首报’‘举报’。此外,还有自首与投首。之后有受理与缉捕、申报与审理、拟罪与执行等程序。”[2]143虽然案件审理过程中,地方官会结合民族地方的特点,在法律适用、定罪量刑等方面进行适当变通,但在司法管辖权方面与内地大致相同。
2.对“生番”司法管辖权
“生番”大多为居于离城镇、营汛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部落,大致相当于清代所称之“生番”或“野番”。在青海藏区,主要包括黄河南面的贵德、循化之“生、野番”部落及后期形成的“环海八族”,青海玉树四十族,洮河流域卓尼杨土司、昝土司等藏族部落。这些地区的藏族主要以游牧为生,其社会组织,基本上沿袭了吐蕃部落的特征:组成一个大的部落的每一个基层部落或组织,多按血缘关系,由同一氏族、族姓的群体组成。部落兼有生产、行政和军事的职能。由于这些部落远离地方政权所在地,且游徙无常,难以控制,强制性地推行内地的统治方式,只能会造成对边疆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因此,为了加强管理,清王朝也采取了明代“土流参设”“以流统土”的措施。对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划分,也体现了这种“从俗从宜”的思想。按照涉案民族及案件性质,清王朝将案件分成了藏族之间、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案件两种,并有针对性地确立了对这两类案件不同的司法管辖权。
藏族与藏族之间发生的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发生在藏族和藏族之间的刑民事案件,由于涉案双方可能同属一个小部落或者分属不同的小部落,案件的管辖和处理一般按照藏区部落管辖规定处理。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清王朝采取了“农牧分治”的办法,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适用土司制度管理,牧业区适用千百户制度。西宁办事大臣管辖的河南贵德、循化之“生、野番”部落、青海“环海八族”、玉树四十族等由于处于牧业区,原始部落制度保留完整,因此,雍正四年(1726)后,清王朝在这些地区实行千百户制度。藏族与藏族之间的案件,由于每一级土官只能调处其辖区内的纠纷,就按照土官的权限分别进行管辖。这种案件如果发生在同一部落之中,则由百长或百户管辖;如果发生在平行部落之间的案件,则由他们的共同上一级首领或行政官员进行处理。在这些藏族部落中,西宁办事大臣衙门总管各千百户,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要进行处罚,对境内发生的藏族之间的重大刑事案件要及时进行管辖和审判④,而一般的刑事案件的处理则一般由各部落中的千百户负责。
洮河流域卓尼杨土司、昝土司管辖范围或者处于农业区,或者处于半农半牧区。为方便地区管理,清王朝多授予该地土司以武官中的指挥职衔,并分别在土司下设立一定数量的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土官。土司也有自己的一套衙门组织。在这种相对健全的层级管理体制下,藏民之间的刑事案件,一般向各旗或掌尕头人起诉,由头人进行调解或审判。凡是土司辖境发生的重大案件,或者头人无法解决的纠纷,则由土司衙门管辖,由其进行审判,这就与牧区的管辖类似。
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地区,行政和司法体制与以上两种类型类似,但也略有不同。在这种体制中,活佛既是宗教领袖,同时也因寺院对地方经济命脉的控制,而使其成为地区具有实际控制地位的行政首领。这种“政教合一”建立在一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内,是“一种与地方基层政治组织并存的具有自治性质的区域性政治组织”[10]。这些政教合一体制中,大多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组织形式。寺院内部组织以活佛为中心,成立教务会议,由总法台、总僧官、财务长、总经头、管理长、管家及秘书组成僧职系统,其下设管理僧人的六大札仓,并设立监狱、法庭等机构。寺院通过这套组织形式对寺院及其属民部落的宗教、行政事务进行管理。对于所属之庄户和藏族部落,寺院没有流官、土官的设置,而是由活佛派出其全权代表进行管理;对于寺院所属之分寺,则由寺院派出活佛的代表,并通过分寺的各级僧官处理寺院事务。藏族部落的刑事案件,先向部落的头人请求调解,部落头人调解不成的,则上交郭哇处理。如果案件重大复杂,或郭哇无法决断,则上交寺院议事处进行审理。在存在大寺院的青海、甘肃地区,一般都采用这种模式进行司法管辖。
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刑事案件可能发生在藏族区域中,也可能发生在藏族区域外,但不管发生在何处,均适用《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及其他相关法律中的处理原则,即在民族杂处地区发生的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刑事案件,多由官府管辖,并负责调解和处理。各种地方志史料中对此多有记载。例如,《循化志》中说:“查乾隆四十三年理藩院议准”,“嗣后遇番民抢窃蒙古及番蒙伙同抢窃之案,事主随时具报各札萨克转报青海衙门查实,即令西宁镇伤营员前往查办,追赃给领,随时完结”。[7]303乾隆五十六年,皇帝在上谕中也曾说,此后,“番子与汉民交涉命盗案件亦归地方官办理外,遇有番子抢掠蒙古之案”[11],均由西宁办事大臣衙门照例办理。此外,“甘肃边民与青海蒙古交涉者,各州县报西宁大臣派员会审,由西宁大臣,陕甘总督复核。”[12]可见,藏族与汉、蒙、回等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刑事案件,均由官府按《大清律例》等法律进行处理,有时为方便查明案情,或者考虑到民族习惯法等特殊因素,也会由分管涉案双方的行政长官会同审理。对于藏区发生的藏民反叛的案件,清王朝首先责令地方官员派兵弹压,必要时动用中央军队进行平叛,而在叛乱平息后的善后事宜中,重要的一项便是要求地方官员迅速拘捕缉拿相关人犯,并对其进行审判。
四、结束语
总之,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涉及案件的处理,而且关乎王朝的边疆稳定。涉藏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又由于其主要管辖藏族和其他民族间的刑事案件,又使得其具有了民族和谐的深层次意义。青海藏区涉藏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划分,是清王朝不断总结经验,适时调整政策,加强统治力度的必然结果。同时,其较好地顺应了农牧兼具的地方特点,及时采取了“农牧分治”的原则,并据此建立了西宁办事大臣和西宁府两套不同的行政司法管辖体制。为便于案件的管辖和处理,又在两种体制内部,按地域和生产方式特点,按“生番”和“熟番”,分别适用了不同的管辖原则。这种制度安排,既能够尊重藏族内部的风俗习惯,又能贯彻王朝立法及刑事政策,便利了涉藏案件的管辖和处理,也强化了王朝的藏区统治。当然,从现代角度看,这种管辖更多地涉及到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囿于篇幅,并未系统阐释皇权下的指定管辖的内容,对此将另行撰文论述。
注释:
①从当时的青海和硕特蒙古社会经济组织看,鄂托克是领主贵族之下的组织单位(类似千户),受其役使和保护,并承担赋役。和硕特汗和大诺颜台吉等世袭贵族的封地一般是若干个鄂托克组成的大的部落集团。鄂托克由若干爱玛克组成,而爱玛克又由血缘关系维系的若干阿寅勒组成。阿寅勒是小家庭组成的放牧圈子,其管理组织虽非氏族制度,但保留着氏族制度的遗留,其首领由年长者担任。这套自上而下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保障了领主贵族对领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全面统治。
②乾隆二十五年(1760)曾短暂撤销,于二十七年复设,此后,一直沿用到清末。
③“番”是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歧视性的泛称,在清代并不特指藏族或蒙古族,但纵观蒙藏史料,清王朝藏区的藏族一般被称为“番子”,蒙古族一般被称为“蒙番”。
④《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获逃解送”条作了例外规定,该条为:“凡无论何处逃人,不拘何处头目捉获者,将首之逃人限二日内速行解送西宁。如违二日之限者,千户等罚骗牛七条,百户等罚骗牛五条,管束部落之百长等罚骗牛三条。”因此,对于拿获逃人的情况,部落都要将为首的逃人解送西宁办事大臣裁决。
参考文献:
[1]陈庆英,冯智.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简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6(1):41.
[2]柏桦,冯志伟.清代涉藏民刑案件研究与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2013(2).
[3][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8.
[4][清]清实录: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289.
[5][清]文孚,著,魏明章,标注.青海事宜节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6][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793.
[7][清]龚景瀚,李本源,校.循化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25.
[8][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1893.
[9]周伟洲.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29.
[10]星全成,马连龙.藏族社会制度研究[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0:14.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上谕档[Z].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第四条.
[1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嘉庆朝《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M].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