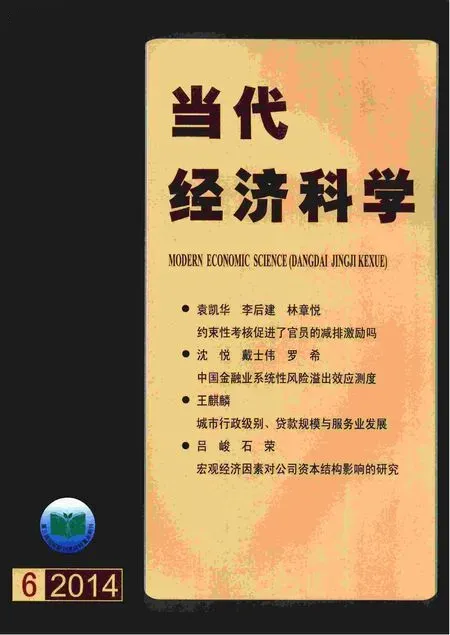约束性考核促进了官员的减排激励吗
袁凯华,李后建,林章悦
(1.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361005;2.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25014;3.天津财经大学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天津300222)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被世人称为“增长的奇迹”。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给予了很好的经济学解释。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却在中国短短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根据国家环境规划院的估算,中国2004-2010年间环境退化成本的增速已达13.7%,远超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如何有效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冲突、提升环境治理激励、避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弊端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面临紧迫的环境问题,继2007年首次将SO2(二氧化硫)与COD(化学需氧量)列为约束性考核目标之后,中央政府进一步将NOX(氮氧化物)、NO2(二氧化氮)列入“十二五”规划的约束范围,以走出当前的污染困境。同样针对环境问题,理论界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最早的污染假说将环境问题视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Meadows et al.,1972)[1]。为了进一步对罗马俱乐部假说进行修正说明,Grossman&Krueger(1995)提出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2],成为不少学者实证研究的起点。但是,当形态设定过于简单的EKC曲线与复杂的国内减排情形相遇时,其稳定性颇受质疑。包群与彭水军(2006)[3]虽然利用 1996 -2000(“九五”期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论证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在工业粉尘、烟尘以及二氧化硫层面的合理性;但是当面板数据扩展到2002年(“十五”期间)时,二氧化硫与工业粉尘的排放总量却呈现出N型转变(彭水军与包群,2006)[4]。而这一时间扩展下“倒U型”假说脆弱性的现象,似乎揭示了当前的污染排放受制于政策变动(五年规划)的特点。继EKC形态争议之后,监管政策成为环境污染研究的焦点。利用外国资本的不断流入可能带来肮脏产业的转移的“污染天堂”假说(Markusen,1999)[5],刘渝琳等(2007)[6]发现低环境规制虽然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却同时带来了高额的污染排放,我国正在沦为跨国资本的“污染避难所”。但是伴随着FDI的研究深入到区域层面,邓玉萍和许和连(2012)[7]指出FDI仅在环境规制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加重了污染排放,污染天堂假说并不具备普适性。不难看出,如果环境规制构成了决定污染天堂假说的关键因素,那么政府行为才是影响污染排放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分权竞争的文献较早的对政府环境行为做出了回应。通过引入官员需求的分权理论,Qian Yingyi(1997)[8]指出政府官员存在着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做出与辖区居民愿望相悖的决策动机,比如降低环境规制,从而吸引高污染的企业进入。在分权理论的基础上,杨瑞龙与章泉(2007)[9]通过财政激励作为切入视角,验证了财政分权程度与环境污染之间正向关联的结论。而为了更加深入刻画政治官员的晋升激励,Jia(2012)[10]巧妙地将政治关系纳入分析框架,发现了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联程度刺激了地方政府牺牲环境、谋取晋升的动机。尽管立足于官员激励角度的文献受到了广泛关注与认可,但此类研究却未真正涉及晋升与污染之间的关系,同样忽略了约束性考核带来的激励变化的特点使其结论是否有效伴随了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根据现有文献不断深化推进的趋势,可以发现虽然官员晋升激励带来的环境难题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的共识,但是针对政策激励、尤其是约束性考核这一首次明确列为官员晋升重要标准的政策研究却相对鲜见,使得激励不足加重污染的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更对当前的环境政策是否有效、进一步的减排政策应该如何推行等问题无法有效解答。同样,面对“十一五”期间约束性减排任务的顺利完成,中央政府进一步将“十二五”期间的约束性考核范围扩大,约束性政策似乎成为扭转生态恶化的关键所在,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11年之后各大城市纷纷上演的“十面霾伏”似乎又给当前的污染减排一记重重的耳光。为何作为雾霾主要来源的二氧化硫实现减排的同时,雾霾现象却日趋恶化?“十一五”减排是否仅仅带来个别污染物的有效控制、约束性指标是否导致“污染之手”伸向其他非考核物的问题值得深思。因此,科学评估当前的环境政策将为“十二五”规划的进一步减排治理提供合理参考。
鉴于现有理论对环境污染问题无法提供较好的解释,本文试图立足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一个新的假说机制:我们认为不断强化的约束性考核压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官员治理环境物品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强外溢物品存在着既无法清楚界定责任归属、又无法将污染成本内部化的弊端,地方官员往往倾向于有选择的强化本地约束性物品的治理,致使约束性考核物品形成差异化的减排格局;而在官员晋升这场零和博弈之中,单维GDP考核与环境压力的双重约束,使得地方官员为了最大程度的提升晋升概率而将“污染之手”伸向非考核、强外溢性物品之上,从而造就了当前“雾霾”现象的日益恶化。本文将以上行为视为约束性考核政策下,激励不足带来的策略性减排困境,并为这一理论提供一个丰富的逻辑框架。同时考虑到晋升官员在政治锦标赛中的示范效应以及约束性考核带来的晋升规则变化的准自然实验事实,本文将通过倍差(DID)模型为策略性减排假说提供合理的经验证据。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本文试图提供一种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即所谓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解释中,我们强调中国解决政府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环境治理问题的理解;其次,本文基于约束性考核这一首个明确列为官员晋升标准的准自然实验,兼顾外溢性差异造就的减排分化,基于倍差模型,客观评估了当前环境激励政策的效用,为进一步的减排治理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最后,本文验证了双重约束下的激励不足假说而非其他环境污染理论构成了当前污染排放恶化尤其是“雾霾天气”的主因,未来的环境政策在强化激励约束的同时,更应合理把握不同公共物品的外溢特性、有效规避环境治理中的策略性排放的短视行为。
根据以上思路,余后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约束性考核下策略性减排假说的提出;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部分进行经验分析;最后为总结性评论与政策建议。
二、策略性减排假说的提出
(一)单维任务下的环境问题
为了改变早期的穷困落后局面,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长期实行GDP单维考核的晋升体系,这种方式虽然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却也加剧了代理人(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周黎安,2007)[11]。单维任务体系下,中央政府无法了解地方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地方官员存在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大限度换取增长的激励,形成了经济增长替代社会发展的畸形模式,从而也造就了“染色的中国奇迹”(聂辉华与李金波,2007)[12]。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便已意识到了合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起步编制了国家第一个环境保护规划。但是1996年之前的环境类规划,多是中央环境领导小组的计划或建议性文件,缺乏相对的政治效力。为了匡正经济增长中的环境问题,国务院中央不仅在1997年的环境规划中首次将环境保护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更进一步提出了控制污染物总量为主线,实现二氧化硫、尘(烟尘及工业粉尘)、化学需氧量、氨氮、工业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10%的减幅目标。遗憾的是,在环境激励的缺失下,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存在着偏离中央政策的动机,导致了“十五”环境规划的基本破产——无论是化学需氧量的2.1%①第二部分的相关减排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或环境统计年鉴。的微弱变化还是二氧化硫27.8%的巨幅增加,都与“十五”规划的削减10%目标相距甚远,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亟待考核力度的进一步强化。
(二)双重约束下的减排困境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十一五”环境规划明确将总量减排列为约束性考核指标,试图改变当前的环境激励不足问题。为了进一步将考核方法可操作化,中央政府2007年出台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将SO2与COD的总量减排作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晋升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表明了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方面更为强烈的决心,更从体制方面弥补了地方官员在环境投入任务方面约束不足的缺陷,对于扭转以往唯GDP是瞻而置环保于不顾的晋升行为具有重大意义。为了避免约束性指标完成不足而被淘汰出局的风险,省级政府在任务制定上层层加码(周雪光与练宏,2012)[13],对于市县两级实行了更为严苛的考核总量,形成了为“及格”而努力的另类“达标竞赛”格局(Zhou et al.,2013)[14]。遗憾的是,层层加码的环境压力虽然增强了地方政府治理污染的约束性,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双重考核任务,但多重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代理人显然存在着任务选择上的偏好之别(Mathias Dewatripont et al.,2000[15];Kahn et al.,2013[16]),从而造就了当前的策略性排放困境。
抛开不同时点上的技术、结构差异,仅从2007年前后的约束性指标排放总量的变化来看,任务考核使得工业SO2与工业COD的治理取得了长足性进展,但其减排效果因类而异:在核密度分布方面,尽管工业SO2与工业COD均实现了左移之势,但工业COD排放的移动速度更为明显;在减排环比变化方面,工业SO2与工业COD均实现了考核以后的同步减排,但在减排速度上工业COD明显优于工业SO2。分化明显的减排差异表明,外溢性特征可能成为影响减排工作的重要因素(Oates,1982)[17]。工业COD强烈致癌、本地污染、责任界定明显以及为本地经济增长带来损失较重的特性,强化的环境压力更易驱使其成为减排目标首选,但相比而言,强腐蚀性却外溢性明显、污染责任难以界定的工业SO2却使政治官员原本较低的环境激励受到了更进一步的抑制、打压。
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H1:约束性考核给予了官员避免考核失败、从而丧失晋升资格的压力,使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得到了部分纠正,但受外溢性差异的影响,污染源难以界定、污染责任难以追究的约束性指标面临着更低减排激励,致使晋升官员在约束性指标的减排方面因外溢性不同而呈现策略性分化的特点。
遗憾的是,约束性考核政策的不足不仅仅局限于此。与经济增长的实质利益与减排考核的强制约束相比而言,未被例如指标范围的物品更易遭受这种选择行为的冲击。一方面,达标竞赛难以撼动GDP晋升竞赛的主导地位,环保事业的投资虽然可以显著改善区域环境,但与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财税收益与晋升利益相比差距甚远,使得以晋升为目的的政治官员缺乏投资环境保护的动力不足(Wu et al.,2013)[18]。另一方面,未被列入考核范围的公共物品面临着宽松的减排压力,而强外溢性的环境物品的无界性,进一步激励着政治官员将“污染之手”转向此类物品之上,以同时满足政治晋升与达标考核的双重任务。

表1 四类污染物的减排变化

图1 1997、2006、2007与2012年四类污染物排放的核密度分布函数
而这一猜想与当前的差异化减排特征十分契合。由于COD的强力致癌与SO2的高度致腐特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虽然同样对地方环境造成了创伤,但受限于种类构成较多的缘故,一直在考核范围边缘徘徊。缺乏有效考核的此类物品,更易成为粗放型经济模式之下的牺牲品。对比主要污染物在约束性考核前后时期的环比变化与主要年份的核密度分布差异,可以发现现有污染物排放因是否考核、是否具有外溢性而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无论是约束性考核政策出台之前阶段(1997-2006)还是约束性考核出台之后的时期(2007-2012),工业化学需氧量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明显好于工业废水与工业废气,表明着当前的地方政府虽然存在着牺牲环境的动机,但在选择上因是否考核而呈现差异分化;其次,无论是哪一时期,工业化学需氧量的减排速度总要好于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的减排速度总是优于工业废气的现象,意味着强外溢性的公共物品容易成为牺牲环境发展模式的首选;最后,比较四类污染物不同时期的污染排放,可以发现即使在环境压力最为严厉的阶段,工业废气排放仍在有增无减的不断恶化,表明考核相对宽松、外溢较为明显的污染物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治理难度。
基于这一特征,本文提出约束考核下的第二个策略性减排假说。
H2:不断强化的考核指标虽然给予了一定的任务压力,但在尚未改变的单维晋升体系下,未被列入考核范围却有呈现强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更易成为最大限度谋取晋升同时完成达标任务的牺牲品,致使污染减排陷入“东拆西补”的泥潭。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前文的理论假说,本文将借助于倍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倍差法又名双重差分,是政策评估中的一种常用计量手段。其基本思路在不可观测的因素不随时点变动成立的基础上,通过选择一个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和一个受到政策影响的处理组(Treat Group)进行某项指标变化量的对比,以此反应政策变化的净效应(Ashenfelter and Card,1985)[19]。由于其理论清晰、数据要求相对较低,在气候变化(Miguel,2004)[20]、官员晋升(徐现祥等 2007)[21]、以及公共政策(周黎安等,2005)[22]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我们认为,借鉴这一模型进行约束性考核政策效应的评估具有如下优势。首先,在已有的中国环境污染研究中,片面的晋升激励的导致地方官员主动降低管制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谋取晋升的短视行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过多的研究依赖于财政分权程度进行晋升激励的衡量。分权指标的缺陷在于其仅仅衡量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方面的变化,财政激励难以直接准确衡量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与此相反,约束性考核作为晋升官员必须满足的任务,利用官员升迁的数据可以直接测量官员晋升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其次,以约束性考核为分界点,通过比较晋升组与非晋升组两类样本的污染行为,我们得以精确的评估约束性考核是否改变了晋升官员的政治激励。以环境污染为例,除了减排考核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难以将考核的单独作用剥离开来,从而导致评估结果的偏误。更为重要的是,环境治理还受到众多不可观测变量的冲击,例如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力度,进一步弱化了政策评估的准确性(包群等,2013)[23]。而通过对比处理组与参照组排污变化的双重差分,我们能较好的控制可观测与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具体地讲,我们把全样本分为两组——发生晋升的省份与未发生晋升的省份,对应于自然实验中的实验组与控制组,再按约束性考核政策的出台时间将全部年份分为改革前(1997年-2006年)与改革后(2007年-2012年)两个阶段,这样就可以通过对比实验组与控制组在两期的变化研究改革政策的效果。按照这一设想,本文将采用公式(1)作为基本的估计方程。其中,lnP为排污量,利用地区工业COD、工业SO2、工业废水以及工业废气年度排放量的对数衡量;dT为约束性考核前后时期的虚拟变量,dT=1代表约束性考核以后的时期,dT=0代表约束性考核实施之前的时期,dT的统计系数代表约束考核时期对排污量的作用力度;dP为各个省份的官员晋升情况①依据陶然(2010)[24]定义的晋升标准进行统计。,dP=1代表处理组,即发生官员晋升的省份,dP=0代表对照组,即没有晋升的省份,dP的统计系数代表官员晋升对排污量的影响;dT和dP的交互作用表示实施约束性考核政策对晋升官员环境激励的净影响,它在统计学上等于处理组在事件年前后的差异减去对照组在事件年前后的差异,即所谓的“双重差分”;ε为随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并非约束性考核指标,本文同样利用倍差分模型进行处理的目的在于检验政策变化下策略性污染转移假说的合理性。


表2 倍差法的基本原理

由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可能受到变量缺失的威胁,我们在遵循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CV以及利用官员外生特征的工具变量IV进行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控制变量CV主要包括:地方经济增长率dlngdp,为了避免不同时点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差异以及过度引入高次项带来的共线性偏误,我们利用省市GDP的对数差分值进行经济增长因素的衡量替代;地方产业结构second,为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进行衡量,以控制产业差异对排污量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水平lnfdi,为各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对数,以考虑“污染天堂”假说的影响。因此,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模型扩展为:

同时基于工具变量选择上的外生性与相关性准则,本文主要利用官员的年龄age以及教育背景school(高中及以下为0,大专及本科为1,硕士及以上为2)进行工具变量的构造:首先,根据常识性判断,官员的个体特征是严格外生的,一般不会对地方排污量构成直接影响;其次,基于我国吏治改革的年轻化与知识化潮流,官员的年龄与教育背景都是政治官员顺利晋升的重要筹码(乔坤元,2013)[25];第三,选择多个工具变量可以根据Sargan检验,以验证工具变量是否具有严格外生的特性。由此,我们选择以上两个工具变量进行潜在内生性偏误的修正。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城市层面的污染数据相对匮乏,本文选择省际层面的样本作为主要观测对象。由于重庆在1997之后开始直辖,西藏自治区在环境污染方面的遗漏统计数据较多。因此,本文选用了1997-2012年除西藏以外的大陆30个省市作为观测样本。在污染物样本选择上,限于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烟尘与工业粉尘等主要污染指标的排放量自2010年以后不再统一公布,考虑到工业废水与工业COD、工业废气与工业SO2之间的从属关系,本文选择以上四类污染物作为模型检验的主要样本。而在官员晋升的样本选择上,按照张莉等(2013)[26]的观点市委书记与市长虽然同样作为地区首长,书记侧重于人事工作,而市长则主管行政命令的下达、负责地区经济的运转,我们选用各地省长作为官员样本。需要说明的是,官员晋升为本文的重要核心变量,但是晋升与否取决于任期内的长期结果,并非晋升当年的经济或环境行为,因此本文仅采用了截止当今已发生省长升迁的省份作为观测样本。以福建省省长苏树林为例,由于其从2011年7月至今一直担任福建省省长而未发生变迁,无法对其未来的晋升做出预期,本文将此类样本剔除在外。而限于省长更替数据尚无官方统计,我们对此进行手工搜集。具体而言,有关省长年龄、教育水平以及工作升迁的数据都是我们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人民网(www.people.com.cn),新华网(www.xinhuanet.com)和“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并经过反复核对而获得的。除此之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经济信息网。
四、经验分析
遵循研究设计的基础上,本文的经验分析主要从基于双重差分的考量、工具变量的进一步纠偏处理以及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分析等方面入手。
(一)倍差模型的初步检验
根据历年环境规划考核物的不同,本文将自“九五规划”以来一直列为考核物品的工业COD与工业SO2和长期未受重视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带入式(2)进行倍差模型的检验。

表3 基于分类污染物的倍差模型检验
表3的结果显示:
1.从约束性考核物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上看,官员晋升dP仅对工业SO2的排放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而政策变化dT与交互项系数dP·dT仅对工业COD起到了约束性考核作用。根据这一结果,我们推断,由于考核指标的敏感性,具有晋升概率的官员不敢在此类物品上贸然排放,同时相对于工业SO2的排放责任难以追究、治理收益与成本不对成的特性(周权雄,2009)[26],弱外溢性、本地危害较重且排放责任容易界定的工业COD治理显然具有更强的全体样本激励性,从而造就了晋升仅对SO2排放显著;而时期系数dT仅在工业COD排放上具有统计意义的原因在于约束性政策的出台仅仅带动了全体官员治理本地物品的积极性;而仅在工业COD方面负向显著的交互项系数dP·dT同样进一步宣判了当前的约束性考核政策的部分失效,即约束性政策指标仅仅加强了本地物品的治理,而对工业SO2方面的治理基本无效。约束性考核物品在减排激励上的差异,意味这一政策虽然提升了对于本地经济增长危害较重、影响晋升概率物品的环境激励,但“达标竞赛”下强外溢性物激励不足问题仍然难以扭转,外溢性差异带来的约束性减排策略政策差异化假说1得到了初步验证。
2.而对于非约束性考核物层面:工业废水的交互项dP·dT与工业废气的政策变动dT虽然均在10%水平上显著,但其作用符号却呈现两极分化之势。强外溢性物品的公共治理难度的结果虽与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27]的结果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双重差分系数以及时期虚拟变量的差异却进一步揭示了当前公共物品治理层面的策略性分化:工业废水的本地性使其受到了约束性考核政策的惠及,地方政府在减控约束性指标的同时,亦强化了本地物品的治理,使得工业废水的排放呈现收敛之势;不幸的是,受限于强外溢性与非考核指标的双重劣势,工业废气排放不但没有因约束性考核的出台而呈现削减趋势,反而成为晋升激励与减排约束双重压力下的政治牺牲品。我们认为,相对于考核指标,非考核指标方面的双重差分结果初步显示了假说2的合理性,即受制于GDP导向的“晋升竞赛”与约束性指标的“达标竞赛”双重影响,非考核、强外溢性物品更容易成为环境约束下最大限度谋取晋升的理想替代品,“东拆西补”的减排困境难以避免,激励不足带来的短视行为被进一步扭曲放大。
3.在控制变量上,始终显著为正的产业结构second符合预期,但作用趋异的经济增长dlngdp与外商投资lnfdi,进一步为当前的策略性减排提供了经验证据。列(1)到列(4)中的经济增长变量dlngdp在工业COD与工业废水方面为负,却在外溢性物品工业二氧化硫与工业废气上显著为正,表明当前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以牺牲强外溢性物品的模式进行发展;差异化明显的外商直接投资lnfdi,虽然在弱外溢性物品排放上显著地起到抑制作用、却对强外溢性物品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废气显著为正的特征与贺文华(2010)[28]研究结果部分类似,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同样在环境污染方面呈现策略性分化的特征。分化明显的统计系数以及作用方向,不仅仅是对以往增长极限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的挑战,同样证明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与引资过程中更加重视本地弱外溢性物品的治理,政治官员的经营动机才是决定污染发生与否的重要原因(邓玉萍与许和连,2013)[7],而其他假说仅仅是是一个晋升体系下的表面现象。
结合以上实证结果我们发现考虑到约束性政策带来的时点变化后,官员晋升虽未直接加剧了污染排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激励不足带来的环境恶化局面已经彻底改善:在不断强化的环境压力与高度竞争的晋升体制下,强约束性的考核物品使得政府不得不为避免晋升资格的丧失而付诸一定程度减排努力,而晋升诱惑以及强外溢性物品的排放责任难以界定,使得理性的官员在强化本地物品、考核指标治理的同时,部分程度弱外强外溢、非考核物品的治理,甚至刻意降低此类污染物治理门槛,从而实现减排约束下最大程度谋取晋升的目的。至此,不难发现,减排效果因是否考核与是否具有强外溢性而呈现出策略性分化的假说得到了全面验证,为达标而努力的减排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晋升激励下的环境问题。
(二)基于2SLS的内生性修正
根据现有研究,晋升锦标赛下官员存在着降低环境规制、增加污染排放的短视行为,而一旦这一策略成功,其他省份的最优反应势必是纷纷效仿,以谋取晋升博弈中的利益最大(陈刚,2009)[29],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的“逐底竞争”。由此,理论上存在着晋升导致污染、而污染又进一步加快晋升的可能。为了削减二者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偏误,我们有必要引入合理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的纠偏参数估计。考虑到合理的工具变量既要满足外生性、又要符合相关性的准则,对其筛选往往是件棘手之事。遵循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官员外生的年龄(age)与教育背景(school)变量引入,利用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检验,以达到修正偏误的目的。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不足检验(Underidentification test)、弱工具变量检验(Weakidentification test)还是外生性检验(Sargan statistic),我们的工具变量都达到了相应的准则。

表4 基于2SLS的内生性偏误修正
基于工具变量有效性验证的基础上,我们对表4的结果进行一一阐述。首先,在约束性考核指标方面,列(1)与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变量仅有工业COD的交互项dP·dT与工业SO2的晋升变量dP依旧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政策变革为约束性考核指标带来的变化仅有本地物品减排激励的强化,而对提升强外溢性污染方面的环境激励基本无效。其次,在非考核性指标层面,与工业废水无一显著的核心变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废气关键变量统计意义的凸显。在工业废水方面,我们仍无法找到约束性考核政策、官员晋升对其影响力度的经验证据。恰恰相反的是,对于具备强外溢性特征的工业废气,虽然负向逆转的晋升变量表明在节能减排的公众压力不断强化下、地方首长的晋升可能存在着与减排工作的正向关联(Zheng Siqi et al.,2013)[30],但是时期虚拟变量 dT与交互项dP·dT的正向显著,意味着和前一时期相比,废气排放日趋恶化、晋升官员抑制废气排放的积极性受到打压,进一步印证了政治官员存在着向非考核、强外溢性产品转移污染假说的合理性,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断强化的环境问责压力下,以“雾霾”为代表的废气污染日趋恶化的原因。
结合以上核心解释变量的变化,我们发现虽然普通面板的估计系数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估甚至方向逆转的偏误,但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假说得到了更为有力的支撑:约束性考核因环境物品的外溢性差异,难以有效地带动考核指标的全面减排;而减排激励不足与GDP导向的双重约束,使得政治官员转移性增排倾向更为强化,减排行动陷入“东拆西补”的困境。
(三)剔除规模效应后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排污量是一个地区污染排放总数的变化,地区之间的规模差异可能使得真实结果收到潜在冲击(Jia,2012)[10]。为了增强研究假说的合理性,我们进一步通过人均变量将被解释变量的规模效用进行剥离。

表5 剥离规模效用后的稳健性分析
考虑到人均变量虽然削弱了规模效用,但对内生性控制问题意义不大,为了避免潜在偏误,本文依旧采用2SLS进行估计。与表4相比,剥离规模效应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在核心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上,其统计符号与统计意义均无明显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十分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为了应对片面追求增长下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央政府先后多次出台规划政策,以纠正激励不足带来的环境治理难题。但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对其效用的评估鲜少,从而无法对于当前的环境政策进行合理评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立足于2007年出台的约束性考核政策,利用官员是否晋升这一基本准则,对四类污染物品进行考核政策进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效用评估。
经验分析发现,在未能改变的单维GDP晋升体系下,约束性考核不能彻底纠正当前政治官员的激励不足下的短视行为:由于约束性考核仅仅作为一个达标任务,这一政策虽然提升了晋升官员在弱外溢性、损害本地经济增长的工业COD方面治理积极性,但受工业SO2排放责任的难以界定影响,未能对强外溢性约束指标的环境激励提升产生实质性效用;不幸的是,考核政策的局限远非如此,在追寻最大化产出以谋求政治晋升的激励下,继续强化的约束性考核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将“污染之手”转向非考核的强外溢性公共物品之上,从而造就了当前的大气污染日趋恶化的局面;而相对于以往的单纯认为经济增长或外商投资的污染假说,环境激励不足带来的策略选择才是造就当前污染分化的重要原因,即使考虑到了变量的内生性以及排放物的规模效应以后,我们的结论依旧十分稳健。
本文的实证结果意味着,当下的约束性考核政策仅仅带来了局部策略性减排,单纯依赖这种政策将很难扭转激励不足带来的环境问题。基于本文的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策考核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对本地物品治理仍十分有效,在环境治理中应坚持合理区分、适度推广的政策,进行污染减排的控制。尽管“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将氨氮和氮氧化物作为考核指标列入,但和张力军司长①资料来源:“十二五”增加减排指标 控制氮氧化物排放难度大,http://www.china.com.cn/news/env/2011-03/12/content_22118995.htm.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外溢性物品单纯的约束性考核很难使得此类物品的减排取得长久的进展。针对此类外溢性物品,中央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废气排放层面的责任人落实制度,避免外溢物品排放责任难以追究的尴尬境地。其次,以激励替代约束,纠正当前激励不足下政治官员策略性减排的扭曲行为,以从根本上提高官员治理污染排放的积极性。虽然污染排放是一种可量化的指标,不存在难以量化的困境,符合周黎安(2007)[11]提出的改进当前官员晋升体系指标设计的原则,但遗憾的是尽管此类建议提出已久,为了避免发展过程中的“政绩”落后、影响晋升,真正付诸实践的地方政府为之甚少。对此,中央层面不能仅将“绿色发展”停留在概念层面,需要将污染排放纳入晋升激励范围,赋予适当权重,以进一步从激励源头上纠正当前的官员短视行为,强化减排政策的激励力度。再次,外溢性污染物品一直因为治理的收益成本不对称性,形成了政策治理的盲区。改变外溢性物品的治理,需要提倡区域合作的共同治理、共同考核,以避免治理过程中的相互推诿。庆幸的是,府际合作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共识。由国家发改委组织推动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方案》章程已于2014年6月初次通过了内部决议,为统一限行、统一限排、统一油品质量、统一环保标准等一系列府际合作措施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政策性保障。虽然这一方案尚未具体出台实施,但这一尝试将对未来减排工作的改革方向提供有效地参考。
遗憾的是,受核心变量缺失所限,本文采用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无法考量污染排放之间的空间依赖。因此,如何将空间因素纳入非平衡面板,将对未来的政策评估具有极大改进意义。
[1]Meadows D H,Goldsmith E I,Meadow P.The limits to growth[M].London:Earth Island Limited,1972.
[2]Grossman G M,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02):353-377.
[3]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06(11):48-58.
[4]彭水军,包群.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06(08):3-17.
[5]Markusen A.Fuzzy concepts,scanty evidence,and policy distance:The case for rigour and policy relevance in critical regional studies[J].Regional studies,1999,33(09):869-884.
[6]刘渝琳,温怀德.经济增长下的FDI、环境污染损失与人力资本[J].世界经济研究,2007(11):55-87.
[7]邓玉萍,许和连.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财政分权视角的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07):155-163.
[8]Qian Y,Weingast B R.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83 -92.
[9]杨瑞龙,章泉,周业安.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R].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报告,2007.
[10]Jia R.Pollution for promotion[R].Unpublished paper,2012.
[11]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12]聂辉华,李金波.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季刊),2007(01):75 -90.
[13]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J].社会学研究,2012(05):69-93.
[14]Zhou X,Lian H.Modes of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A“control rights”theory[J].Sociological Studies,2012,61(5):69 -93.
[15]Dewatripont M,Jewitt I,Tirole J.Multitask agency problems:Focus and task clustering[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44(04):869-877.
[16]Kahn M E,Li P,Zhao D.Pollution control effort at China's river borders:When does free riding ceas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3.
[17]Oates W E.Fiscal and regulatory competition:Theory and evidence[J].Perspektiv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2002,3(04):377-390.
[18]Wu J,Deng Y,Huang J,Morck R,Yeung B.Incentives and outcomes: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R].NBER Working papers 18754,2013.
[19]Ashenfelter T A,Attfield C,Becker G,et al.A profitable approach to labor supply and commodity demands over the life - cycle[J].Econometrica,1985,53(03):503-544.
[20]Miguel E,Satyanath S,Sergenti E.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04):725-753.
[21]徐现祥,王贤彬,舒元.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42(9):18-31.
[22]周黎安,陈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J].经济研究,2005(08):44-53.
[23]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J].经济研究,2013(12):42-54.
[24]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3-26.
[25]乔坤元.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J].经济科学,2013(01):88-98.
[26]张莉,高元骅,徐现祥.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J].管理世界,2013(12):43-51.
[27]周权雄.政府干预,共同代理与企业污染减排激励——基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09(04):109-130.
[28]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J].管理世界,2008(08):7-l7.
[29]贺文华.FDI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基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证据[J].当代财经,2010(06):99-105.
[30]王慧军.政府公共政策的时滞效应分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05):28-31.
[31]陈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J].世界经济研究,2009(06):3-7.
[32]Zheng S,Kahn M E,Sun W,et al.Incentives for China's urban mayors to mitigate pollution externalities:The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ism[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3,47(04):61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