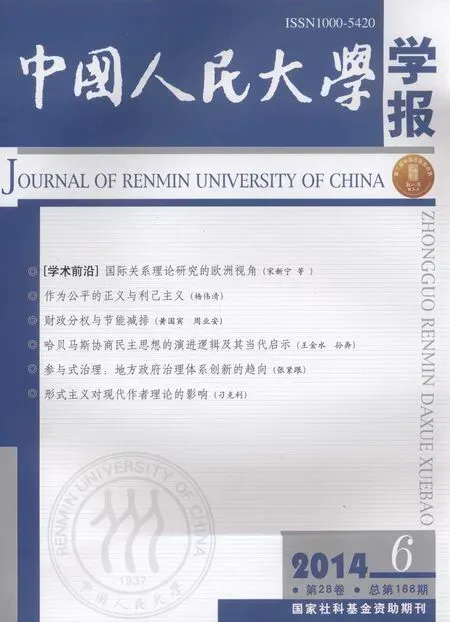形式主义对现代作者理论的影响
刁克利
形式主义对现代作者理论的影响
刁克利
形式主义对现代作者理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对作者理论的直接论述,而在于它对现代作者理论发展进程的巨大影响。形式主义以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终结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文学观改变了现代作者理论的方向,它对作者意图的辨析开启了隐含作者等新的思路,它与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细读的策略和批评方法丰富了文学阅读体验和创作技巧。其后继者提出“作者之死”之时,正是以培养作家为己任的创意写作教学兴盛繁荣的开始,这种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悖论也应该引起我们对现代文学理论的深刻反思。
形式主义;现代作者理论;创意写作
通常认为,形式主义与作者理论并无直接联系,因为它是以否定作者研究为前提的,它所倡导的文本中心论也与作者理论背道而驰。实际上,形式主义对作者理论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在于它对作者理论的论述,而是在于它以否定的方式对现代作者理论产生的巨大影响:它不但终结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而且改变了现代作者理论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作者理论将形式主义作为开端,既有理论依据,又符合其实际进程。
一、文本中心论对作者的拒斥
传统的作者理论因循浪漫主义以来对作者个性的强调,认为文学创作是作者个性的凸显和表现。到了19世纪末,这种趋势成为对作者个人生活的关注,文学批评演变成为作者生活研究。大学开设的英国文学课被视为只关注传记中作者个人的逸闻趣事。1869年,英语文学与逻辑教授亚历山大·贝恩针对这种情况,认为大学里的英语教学应该被限制在修辞研究或“写作”的研究中,因为“当人们进入文学批评时,总会受到偏离主题的诱惑,去谈论对英语教师毫无价值的事情。他们偏离主题谈论作者的生平、性格、个人好恶、作者之间的争吵和友谊,甚至被卷入他们的信仰和思想矛盾中”[1](P213214)。
从当时这种对作家研究的批评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当时文学批评的褊狭,将作者个人生活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甚至主要内容;二是19世纪晚期出现了对文学批评专业化的呼唤,希望能够对文学批评的领域予以界定和澄清。
在这种背景下,形式主义的初衷是保证文学研究不堕落为流言逸事,它的兴起代表了20世纪初学术批评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努力方向。形式主义批评家主张文学批评研究文学问题,反对当时流行的以作者为中心的心理批评、传记批评和历史批评,这些可以看做是“对作者作为文学阐释的中心这一观点的反驳”[2](P73)。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和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首先抨击了文学批评过分强调传记因素。他认为文学史学家就像警察一样无所不管,对环境、心理学、政治、哲学等无不涉猎,而形式主义的诉求是“促使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他主张把文学研究转换为文学科学,认为它不能始于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和社会时尚的研究,因为这些外在因素不仅不能恰当地阐释文学作品的内在特性与规律,反而易于产生误导,把文学作品或者视为作者的传记,或者视为社会生活的机械摹写和教育读者的工具。他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literariness),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3](P378)
早期的形式主义观点倾向于否认作者与文本的任何联系,希望保持文学批评的纯洁,以语言和文本为基础,把文学文本作为批评的中心,将文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作品的形式上,包括文体、语言、结构、技巧、程序等。
形式主义并非不知道作者研究的重要性,而是严格界定了文学批评与作者研究的界限,把作者的生活与作品分离开来。在《形式主义批评家》中,美国新批评主要代表人物克林思·布鲁克斯认可“作品表现了作者独特的个性,作者在创作中怀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但是,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对作者思想状况的研究会使批评家将注意力从作品本身转向对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心理的研究”[4](P280)。布鲁克斯认为,这类研究属于创作过程研究,这类研究工作虽然“很有价值,很有必要,却并不能等同于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5](P281)。通过强调文学性和科学性的主张与实践,形式主义建构了新的领地。它从文本中心论的角度界定文学批评,不关注作者创作,而强调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它把文本批评等同于文学批评。
如果我们对形式主义作者观进行总结,就会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形式主义作者观认可作者研究,认为它自有其重要性。它也认可作者研究的基本原则:作品表现作者个性,作者创作各有动机和意图。它不认可的是作者研究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
其次,形式主义作者观关注“作者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在《形式主义批评家》中,布鲁克斯认为,作者意图是作者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而非构思过程中或未获得体现或未能成功体现的意图。“只有作者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能算数,至于作者写作时怎样设想,或者作者现在回忆起当初如何设想,都不能作为依据。”[6](P281)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形式主义不关注作品的构思和创作过程,而是关注作者创作结果,即作者意图在文本中的实现。它关注的是作品中的作者意图,并且认为形式主义的批评可以对作者意图作出解释。
形式主义以其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努力划定了批评的领域,分离了作者研究和文本批评,使得批评的对象由人(作者)转向物(文本),从而终结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同时,它以作者与文本阐释的联系作为纽带去研究作者,将作者研究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如果说传统作者理论重在作者的生成和对作品创作的研究、现代作者理论重在作者的意图体现和对作品阐释的影响研究,那么,这种分野和界限正是由形式主义的作者观所奠定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界定作者与文本的特殊关系,形式主义奠定了现代作者理论的基调,开启了现代作者理论研究的新道路。
二、意图谬误与为作者辩护
作者意图是现代作者理论的核心术语,对于作者意图的争论构成了现代作者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意图谬误》中,威廉·K·维姆萨特对作者意图下的定义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意图同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他的看法,他动笔的始因等有显著的关联。”[7](P295)他承认作者意图的存在,但是,不认为其可以作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
“意图谬误”并非否定作者意图,而是强调作者意图不等同于作品研究,两者各有分野。“诗的批评和作者心理学是两个领域。对作者心理学的历史研究就是文学传记,这是一个合理的、有吸引力的研究工作。当人们指出在文学研究的大雅之堂上,关于个人身世的研究同关于诗本身的研究有明显区别时,也就不必抱着贬抑的态度。然而,混淆这两种研究的危险是存在的。”[8](P298)作者研究与文本批评无高下之分,而是各有领域、各有侧重,不可混淆。如果作者意图得到了体现,它就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否则就毫无意义。
“意图谬误”反映了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也道出了它对作者研究的疆域限定。它把作者研究限定为创作心理学和创作论研究等。如果按照形式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定义:文学批评就是对文本的艺术性研究,那么,创作心理学和创作论研究都不属于作品论,作者研究因而不能成为专业化的、科学化的文学批评的范畴。从形式主义对作者意图和“意图谬误”的论述中,可以引出不同的文学观念,以及什么是有效的文学批评等争论。
“意图谬误”论的确遭遇到了不少挑战。对此做出的重要回应有:艾瑞克·赫施(Eric Hirsch)的《阐释的有效性》与《阐释的目标》,威廉·厄文(William Irwin)的《意图主义者的阐释》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赫施在《阐释的有效性》中从意图主义观点出发表达的“为作者辩护”的思想。
赫施的核心论点是,作品的意思由作者的意图决定,文本意味着其作者所指的东西。他提出为作者辩护的主张,反对现代主义的非个人化和新批评的反意图论,将其视为使文学失去个性。艾略特和庞德等现代主义者认为,文本独立于作者的控制,最好的诗是非个人的、客观的、独立自主的,与作者的生活切断联系,自成一体。后来的海德格尔和荣格则推波助澜,前者主张语言的语义学自主性,后者认为,作者不知不觉地表达原型的集体无意识,这些导致了作者的放逐。作者的放逐的结果是“当批评家们蓄意要撇开原作者时,他们自己就篡夺了作者的位置”[9](P371)。对作者的放逐导致理论的混乱,其结果是:“在过去只存在一个作者的地方,现在涌现了一大批,每个人都有着像下一个人一样多的权威性。排除了作为意义源决定者的原作者,就是拒绝了唯一令人感兴趣的、能把有效性赋予解释的标准原则”[10](P371)。另一个结果是:“并不真的存在着一个支配着本文解释的标准的理想。这是种种背离作者的观点必然会出现的情况。结果会是文本的无意义,或无确定意义。如果有位理论家想要拯救有效性的理想,他就必须拯救作者”[11](P371)。赫施把理解作者意图视作有效的阐释,把作者意图提高到了衡量文学批评标准的高度。
在《阐释的有效性》中,赫施对“作者的放逐”、“本文的意思在变化”、“作者想要表示什么无关紧要”、“作者的意义是难以达到的”、“作者常常并不知道他要表示的意思”等进行了逐一辩驳,从多方面为作者意图进行了辩护。赫施重新定义了作品的意味(significance)和意思(meaning),解释了意义体验(meaning experience)的不可复制性与意义的不可复制性的不同。他还指出了关于作者意图和公众舆论这两个“神话”的不当之处,并对书写的文字和作者心中持有的东西进行了对比。赫施的观点和结论虽然并不彻底和令人信服,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巨大的理论和思辨空间。
意图主义者为了在作者意图的论战中守住作者的阵地,对文学批评进行了多方位的理论拓展。由此也带出来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文学文本阐释中的作者身份、作者位置、作者意图如何理解?作者是一种人物、功能,还是一种角色?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实际作者、在文本中显现的隐含作者、作为故事展开的叙述者有何区别?表面作者、暗含作者和假设作者如何界定,这种界定和区分的动机何在,有何必要?作为文学阐释的目标的应该是哪种作者?阅读与阐释、批评的区分与关联何在?何为有效的阅读、阐释与批评等等。这些区分至关重要。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争论构成了现代作者理论的重要内容,使得现代作者理论呈现出和传统作者理论不同的面貌。换言之,形式主义在作者与文本联系的角度界定作者,强调作者的文本属性,将现代作者理论引向深入,改变了现代作者理论的方向。在辩驳和论争中,文论家提出了作者理论的新范畴、新概念,开启了新的思路。可以说,现代作者理论方向的改变是从形式主义肇始的,由形式主义奠基的对于文本与作者关系的争论主导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文学理论主潮。
意图主义者对意图谬误的反驳和作者建构的提出,旨在加强和争取作者在阐释中的地位和作用,非但未能摆脱形式主义的文本阐释的轨道,实质上却正是沿着形式主义设定的作者与文本的联系这一思路向前推进。而真正意义上的作者理论建构并不仅仅是争取作者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强调作者在文本阐释中的作用,更在于说明作者对于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所以,更彻底的作者建构应该在反思和批判形式主义的作者理论的基础上调转方向,开辟新的天地。
这一新的方向就是由阐释为中心的作者理论向创作为中心的作者理论转变。只要不摆脱形式主义,无论多么彻底的作者理论都是作者阐释理论,都是文本阐释中的作者问题研究。真正不依附于文本中心的作者理论应该而且必须从文本阐释中挣脱出来,只有如此,作者理论才能有其独立性,才能确立其独立的问题和范畴,才能彰显作者理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独立的、富有特色和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作者理论建构不能因循文本阐释的老路子,必须另辟蹊径。新的作者理论建构所包含的基本理念是:作者既是在文本中体现其意图的作者、阐释中的作者、意图达到了的作者,更是现实的、历史的、作为群体或个体的作者。新的作者理论是作者阐释理论和传统作家研究的综合,此是另外的议题,当另文论之。
由形式主义对作者谬误的论述,以及意图主义者对作者的辩护而引出作者理论重建的话题,看似反差巨大,但其实形式主义理论自身就蕴含着这种巨大悖论的可能性。创意写作的兴起与繁荣足以佐证。
三、文本细读与作家培养
形式主义批评家声称“不从作家创作的角度,而从作品本身结构的角度来叙述”[12](P283)。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他们研究作品中的张力、象征的展开,以及反讽和反讽的解决,关注作品的技巧,从作品本身的能动形式来描述棘手的素材如何被认识和处理等等。当这些技巧被形式主义批评家娴熟地运用到文学课堂上的时候,无论文学批评还是创作都从中受益。它所倡导的文本细读的策略和批评方法丰富了文学阅读体验,有利于培养有见识的、专业化的阅读者,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文学鉴赏能力的提高无疑会促进文学创作。形式主义的批评实践和文本理念提高了作家对文本的细读和剖析能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借鉴,也启发作家对于文学经典的学习和探索文学创作技巧的自觉意识。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当代西方文学不断出现文学试验的原因所在。
根据形式主义的批评观及其对理想文本的期待,我们可以推断出形式主义的理想作者:具有敏锐的文学鉴赏能力,具有系统与扎实的文学传统知识和技巧学习能力,具有对文学技巧积极探索的精神和自觉意识,愿意不断探索文学创作的手段,自觉革新文学创作方法。或者说,他们以文学手段创新为己任,以革新文学形式为要义,勇于创新。要言之,形式主义的理想作者应该具有系统而扎实的文学理论和自觉的文学创新意识,是专业化、职业化的作家。这种作者意识或者理想作者形象在创意写作教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20世纪30年代起,在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教授统治英美文学课堂的时候,创意写作悄然出现。这些批评家既是教师,又是诗人。他们的批评方法和作家工作室的阅读方法近似。通过在文学批评和创意写作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他们共同开始了培养职业作家的事业,开启了一种新型的教学机制——建立研究生作家工作室。创意写作以作家工作室(workshop,一译“工作坊”)为核心教学模式,即以导师组织学生创作和研讨各自的作品为主。导师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传授切实有用的创作经验,发展学生的创作个性是主要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创作出具有一定水准的文学作品,工作室的工作方式类似同行评议。导师的角色既是写作指导教练,又兼具有经验的同行,倡导气氛平等、民主,又有竞争,突出以作家为中心的阅读方式。
创意写作的开展对美国文学的繁荣、创新能力的增强,以及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迅速增强,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创意写作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量潜在的作家,很多人具备了文学写作的能力。文学创新、思潮更迭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成为诸多新的文学技巧探索、新的文学思想的发源地。创意写作项目的兴起被认为是美国战后文学史的最重要的事件,关注文学成就与高等教育之间不断增长的密切关系成为理解美国文学动力和原创性的关键。[13](Pix)
至20世纪60年代,在“作者之死”甚嚣尘上之时,创意写作教育蓬勃兴盛于英美校园。目前,创意写作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创意写作成为艺术与人文教育中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创意写作课程是本科生中最受欢迎的选修课。与快速发展的创意写作相比较,作为所有学科中文科学士学位的一部分,英语学士的比例不断减少。由传统的英语专业(文学专业)承担的文学教育的任务部分转移到了由创意写作项目来承担。现在的英美大学的传统文学课程数量和选课人数都在逐步下滑,而创意写作项目却空前繁荣,数量不断增加,由硕士到博士不断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者。
创意写作教育作为一种以作家创作为中心的阅读策略与文本批评方法。在理论上,创意写作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疆域,界定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新关系。“它重申了文本在课堂教学中的客体性,以及作者意图和主体性在文学学习和研究中的重要性。”“相对于作者之死,它把作者放回了文本。”[14](P5)创意写作的兴起正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在文学批评中逐渐式微的时期。创意写作蓬勃开展的年代,正是文学理论宣布“作者之死”的时候。这是形式主义作者理论的悖论。
四、形式主义作者理论的悖论及其思考
形式主义作者理论的悖论具体表现在:一是以否定作者的方式开启了现代作者理论的方向;二是以终结作者的宣言及其引发的争论将作者理论带入理论争论的中心;三是它倡导的文本细读的方式以否定作者为出发点却起到培育作家的目的。这既是形式主义作者理论的悖论,也是20世纪初直到目前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脱节和反背。这应该引起我们对文学批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的多重思考,也应该把我们对文学与文学性等基本命题的反思引向深入。
形式主义关于作者的探讨是封闭型的。作者构建与作者身份在形式主义那里缩略为作者的文本功能、阐释功能,抹杀了作者的社会属性、历史属性和作者身份的文化属性。就文本功能而言,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到被阐释的意图,已经远离意图本身,作者意图演变为批评家意图。这种封闭型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理念使得作者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重要性,缩小了作者存在的空间和领地。形式主义试图把文学批评划入所谓科学化的范畴,背离了作者作为人、文学作为人学的基本命题,以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科学化为标榜,使文学失去了对于一般读者的吸引力。形式主义对作者的拒斥,最终导致了“作者之死”的产生,引发了20世纪中期直到现在的关于作者的最大争论。
隔断文本与作者的联系,此为形式主义理论上的失误。其细读文本的策略和教学方式,客观上起到了对作家的精细化专业化的培养,推动和保障了创意写作的繁荣。这既是形式主义对于文学创作实践的作用和意义,又是对其忽视作者之理论主张的讽刺。具体说来,作家在形式主义切断文本与作者联系的课堂上会时时想到自己,从而学会了成为作家的最大原则:背叛。这种背叛是对传统的背叛,对形式主义理论说教的背叛。换言之,形式主义的作家既是形式主义的受益者,又必须是形式主义的叛逆者。在掌握形式主义技法的同时,即要抛弃其割裂作者与文本联系的主张,立刻要回过头来寻找形式主义批评中缺失的“人”,意识到作家作为主体的创造性和自觉性。这是形式主义的实践悖论,意味深长,具有讽刺意味。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训练了新一代的文学阅读者、文学批评者和新一代的作者。其文本细读的策略和方法成为批评家的基本功。同时,它的后继者以决绝的方式提出的“作者之死”并未将作者逼上死路,相反却激起了新的争论,将作者问题重新带入文学理论的视野。这是形式主义的理论悖论。
形式主义所隐含的对作者的否定和边缘化的悖论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文学世界中作者的边缘化和现实世界中人的边缘化高度一致。这既是理论的尴尬,也是人的尴尬,它把我们带回到形式主义的思想起点:当以职业化专业化之名,将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由人转变为物,这种起点是悖论的肇始和缘由,这种尴尬也许早就注定和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反思形式主义作者理论的悖论的时候,也许还应该思考这种职业化专业化的对与错、是与非,以及这种转变带来的理论的尴尬、人的尴尬。职业化和专业化对于科学研究或许是必须且有益的,而对于文学抑或整个的人文学科则并不一定是必须且有益的。文学理论也许应该重新界定它关注的对象和疆域,人也许应该重新安放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定义自己的存在及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作者理论则有必要挣脱形式主义的枷锁,重新找回作者与文本的密切联系。
[1] Alexander Bain.“On Teaching English”.The Fortnightly Review,1869,31(6):200214.
[2] Andrew Bennett.The Author.New York:Routledge,2005.
[3]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5][6][7][8][9][10][11][12] 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3] Mark Mc Gurl.The Program Era:Postwar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eative Writ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4] Michelene Wandor.The Author is Not Dead,Merely Somewhere Else:Creative Writing Reconceiv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The Influence of Formalism upon Modern Author Theory
DIAO Ke-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Formalism is of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modern author theory.The significance lies not in its direct contents but in its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uthor theory.The professionalism and academic pursuit of literary criticism put an end to traditional author-centered criticism, its text-centered criticism changes the direction of modern author theory.The argument of the author intention opens new clues to such concepts as the implied author.The strategy and critical methodology of close textual reading enriches literary reading experience and writing techniques.The time when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was put forward was the day when creating writing program with its goal of professional writer training started to flourish.The paradox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and writing practice should be of a serious reflection on modern literary theory.
Formalism;modern author theory;professional writer training
刁克利: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张 静)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代作者理论研究”(12YJA75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