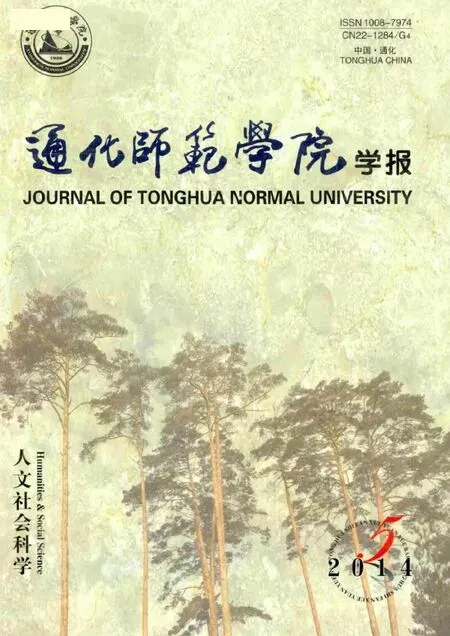“底层文学”研究的困境
王学胜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底层文学”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虽然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好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底层打工者为了抒发打工生活的孤寂,为了排遣“监狱式”管理对心灵的压迫以及其他种种不公待遇,往往会把亲历的或听闻的苦难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出来。读者,尤其是打工读者,看到描写自身境遇的作品自然就会有所偏爱。就像曹征路小说《问苍茫》中的毛妹一样,虽然不懂诗歌,但看到柳叶叶在公司黑板报上写的关于汇款的小诗时也被深深打动。读者如此买账,批评家们和期刊编者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雷同和苦难见诸大部分底层作品当中,其中不乏精英作家之作。最后,随着“底层文学”成为时尚,苦难也就演化为“底层文学”的标签,至于行文粗糙、人物干涩、情节突兀等缺乏文学“诗性”的方面都被掩盖了。好作品和题材有关系,但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好的作品,除了语言之外,笔者认为应该主要看其是否写出人性的深度,这种深度不会因为作品不写贫困的底层而打折,也不会因为作品未采用创新的文体而逊色。其深度如何关键是要看作品中是否体现出审美的超越性——超越历史和当下、超越世俗道德、超越宗教,最终抵达人性深层的所在。因而大量的以苦难作为噱头的“底层文学”,即使是取自生活中真实的实例,仍免不了让人怀疑是作者为“悲剧”的震撼效果故意把主人公往死路上赶。如尤凤伟的小说《泥鳅》中,进城打工的姑娘要么去当小姐如寇兰,要么被逼疯如陶凤;进城的小伙子如果不做违法的勾当,结果是非死即残。 这种过于刻意或者模式化的写作导致“底层文学”嘘声四起。尽管文学期刊中一如既往地刊登“底层文学”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期刊仍旧开设“底层文学专栏”,但读者仍然怀疑:“底层文学”作品是数量重要还是质量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们对“底层文学”的研究状况难脱其责,其中既有研究本身的局限亦有逻辑建构问题。
一、“底层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底层文学”的边界模糊,很多分歧意见和难题在“底层文学”的相关研究过程中频繁出现。当代文学批评者品格的缺失以及批评实践中的懒惰在此显露无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底层文学”大多只是历史性的描述却很少文学描述,因此在评价该类作品时,所要考虑的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当中,往往不会包含人物、语言、象征、意象等,这具一定的合理性。可是问题却随之而来,因为无法归纳出“底层文学”的艺术边界,于是我们往往只是凭借印象而定或者不再思考“底层文学”究竟包含哪些作品。由于“底层文学”的范畴不确定,造成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围绕相类同的内容进行,这就导致了评价结果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让当代文学批评的惰性展露无遗。像前面所说,对“底层文学”评价不是基于文学艺术水准,而是更多地考虑是否合乎事实,因此在评价 “底层文学”优劣时,最主要的评价因素并不是它的人物形象、语言推进、细节展现、氛围营造等。这种状态如果发展下去,一个临时的“底层文学”无法准确地勾勒出它的艺术范围,究竟什么作品算作“底层文学”,什么作品不能界定为“底层文学”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所处的经济地位来说,农村留守的老幼病残、进城打工人员、失业的城市贫民可以算做纯正的“底层”,以此为题材,描写刻画他们的生存境遇,揭示他们的人性内涵的文学作品,可称作“底层文学”。
第二是样本问题。“底层文学”研究对于样本的选取是有很大局限的,这主要是因为样本选取主要是近年来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上的作品。这种选取方式造成了一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优秀作品被漏掉,导致了研究的片面性和狭窄性。另外样本选取还主要集中在知名作家身上,这就更局限了研究的视野。由于知名度高,以知名作家的作品作为讨论的起点势必更容易为大部分研究者接受。然而,有些知名作家从未在底层生活过,即使是去底层体验过生活,更多的只是走个过场,底层的内心想法他们是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他们的“底层文学”创作纯粹是出于“想象”,或基于已有的主题及事先设定的故事模式。而那些出自“无名之辈”的作者之手的作品难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无论它们是如何的优秀。研究样本的选取局限暴露了“底层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合谋”现象。作协中的精英作家的创作与研究所或高校的研究者的研究都指向了底层关怀和构建和谐社会。前者在创作中演绎这种既定的思想,后者带着相同的思想来解读作品,两者演出了一场精彩的“双簧”。
第三,惯性思维也是影响“底层文学”作品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关键因素。例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让很多研究者把“底层文学”作品中展示的复杂矛盾简单地纳入城乡对立的逻辑思维当中。至于作品中所展示的人性弱点与社会的不公,研究者除了习惯思维当中固有的几种思维模式之外,就找不到更有效的剖析方式。
第四,鲜有创见的观点重复。众多的学者通过解读不同的作品阐释大致相同的问题,已经成为痼疾。这种没有创见,重复他人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剽窃。比如关于“底层文学”过度渲染苦难的观点,就在几十篇论文当中出现过,当然所选用的例子是经过替换的,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表面上是丰富了文本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懒惰的表现。鉴于作者的名气以及洋洋洒洒的流畅行文,即使有上述弊病,仍能占领各大权威期刊的阵地。
第五,“阐释大于创作”,这是一个“底层文学”研究当中容易忽视的问题。文学的信仰时代已经远去,再也不会出现1980年代时的情形:社会热点题材的电影一公映,便万街空巷。这不仅仅是因为读者素质的的提高,更主要的是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它们都无法解决经济学家都难以解决的难题。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中的主人公工会主席“我”的小舅朱卫国因为享受正处级待遇早已被工人阶级看成是“外人”,他两次集资救厂,均以工人血本无归收场。加之初恋情人杜月梅做妓女夜归时被朱卫国所养的狗吓瘫痪了,原本自视为工人阶级代表的他,生存支柱轰然倒塌,在打了一大堆镰刀斧头之后,他用自制的气锤砸瘪了自己的脑袋。曾经以共和国“主人”自居的工人阶级一夜之间沦为失去了起码的生存保障的社会弃儿,不能接受欺骗过他们一次的工会主席的第二次“欺骗”,因为他们知道了厂方给朱卫国股份的事情。作为解释更是为了捍卫心中的理想,朱卫国选择自杀作为扭转工人困境的筹码,小说中工厂的非法并购被终止。但是稍有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更多只是一种幻想,中国内地国有资产借着盘活的名义很多都流进了权势者的腰包。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那儿》给我们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案,但是小说设计主人公的自杀情节来博取读者的同情心,目的是为了拨开政府宣传的虚假幻象,从麻木中拨开迷雾,逐渐去改变各种社会的不合理的事实。这些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赚取读者泪水的过程,加之人物形象虚假,结尾的失真都让《那儿》在实现思想主题时留下了生硬的痕迹。为了免受质疑,曹征路多次在访谈中和会议中阐释自己作品的创作初衷和目的。一些对曹征路持赞赏态度的批评家,也对小说进行了过度阐释。莫言所提倡的 “为老百姓写作”演变成 “主题先行的写作”。就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言,读《那儿》显然没有读郎咸平的一篇学术论文更有意义。文学活动或文学创作需要厘清自身的限度,除去生动的语言、细腻的细节、丰富的想象,文学作品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实际上没有多少作用可言。因此如果处理不好创作意图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就可能成为一种僭越,既解决不了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也发挥不了文学独特的社会作用。
二、“底层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
(一)如何表达底层生存。在做这个层面的研究之前,需要确定一个前提:暂时抛开目前的争议,把“底层文学”的创作主体限定为精英阶层作家和从“打工”等底层身份逐渐成长起来的底层书写者。于是,需要我们花费精力且用心面对的是如何更好地表达“底层”,以及精英阶级是否被允许书写底层就一点也不重要了。如何更好地表达底层。其一,“底层文学”的“文学性”与“大众性”,即“雅”与“俗”的问题。“底层文学”若想成就当代及后世的经典作品,“文学性”是撇不开的内容,而“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范式的独特性又要求其符合“人民性”的要求。一种只讲求形式的文学不可能既有效地获取丰富和复杂的底层经验,又饱含深邃的审美意蕴。二者既然不是水火难容的宿敌,如何才能找到最佳的“黄金结合点”?其二,“底层文学”和左翼文学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后者的某些光荣传统能否成为前者的典范?其三,“底层文学”如何脱离现实主义的束缚? 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的精神内部,真切地融入到生命的性灵当中。其四,情感距离的把握。“底层文学”作家的理性思考因为同情心的“泛滥”而缺失在很多作品中普遍存在。如曹征路的小说《问苍茫》中将化解劳资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的法律维权意识的觉醒上,显露出作者对问题理性分析的不足。作者站在打工者的立场上完成小说的叙述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囿于对打工者的同情心理,否定资本在经营管理中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则是根本未触及当今社会经济复杂问题的实质。洪治纲毫不留情地道破问题的症结所在:“作家普遍地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1]124洪治纲又进一步指出:白壁德作为一位新人文主义的大师,他认为只有用判断与思考来制约同情,同情才不会泛滥,人文主义才能与其身份相符。“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1]124本人是十分赞同洪治纲的观点的,我认为如何克服情感对于思考的僭越是“底层文学”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作品文本价值的评价。文学基本价值的分析和认定,是所有文学研究都不能动摇的核心,“底层文学”当然也是如此。目前对“底层文学”文本价值体现出两种取向:一种是从文学性角度的“棒杀”或从关注现实的角度的“捧杀”;另一种是“和稀泥”式的价值判断,先说出作品的价值所在,接着再找几点不足,这样既不得罪作家,也显得考虑周全、思路周密,但是在分析文本艺术价值的不足时,大多是笼统地讨论,很少有较强说服力的细致剖析。这些停留在作品主题、人物和情节层面上的分析,因不能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既不能阐释作者的审美追求,也无法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文学艺术的本性决定了“底层文学”优秀作品的筛选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时间的磨砺和淘洗。我们若想建立对单篇作品乃至“底层文学”整体进行准确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光凭借理论话语的堆积是实现不了的,只有进入个体文本中去发现其审美的独到之处,并且还要杜绝片面、角度单一的毛病才有可能。
实际上,文本分析做得如何直接关系着文学研究的发展。通过文本分析可以评判文本传达是否有效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从而把作品与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作出比较,为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作好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富有见地的文本评析,才能找到作品中真正的“诗性”所在,从而建立作者提升作品艺术空间的方向和目标。在“底层文学”创作的一线作家中,有很多人对自己的作品,不仅充满自信,而且在访谈录中为自己的创作理论寻找经典作家的言论支持。例如陈应松就与李云雷的访谈中说:“有一天我读高尔基终于看到了他的这么一段话:‘对人类和人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这段话就让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好像找到了组织。”[2]43-47现实主义是否是“底层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在冷静地仔细研读作品并提供各种卓有成效的艺术分析之后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三)“底层文学”接受者研究。“底层文学”把当下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作为书写对象,社会底层小民的穷苦伤悲成为其关注的重点,无论能否成为当代或未来的经典,它都要面对当下的接受群体——主要为高校学者、大学生或中产阶级等不为生活所累的人群构成的读者圈。他们中除去原本来自底层而正在求学的大学生们以外,都对底层社会的生活实际所知甚少(即便是出自底层的学者、中产阶级对曾经的底层生活体验已今非昔比),而他们对“底层文学”优劣的价值定位是“底层文学”向前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但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底层文学”读者接受层面的研究。与此同时,“接受美学”早已在中国“扎根落户”,其他范式文学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已经深入人心。当下“底层文学”研究明显缺乏从“接受美学”意义上对读者群的分析和综合,这种缺憾是当前“底层文学”研究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重要难题。
此外,“底层文学”经典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要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情况,即读者是否“买账”。黄也平教授在2005年谈到文学经典能否产生的问题时,不赞成于盖生所重视的“‘典’代表当时写作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文本’的观点。而是取决于人们是否把文学文本当作经典来阅读,取决于人们对文学文本是否采取了 ‘经典态度’。”[3]可实际上,底层读者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和审美情趣等决定了他们无法介入“底层文学”的创作和争论。他们与“底层文学”是存在隔膜的,导致其阅读范围往往局限在冒险、色情、凶杀等低俗读物上,这种局面如果无法改变的话,经典就难以真正产生。
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无论理论界争论得多么热闹,无论创作技巧上总结得多么有力,无论评论界阐释得怎么深刻,必须对底层读者对“底层文学”的整体接受状况及接受效果展开有效的研究,否则基于“底层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必定是不完整的。底层平民的生活是“底层文学”主要展现的对象,如果他们对“底层文学”的好坏漠不关心,实在有些尴尬,然而这些不利局面将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有所改变。与此同时,文学相关理论的研究毕竟不同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它们更加独立并且能够超越日常生活本身,这种特点让它可以摆脱大众文化程度和审美情趣高低的束缚。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如果缺乏“接受美学”的研究,任何研究都是难以健全的,特别是“大众化”的文学现象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提倡应该在两个层面对 “底层文学”的读者展开研究,是作者的审美出发点与接受效果,即创作主体与阅读主体之间的隔裂与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