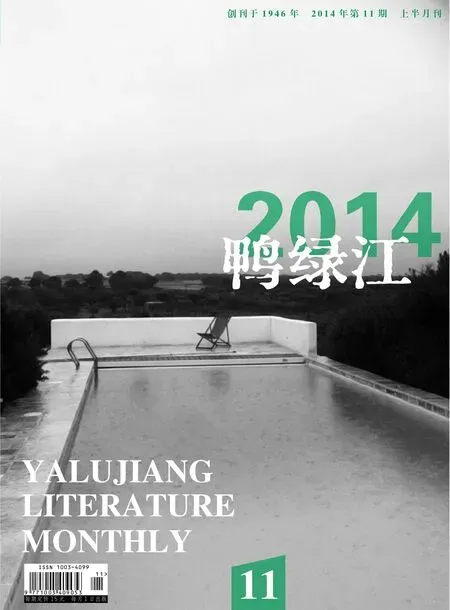以正“视听”说“改编”
——为电影导演辩护
郭 明 罗 娟
以正“视听”说“改编”——为电影导演辩护
YIZHENG“SHITING”SHUO“GAIBIAN”
郭 明 罗 娟

郭 明,曾任辽阳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浙江横店影视学院副教授,辽宁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红学会会员,有纪录片《董村故事》《渔光新曲》、著作《烛影摇红》等行世。

罗 娟,江苏扬州电视台新媒体“无限扬州”总编辑,多年从事电视节目的编辑和主持工作,其参与主创的作品曾多次荣获多类大奖。
一
“以正视听”是个成语一一动宾式成语;“以”:利用,使用;“正”:纠正,正名;“视听”:看和听或者见与闻,指对事物的感觉、印象和看法。成语用法:作谓语、定语。
本文章所用“视听”,是取其字面意义,特指电影媒体的造型语言“视听语言”;“改编”,是指由文学改编为电影的过程和结果。题目结构为倒装句,则全句意为:谈一谈改编相关问题,为“视听语言”正名。这样做,也是为导演的改编电影做一辩护。
我们看一看近日上线的张艺谋新作《归来》的一篇评论:《归来:剧本硬伤背后的情怀沦丧》
陆焉识逃跑回家的人物动机缺失。而在原著小说中……对女儿的迫切思念,是陆焉识逃跑的最大行为动机。
电影《归来》篡改了这些剧情。女儿也不是什么生物学女博士,却是一个跳芭蕾舞的”。
陆焉识被释放回家后的剧情堆砌叠加。……而在原著小说《陆犯焉识》中,严歌苓对陆焉识“归来”后的故事处理,力在彰显错误时代对子女们的错误影响。
网络上署名孙华钰的这篇评论前面还有“编者按”:
在本文作者看来,《陆犯焉识》的最大价值,在于用小说的方式艺术化了劳改犯的狱中笔记,用真切的语言向后人展示了我们历史时期的错误;但在电影《归来》中,没有历史灾难,只有无缘无故的纯善。1
这是一篇很典型的关于改编电影的评论文章,作者站在文学的立场,以“而在原著小说中”为判断依据,以改编电影与原著契合度为评价标准,完全无视小说与电影两个媒体之间的本体论的形式差异,混淆了文字语言与视听语言的审美区别,给电影改编与观众欣赏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充满了改编研究的偏见。
所以,类似的研究与批评,显然是亟待厘清的理论误区与需尽快纠正的评论方法。
二
改编现象源远流长,改编研究则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作为跨学科的存在,有人赞同,有人质疑。支持改编的理由是:“面对这样的视觉时代,传统的单从文学批评或媒体学角度来分别进行的文学研究及电影研究便显得力不从心,需要对当今社会中各种类型的改编现象进行有意识的系统研究,找出相互之间的区别点及共同规律,并对各种改编进行分析批评,以提高我们对各种类型改编的认识,更好地应对视觉时代中文化信息和传统,特别是经典文化传统的承续、交流和拓展”。这里的改编是广义的。狭义而言,就改编电影来说,改编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应对“经典文化传统的承续、交流和拓展”。电影当然不是“经典文化”,所以,研究者的立场就是站在文学的角度,以文学为标准,“分析批评”电影这个改编媒介,在文学到电影的承续、交流和拓展中,是否尊重了文学。
据此我们看到,改编研究开宗立派一开始就充满了偏见。他们认为,“改编自经典文学的电影,本身就多少是对经典文学有意无意的‘误读’和‘歪曲’,是对经典文本的‘侵蚀’,对经典文学的传播和研究有害无利。”如果说对经典文学顶礼膜拜情有可原的话,改编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则显得莫名其妙了:改编不如原著,“这透露出‘改编’一词长期以来带给受众的心理暗示。……改编作品不仅会陷入无谓的忠实与戏说之争,也会被先行者的光辉所遮蔽。除此之外,文学具有的精英意识在无意识中与研究者的身份暗自契合,‘文学优越’心理在研究者这里也是根深蒂固,在学术研究中也难以保持评价的公正。”如果说改编研究者挟文学以自重也可以理解,那么,对第七艺术电影的集体无意识的误判则显然匪夷所思了:“在艺术史中的后来者有一种迟到的焦虑,笼罩在前辈阴影中的狂躁,于是捡拾起个性独立的武器与伟大的传统抗争。影视艺术的后来者身份更为显见。然而,这个后来者非但不焦虑,反而具有一种优越感。它后来居上,对其他艺术形成了‘殖民化’的倾轧。”正是改编研究领域的种种偏见,使得改编研究进退维谷、故步自封、处境尴尬。改编研究者一方面指责改编“从研究方法看来,注重差异比较,特征归纳的影视改编研究带有现象研究的痕迹,概括、总结几种改编方式就结束了自己的思考”的同时,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改编研究从术语来看就已经把研究对象严格限定了,强调研究原作与改编的区别。这反映出影视艺术与小说这两种叙事媒介的差异,但是不一定能探知改编创作的真正动机。”耐人寻味的是,改编电影本来是导演的艺术,在改编研究连篇累牍、著书立说的热闹中,改编的始作俑者导演却一言不发,他改编完成,影视放映,就把银幕或者荧屏给予观众,把评论留给研究者。
三
文学与电影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否则也就无所谓改编了——有着不同的本体论。
本体论(Ontology)一词是个哲学概念,由ont加上表示“学问”“学说”的词缀——ology构成,即是关于ont的学问。ont源出希腊文,相当于英文的being;也就是“存在”,即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用于描述事物的本质。根本问题是:“存在的最初分类是什么?”回答则是一个同义反复:“是什么就是什么。”
关于本文所论,即文学就是文学,影视就是影视。
文学是用语言构成文字形象,即语言文字通过意义和表象的符号刺激大脑皮质后在脑海中引起的某种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文学文本的视像迁移总体上说,是一个从抽象间接的文字符码形象体系向立体空间形象体系的艺术转换过程。
视听语言,即我们一般称“影视语言”,以区别文学的文字语言。
影视语言包括两个元素,即音响——声音(听),镜头——画面(视)。声音镜头是就技术而言,音响画面就是艺术而言。
音响包括人类声音(台词、旁白、内心独白等等)、自然声音(风雷雨电、鸡鸣狗叫等等)及人造声音(主题歌、主旋律、背景音乐、超现实声音等等)。画面包括镜头景别、运动、表演、服装、道具、光线、色彩、剪辑、特效等等。又因为影视创作呈现的一个特点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因此影视语言是以“视”,即画面为主的造型语言。这也是一般要求影视语言“有画面感”的原因。
因为是“视”,所以影视语言对抽象的东西——如意识、思想、心理活动等等——无能为力,只能摄入具象的东西。当然,具象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限制了想象力,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或者林黛玉了。因为是“视”,画面也具有模糊性与多义性,必须依靠剪辑来确定确切意义,所谓库里肖夫效应。因为是“视”,镜头画面对观众的影响是非理性感官的、潜意识的。因为是“视”,画面也具有不可言说的特点。例如:“意大利电影……是不是?”语言本身表述不是自足的,所以听不懂,需要看见说话人“竖起大拇指”的手势动作才视听完善地表达了确切的意思。
另外,影视媒体基本上属于时间媒体,在时间流中依次呈现,所以,影视结构的技巧偏向于制造悬念来吸引观众看下去。这个也是“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及作品《眩晕》被誉为电影发明百年来第一导演和第一电影的原因所在。

四
文学语言与视听语言是各有长短优劣的,试举《红楼梦》为例:
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马瑞芳女士在《红楼故事和文本写法》中评论到:“黛玉到荣国府,王熙凤登场,如此恭维黛玉:‘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自算见了。’黛玉具体标致到什么程度?作者不写。林黛玉那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必须用宝玉眼睛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电影发明以后,这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学技巧,即通过贾宝玉眼睛看林黛玉来表现林黛玉,仅仅是一个电影的所谓的“主观镜头”而已,即摄影机的镜头与故事中主人公的眼睛重叠的拍摄技巧。
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秦可卿卧室描写的那段游戏笔墨:“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可卿“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视听语言无法呈现这里面暧昧旖旎的含义,入画面的仅仅是镜子、盘子、木瓜、榻床、帐子、纱衾与枕头等道具而已。
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里薛蟠过生日的场景,他对宝玉说:“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他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猪。”这些东西到底是多大多粗多长,这样夸张的文字,文字语言完全依靠想象才能感觉一个大老粗的形象,而视听语言凭借演员的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比比画画就活灵活现地塑造了滑稽粗鲁语言贫乏的生动形象。
如此比较,例证多多;限于篇幅,浅尝辄止。
五
科学研究的方法,前提是将研究内容分类。关于改编,安德烈·巴赞《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将改编方式归纳为四种:
A.文学仅仅为电影提供人物和情节,电影借题发挥。
B.在文学创意基础上重新创作故事,原著无关紧要。
C.电影借鉴文学详细的故事梗概,复述故事全部内容。
D.改编“忠于原著”的“精神”,涉及新的创作标准。
巴赞在这里提出几个(D)与(C)区别的标准要素:风格、心理、伦理或哲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巴赞所认可的改编,是所谓“忠实原著”的改编。
巴赞英年早逝,理论的局限性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在所难免,毋庸讳言。关于改编电影的方式方法,后人发明多多。
就中国方面考察,电影改编理论,大致可分为“忠实观”“创造观”和“戏说观”三种:从原著的视角归纳分析“忠实观”的艺术主张,分为“绝对尊重文学作品”“力求忠实原著”及“以电影的方式忠实原著”三个时期;从电影的视角归纳分析“创造观”的美学表征,分为“增删”阶段、“再创作”阶段、三是“自由再创造”阶段;从受众的角度梳理“戏说观”,一方面“赋予了原著或经典的再生价值”,另一方面表现出“娱乐的滥觞与人文的缺失”。美国电影理论家杰?瓦格纳把改编分为三种,即移植式、注释式和近似式。迈克尔·克莱恩与吉利恩·帕克也将电影改编分成三种:忠实式改编、批评式改编与相对自由式改编。美国电影研究学者达德利·安德鲁把改编分为借用、交叉和变形三种。还有的学者将改编分为解读、解构与重构三种。电影改编理论,其实最值得称道的还是电影这个人类第七艺术发明地法国的探索,他们不纠缠改编理论。让·爱普斯坦说:“我对待所有的剧本,例如原版的剧本,就把它当作是属于我的,从开始导演的第一刻到最后一刻。”大名鼎鼎的“诗意现实主义”导演让·雷诺阿,所选择的故事都是出自那些线条明朗、一目了然的小说,而这些情节纲要也正好完全符合他的想象。小说的主题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载体而已,如果能使出自于现实中的虚幻大放异彩,他便毫不犹豫地打乱原有的故事情节而使其成为一种可利用的价值,甚至可以仅围绕一些次要的细节而展开他自己的情节。中国导演田壮壮披露张艺谋的改编,“基本上是找一骨节儿改,比如《红高粱》《菊豆》”。所谓“找一骨节儿”就是“只抽取了其中某一‘骨节儿’来重新创作”。实际上是导演“依照自己的需要,对被抽取的部分加以完全主观的改造”。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介绍说:“鲍十与张艺谋合作的《我的父亲母亲》几乎从内容到形式全部推倒了原著《纪念》(仅保留了一些人名地名),主要是在张艺谋的讲述中,一场场地‘捋戏’。”“李冯与张艺谋合作《英雄》,动笔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戏,甚至台词都已经谈出来了,主要是张艺谋谈,每一次都要把剧本说得非常非常详细。”姜文导演改导演编《鬼子来了》,原著作家尤凤伟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他说“《鬼子来了》剧本(二稿)从本质上背离了我的《生存》小说剧本原作”。在比较了原作与电影后,他的结论是:“《鬼》本在人物、情节、细节等方面对原作及《生》本进行了肆意篡改与砍杀,用姜文的话说只是保留了原作的前半部分。实际情况比这要严重得多……《生》本总共有68个场景(自然段落),《鬼》本没有完整保留下一个场景,重要情节全部改变,简单统计一下,被肆意砍删掉的场景达95%以上。”这些鲜活生动的例证,说明改编或许并不如研究者所说,如何从原著找镜头。改编过程存在于导演或者编剧的脑海之中,他的思维不是文字的,而是一个视听语言思维的特征,是一个空间音画想象的过程,有其自身形式的限制,或者说艺术表现的考量与无奈。作家的抱怨当然无可厚非,我们感兴趣的是,导演为什么对原作肆意地“砍删掉”?应该不仅仅是态度“尊重不尊重”的问题,也不是原著“经典不经典”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捡拾起个性独立的武器与伟大的传统抗争”的问题,客观看待,还是电影创作自身构思的需要。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导演不会迁就作家,当然,也不会因为尊重作家而放弃电影独特的艺术创作形式。
对改编来说,巴赞划分的低级改编,“借题发挥”“重新创作”的改编,恰恰因为电影形式美学放到优先地位考虑,本体论得到尊重,借助于文学因素,尽管它与文学的契合度低了,但也许更能够创作出一部意义自足赏心悦目的好电影。反之,按照改编的高级标准,“复述故事”“忠于原著”,这样改编的电影,因为两者本体论各异,即艺术表现形式根本不同,受制于原著的影响,可能绊手绊脚、邯郸学步,反而影响导演才华的发挥,致使创作出一部不伦不类的电影。
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越是经典名著改编越难于成功,而二三流小说则可以改编为很成功的电影。
六
例如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先生生前所言:“我的意见,认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演的。”后来,陈白尘导演、严顺开主演的同名改编电影《阿Q正传》上映了。我们看到,开篇让作者鲁迅先生出镜来介绍阿Q身世的暗淡,好像是穿针引线的作用,却显得莫名其妙。问题出现在哪里?鲁迅的开篇第一人称叙述不仅仅是行文的方便——如《祝福》——而是一个“元小说”结构。先生在开篇讲述的是如何给阿Q起名,是在小说中讲述怎么写小说。元小说结构对应的不是第一人称,是元电影,而元电影是“戏中戏”式的套壳结构,即在电影中讲述如何制作电影。元电影开山之作是前苏联导演狄加·维尔托夫的纪录片《持摄像机的人》,成功之作是著名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
不仅如此,鲁迅在小说中深刻阐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喜悦;假如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感到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证据了。” 由此看来,这样精辟的阐释,所谓“深刻”,是挖掘出来的,是对形象深入挖掘的结果,即使电影应用画外音来扩延,仍然是文学的,不是电影本身形式固有的。
相反的例证是,美国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华盛顿广场》一开始就遭到作者本人的嫌弃,认为“故事单薄”“内容乏味”“引不起广泛兴趣”,但是,这部在文学界受到冷遇的作品却成了电影人的宠儿,被五国人十三次搬上银幕。更典型的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逝》,本是二三流小说,因为改编电影《飘》却华丽转身为世界经典名著。
文学名著改编电影反比例,原因若何?当然不仅仅是导演与作家天才匹配的问题,根本问题仍然是本体论问题:文学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文学性。文学性是形象刻画、心理描写、语言风格、思想哲理等等,这些,正是视听语言的短项,或者说是视听语言所排斥的。
七
另外,更令改编研究者沮丧的是,究竟什么是“改编”,至今理论界都不明不白。20世纪90年代,中国有关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汪流、王晓玉认为,电影改编是“艺术创作过程”。 不同的是转换到电影杀青还是电影剧本,显然前者正确。陈林侠则提出了“生成说”,主张以“生成”术语替换“改编”术语,提倡一种影视生成研究。国外文献对于“改编”的含义表述也不尽相同,有翻译、移植、模仿、阐释、转译、反思等等。安德烈·巴赞用的是“借鉴”说。
同时,对改编研究持有异议的也不在少数。张冲主编的《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理论与应用》中介绍改编研究进入学术界的情况,标志是2006年,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惠特拉与卡特梅尔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里根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学术组织“文学与银幕改编研究学会”,2008年更名为“改编研究学会”。但是,这个研究,一直处于学术夹缝之中,一方面受到“正统”文学研究者的质疑,认为改编自文学的电影是文学文本的附属或者“衍生”产品,不具备必要的“学术性”;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电影研究学者的质疑,改编的产品是电影,与普通意义上的电影研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能让它“回归”电影研究的范围?结果是,在文学院系,改编研究在学术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而在电影院系,改编研究基本处于电影研究的最边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这样的研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因此,改编现象分析其实只有区区两个意义:一是对于电影来说,是个票房问题;二是对于原著来说,是个版权问题。前者如马塞尔与克莱尔所言:“在电影改编以特殊的方式影响电影制作的主要原因中,占据首位的是商业上的原因。”后者如中国作家池莉所言:“小说的好坏与电影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电影再好也是导演的,不是作家的……我的小说与电影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金钱关系,他们买拍摄权,我收钱而已。”
八
当然,改编现象的存在,或者说电影的发明,使文学与电影,还是建立了友好的互动关系。
法国的艾·菲兹利埃说过:“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文学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
电影对文学的影响是两极分化的。
一种是作家刻意躲避电影改编的侵扰,调动一切文学手法,创造诸多语言、叙事、结构文体等等诸多技巧,寻找不被电影改编的命运。
例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运用了浪漫主义恋爱小说文体,写了意识流,借鉴了剧本的形式、宗教问答体,还有滑稽剧、新闻、散文、教科书等等文体,使小说呈现“整个是一个英语文学语言演变史”“一部结束了所有小说的小说”。 这样的文体,以画面声音见长的电影还怎么改编?作者还告白:“我在《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作者让你读者、研究者、改编导演等猜不出“原意”,你还怎么“忠于”原著?
前面说了,电影作为时间媒体的特征,就是保持悬念。但从小说学来说,“一部小说中有太多的悬念,那么,小说就会逐渐衰竭,逐渐被消耗光。小说是速度的敌人,阅读应该是缓慢进行的,读者应该在每一页一个段落,甚至每个句子的魅力前停留。” 吴晓东博士在谈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设悬念时还说:“昆德拉在《生命》打破了悬念,他的小说所依仗的吸引读者的手段就只能是别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姑且说是一种命运感。对主人公命运的无奈和悲悯。昆德拉失去了悬念,却得到了比悬念更丰富的东西。”其实,这样的技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早就使用了:后果前置。
另一种影响是刻意直接模仿电影写作。巴赞文中列举了某些作家,例如美国小说家多斯·帕索斯《曼哈顿中转站》《一个青年的奇遇》《北纬四十二度》;埃尔斯基·考德威尔的《烟草路》《小坟场》与《七月麻烦》。某些通俗作者的写作有着双重目的,显然另一个目的即是同时兼顾电影脚本。美国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一看小说,就知道作品写作的潜意识中已经兼有改编电影的预设了。巴赞说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在这种影响或应和过程中,小说的风格的发展方面最明显。譬如,它极巧妙地运用了蒙太奇技巧和时序的交错。尤其善于把一种缺乏人性和冷冰冰的客观主义效果升华为真正的形而上寓意。”笔者有限的了解是,这样作家典型的例子是秘鲁作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略萨《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将电影蒙太奇的声音匹配技巧玩得得心应手,运用于家庭、军队、祭祀三个场景的转场。
除此而外,电影还修改了小说的评价标准。有了电影作为参照物,评论家的立足点当然也是本体论的坚持,所谓好小说也就由以故事人物性格情节刻画擅长的雨果、左拉、大仲马、福楼拜、契科夫等等,定位于可能是回忆(普鲁斯特),可能是对深层心理的传达(乔伊斯与意识流),可能是呈示荒诞与变形的存在(卡夫卡与存在主义),也可能是“物化”世界(罗伯—葛里耶和新小说),或者魔幻化的现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当然,还有拉伯雷的《巨人传》。

九
文学对电影的影响意义巨大。俄国电影大师蒙太奇发明者谢尔盖·爱森斯坦曾经说过,他所需要的电影技巧的百分之七十能从巴别尔小说中找到,而巴别尔的电影剧本只能提供百分之三十。仅在他的日记中,就有很多描写让人感到电影语言的长镜头与广角镜头混用、远景与特写并置、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交织、相关与相反画面的拼接、画外旁白与现场同期声叠印。我们仅举《骑兵军·泅渡兹勃鲁契河》一段为例:
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紧扎。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流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巴别尔·柳托夫的文笔,具有强烈的画面意象和音响效果,虚实变焦,远全中近特、推拉摇移跟的镜头感,甚至还有光线,当然还有风格。
中国的作家有诺贝尔获奖者莫言的例证,张艺谋导演的改编电影《红高粱》够经典了,大部分镜头皆来自莫言的首创,包括那些仪式化的颠轿、野合、祭酒等等的桥段,还有那满眼红晕晕的高粱地意象。张艺谋说:“我觉得莫言笔下的这些人活得有声有色,活得简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抢女人就抢了,想到高粱地里睡觉就睡了,我喜欢他书中表现的那种生命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自由放纵。”“咱要传达出莫言小说中那种感性生命的骚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真活得挺自在,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想折腾就折腾,把这点事儿说圆乎了,把人对生命热烈的追求说出来,有这点小味道就差不多了。”“它最打动我的是爷爷和奶奶的爱情传奇,是充满活力的人,是那种豪放舒展的活法。”“我觉得,生命的崇高表现就是爱和死。死是很残酷的,爱是很诱人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对爱和死都是顶礼膜拜的,认为它们是生命中很神圣、很美丽的东西,我是怀着对生和死的深情礼拜,来拍这些戏的。”被誉为“作者导演”的香港王家卫,其《重庆森林》利用了文学中的互文结构技巧,简直可以追溯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了。
十
行文到此,试作几点结论:
(一)文学与电影两个艺术形式,因为改编,有了缘分。但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改编学却因为偏见所致而差强人意又未尽如人意,对影视方面外行的分析与对文学方面过度的阐释,可能只是研究者自说自话而已,对文学与电影的创作、欣赏、批评与指导除了误导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特别是分类比较、改编评价,更是无视本体论的差异。文学作者与电影导演都不会承认与认可。这也是笔者看见一些涉及改编的电影评论不以为然或者翻阅许多改编理论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所在。
(二)改编电影,诚如巴赞所说:“既忠于原著,又特立独行,确是逆乎常理,不同凡响。” 在创作上,我们认可改编的合理性,不同意持纯电影观点人的主张:“把属于戏剧和小说的东西归还原主,把电影独有的东西留给电影吧。”但是,在改编的评价上,我们似乎应该承认并且遵循这样的主张,“小说家最终改变了电影,当然,电影毕竟还是电影”。文学与电影本体论不同,评价就不能纠结纠缠,不清不楚;倒是何妨牝牡骊黄,各行其是。如钱钟书所说“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直白说,评价改编电影,必须并且只能抛开原著因素,视文学素材为生活素材,就电影论电影。在电影的系统美学标准下,衡量其电影的艺术成就。
(三)电影的发明,文学与电影相互影响,促进了文学与电影各自争锋,齐头并进,确实使得两者艺术形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改观,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天地因此开阔起来,作品也日益丰富多彩。认真总结电影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对电影的影响,是饶有兴味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所谓纯电影与纯文学,就是各自艺术探索的先锋派,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在文学尊重电影改编态度的同时,文学也不必因为电影的出现而割地退让,自丧领土。这样,文学才能够在为电影改编提供丰富多彩的题材的同时,在提高电影艺术品位的同时,扩大文学的成就、影响与传播。
责任编辑 陈昌平
1、http://club.kdnet.net/dispbbs. asp?boardid=26&id=10066146
2、《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张冲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一版
3、同上2
4、《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陈林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一版
5、同上4
6、同上4
7、同上4
8、《电影是什么》,(法)安德烈·巴赞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1月一版
9、《中国电影改编理论研究》毛攀云http://www. doc88.com/p-994218674268.html
10、同上2
11、电影与文学改编》,(法)莫妮克·卡尔科·马塞尔与让那·玛丽·克莱尔
12、《从文学到电影:第五代电影改编研究》,傅明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一版
13、同上4
14、同上2
15、同上9
16、同上2
17、同上11
18、同上4
19、《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吴晓东著,三联书店2003年8月一版
20、同上8
21、同上8
22、《与巴别尔发生爱情》,王天兵编著,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一版
23、《骑兵军》(苏)巴别尔·柳托夫著,戴骢译,王天兵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月一版
24、同上12
25、同上8
26、《钱钟书论学文选(2)》,钱钟书著,舒展选编,花城出版社1990年1月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