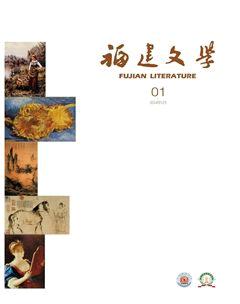音乐天使
海滨都市的一场钢琴音乐会就要开场。
翻谱女子出现在音乐厅的舞台侧翼,向着台上走来,比钢琴与大提琴演奏家稍后几秒,在欢迎的掌声刚开始减弱之时,走进灯光。根据精确的计时,翻谱女子知道这掌声不是为她而响。并非过于谦卑,而是分外清醒,她决不想分享哪怕一丝不属于她的掌声。她只为一个使命登台而来,一个有点荒谬却颇为值得的使命——在即将降临的光荣与辉煌之中,成就一种让步,一种对世事之极限与精神之极限的让步。
精确的计时,毋庸置疑,是翻谱者最必要的素质;而谦恭,对于她也同样重要。虽然翻谱女子可以尽力表现得谦恭,用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方式减弱自身的光芒,她却无法使自己完全不引人注目。她的突然登台与两位音乐家的登台一样令人兴奋,甚至令人惊喜。她肩披如瀑布般的黑发,黑发的色泽像春光四射,与舞台的灯光交相辉映。比起两位演奏家,她显得那么青春,颀长的身姿在台上亭亭玉立。她着一身米黄,米黄色是力显谦恭、力蔽锋芒者的首选。然而,这身米黄的衣裳却以如此引人的气质裹住她的肌体,虽然肌体仿佛是按照这身米黄衣裳塑造而成,但却调皮地抵抗着将它裹住的“米黄色的谦恭”。她的米黄色长袖针织衫衣长过腰,米黄色宽松裤在她纤细的大腿周围颤动,在裤腿边下,可以瞥见隐隐闪光的米黄色高跟靴。她的梨形脸庞,似童话《绿色森林》中的苏菲公主,又似春天初放的栀子花。唯一没有被米黄色裹住的脸、颈子和双手,肤色白净得如同纯奶油,双唇则抹上了淡淡的玫瑰红。
从翻谱女子的稚气表情来看,她显然不是公主也不是为舞台伴演的职业女郎,她很可能是城市的某个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为钢琴家翻乐谱是对她的奖励。她或许是被请来演示如何端坐,并在最恰当的时刻翻过每一页乐谱,她或许是自愿为了任何实际的需要而来:为挣钱付学费,为赢得经验。她可能并不称职,因为她有着太吸引人、与音乐争夺听众的外貌,但根据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原则,美丽外表的主人并不意味着比相貌平平者在专业技术上逊色。不论她有着怎样的台下人生,在她登台的这一刻,她的真实自我即被远远抛开,一如她那瀑布般的黑发从高高的额头向后梳去,像一件披风遮盖了她的后背。
在等待的寂静中,翻谱女子将坐着的上身向左倾斜,略略靠近钢琴家,裤子也随之适应着她那不驯服的臀部,裤腿上移,露出了更多的靴子。她耐心地将双手作莲花状放在大腿上,就像睡莲小憩在暗色的池塘。她的双眼注视着谱架上的乐谱,身体虽然平静但不失警觉,随时准备履行她的职责。
两位演奏者习惯性地进行着肢体与脸部的各种准备动作,当钢琴家的手向着脸与头发最后一挥击,当大提琴手在缓慢而极其挑剔的正音后将外套一甩以使他的身体呼吸更畅,音乐会终于开始了。翻谱女子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顷刻,她无声地直起身向前微倾,随着她的右上身越过钢琴家,观众很自然地想象并感觉到他闻到了她胸部和手臂的暗香,还有她山间瀑布般秀发的芬芳;观众想着,她散发的幽雅香气虽有那么一点诱惑,但也不致令演奏者分心,因为这香味不会“喧宾夺主”,不会盖过乐曲的魅力。
在无需翻谱时,翻谱女子一直保持着倾斜而又平衡的身姿,而一旦需要,她会飞快而敏捷地将手伸到乐谱的右页——这个动作是那么突然却又并不令人吃惊。右页的上角已经折过一下,这是翻谱女子事先做的准备,她耐心而又干练,将所有必须翻的乐谱的右上角折好,以免在音乐会上有半点耽搁。在钢琴家几乎不被人察觉的点头示意下,她将右页左边的圆弧拱起处一推,该页即一翻而过,她随即将页面抚平,人坐直了回去。她的肢体动作极其微小,要待完成每个瞬间的翻页,再回归到身体的原位后,才显得坚定无比。她上衣的下边也再一次地回到了腰围处,裤子的褶皱则滑稽地在臀部周围聚集,裤腿上提得更高,发光的靴子也就露出更多。重新笔直地坐好后,她的身体形成了一个苗条的米黄色L形,双手又缩成莲花状地搁在大腿上,需要时飞速倾身而起、翻谱、坚定地返回,周而复始地表演着全套动作。她的工作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仪式,观众期待这仪式的一再重现,欣赏它并陶醉于它。
翻谱女子虽然注意地听着乐曲,却似乎并不为音乐所动,她全身心地服务于她的使命。这个至高无上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在需要的那一刻翻谱;这个至高无上的使命,是尽力地减弱她自身的存在,阻挡她自身任何光芒的显露,除了显露对音乐的全神贯注。但是,正如她那无法否认的翻谱能力,绝不会迟疑哪怕半秒,绝不会在页角上有半点磨蹭,绝不会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与手势。她自身的光芒也无法不吸引全场观众的眼睛。音乐家的演奏是献给所有耳朵的礼物,而当所有的耳朵满足地欣赏音乐之时,演奏家是那样的优秀,不仅仅是优秀,他们奉献的简直是天使之声,而眼睛们却无所事事。演奏家并不能强烈地吸引观众的眼球,而眼球却渴望与耳朵一样有天使般的东西将它们吸引。当眼睛们找到了令它们心醉的礼物,它们就欣然接受。目光再也不愿从翻谱女子身上转移:洁白的皮肤,米黄色的服装,黑色的瀑发。她当然知道自己被全场观众所注视,但她无法将注视的目光折射,而只能吸进她静若止水的身躯。这种“静若止水”正是她刻意达到的境界,也正是这种无时不在的“刻意”,分散了音乐对她的真正吸引。
任务的极端平凡恰恰赋予了翻谱女子一种尊严,使她本已丰富的个人色彩更加丰富,因为真理从中得到体现:辉煌的音乐离不开平凡,任何辉煌都离不开平凡,正如钢琴家要将指甲很好地修剪,正如大提琴手要将松香涂于琴弦,虽然这样的平凡小事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成就了辉煌。
于是,当所有的眼睛都爱上了翻谱女子,她的任务就不再那样平凡,她也不再只是一件吸引眼球令眼球的主人从音乐中分心的礼物。相反,她与音乐有着非凡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她不是音乐的具体表达者,不是音乐的活符号——要将音乐表达出来是太容易了。她的存在要微妙得多,她是音乐的产物,是上天下凡的天使,一个被音乐之声变成了凡人中的天使。但是她在人世的真实存在,以及时尚的服装和闪光的长靴告诉我们,她本来就是一个凡人,绝然不是精灵。在音乐会开始之前,观众亲眼见她步上舞台,亲眼见她是一个有着独立性格的生命。不,她与音乐的关系一定是这样的:虽然钢琴家在十分清晰地敲打着键盘,虽然大提琴手面带着丰富的表情拨拉着弓弦,但是,观众的强力注视,或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超自然的力,使得音乐似乎来自静静地端坐在音乐旋律中的翻乐谱的女子。跟随着音乐的推进,观众更加深情地凝视着她。由于她的美丽和他们的凝视,她升华为一件妙不可言的伟大乐器,不再使人从音乐分心,而是音乐的真正源头。
时间在一秒秒溜逝,音乐会已经持续得很长很长,但音乐厅的气氛却始终充满着活力。天使般的音乐令大厅弥漫着欢乐,欣喜若狂的观众默默地为翻谱女子祈福。或许是音乐会实在太长,或许翻谱女子终究只是凡人而不是童话中的公主,她终于无法再保持那种超凡脱俗的形象。虽然对自身的任务仍然未显疲态,翻乐谱时仍然未有半点疏忽,她却开始显露出凡人那样的对音乐的欣赏:她的眼皮会为一个演奏得恰到好处的转折而轻轻颤动,她的嘴唇会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和弦而略露微笑,她不再静若止水,她呼吸的节奏显而易见,上身伴随环绕着她的音乐波浪般地晃动。这一切虽然看上去赏心悦目,但这种自我约束的放松却是不祥的预兆,它暗示着音乐会已进行得够长应该结束,暗示着“超凡脱俗的美”不能无限地坚持,也暗示着我们不可能永远陶醉于光芒四射的静止。我们是无法超越极限的凡人,甚至欣喜若狂的迷醉也有极限。此刻,平凡终于将我们拉回它的怀抱,显得乏味而松弛。翻谱的女子常人般随着音乐而起伏的身姿,是音乐会快要结束的象征。观众开始对刚才听过的,甚至即将要听到的最后的音符依依不舍,怀念起音乐会的整个过程。音乐的开篇引领我们进入一片诗意而美丽的音乐绿地,那是听觉的伊甸园。但是当我们意识到音符的弧线开始掉头向下,把我们带离伊甸园时,音乐会的高潮已经回落,我们不得不回到寂静与严肃的现实。
钢琴家不时半带微笑地向翻谱女子投去会意的一瞥,或在表露他与她对乐曲的共鸣,或对她在翻谱中成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表示赞许,这种观众永远不会理解的公众表演中的私人表演,让我们有一种被排除在音乐之外的失落,也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已被遗憾地引领回人间。随着音乐会接近尾声,演奏者开始微微纵容自己,他们开始提前体验不可避免的伤心时刻,这是当他们像普通人一样走出音乐厅,走回平凡的生活的时刻,这是他们的光荣不再,压力被释放的时刻。
而当音乐会真的进入尾声,翻谱女子却并不像演奏者那样立刻进入胜利的放松状态,她仍然笔挺地坐着,保持着平静。两位演奏家频频向观众鞠躬致意,愉快而友好地互拥着肩,在胜利的喜悦中,亲切温暖的目光不断投向对方。这是翻谱女子所无法分享的,无法分享观众的掌声,无法分享胜利的喜悦。她耐心地站在钢琴旁的椅子边,与音乐会开始时的出场一样,极其精确地计算着离场的时间。她在演奏家离场的几秒钟后,迅速收集好谱架上的乐谱,整理乐谱的干练一如一位称职的侍女。
音乐家再一次出来向观众鞠躬,翻谱女子则不再出现,她的使命已彻底完成。我们理解她的不再登台,但我们却是那样地希望再见到她。失缺了她,仿佛一场令人流连忘返的愉悦失缺了核心;失缺了她,仿佛发出最动人音乐的乐器随着音乐一并消失。我们不愿去想象离场步入后台的翻谱女子会有哪些凡人的举动:放下乐谱,尽显疲态地将披肩的瀑发挽起,终于将在台上长时间被注视的压力释放。我们不是无视她的真实生活、无视她的将来,但我们却希望她永远保有舞台上的超凡脱俗。我们会不再记得演奏家的模样,但只要我们重温那天的音乐,我们就会看见翻谱女子:米黄色的礼服,黑色的长发,公主般的身姿,光芒四射而又静若止水。只消片刻,我们就会融化在她那令人如痴如醉的音乐之中。
理想的午后
“一个内心安详的人,总珍藏一个诗意的午后。”当回现诗人兰波的这句哲语时,我刚从一个周末午后的梦中醒来。
时针指向午时一点半。我穿戴整齐后下楼,到户外自由地吐纳空气。
阳光斜斜地照着,人一出门,它便呼拉一下泻在我身上,明媚地晃我的眼,眼前的五彩斑斓,浮浮沉沉。小城宽阔的街道,恣意流淌的全是日光。
没有目的地漫步,使目光显得更悠远。
夏末的气息逐渐褪去。日光穿过路边古樟树的间隙,温软地落在肩头。在这样的阳光笼罩下,这座称作“霞浦”的古老小城似乎变得和往日有些不一样了。车水马龙,人流如潮,马路上不断擦肩而过的人群,这一切在柔和的光泽笼罩下远远看来,就像一幅和平安详诗意盎然的水彩。在日光拂照下,没有了小城的闭塞与破败,没有了古城的偏执与小气。这使我,一个虽栖息了三十多年的原住民,仍抬起头来仔细打量这座自己熟识的古城。
朝北放眼而去,老城区整块整块的砖墙,泛着一大片苍茫的红色。红色分很多种,而砖红在其中最具沧桑意味。它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耶路撒冷的哭墙,柏林的倒墙,长城的一眼望不到尽头——都是一种时光流过墙的痕迹。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午后二点的淡淡薄雾中,那些红砖墙的高大朦胧的影子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与教堂边,哈里路亚的清亮歌声在耳畔弥漫。白色的鸽子展开翅膀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砖墙的红色当仁不让地成为最衬纯白的底色——好像遗落在冬雪上的血迹,残酷并且唯美。
目光所及,老护城河自西向东流过。南峰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鸟鸣啾啾,花香四散。沿着山路望去,依稀可见杂花生树,小鸟飞翔。偶尔也有人携妻扶幼上山,俨然一派白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景象。
就在凝眸间,家乡霞浦,让我感觉她是一座无比美丽的县城。她的唯美至极,让我此时甚至惊讶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些是再普通不过、随处可见的景象,但是,我依然觉得美。也许,那更是因为:任何事物,用带了感情的眼光去看,总是美丑分明的。而对于自己家乡,我只能用这个有时简单有时虚幻有时繁杂的动词来形容我对她的感情:我爱她。
往南来到郊外,感受乡野的风。天空中,飞鸟在嘻戏。金黄的大地被夏末的阳光照耀着、抚摸着,微微地沉醉于临近收割的丰姿中。这些情景,让我的内心涌上一阵阵感动:好一派大地的恩典呵!
这一路走来,俨然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徐徐展开,不断送来缕缕的愉悦。
“家乡如画,每人心里都有一张。”我耳边掠过了这句箴言,寻思之下,越是理解它的经典内涵了。
沿着三河岸走走停停,是寻梦的开始。有一些年青人沿着河边转悠着电动车,享受着悠闲之乐。远处,传来悠扬的唱闽剧的声音。寻声而望,有许多喜欢戏剧的中老年发烧友表演真切动人,乡音浓软,声腔清悠婉丽。忽然,在我后面有人用柔美的声音,叫唤着“叔叔,叔叔。”我转身回头看,是一个小女孩,她拿着傻瓜相机微笑地请求我给她拍几张照片。我欣然接过相机,让小女孩和玩伴们高兴地摆各种姿势,让一张张清纯美丽的笑颜定格在三河之畔。
日光一点点流动着,我回头往城区的大道走去。
车流,人群,推着两轮木车的乡村汉子一路吆喝着果红瓜绿,上空偶尔掠过一两只流浪的鸟儿,都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晕圈,富于生机而安详。
日光的影子,长长的。光线把人和建筑物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夸张地膨大。人,其实是不用孤单的,形影想随,不离不弃。不管你现在是灿烂的微笑还是明媚的忧伤,日光里的影子一律是快活地手舞足蹈。从某种意义上,影子是快乐的延伸吧。
路边不远处,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儿,一路“咯咯”地笑着追赶自己的影子,满头银发的奶奶,掂起小脚,张着双臂,象只臃笨的老母鸡恨不得一把将小鸡儿掩于自己温暖的翅下。一长一短两条快活的影子,交错,缩短,重合,笑地一漾一漾地。
上述的小小风景和的日常生活的光芒,时常被我忽视了。有时我想,自己的眼睛也好象只是为了维持面部的协调了,形同虚设。这如同我前段时间刚刚拔掉的那颗蚀牙,疏松褐黄,多年不用,只能配合上下颌骨的运动来装饰微笑。
在视线迟疑间,那刚才嬉戏的一老一小已停驻在一个卖小吃的小摊前,孩子指点着嚷嚷着,奶奶便忙不迭地从衣襟深处摸出一个手绢包来,剥糖纸壳一样地抖搂开,孩子手中便多了一串红艳剔透的冰糖李子。懂事的孩子固执地把李子棒举到奶奶嘴边:“奶奶先吃,奶奶先吃!”年迈的老人用手撑着膝盖,俯下身子,向征性地咬一下:“乖孙哩!”知足和笑意,在菊花一般的皱纹里充盈得满眼。站在光线的近处,我能清晰地看到细微的尘埃在漫延,在跳跃,迟迟不散。
许许多多过往的时光情景,似曾相识地摇晃着,在无声地消逝着。
顺着日光,我下意识地看看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着:2007年9月15日,15时35分。这个安祥的午后,我独自走在大街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滚滚流动的车队,所有人似乎都有些忙忙碌碌的样子。大家忙着回家,忙着约会,忙着逛街,忙着消费一个平实的下午时光。
此时,我似乎突然来了兴致,看着从身边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那些和我一样从这个街口走到下一个街口的人,看着他们的一个眼神,一个与我无关的表情,心里暖暖地笑。我不由猜测起他们的生活,猜测他们在流年似水的日子中,是否感觉快乐是否感觉幸福——
那个街角卖鞋垫的老人,生计应该不赖吧?
邮政窗口柜台上的那个女人,从前表情淡漠的她,今天怎么也露着难得的笑颜?
婚纱影楼永远都是温暖得近乎暧昧的光,那些漂亮的婚纱挑逗着街上每一个年轻女孩的眼睛和心灵。
蛋糕铺的玻璃橱窗前,那个戴白口罩的人真在认认真真做着一个蛋糕,一个小女孩趴着认认真真地看,她在想象自己长大了也做一个蛋糕师吗?
从珠宝店门口经过,有人递给我一张DM单,精致华丽,上面的货品那么璀璨,写着“到爱恋珠宝来领您一辈子的幸福”,暧昧的语言,正诱惑着有情男女去那里领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呢。
一个卖麦芽糖的小贩挑着小筐从我身边经过,敲糖的小锤和贴片敲得叮当作响,那是响彻我整个童年的声音,甜甜的,黏黏的。
一个卖柿子的,竹制小筐上整齐地码着红得发腻的柿子,很是诱人。没有城管紧盯的眼神,他可以守着担子悠然叼起烟。
茶行永远飘散清香,玻璃柜中的茶叶展现着优雅姿容。只是我总会想,这样的门面里,其中的茶叶价格是否有着深不可测的市场秘密?
这样想着,我的脑海浮现起多年来乡村与城市嬗变的一幕幕情景。
朝着滨江大道行走,我抬头看到一家房地产的巨大广告牌,大大地印着几个字“喜欢城市生活的理由?”是啊,喜欢城市生活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也许是诗意,物质上的丰富,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城市气息吧。就像大型超市橱窗里那张宣传海报的画面:明眸皓齿的女孩,时尚无比,一枝妖艳的花朵衬着她的俏脸,人面桃花相映红。小城的上空,也因了这些眩目的海报,弥漫着现代生活的香气和活力。
在一家民族乐器行前,我为拂耳而来的一溜乐音驻足。是一首古琴曲《梁祝》。这样的音乐诱惑,突现在喧嚣的背景中,最是难忘记。而这琴声也并非刻意地要灌入人的耳朵,它不是一首完整的曲子,是随性,是因了随性而带上了韵味。木质的琴音中,隐藏着暗语与姿色,以及拉琴者对鲜艳容颜的欲望,和让琴声传达对经典情致的渴望,使它在不老的时光里风情万种,千娇百媚。在这个充满了阳光的下午,在光的过滤下,这古典的乐音也更灿烂更煦和了。
日影西斜,光线慢慢地灰暗下来。
此时,我来到位于小城中心的文化广场上。广场不大,但却显示着一些隐约的味道。在黄昏的微光下,喧哗的各种声音嘈杂在一起,有流行着的《有没有人曾告诉你》,也有来自新疆的民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但最吸引我的声音,是从广播电台中传出的磁性和回忆,一曲《十年》让我回想到中学时代,回到苦读时光,我就是在家乡小城的广播声中走向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的考场。参加高考那天,路边的香樟树都张满了鲜绿的裙摆,天空也渗透着希望和喜悦。细想来,人生一直在路上,像一条漫长的红领巾,围绕在脖子前,让人始终无法忘怀这种眷念。树枝上,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气息,要低下头,默念着生活的给予,才能穿过预设的林荫。然后,开始爬树。在春天,可以欣赏到树枝上女性般的温存,但是,很快,梦想的锤子会从头顶上垂直落下。
在记忆的河流徜徉之时,我的手机传来了海南文友许君的短信,他说他妻子快生产了,他快要当爸爸了!短信中充盈一个男人幸福的气息,让我的内心也随之饱满起来。
我望了一眼天空,路边的槐椿树叶已开始微微发黄。是呀,跨过夏天的台阶,要迎来秋天了。熟夏的南风徐徐而来,我在心中默念起兰波的《黄昏散曲》:
夏日蓝色的黄昏里,我将走上幽径
不顾麦茎刺肤,漫步地踏青
感受那沁凉渗入脚心,我梦幻
长风啊,轻拂我的头顶
我将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动
无边的爱却自灵魂深处泛滥、、、、、、
夜幕就要降临,我悠然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着走着,突然,街头的一出爱情故事像影视剧一样,在我的视野中上演了。
一个戴眼镜的英俊小伙子,一副学生模样。他追着给一位俏丽的女孩子送玫瑰花,那女孩子推说不要,那男的就跪地求情了。此刻,正好有一个吹笛子的卖艺人走了过来,吹着《一路上有你》的情歌。在朦胧的光线中,大街上人来车往,女孩子扶起了男孩子,就是不要鲜花。在相互僵持的过程中,吹笛子的人又吹起了《最浪漫的事》,随之几个路人也唱和了起来。最后他俩拥抱在一起,渐渐沉醉在了夕光中。
( 林文钦,1974年生于闽东霞浦,作品发表于《光明日报》《文汇报》《文学报》《中国作家》《大家》《散文》《散文诗》《诗歌》等报刊,获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奖、孙犁散文奖等。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星空》。)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