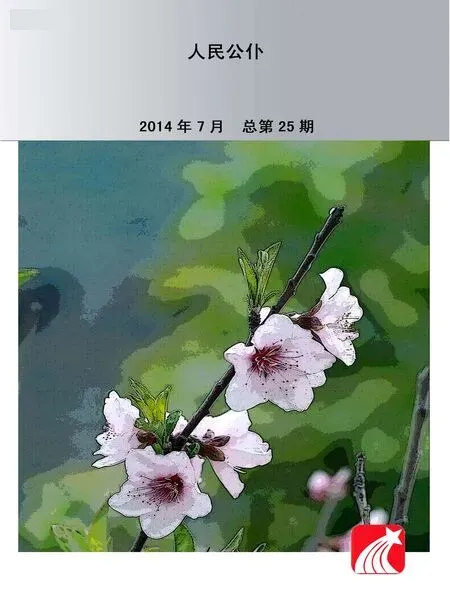时势观察:释解中国GDP“第一”的困惑
■ 文 森
时势观察:释解中国GDP“第一”的困惑
■ 文 森
前不久,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简称ICP)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项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刻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此项研究结果比按现行汇率计算GDP排名,中国至少提前了六七年超过美国。
如何看待这一结论,既事关对中国经济地位的判断,也关系到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判断。
以平常心看待今天的“第一”
其实,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一两百年前早已“是之”。但后来,由于中国的封建王朝陷入了闭关锁国,脱离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又衰落了百余年。
近几十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重新拥抱世界。在新的纪元,中国又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先不看经济总量,如今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量、外汇储备、制造业产量、粮食生产等等,按照统计口径,已经排名世界第一。若以中国的人口总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且不考虑是以购买力平价衡量,还是按照现行汇率比较的统计科学性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当然也是可以预见之事情。
所以,此次ICP调查显示的“中国经济总量”的结果一经公布,并未在坊间产生多大的波澜。当然,统计学家可以从一国GDP的统计方法上,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合理性的解释,但需要把握的是,经济规模排序的第一第二位置,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也只是一个数量概念。我们需要更加审视和关注的,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社会发展的潜能和活力,中国发展对世界将作出怎样的贡献和担负的责任。集中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做大了,但如何尽快成为一个强国、富国和责任大国,也是回避不了的现实课题。“登泰山之巅,可揽无限风光”,但登顶也不忘忧。
就此,我们不仅要有平常心看待排名,更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把握中国继续前行的历史方位。
需要回答好三个命题
中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是一个大国,也一直为世界所关注。
面对这样一个大国,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提出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其称为李约瑟难题。后来很多学者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一系列疑问。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他从科学方法的角度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维成果,认为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等等。
李约瑟难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需要我们回答的第一个命题。
第二个命题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即人均GDP在3000至5000美元区间的发展阶段,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以及东亚许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学者归纳“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很高,但按照人均计算,恰恰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上限,并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社会特征。
第三个命题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也就是说,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会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会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纵观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国际社会不断传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将“修昔底德陷阱”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但客观上,中国的大国地位事实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借此煽风点火,影响中国的外交形象。
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排序第一还是第二,倒不是个问题,而绕不过去的确是要回答好这三个命题。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要继续解决上世纪初进步人士就提出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如何引入“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而“民主与科学”在文明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发扬光大;回答第二个问题必须要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破解体制机制和利益格局的束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回答第三个问题,就是针对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认真研究和扮演好一个全球领先者的角色,在与其他大国的政治经济博弈中,需要重新审视甚至是重塑自己的价值观,特别是要在物质文明基础不断夯实的背景下,不断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切实定位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可能担负的责任。
做好三篇文章
对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这样的研究成果,不管接受不接受,应该来的总归要来。但数量代替不了质量,总量掩盖不了结构,发展回避不了问题。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解决眼前的问题。
首先是树立“乘法与除法”的思维。这几年,我们经常提出“底线思维”。这是考虑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可接受底线。在中国,任何一件小事,如果乘以13亿人都是件大事;任何一个总量,除以13亿人,也都是一件小事。不如中国经济总量大,但人均GDP排名还在一百多个国家之后,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少资源储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占有率目前还很低;不少民生问题看起来鸡毛蒜皮,但放大起来,确是全社会的一种公共服务诉求,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依靠全中国人民的智慧,无往而不胜;同时,作为治国理政者,也丝毫不能忽视草民的基本需求。
其次是把握“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如果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存量资产价值的确已经很大,可以盘活的实体存量资本大体会有五百多万亿人民币,还不计我们的生态资源价值。如果能够充分盘活存量资本,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瓶颈制约,解决助推新一轮新型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推进产业重组和转型升级、化解区域经济不平衡等现实经济问题所需要的撬动资金,应当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里需要平衡的是政府与经济主体、与社会,中央和地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何解决好“强国”与“富民”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节点。还有,就是进一步做大做实增量,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进入稳增长阶段,结构转型必须突破,增量必须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劳动者素质提升来增进,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已经无法维系,也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是进一步激发“潜力与活力”。中国今天的发展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回归,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实现“中国梦”,也正是昭示对民族复兴的责任和担当。绵延几千年中华文化历史的基本价值曾是儒家文化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但其间也夹杂了许多不适应现代文明潮流发展的思想束缚,也缺少了破解“李约瑟难题”的科学、民主、实证等关键钥匙。因此,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包容观、和谐观等,不仅仅是处理当下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激发全社会创造潜能和活力的总开关,也是夯实中国大国地位、助推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开放强国,并在未来进一步融入国际发展进程中扮演好大国角色的价值准绳。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