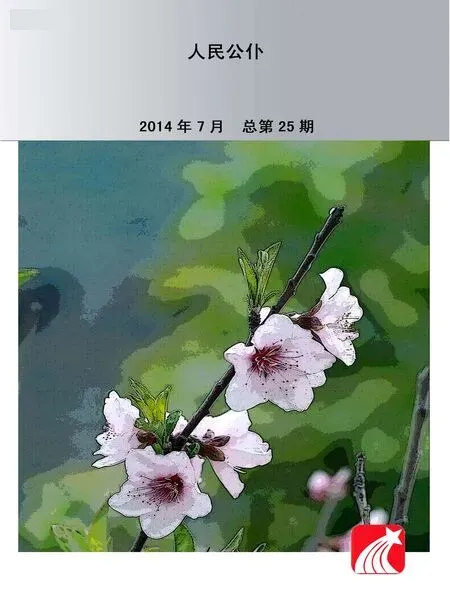解谜党的“一大”
■ 杜玉芳
解谜党的“一大”
■ 杜玉芳
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它在召开的当时和其后的一段岁月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曾一度被 “轻视”。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最大的两位人物,他们一南(上海)一北(北京),被称为“南陈北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党史佳话,道出了他们二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杰出贡献。但在出席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却不见“南陈北李”的身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主要的创始人,二人为什么双双缺席“一大”?
两人缺席“一大”的直接原因是 “公务繁忙”。当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李大钊身为北大教授,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校务繁忙,且还要筹备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难以抽身前往。然而,人们对事物的排序后面都有价值准则,透过“公务繁忙”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二人对“一大”意义的低估。作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其“公务”甚至比建党工作更重要吗?两人在诸“公务”中不约而同地都没有出席“一大”,明显反映出两人对“一大”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这一点,从部分“一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表现可以看出。陈公博是“一大”来自广东的代表,周佛海是旅日代表。关于他们二人在会议期间的表现,张国焘回忆说:陈公博“带着他漂亮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刘仁静也回忆:他们二人“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豪华的大旅馆,出手阔绰。周佛海则在开会期间不忘谈恋爱,甚至还带来了桃色纠纷”。 一个既开会又蜜月旅游,度蜜月似乎比开会更重要;一个大会期间闹出桃色新闻,他们的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参加者对“一大”召开并不很看重。
一些早期党员也回忆当时对“一大”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大代表刘仁静1979年2月回忆当年当选代表的情况:“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由于当年党内对“一大”的“轻视”,“一大”的参加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将最终创造一个伟大的组织,并导致一个新政权的诞生,所以事后全党对“一大”的许多信息几乎集体“健忘”,致使围绕着“一大”留下了许多历史谜团,如开幕日期、闭幕日期、会议召开的地址、代表人数等。特别是“一大”开幕日期之谜,困挠了人们半个世纪,并导致了中共中央将“七一”定为党成立的纪念日,与“一大”开幕实际日期不符。
“一大”召开后全党的反映相对冷淡。胡乔木回忆说:“一大”召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大革命失败前,土地革命高潮时,革命环境相对较好,完全有条件纪念“一大”,但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极少提及“一大”及其意义,更没想组织活动来纪念党的诞辰。1937年中央进入延安后环境稳定,加上需要在全国扩大影响并凝聚全党,决定纪念党的诞辰。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二人只记得“一大”是7月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日期,于是就把7 月的第一天,象征性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但在之后的三年中,7 月1 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没有得到普遍采用。这三年中,除撰文纪念党的诞生外,党中央并没有正式规定“七一”为党的纪念日,也没有在延安组织纪念活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指示的方式明确规定7月1日为中共建党纪念日。自此,全党范围的建党纪念活动拉开帷幕,“七一”成为中共重
“一大”的命运流转和历史境遇,意味深长。穿越90余年岁月的漫漫烟尘,“一大”见证给岁月的是串串的火红;留在我们心头的是澎湃的激情;沉淀给历史的是深沉的思考。要而又固定的纪念日。
应该说,当年毛泽东和中央还是相当慎重的,讲话和文件中只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而没有说这一天就是党的“诞生日”。此时,党的生日仍是未解之谜,这个谜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被党史研究者解开。
“解谜”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考证过程。党史专家首先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并多次寻访健在的亲历者,通过分析代表的行踪,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仍然不清楚。接着,研究者开始查找苏联原始档案。苏联档案中有“一大”于7月23日开幕的记载,但孤证难信,需要国内材料佐证。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的考证中,发现一件看似毫不相关的“谋命案”,正是对这一命案的考证最终揭开了“谜底”。
当年一大代表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当了汉奸,但他们的回忆还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两人在回忆中都说,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的当天晚上,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发生了一件情杀案。陈公博回忆说:“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周佛海也回忆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
陈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和《申报》刊登的关于大东旅社谋命案的相关报道。《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是完全一致的。当事人的回忆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都称会议在上海开了8天。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日后,有人笑言,党史专家是从一桩“情杀案”里查出了党的生日。
党史专家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考虑到由于几十年的惯例,“七一”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和中央只是象征性地将“七一”确定为建党纪念日,与“一大”开幕日是两回事,因此,最后中央决定建党纪念日不作改变,但要将“一大”的准确开幕日期向公众宣传。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历史从来是今天的一面镜子。历经半个世纪的探寻,“一大”开幕日期之谜终于揭开。科学求是是揭秘历史的钥匙,是史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我们对待一切工作的基本态度。
由于当年对“一大”的“轻视”,导致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党的早期领袖双双缺席“一大”,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同样由于这一“轻视”,“一大”曾经迷雾重重,并留下了党的诞辰纪念日与党的实际“生日”不符的历史现象。当然,“一大”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后来者的总结和赋予,早期的共产党人对此认识不足,是完全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次会议的作用意义有多大,往往要靠历史去证明。当年的人们没有看重“一大”,但“一大”并不会因为当时人们对它的冷淡而减弱了它的意义。28年后,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当年的“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一句话,精辟地道出了“一大”的重要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董必武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参观“一大”旧址时指出:“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一切伟大都是从简单开始的。一个政党是否伟大,并不在于成立之时有多么的轰轰烈烈,而在于是否顺应时代要求,担当起救国救民的使命。“一大”从悄无声息的“简单”开始,启动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过程。它于无声处蕴育了中国革命的惊雷,不动声色地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时光飞逝,岁月流转,当年处于“地下”、只有50多个党员的革命党已成为今日拥有8000多万党员,领导着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一大”也从当年的不为人知到现在的世所共知,从不被看重到被誉为“开天辟地”。“一大”的命运流转和历史境遇,意味深长。穿越90余年岁月的漫漫烟尘,“一大”见证给岁月的是串串的火红;留在我们心头的是澎湃的激情;沉淀给历史的是深沉的思考。
杜玉芳简介:
杜玉芳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及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西藏问题等。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与西藏和平解放》,合著专著、教材14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参加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转型期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问题研究”和“宗教学教材编写”,负责及参与省部级、院级各类科研项目7项,教学科研获各种奖励1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