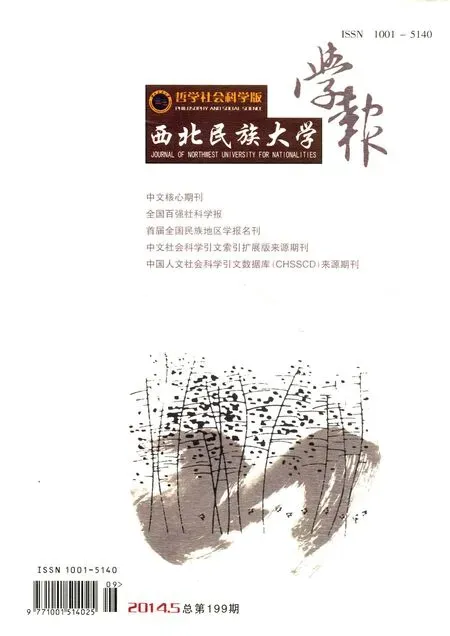冒顿单于的战争策略透视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70)
冒顿单于是匈奴民族的杰出领袖,游牧文明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南征北战,东击走东胡,西大败月氏,征服西域各国使其俯首称臣,迫使汉朝订和亲之约,统一了北方草原各部。“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1],冒顿单于在战争中屡获胜利,建立起与中原汉王朝相抗衡的匈奴帝国,他也被誉为草原民族具有高超谋略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可以说是游牧民族的早期“战争之神”。对于冒顿单于,人们多从他的历史地位、具体战役中体现出的军事谋略、与汉王朝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加以研究[2],而对于冒顿单于整体的战争策略和军事思想,目前学者尚缺乏深入的探析。也有学者认为冒顿单于残忍好杀、穷兵黩武,说他“以残杀和掠夺手段摧残他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对外推行压迫和掠夺的霸权政策,发动不义战争,造成各方军民的重大伤亡和严重的经济破坏,还掠夺了大量的良民并驱之为奴,丧尽天良……所以冒顿和历代坚持他的掠夺劫杀和军事霸权政策的单于都是历史的罪人”[3]。这样的评价过分简单化,并带有明显的偏见。对冒顿单于总体战争策略和战争观的深入分析与准确把握,对于我们客观评价这一草原民族的代表人物,对于我们更加理性的认识游牧民族的战争观都有重要的价值。
一、战争目的的政治性与功利性
冒顿单于一生经历了多次战争,战争对象包括自己的父亲、东胡、月氏、西域诸部、秦汉王朝等,但战争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统一北方草原、威慑中原王朝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在与父亲争夺政权的对决中,充分表现了冒顿的军事才干和政治谋略。头曼单于为了把所爱阏氏的儿子立为接班人,派太子冒顿到月氏做人质,然后派兵进攻月氏。面对月氏的追杀,“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4]在生命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当机立断,从容逃脱,表现了他处理危机情况的胆略、智慧及高超的骑射能力。草原民族是崇尚英雄的民族,冒顿能够逃脱月氏的追杀,成为草原上传奇的神话,也赢得了父亲头曼单于的刮目相看,“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人质事件使冒顿意识到亲情的不可靠,激发了从父亲手中夺取政权的野心。为此,他日夜练兵,全力训练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军队。为了统一指挥,冒顿发明了一种响箭“鸣镝”,并下令,“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5]为此,他先后把鸣镝射向自己的宝马、爱妻、父亲的善马,他的部下也从迟疑到不假思索地听鸣镝指挥。冒顿认为这支部队是可用的,就利用打猎的机会射死了父亲头曼单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又杀死了自己的后母、弟弟和不服从自己的大臣,消除了异己力量,并且自立为单于,成为了匈奴民族新的领袖。
夺取政权后,匈奴仍面临着多方的威胁。当时,东有强盛的东胡。西有敌国月氏,南有中原政权的威胁。特别是东胡,想趁匈奴内部权力纷争的时机征服之。为此,东胡先后向匈奴索要千里马,进而索要冒顿单于的阏氏。为了协调内部力量,巩固政权,并麻痹东胡,冒顿单于全部答应了东胡的过分要求。当东胡进一步提出索要东胡与匈奴间空余的土地时,冒顿大怒:“地者,国之本也,奈何弃之。”[6]斩杀了建议答应割地求和的大臣,倾匈奴全国之力,对东胡发动了突然袭击。东胡正得意洋洋地等待匈奴回应,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匈奴打得大败。接着,冒顿单于乘势“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7],向北则征服了西域各国。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使冒顿单于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匈奴社会中的地位,而且赢得了匈奴部众的衷心敬佩与拥护,“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8]。在这些战争中,冒顿单于把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统一北方草原作为主要目的,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宝马、爱妻,甚至名声、亲情,这些充分体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匈奴民族面临严酷的自然环境,战争掠夺也成为度过生存危机的重要手段,“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9]匈奴鼓励对敌奋勇作战,崇尚英雄,也把夺取财富作为战争的重要目的。“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10]
在对西汉王朝的战争中,冒顿单于把获取经济利益,得到中原农耕民族的财富作为最主要目的。为此,他主动解开平城之围,与汉王朝结和亲之约。多次出兵逼迫西汉王朝履行和亲约定,向匈奴政权输送物资。汉朝派刘敬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时,刘敬建议汉高祖只有把长公主本人嫁给冒顿单于,才能真正达到和亲的效果,由于吕后的阻挠,汉朝最终派出了家人子假冒公主,与单于和亲。对此,冒顿单于并不以为意,因为不论战争还是和亲,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汉朝的财富,只要达到了这一目标,冒顿单于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汉皇家婿。
二、战争手段的多样化
在冒顿单于一生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对每一次战争,都不是率意为之,也从不轻举妄动,而是精心准备,巧妙安排,这为他取得一次又一次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成为游牧民族的“战争之神”。冒顿单于的战争手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以弱示敌,诱敌上当。冒顿单于对于每一次战争,都进行精心的谋划和准备,而以弱示敌,诱敌上当则是他惯用的手法。在对东胡的战争中,他通过满足东胡求千里马、求阏氏的做法,使东胡人感觉到匈奴的胆小畏惧和软弱可欺,“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11]结果被冒顿一举击败,毫无还手之力。这样的战术在对付汉朝的战争中使用的更加纯熟。为了把刘邦的大军引入自己设定的包围圈,“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徒见其老弱及羸畜。”这种做法竟然骗过了汉朝派出的一批批侦查人员,“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易击。”[12]在与高祖刘邦的初次交战中,冒顿继续伪装出不堪一击的样子,“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13]这一招果然奏效,甚至骗过了饱经战争历练的高祖刘邦。刘邦不仅继续派三十二万步兵追赶,而且为了抓住战机,甩开步兵自己亲自帅骑兵深入平城,进入了冒顿单于设好的包围圈。对此,王庆宪先生曾经有专文分析[14],此不赘述。
2.乘胜用兵,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打敌人以措手不及,是冒顿单于又一常用的战争策略。在冒顿单于激战东胡之时,西方的月氏则隔岸观火,或许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念。没想到冒顿大败东胡之后,立即挥师西向,直接把兵锋指向了月氏。月氏来不及反应,被迫离开故土,向西迁徙。接着冒顿单于又率师南下,兼并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并趁着中原地区楚汉相争之际,夺回了被蒙恬攻取的河南地,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匈奴再败月氏,征服西域地区二十六国的战役更能体现冒顿单于的这一用兵战略。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组织军队对汉朝上郡(今陕西榆林)大举进攻,直接威胁到汉朝的首都。汉文帝亲临太原指挥,并命令丞相灌婴调发八万五千名士兵迎敌。冒顿单于借此威吓汉朝,使汉朝履行和亲之约,继续向匈奴提供财富和物资,同时麻痹西域各国,使他们误以为匈奴的主攻方向是西汉王朝。正当西域各国放松警惕之际,右贤王突然从汉朝边境撤军,挥师剑指西域。西域各国毫无戒备,在匈奴大军压境之际竟无还手之力。匈奴大军在西域地区节节推进,势如破竹,“以天之福,吏卒之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5]把匈奴帝国的势力推向了新的高峰。冒顿单于在用兵过程中,善于一鼓作气,乘势发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敌人猝不及防之际,获取战争的主动权。
3.集中兵力,慑服敌人。对于关键性的战役,冒顿单于总是利用骑马民族移动速度快的优势,调集一切力量参与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形成极大的威慑力。在对东胡的战争中,从国力上讲,匈奴或许并不占优势,否则就不会一再答应东胡的无理要求,献出自己的千里马和心爱的美人。当决定与东胡开战时,冒顿则动员全国之力,“令国中有后者斩”,整个匈奴民族全民皆兵,向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16]。在与汉高祖刘邦平城决战时,冒顿单于本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7],为了一举击败汉朝大军,除了征调全部精壮骑士外,他可能动员了族中老幼之人,“冒顿单于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完全切断了高祖与外面军队的联系,对汉朝军队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为了从心理上威慑汉军,冒顿单于精妙布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驪马,南方尽骍马。”[18]四周不同方向用不同颜色的马匹,表明匈奴骑兵的精良与强大,并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对汉军形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力,迫使汉军主动讲和,并答应匈奴的和亲要求。白登之围对汉朝形成的心理威慑持续了几十年,以致汉武帝时期仍念念不忘高祖白登被围之耻。
三、南北不同的用兵策略
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帝国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冒顿本人也成就了草原不朽的神话,但冒顿单于本人并不是一味穷兵黩武,肆意残杀的莽夫,他只是把战争作为谋取匈奴民族最大利益的手段,并对南北地区采用了不同的用兵策略。
在草原地区,冒顿单于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各个游牧部落,进而统一北方草原。为此,冒顿首先征服了最强大的对手东胡,接着,又击走月氏,兼并河套地区的楼烦、白羊部落,然后出击西域地区,使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9]。这个过程中,冒顿单于对各个游牧部落也采取了不同的战争策略,如对东胡,冒顿单于采取灭掉其国,虏获那里的人民和畜产的做法,使匈奴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国力进一步强盛。但也没有对东胡人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东胡的基本部众保留在了乌桓山和鲜卑山,发展成为乌桓族和鲜卑族。《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20]同书《鲜卑传》则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21]月氏本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早在先秦时期,他们就活动于西北广大地区,曾经一度控制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冒顿单于打败东胡后,接着向西进击月氏,迫使月氏让出了大片草原,活动区域大大缩小。几十年后,冒顿单于又派右贤王进攻月氏,“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22]这场战争对月氏造成了巨大打击,但也并没有消灭月氏,月氏被限制在了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地区。对于西域绿洲地区的各个或游牧、或农耕的国家,汉文帝时期,冒顿单于派右贤王对那里展开征服战争,定楼兰、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把西域纳入到了匈奴的统治范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离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23]冒顿单于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方式,应该是向这些国家征收赋税,要求他们贡献物资,这对补充匈奴人的资源不足,巩固匈奴帝国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冒顿单于对北方草原各个民族发动的战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蒙古高原。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建立了统一的中原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而北方草原地区则全面进入了游牧化生产阶段。游牧生产方式需要大范围迁徙移动,以保证生产的持续与生态的平衡,同时,游牧生产方式由于其产品的单一性与不易保存性,需要从农耕民族得到一定的物资资源。这就要求北方草原各民族结束原来“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24]的局面。因为众多游牧部落的分散割裂状态,容易在追逐草场资源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从而对正常的游牧生产造成破坏。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后,可以统一分配草场资源,合理安排各个部落的迁徙移动路线,划定各个部落的游牧区域,使其“各有份地,逐水草迁徙[25]”,有利于游牧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中原地区,冒顿单于则采取了不同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战争策略。冒顿单于发动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胁迫、威吓中原政权,使中原王朝能够满足其经济要求。白登之围中,冒顿单于包围汉高祖刘邦七天,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对汉朝皇帝采取围歼、俘获等手段,而是听信阏氏的话:“两主不想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26]主动解开包围圈的一角,放刘邦撤去。刘邦也被迫与匈奴订和亲之约,答应嫁公主给匈奴单于,每年向匈奴输入一定数量的金银、锦绣、酒曲、食物等。通过和亲,匈奴以比战争更小的代价,从中原王朝得到了更加稳定的收益。
谈到冒顿单于解开对刘邦包围圈的原因,人们多津津乐道于所谓的陈平秘计,认为陈平以财宝和威胁打动了冒顿的阏氏,在阏氏的求情下冒顿才解开了对刘邦的包围。实际上,阏氏所说的“两主不想困”的思想,与冒顿的思想是相契合的,否则,在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冒顿单于是不会因为阏氏的求情而改变自己主张的,这从以前冒顿以鸣镝射杀自己的爱妻,为麻痹东胡献出自己阏氏的事件中可以得到佐证。
白登之围后,冒顿单于对西汉王朝采用以武力胁迫威吓汉朝行使和亲之约的策略。至冒顿去世,匈奴对汉朝发动了三次进攻。汉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匈奴寇狄道,攻阿阳”。汉高后七年(公元前191年),“匈奴寇狄道,略两千余人”[27]。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掠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28]。分析冒顿单于对汉朝发动的三次战争,可以看出,前两次战争的规模较小,匈奴意在掠夺汉朝财物、人口,双方无持久战,第三次战争的规模较大,但汉朝军队一出,匈奴立即回调军队转打西域,似乎攻汉朝是假,麻痹西域各国而对其突袭是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汉匈双方并无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基本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右贤王进攻汉朝上郡一事做了解释。认为是汉朝的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一时冲动,没向冒顿单于请示,就擅自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右贤王的行为破坏了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所以冒顿单于罚他去进攻月氏及西域各国,并大获全胜。冒顿单于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汉匈关系,提出:“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29]在这封信中,冒顿单于一方面要修复因右贤王事件被破坏了的汉匈关系,另一方面则借助匈奴对西域战争的胜利来胁迫西汉王朝履行和亲约定,从而保证匈奴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招果然奏效,汉朝接到冒顿的信后,立即商讨是出击匈奴还是继续和亲,大臣们一直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30]两年后,汉文帝回信冒顿单于,对他来信中的意见表示赞赏,重申:“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31]并向匈奴赠送黄金饰品、衣服、锦绣、赤绨、绿缯等贵重物品。
四、保持适当的战争节奏与限度
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冒顿单于始终保持了战争的限度,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中原政权的统治并取而代之,也不是为了攻战内地的城池并为己有,更没有占领土地进行农业开发的想法,而是为了通过战争威胁获得物质财富。冒顿单于的这一做法也被后来的北方游牧统治者所效仿。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将其概括为“外部边界战略”,“他们的‘外部边界’战略充分利用了游牧民族能力上的优势突袭中原,并在汉人实施报复之前撤退。它有三个主要部分:暴力突袭以震慑汉朝朝廷,时战时和以增加从汉人那里得到奉供数量和贸易权,而且,即便是在大捷之后,也有意拒绝占领汉地。”为此:“匈奴并不纯粹使用暴力,他们确实是将暴力作为与汉朝讨价还价的一种策略。汉廷从来不会忽视匈奴及其需求,同时也被迫将单于视作与普天之下至高无上的汉朝皇帝平起平坐的统治者。”[32]这一战争策略对汉匈双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匈奴避免了同强大中原王朝的大规模决战厮杀,便于把主要精力用于统一北方草原上,并能够从汉朝持续不断地得到物质财富,有利于游牧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匈奴帝国的统治,建立了称雄大漠南北的草原帝国,成为匈奴历史上最显赫兴盛的时期;中原汉朝政权则获得了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良好时机,实行了轻徭薄赋的统治政策,恢复了经济,增强了国力,为文景之治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冒顿单于在位的时间为秦二世元年到汉文帝前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到公元前174年。在35年的时间里,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冒顿单于发动的重要战争包括击败东胡的战争,第一次击败月氏的战争、兼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及夺取河南地的战争、向北降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的战争、白登之围、侵入汉朝上郡的战争、第二次西击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战争等。大规模的战争共计7次,平均五年就有一次。保持适当的战争力度,有利于冒顿单于巩固自己的位置,提高自己的威信,增强匈奴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并从汉王朝获取了一定的物资,建立起强盛的匈奴帝国。但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对草原游牧民族来说,与中原农耕民族相比,尽管发动战争具有种种优势,但战争,特别是力量均衡的长久战争,同样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游牧经济本身具有分散性的特点,而战争则需要高度统一与集中。把大量的男丁集中起来,会极大地减弱游牧民族在生产活动中对抗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为了保证后勤的供应,需要把大量的牲畜集中起来,不仅会造成草场的过度啃噬,还可能带来畜群的瘟疫。游牧生产方式的移动性特点,也使战争中的伤员难以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治疗,战争还会导致闭市封关,使游牧民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农耕民族的资源。游牧骑兵虽然具有很强的机动性与战争力,但却难以进行攻坚战与持久战。正如后来拓跋力微所总结的那样:“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33]冒顿单于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既保持了一定的战争节奏,利用战争扩张自己的势力,又避免与汉王朝进行持久决战,保持了战争的限度,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冒顿单于是匈奴民族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处于秦朝的统一及崩溃之间,项羽与刘邦及冒顿三人,超越了草原及中原的界限而浮出表面。至少到司马迁的时代为止,冒顿应该才是最终最终的胜利者。”[34]这样的评价或许有所拔高,但从与秦始皇对匈奴的政策相比,冒顿单于对中原王朝的政策似乎更为成功[35]。从总体上看,冒顿单于的战争策略体现在:他发动的战争目的明确,战争中使用的手段灵活多变,善于以弱示敌,麻痹对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优势兵力威慑敌人。对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冒顿单于审时度势,制定了不同的军事战略,北方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征服、占领为主,意在统一北方草原;南方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以胁迫、恐吓为主,保持战争的限度,意在获取中原地区的物资和财富。冒顿单于的军事策略的成功实施,把匈奴帝国带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避免了汉匈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客观上为汉朝修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1][4][5][6][7][8][9][10][11][13][15][16][17][18][19][22][24][25][26][28][29][30][31][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Z].北京:中华书局,1959.2890,2888,2888,2889,2890,2893,2879,2892,2889,2894,2896,2889,2890,2894,2896,2896,2883,2891,2894,2894,2896,2896,2897.
[2]吕喜林.评冒顿单于[J].阴山学刊,2001,(5).
[3]周锡山.汉匈四千年之战[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27-28.
[12][东汉]班固.汉书·刘敬传[Z].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七册).2121.
[14]王庆宪.从平城之役看冒顿单于的“诱”兵之策[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3).
[20][2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Z].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十册).2979,2985.[23][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传[Z].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七册).3872.
[27][东汉]班固.汉书·高后纪[Z].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一册).99.
[32][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63.
[33][北齐]魏收.魏书·序纪[Z].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一册).5.
[34]杉山正明.游牧民族的世界史[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79.
[35]王绍东.关于秦朝北击匈奴的若干问题辨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