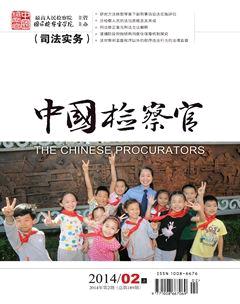陈旧“疑案”证据的审查运用
文◎雷红英朱才琴陈珍建
陈旧“疑案”证据的审查运用
文◎雷红英*朱才琴**陈珍建**
[基本案情]1995年7月26日晚上,长期在成都打工的吴甲回到四川省简阳市石板凳镇芦永村2组,想到妻子和自己的二哥吴乙(同父异母)有不正当关系后又离家出走,便心生怨气,产生了“教训”吴乙的想法。次日凌晨两三点左右,吴甲拿着在回家路上捡的一根木棍,进入隔壁吴乙与其妻胡某的卧室,走到床边,用手中的木棍向床上猛击两下后离开,并将木棍丢弃在离家约50米远的庄稼地里,后乘车逃往成都。当日早上5点左右,吴乙从疼痛中醒来发现自己右眼部受伤(未作伤情鉴定)、妻子胡某头部大量流血并呼叫不应,已死亡。经法医鉴定,胡某系头面部遭受有一定重量的钝器打击致颅骨碎裂骨折,脑组织挫裂伤死亡,性质系他杀。公安机关立案后,于2008年对吴甲决定刑事拘留并网上追逃。
2012年3月2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瓜子坪派出所接辖区一居民赖某某报称:有一杀人在逃人员叫“曾崇高”。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将“曾崇高”抓获,经审讯其供述了真名叫吴甲及1995年在简阳老家“打人”的动机和经过。2012年5月25日,简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受理了吴甲涉嫌故意伤害案。虽经两次退补,但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证据仍然存在较大缺陷,检察机关对诉与不诉存在严重分歧。
一、本案审查起诉分歧
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本案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且未过追诉时效,对此无异议。但对本案诉与不诉,检察机关内部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作存疑不诉处理。主要理由和担心:一是本案完全没有现场目击证人,没有收集到作案工具这一关键性实物证据和其他有关直接证据,整个作案过程的描述依赖于吴甲的供述,且吴甲自身对作案细节、后果不很清楚,依据刑事诉讼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只能存疑不诉。二是本案虽然有举报人、吴甲亲人等提供的吴甲曾经简单说过1995年对吴乙及妻实施伤害行为的证言,有鉴定意见证明胡某死于有一定重量的钝器打击,有证据证明吴甲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但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疑点,如:鉴定意见并没有指明“钝器”的种类;吴甲实施伤害行为与吴乙醒来发现妻子已死亡之间有一定间隔,之间是否有其他人介入或自身疾病导致胡某死亡等。本案主要依赖吴甲的供述,证据难以形成锁链,一旦吴甲翻供,脆弱的证据体系可能崩塌,且已经退补两次,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存疑不诉。三是本案证据缺陷比较明显,如果起诉,法院可能作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办了错案,对目标考评和单位形象不利,起诉风险较大。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主要理由:本案虽然存在证据缺陷,但可以达到“两个基本”的要求。吴甲出于伤害的故意,对被害人胡某和吴乙实施了伤害行为,且伤害行为与胡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他人介入致胡某死亡的怀疑缺少依据且可以排除。这些事实有吴甲多次稳定的供述和其他证据相印证,即使吴甲翻供也不会导致现有证据体系崩塌,胜诉的几率比较大。
二、本案证据的审查运用
本案与其他很多历史积案一样,由于时间久远,执法理念、证据采集、法律适用标准变化大等原因,往往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且通过补查完善证据体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处理上出现严重分歧在所难免。但本案是人命关天的案件,诉与不诉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建立在仔细的证据分析和运用基础之上,才能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努力实现不枉不纵。这使承办人既深感责任重大,又有一种接受挑战的动力。责任和挑战,促使承办人认真对待各种分歧和担心,反复、仔细审查案件,通过梳理证据、分析证据、组合证据,逐步理清了思路,坚定了信心。
不可否认,本案发生在被害人和村民熟睡的深夜,整个作案过程、细节完全没有他人能够证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但这是否意味着就“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呢?是否意味着缺少直接证据,其他间接证据就无法形成证据链呢?承办人认为,对于陈旧积案,由于各种原因,要将与犯罪有关的所有证据收集齐全、所有事实全部查清,显然是无法做到也没有必要的,只能围绕“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这一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展开,看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能否形成锁链。经仔细梳理,承办人认为本案证据能够形成锁链,达到“两个基本”的要求,可以起诉。
(一)本案犯罪嫌疑人的多次供述自然、稳定,与其他传来证据相印证
1.吴甲归案后在攀枝花、简阳侦查机关和审查起诉环节共6次供述自然、稳定,内容基本一致。这些供述大体还原了作案的动机、手段、行为等过程和细节,要点有:一是犯罪嫌疑人身份。吴甲供述称:“我叫吴甲,因害怕打死嫂子被刑事追究,悄悄拿了堂哥曾崇高的身份证长期在攀枝花使用。”二是作案动机及工具来源。吴甲供述称:“因发现妻子与哥哥吴乙有不正当关系心中一直气愤。1995年夏天的一天晚上7点多,从成都打工回到简阳棉丰乡,一个人喝酒,想起吴乙与妻子的事,越想越生气,就喝得有点醉。在回家路边拣了根一尺多长、直径大概4厘米的木棍,想去教训吴乙。也没有想过要把他打死或者打残,只想为自己出出气。”三是作案过程。吴甲供述称:“到家时大概凌晨三点钟左右,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感觉很孤单,就越想越气。由于两家的屋连在一起,吴甲从自家后门直接到吴乙住房的一个小门,轻轻推开进入到吴乙和他老婆睡的房间。进去后什么也没看到,只是估计到了床的位置,便右手握住木棍朝床上打去,只听到啪、啪的声音响了两下,也没有听到谁叫喊。之后,从卧室跑出来将后大门打开,又跑了一段路将木棍扔了,然后沿机耕道向莲花街上逃跑,并乘车逃到成都。”
2.吴甲对伤害事实的供述有其他证言印证。在归案前,吴甲曾经向母亲、姐姐、其他人提起过“打人”的事情。一是吴甲曾经向母亲和姐姐说过。吴甲供述称:“在2010年去内江隆昌县给母亲过70岁生日时,跟母亲和姐姐提到过1995年夏天那个晚上‘胡乱打了两棒棒的事情’。”其姐证实:“2010年母亲70岁生日时,吴甲跟我提起过他把他二嫂胡某打了的事,具体情况没有说”;其母证实:“2010年吴甲到隆昌给我过70岁生日,给我提过他1995年时打过胡某,他不知道打死没有”。二是吴甲曾经酒后向其他人说过。攀枝花市居民赖某某2012年3月20日向派出所举报称,吴甲向他说过身份证和名字不是自己的,因他老婆被一个男的骗走了,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男的老婆杀了。且证实,在公安机关清网行动时,吴甲天天都躲在茶馆里面到深夜一两点才回住处。
综上所述,吴甲的多次供述自然、稳定,有同步录音录像和归案前其他人的证言相印证,可以排除归案后迫于压力而作假口供的可能性,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使用。
(二)吴甲供述的作案动机、时间等有其他证人证言相印证
被害人吴乙印证了吴甲回家时间和作案的动机、大体时间及开门等部分细节:“我被打伤后醒来之前没有听到声音也没有看到什么,因为出事后一个多小时才天亮。醒来后还看到卧室门和外面大门是开着的,我记得睡觉之前这两个门都关了的。我和吴甲妻子之间确实有不正当关系。我之所以确定是吴甲打死我妻子的,是因为我和吴甲一直都有矛盾。妻子出事头天下午六七点钟我和大舅子胡某某从简城打工回家,走到棉丰乡变电站时遇到吴甲,他正向家的方向走,当时没有给他打招呼也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胡某某关于看到吴甲回家的证言与此相同)”。莲花乡卖副食的傅某证实:“1995年事发当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看到吴甲拿着一个包包从副食店经过往车站方向走,他还用包包一挡一挡的,感觉不想让人看到,我没有招呼他”。这证实了吴甲供述的逃离时间、路线。此外,村干部和多位村民证实:吴乙与吴甲的妻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三)吴甲供述的“打人”情节与鉴定意见、相关照片等相印证
一是死者创口大小、致伤器械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相吻合。尸检报告显示:死者胡某死亡时间为1995年7月27日凌晨5点左右(说明被打后可能未立即死亡);根据右颞部(右耳朵上方的部位,靠近太阳穴)有3.5cm*1.6cm的创口,创口边缘不齐,右颞骨凹陷性环形骨折(环形骨折线长10cm),硬脑膜破裂,脑组织外溢等特征分析,致伤工具应为有一定重量的钝器。这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使用1尺多长、直径约4cm的木棒打击相吻合。二是被害人受打击次数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致。照片显示,被害人吴乙和胡某头部各有一处伤口,符合犯罪嫌疑人在漆黑一片的情况下估摸着打了两棒的供述。三是被害人位置不同与受伤程度不同相吻合。死者胡某睡床边,被害人吴乙挨着胡某睡里面。从常识看,犯罪嫌疑人摸黑站在床边用1尺多长的木棒打击,离得近的胡某受打击力度较大伤情较重,稍远的吴乙受打击力度较小伤情较轻。
(四)吴甲的“打人”行为与胡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鉴定意见揭示了胡某被打与死亡之间的直接关系:死者胡某系右侧头面部遭受有一定重量的钝器打击致颅骨碎裂骨折,脑组织挫裂伤死亡,性质系他杀。吴乙的证言:“我睡着之后不知为什么突然感觉头很痛,把我痛醒了之后我开灯发现自己右眼处流了很多血,妻子的太阳穴也在流血,我就喊妻子但是喊不醒。之后我父亲通知了村书记同时还找了一辆车把我和妻子送到医院,医生说我妻子已经死了”。当天早上,还有村干部及其他村民到吴乙家看到了同样的情形。
(五)本案的几个疑点解析
一些检察官对本案提出了若干疑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疑点可以通过证据梳理结合常识、常理、常情予以排除,形成真正的“内心确信”。
1.吴乙被打后受伤不是很重为什么没有立即醒来?言下之意是胡某的死是否与吴乙有关,或者放任或者故意?公安机关在侦查中特别向村干部和知情村民作了调查,均证明吴乙虽然与吴甲的妻子有染,但与妻子胡某的关系不错,生有一儿一女,没有明显的矛盾和吵闹。吴甲在供述中说:“只听到啪、啪的声音响了两下,没有听到谁叫喊”,也证明吴乙确实没有醒来。从常识判断,一个深度熟睡中的人,一般响动难以惊醒,遭受突然打击后除非处于继续昏睡或直接转为昏迷状态,否则会有下意识的应急反应,而不可能深思熟虑一个“阴谋”后假装无反应。综上,胡某的死与吴乙有关的怀疑可以排除。
2.胡某被打与发现死亡之间有一定间隔,是否有其他因素介入?言下之意是胡某的死是否完全由吴甲的伤害行为引起,比如期间是否有其他人进入再次危害、胡某自身有无重大疾病?证据显示,吴乙家当晚没有遭受盗窃、抢劫,只有两个人被打;胡某头部只有一个伤口,没有遭受二次伤害;胡某是否有其他重大疾病没有证据认定或排除,但鉴定意见明确胡某死亡与被击伤口有直接关系。
3.吴甲对胡某只打了一棒能否造成这么严重的颅脑损伤?尸检报告显示,胡某右颞骨凹陷性环形骨折,凹陷深度0.2cm,环形骨折线长10cm,形成骨碎片5块、脑组织外溢。吴甲对打击方式记不清了。但从创口形状、大小、深度和常识推测,吴甲在气愤之下,使用1尺多长的木棒,便于近处用力,站着打睡着的人,居高临下其打击着力点应在木棒端部(近似圆形),且先是边缘较窄处(类似钝刀)接触胡某,逐步中心较宽处侵入,才可能形成鉴定所描述的伤口形状及大小。如果打击着力点不是端部,则受损状况不是这样,程度也会轻一些。据此,一棒打下去完全可能致较薄的头骨破裂,导致脑组织外溢而死亡。
(六)结论与处理
作为一起故意伤害案,基本事实可以归纳为:是谁?实施了何种伤害行为?这种行为造成了何种伤害后果(包括因果关系)?如果有关这些事实的基本证据能够依法查明,则可以认为形成了锁链,达到了“两个基本”的要求,即使吴甲翻供,也不会导致证据体系崩溃。综合以上分析,承办人认为,本案的基本证据可以锁定以下基本事实,符合起诉条件:吴甲为了泄愤报复,在黑暗中用木棒对熟睡的吴乙及妻子实施了伤害行为,这一伤害行为导致吴乙受伤及妻子受伤后死亡的后果。
本案经检委会两次研究,最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吴甲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甲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吴甲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简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及量刑情节成立。据此,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吴甲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吴甲对此没有上诉,目前判决已生效。
三、办理本案引发的几点思考
本案是众多陈旧积案的缩影。诉与不诉的分歧,既反映出对证据审查和运用的不同认识、技巧,更反映出执法理念的碰撞。总结本案成功办理的经验,可以对审查起诉陈旧“疑案”得出几点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正确把握和运用“两个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是案发后以证据为基础还原案件事实的过程。由于主客观因素制约,要将与犯罪有关的所有证据收集齐全、将犯罪事实完全查清,既无法做到也没有必要,陈旧积案更是如此。面对存在较大证据瑕疵或缺陷的陈旧积案,司法机关往往陷于两难:一方面很多犯罪嫌疑人就是实际作案人,但因证据缺陷可能难以定罪处罚,被害人得不到抚慰;另一方面虽然案件处理依法应当从旧兼从轻,但证据标准和司法理念却不能“从旧”(如:疑罪从有、轻视人权)。解决陈旧积案历史与现实、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冲突,更有必要正确把握和运用“两个基本”原则。“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作为一项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司法原则,对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保障刑事诉讼公正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我们既要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又要坚持“两个基本”,防止纠缠细枝末节,宽纵犯罪。[1]部分事实不清不等于“基本事实”不清,若干环节不清也不等于“基本事实”不清。[2]抓住“两个基本”,就抓住了对案件正确处理起关键、根本和决定作用的事实和证据。本案是历史积案,既要坚持现行的执法理念和基本证据标准,又要兼顾历史状况,不可过分苛求。如果纠缠于细枝末节,则只能成为“死案”,因为根本没有补证的可能。当然,如果连“两个基本”都达不到,则不能定罪量刑,这是底线。
(二)正确把握和运用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现代司法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如何界定“疑罪”却是正确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的关键。我们认为,有证据瑕疵甚至缺陷不能等同于就是“疑罪”应当从无,而必须看瑕疵或缺陷在定罪量刑中起多大的作用。如果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证据缺失或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基本事实不清、合理怀疑不能排除,可以认为是“疑罪”;如果证据瑕疵或缺陷不影响基本事实清楚,则不宜定性为“疑罪”。本案中,虽然作案工具木棒这一重要证据缺失,其他直接证据很少,但并不影响基本事实的认定,并非真正意义的疑案,如果把证据缺陷等同于“疑罪”而从无,显然不恰当。
疑罪从无是防止冤案不可动摇的底线。但是,不枉不纵才是司法的最高追求和公正体现。放纵犯罪和冤枉好人都是有害的错案,疑罪从无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比疑罪从无更高层次的理念是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但保障人权是双向的,包括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和维护被害人权益;公平正义也是双向的,包括让无罪的人不被冤枉和让有罪的人受到制裁。因此,坚持疑罪从无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轻易把可以追诉、能够追诉的案子当疑案从无。同时,疑罪从无体现的程度要因诉讼环节而不同,对侦查环节不能过分强调疑罪从无,因为侦查需要根据蛛丝马迹去假设、去推理,确定侦查方向;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尤其是审判环节要坚决贯彻疑罪从无;检察环节则要体现疑罪从无,注意区分属于证据缺陷、瑕疵还是真正的“疑罪”分别处理。如:一些证据存在较大缺陷但基本犯罪事实能够锁定的案子,或者有罪证据居于优势的案子,不能轻易作从无处理,起诉毕竟不是最终环节,由法院多一道审查和制约,并不违背疑罪从无原则。许多国家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在追诉犯罪上应该保持一定的张力,有的还将起诉标准规定为低于审判标准。[3]
(三)正确评估和看待无罪判决风险
一定数量的无罪判决是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公正的正常现象,既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冤案,也可以防止因检察机关过于谨慎而不必要的放纵。目前的问题是,检察机关目标考评往往追求零无罪判决,把无罪判决视同办了错案。我们认为,这一导向的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一方面,如果提出诉后要100%判决有罪的目标,公诉人员就会把保险系数留得过大,只起诉那些事实证据不存在任何不同认识、明显构成犯罪的案件,而将处于模糊地带、存在不同认识的案件作不起诉处理,从而造成打击不力。[4]另一方面,对于可能判无罪的案件通过协调等非正当手段要求法院作有罪判决,或者不经庭审而撤回起诉。这就可能混淆了错案的概念,造成真正的错案。因为,就司法的整体来说,如果真是无罪或“疑罪”的,法院作无罪判决恰恰是防止了错案(协调判决有罪则错了);如果经庭审证明不是无罪的,法院作有罪判决也是防止了错案(撤回起诉则错了)。本案是人命关天的案件,但不属于死刑案件。所谓起诉风险,无非就是无罪判决的风险,实质上是考评风险,而非真正的司法风险。这个风险与人命和公平正义相比,不足为重。这既是职责所在,又是司法为民、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
注释:
[1]朱孝清:《对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几点认识》,载《检察日报》,2013-07-08。
[2]万尚庆:《论两个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http://www.ahjcg.cn,访问日期:2013-12-05。
[3]同注[1]。
[4]同注[1]。
*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检察院[641500]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检察院[641400]
——以被告人翻供为主要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