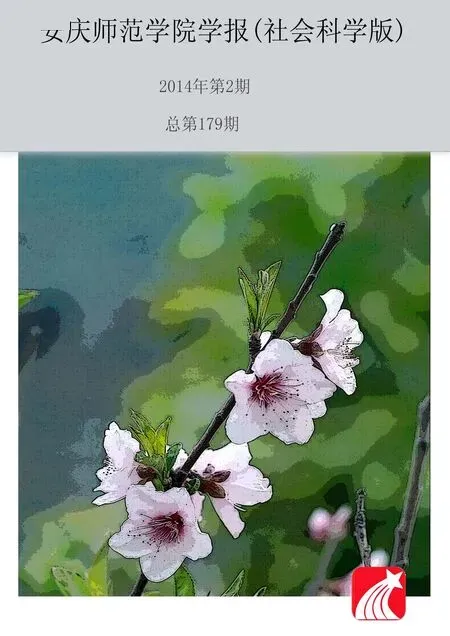“五四”时期冰心文学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关系
薛 昭 曦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五四”时期冰心文学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关系
薛 昭 曦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冰心早期的文学创作是从传统家国伦理观念出发,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建构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新的伦理标准和道德理想。这种追求个体人格完善和社会功用的启蒙主义立场,是一种理性之爱,是世俗观念中道德的思想境界,而非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赎之爱。
冰心;“爱的哲学”;基督教文化
长期以来,许多证明冰心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论据,多基于冰心早年的教会教育背景以及早期文学创作中流露出的鲜明的宗教情感体验。于是,在诠释冰心“爱的哲学”时,便不证自明地找到了基督教文化中爱的精神。这二者看似联系紧密,也确实存有思想上的互涉性,但是,如果认真、严格地进行比较和分析,就会发现冰心文学创作中“爱的哲学”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泛爱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中的爱的精神实际上貌合神离,甚至还有较大的思想偏差。
一
“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基督教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五四”时期迅速地传播,一方面与当时殖民语境下帝国主义的文化策略有关,另外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为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作为文化的代言者,“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为建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而四处奔走,向西方寻求各种文化、思想武器,以达到改变社会、启蒙民智的文化政治诉求。而基督教以其向上信仰、人格道德与博爱精神等世俗面目赢得了“五四”文化先驱和作为社会精英的作家们的普遍青睐,被寄寓了深重的期盼。冰心早年所接受的教会教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在当时它有其纯粹性和先进性,但也存在不可摆脱的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激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和基督教文化的结合,造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生态。而冰心在“五四”时期走上文坛并且所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从这里进入,我们就可以看到冰心在“五四”时期所创作的那些作品,并非如许多论者所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基督教文化的思想特质。相反,在这一时期,冰心的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基督教思想层面上的“爱”是相当模糊的。
纵观冰心早期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这样几种类型的“爱”:
(一)人伦之爱。涵盖在这一范畴之内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母爱”主题,这也是冰心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典型。“母爱”的指涉,在其作品之中不仅仅只是对于某个个体的情感倾诉,而常常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情怀。甚至,我们透过“母爱”的情感视角,可以窥见其对世间万物,小至花草树木,大到宇宙万有的“博爱”。这种博爱确实带有基督教博爱的文化精神。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是,冰心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于“父爱”的深层认同,而这种“父爱”的力量似乎超过作品中所常常表现的“母爱”主题。冰心在《梦》、《往事》等散文中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大、威武的父亲形象。显然,在这一类的作品中,军人形象的“父亲”连着那广袤无涯的大海构成了冰心最初的心理记忆。正如她自己所说,“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梦》,1923年4月《小说月报》第14卷第4期)隐藏在冰心童年这份深刻的梦的背后,其实正是她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某种认同。渴望建功立业和兼济天下的文化情怀,很早就在冰心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在后来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她经常提起童年的这些与大海有关的梦,以及对她早年成长产生巨大影响的祖父和父亲。这些“父爱”对冰心文化人格的塑造比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母爱”,显得更加真实而富有约束力。因此,说“父爱”是冰心作品中“母爱”主题的另外一种投射,还不如说,对“母爱”的倡扬其实是在父爱基础上的进一步注解和阐发。但不论是父爱还是母爱,冰心在对其进行文学化的表现中体现出的依然只是一种具体的、世俗的人伦之爱。这种“爱”是在现实的家庭以及社会场域中铺展开的,尽管它以陌生化的形态坐实了“五四”时期破旧立新的道德努力与读者期待,但是其中所暗含的孝慈、隐忍、人伦亲情等理性的人伦观念仍未背离传统道德的内涵。这样的一种人间之爱,与基督教当中所弘扬的圣爱是有差别的。
(二)自然之爱。对自然主题的描写和关注也是冰心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在冰心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在小诗和散文上,自然主题几乎成为理解冰心文学思想不可回避的精神通道。我们可以透过一朵花,一片云,一阵风,看到一个女性作家笔下对于自然的独特眷恋和细密情思。但是,自然的风物在冰心的笔下又不像其他的女性作家一般,只是停留在一己情愫的寄寓之上,而逃不出女性缱绻含蓄的拘囿。当自然的主题被放置于“爱的哲学”这一思想统摄之中时,同样是熟悉的花鸟草木却显得别有一番风味。灌注在自然风物之中的,是冰心对“爱”的一个独特理解和超越。由伦理的世俗的爱上升到此时对宇宙之间一切生命景象的爱,这其实已经超越了基督教“爱”的绝对内涵,而走入了一种相对的、普泛的泛爱主义。如果我们仔细回味,就会发现这种“爱”更多时候是源于一种生命意识,对生命的热爱才促成了她对于自然的独特视角。而如果我们稍微熟悉道家思想文化的话,便会发现这样一种自然之爱与道家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竟是如此相似。这应该不单纯地只是一种巧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冰心接受基督教文化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作为一种心理沉淀留在她的文化记忆之中。当基督教的一些教义重新进入她的文化构成当中时,更加强烈地诱导了先前这部分的文化记忆。这时基督教文化当中的爱的精神打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零碎的片段,将其变得丰富起来。二者的结合,才形成了冰心“五四”文学创作当中鲜明的泛爱主义的风格特征。同时,宇宙自然在冰心的文学创作中,常常被作为“上帝”的替身而成为祷告的对象。她在两篇写“晚祷”的散文中那种神秘的宗教式的体验以及内心所生发的“虔诚静寂”之感,并非“万能的上帝”的默示,而是一种自然的启示力量,是“慈怜的月”和繁星的“点点光明”所带来自我灵魂的觉醒。于是,在冰心的文学创作中,祷告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所指,实际上却成了她个人自我人格灵修的形式。这种无所确指的个人精神体验的“祈祷”方式,实际上只是思想上的泛神论与美学上的感伤主义风格的表现,是一种艺术情感的表达方式,而非宗教仪式中的“圣爱”。
(三)社会之爱。这是冰心“爱的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果少了这一个“爱”的维度,那么对冰心“爱的哲学”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也就无法真正认清“爱的哲学”与基督教文化思想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且很容易将基督教文化简单化为冰心文学创作中唯一重要的影响因子。其实,吸引冰心走上文学道路的,并非只是文学的艺术特质,而是文学的功用。在“五四”功利主义的文学语境里,坚持纯文学的创作几乎不太可能,就算存有少之又少的“无用论”的文学创作,其实也是对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潮的逆向回应。冰心也正是被当时启蒙与救亡的文学之用的浪潮推上文坛的。因此,冰心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带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风格。她急切地想利用文学这一形式进入人生和生活的现场,从而为愚昧和麻木的大众指明一条出路,这是“五四”一代的小知识分子典型的启蒙姿态和文化心理。而基督教所主张的用宽恕、顺从、忍耐、受苦来消除社会罪恶,用仁慈、博爱拯救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正好符合“五四”面向群体启蒙的特殊需求。传统的人伦观念未经理性的挑拣而成为众矢之的,已然失去了改良社会、塑造人格的合法性。基督教思想在此时成了重新构筑伦理法则的重要手段,以“爱”为核心的宗教情感的伦理化和道德化与西方人道主义一起成为新道德的鲜明旗帜。显然,在此“爱”已经不再具有纯粹的宗教意义,而成为一种新的道德原则和伦理标准。从作家的创作行为上来说,那些具有基督教意识的文本背后,也并非一种宗教行为,而只能看做是一种文化行为或道德行为。作家们一开始便是以文化人、思想者的姿态出现的,而非以宗教作家或基督徒的姿态来对待这个世界。
总之,基督教给中国现代作家道德批判带来一个独特的领域[1]。这样看来,冰心文学创作中有意营构的“爱的哲学”,实际上也是她为“五四”时期青年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人苦难问题、反战情绪等一系列人生现实与终极所指出的归宿[2]。如单纯将其理解为是基督教文化视野内的爱的话,就不免有失偏颇。作为“五四”时期开始写作的作家,或许冰心在创作之时并未意识到这些,但是无论如何她是无法逃脱一个时代的桎梏的。她有意无意中所选择的文化姿态其实早就使她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和理解打上了时代的局限和偏差。
二
当然,冰心的“爱的哲学”所建构的爱的体系远比上述三种类型多,但却都没有越出这三种类型的价值范畴。以冰心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为例,这三种类型的特征就更加明显。那么,以“爱的哲学”为中心话语的冰心文学创作到底与基督教文化存在着多少重合?冰心笔下的“爱”和基督教的爱到底呈现出怎样一种影响关系呢?
基督教的爱,其意义的取向是多层面的,它不仅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爱世人以及世间的一切生命,同时爱也是一种信仰、宽恕、忏悔和牺牲。而后者恰是基督教文化鲜明的身份特征。基督教的重要教义之一,便是“全心全意地爱你的主——上帝”,这种爱对于中国人是十分陌生的也是难以理解的。如果可以用一些词语来替换这个“爱”,那就是怕、敬畏以及绝对的相信。基督教当中有一个绝对的最高存在,那就是上帝,上帝是自在自明的,因此对于上帝的信仰也是绝对的而不能被证明的。这样的信仰与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鬼神都是人的化身,并且他并非是唯一和绝对的,人们对他们的信仰也大多存有功利主义的心态。换言之,中国的鬼神观念仍是建立在人伦范畴之上。如果我们从信仰的层面评判冰心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文化思想,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尽管受过严格的教会教育并受洗入教,冰心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宗教意味的爱却仍然十分模糊,或者干脆只是停留在教义的最表层上。作为“事实”基督教徒的冰心不仅不注重宗教的仪式,对于“上帝”的情感也是淡薄的,“三位一体”的耶稣在她那里只是“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3],这些所表现出来的都不是“因信称义”的基督教徒所应有的绝对信从。而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认为上帝具有不受神圣与凡俗界限限制的能力。从这里,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冰心对于基督教的接受或许存有她自己都无法自觉意识到的偏误之处。
如果说基督教中爱的反义是忏悔和救赎的话,那么冰心笔下的世俗之爱,常常无法超越人伦范畴,其反义也是指向一种仇恨,这一点与基督教中爱的精神相去甚远。这种人伦范畴在冰心文学思想里就表现为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于儒家传统文化和人格的认同。例如她在对童年的记忆中,常常伴有对于横刀跃马的军营生活的回忆和向往,对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内圣外王”等儒家道德理想和人格模式的追求。而基督教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实际上只是旧瓶装新酒,成为一种缺乏情感投射的空洞概念。上帝也被作为具有“伟大人格”的人接受作家的理解和改造,并不再具有神的形象。除此之外,在冰心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童真”主题所透射出的道家复归思想的精神影子,也正说明她对于基督教中爱的理解更多的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作为“前理解”。也就是说,她是“从精神的和伦理的层次接受基督教”的,她“或从基督教中摄取‘爱’的哲学,或从基督教中获得使自我精神平静而充实的理性”,从而“变宗教的目的为手段”[1]。对于冰心,“提倡宗教,其目的不是通过神秘的宗教体验,获得与上帝同在的‘最高幸福’,不是为了通过信仰宗教来解脱自我的和民众的不幸和苦难,而更多的是借用宗教净化情感,增强与苦难和黑暗作斗争的勇气”[1]。因此,在面对现实的苦难时,冰心文学作品给出的精神出路就不是宗教式的忏悔和救赎,而是道德的完善和弥补。在冰心的“爱的哲学”中,道德理想高于绝对的信仰。这种道德模糊了人与绝对存在的界限,而认为只要通过人的自身努力和道德修养,就可以成圣为王。因而,爱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这种爱建立在自我之上,由自我从而烛照世界。这不正是儒家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一个生动表现吗?冰心对于爱的理解其实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出发,从而上升到一种泛爱主义。同样,这种泛爱主义与基督教文化也是大相异趣的。泛爱主义的最终指向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上帝,上帝就是自然,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神”的形象。因此,人类罪恶的解脱不需要等待末世的审判,而只需要人自身可以完成,这也正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所提出的理性的宗教观。
如果说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冰心的文学创作与真正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之间存在貌合神离之处的话,那么冰心在对现实的过分关注中所倾入的那份爱,更加鲜明地展现了她的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深层断裂和背离之处。在冰心笔下,爱和革命、斗争、启蒙和出走等等“五四”时期的文学主题具有相同的价值内涵。爱同样也只是一种解决世俗问题的工具,只不过这种爱有了直接的思想资源,那就是基督教的教义。然而,这一种的“爱的哲学”和许多“五四”文学所提出的精神药剂一样,并未能够医治中国文化的深层创伤。所以他们这种带有书斋精神体验性质的启蒙姿态,被后来左翼文学极力反对和批评也是不无道理的。也就是说,冰心在文学创作中对于爱的理解并没有为中国文化或是文学呈现一种新的异质的经验,却被中国强大的文化消融机制所销蚀和利用,最后成为代言。其实,并不是说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爱排斥世俗,而是在面对世俗时,冰心文学创作中所呈现的“爱”的方式以及对待世俗的启蒙态度,和基督教文化是不尽相同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文化中,“上帝并不关心一个关乎社会群体利益的幸福现世的建立,‘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只侧重宣扬作为个人的每一皈依者的灵性修炼和最终悔改得救的可能”[4]175。而启蒙本身就是与基督教教理相悖的。在基督教文化视野中,人类是带有原罪的,本身就是愚昧的,人只有依靠不断地忏悔才能获得救赎,他并不拥有拯救自身的力量。正是基于对人的“罪性”命题的反复言说,基督教才建立起了跨越各个时代的观念体系。然而,启蒙却是一种隐蔽的对抗,它其实是在宣布人的力量可以超越绝对存在和绝对信念,从而自己拯救自己走出罪恶的深渊,因此启蒙的主题是“理性”而非“救赎”。如果从这点上看,冰心笔下的“爱的哲学”显然是在提供一种自我解救的方法,这是一种世俗的爱,最多称之为带有某种神性色彩的爱,但它永远不是基督教中所弘扬的“救赎之爱”。与基督教文化中灵肉二分的人恶论信念不同,冰心依然是站在中国传统人论的立场,“唯人万物之灵”,依然将“人”放在以血缘建立的宗族社会中加以检视。因此,在人与人、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也就无法脱离家国观念的窠臼,所宣扬的还是“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古仁人之心”。冰心借助基督教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正是从伦理建构和道德人格方面思考社会变革与拯救民众的途径。
总而言之,由于整个历史语境对文学话语的期待,“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从西方借鉴的各种思想都不免打上了功利之用的历史印记,从而使得文化的接受、选择和传播显得慌不择路,建设和破坏是并存的。冰心在“五四”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也同样带有这样仓促和短见。她借助文学所提出的“爱的哲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和理解既是一种洞见,也是一种遮蔽。
[1]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J].文学评论,1999(2):120-130.
[2]戚真赫.论冰心的良知意识与人格模式[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5):25-29.
[3]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J].收获,1984(4):70-73.
[4]喻天舒.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
责任编校:汪孔丰
2013-05-07
薛昭曦,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4-18 17:23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2.004.html
I206.6
A
1003-4730(2014)02-0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