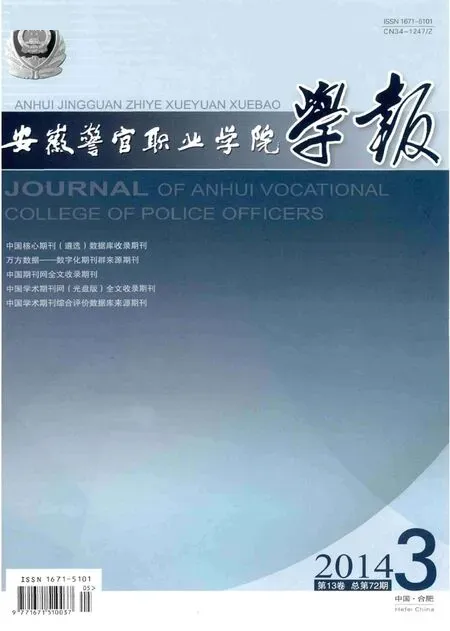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牟瑞瑾,段 旭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牟瑞瑾,段 旭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刑事诉讼法的两项基本任务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必须要以平衡这两项任务为切入点。非法证据包含非法的实物和言词证据,两者所适用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落脚点都是在于平衡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项基本任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时间较晚,发展也并不充分,但随着理论学说和实践应用经验的不断丰富和修正,尤其是在立法、启动程序、审查时间、证人证言质证、相关人员的追责等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定会再次获得有一个质的发展和飞跃。
打击犯罪;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其中,打击犯罪是刑罚权的首要目标,刑法的最原始初衷即在于此。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大家逐渐发现,被追诉人也是有人权的,也需要法律予以保障。人权,顾名思义,即人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是每个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维护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道义原则,已成为评判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打击犯罪时如何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不受侵犯,是现代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任务和主要价值所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刑诉法规则中能够平衡这二者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尊重和保障被追诉人人权这一思想。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和历史渊源入手,对于如何在立法中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尽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与执行,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大价值的平衡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和分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渊源
非法证据,又被成为“瑕疵证据”,是指的是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法律程序而采集得来的证据。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非法证据即是指因采集证据主体、证据的形式、证据所呈现的内容以及采集证据的程序或方式等方面不合法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法定主体违反法定程序或者采用了非法的手段采集而来的证据。本文所探讨的非法证据即是指狭义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法定主体违反法定程序或者采用非法手段采集来的证据,应当被依法排除,不得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规则。纵观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总体上具有三个特点:即规范对象为审判行为;仅适用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收集的证据以及仅限于违反法律规定或者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见于美国1914年Weeks诉合众国一案,在此之前,世界各国普遍没有对非法的实物证据设立排除规则。在1914年的这个案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刑事审判中禁止使用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即禁止通过非法扣押和搜查所获得的证据。[2]其后,历经近百年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大体采纳了这一规则,我国亦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这一规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平衡作用
美国证据学学者华尔兹教授有言,“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被接受为证据的问题——可采性的问题”。[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并不是保证获得证据的真实性,也主要不是规范取证行为,而是为了维护证据收集过程中对相关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证据排除规则在建立和适用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权衡和选择:一方面是证据的证明价值;另一方面是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4]法律向来是各种利益价值的相互冲突妥协的结果,不可能只为一种或某几种价值和利益服务。打击犯罪固然重要,然正如我国著名人权法学者李步云所言,罪犯也是公民,除了被剥夺的权利以外,其他合法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包括人身不能任意伤害、财产不能任意剥夺、人格不能肆意侮辱等。[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恰恰就是为了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使其人格尊严得到尊重。
非法证据规则的确立无疑是人类法治史上的巨大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人类历史上,虽然各个国家因各自具体国情、社会状况、宗教信仰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确立了各有特点的证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自是如此,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保障人权不受侵犯是各个法治化国家法律的共同价值目标,打击犯罪绝不能成为践踏人权的借口。当今社会,对于公民权利侵害最大的主体并非不守法的不良公民,而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证据规则确立的最大意义即在于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是主要方法之一。
美国学者认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在于,第一、维护公民隐私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等宪法性权利不受侵犯;第二、抑制违法侦查,打消侦查机关违法收集证据的诱因,使其承担违法收集证据的不利后果;第三、保持司法程序的纯洁性,使其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第四、为公民遭到非法取证时提供救济。[6]日本学者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是规范说,即使用违法证据是违反法律程序的;二是司法廉洁说,即使用非法证据有损司法机关的廉洁形象;三是抑制效果说,即为了抑制将来可能发生的违法侦查,排除违法收集的证据。[7]德国学者的主要观点为,一是保证法律事实发现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而是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三是保障审判的公平公正;四是保障司法机关的纪律性。[8]无论世界各国学者的观点有何差异,人权保障、法治理念、正当程序等都无疑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其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刑罚权的灵魂和意义即在于打击犯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绝非为真正的犯罪分子开脱而设。笔者认为,定罪需要证据,但若依照经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筛选的证据来定罪的话,此项判决必定能让绝大部分被追诉人心服口服,因为其所有的权利都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得到了保障,也使其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对于增加我国司法判决的社会效果,减少上诉率和错案率都是有极大好处的,同时也能让正直无辜的公民没有了错案冤狱的忧虑,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争取到一个更为和谐稳固的群众基础。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大价值在于在庭审过程中的适用,其适用过程实质上是对多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进行价值大小的选择过程。基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和对法律程序正当价值的维护,毫无疑问需要排除非法证据,但是,基于案件事实发现和实现真正公平正义的价值来看,一味地排除非法证据又是值得商榷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都是采取原则上排除、特定情况下不排除的做法。
非法证据的排除分为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个类别的排除,这两个类别适用的排除原则是不同的。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各国的做法近乎一致,即是绝对的、无例外的排除原则。这主要是因为,第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收集对于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往往会造成较为严重的侵犯,刑讯逼供即是最好的例证;第二,非法言词证据的虚假性极大,言词证据本身证明力就不及实物证据,更何况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此类证据对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害无益;第三,言词证据存在着被重复收集的可能性,故必须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一般不会存在紧急到必须违法收集的状况。非法实物证据一般采用原则上排除的原则,其并不存在绝对排除的状况,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达到一定的危害程度或者程序上的瑕疵可以采取措施予以补正的非法实物证据,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采纳与否。
出于对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目标平衡的考虑,非法证据排除往往会存在一系列的例外情况,即是指非法证据虽然存在,但是不适用排除规则而是作为定罪证据采纳的特殊规则。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一系列例外情形:第一,“质疑”的例外,即当被告人在法庭作证时,控方可以在法庭上提供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来质疑被告人证言的可信性;第二,“因果联系减弱”的例外,即如果官员的非法行为与取得的证据之间的因果联系由于另外因素的影响而被削弱或打断,从而消除了被污染证据的污点,那么这些证据具有可采性;第三,“必然发现”的例外,即如果控方能够证明,即使不发生违反《宪法》条款的情况,某项证据也会被最终或必然地发现,那么该证据具有可采性;第四,“善意”的例外,即尽管执法人员进行搜查时许可证表面上有效实际上无效,但如果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真诚地相信这份许可证是有效的话,执法人员依此进行搜查所取得的证据则具有可采性;第五,“独立来源”的例外,即对非法手段以外的独立来源取得的证据可以不予排除。在德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若违法取证行为没有影响到被告人,仅影响到了其他人的法律权利范围,则被告人不得在上诉中主张法院不能使用该证据对其定罪;第二,只要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合法的取得手段,法庭就会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第三,证据的排除必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服务的,若排除证据并不会促进被违反规则的目的的实现,法庭就会采纳该证据,因为这样做就会在没有达到任何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干扰对事实真相的查明;第四,证据的排除不能与根据“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查明真相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被告人的利益,证据则仍然被采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也简略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即“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发展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证据法对我国的证据制度加以确立和规范,《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的内容被认为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渊源。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被认为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标志。在此之前,除了刑诉法中原则性的表述之外,另有多个司法解释有所表述。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规定对此规则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表述,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不能得到贯彻执行。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用多个条款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例如第54条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第一,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予排除。第二,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予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予排除。第55条、第56条规定了提出和审查非法证据动议的主体等等。
新修订的刑诉法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无疑是一大进步,对于我国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相比,还是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界定不清晰,排除范围依然有限,尚不足以完全打消侦查人员进行违法取证活动的诱因;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规定并未形成严谨的体系,尚不能覆盖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再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监督保障体系的规定并不成熟,缺乏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最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启动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和宽泛化,缺乏可操作性和保障性。
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外的发展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在各国虽然大体一致,但是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确是不尽相同,尤其是两大法系各自的特点更是导致了这一规则发展状况的差异。英美法系的美国虽然在1914年就通过案例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是直到1961年Mapp诉俄亥俄州案件后,美国联邦和各州才全部适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为“毒树之果”理论的提出,其是指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而获取的其他证据,被认为是“毒树”结出的“毒果”,应该在审判中予以排除,主要包括下列六种情形:非法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与违法收集证据密不可分的证据;以违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发现的证据;以违法取得的证据引诱他人所获得的证据;违法取得口供后再次询问得到的口供;非法行为后多重间接得来的证据。[9]“毒树之果”理论建立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上,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容的延伸,其通常被认为是最彻底最极端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美国联邦法院对“毒树之果”理论创设了一些例外,例如独立来源例外、稀释例外、必然发现例外、污染中断例外等等。[10]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定显然没有美国那样地彻底与极端,以“毒树之果”为例,英国是坚决排斥“毒树”的,可是对于“毒果”却是予以使用的。大陆法系国家,由于传统上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的任务是主动发现案件真相,故对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的非法证据并不进行排斥,但是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交融,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渐意识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并且各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德国学者柏林在1903年就曾系统地提出证据禁止的概念,法国刑法也有“不可为了寻找证据而采用任何有损于文明之基本价值的手段”的理念,[11]日本最高法院也在1978年确立了违法收集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采纳,是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等诸多国际文件也都充分肯定和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从上述发展历程看,世界上倡导法治的国家均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作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工具。在被追诉人人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时,各国立法机关和法院便强化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通过完全彻底地排除非法证据来打消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诱因,从而强化对相关人人权的保障;而在人权保障达于顶峰且有矫枉过正之虞时,各国立法机关和法院再通过几项合理的例外规定来保证打击犯罪这一目标不因过度保护人权而无法及时实现,保证刑罚权正确实施,保证让无罪的人不受牵连,让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当今社会,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不能偏废,两者辩证统一,不管少了哪一半,另一半都不能得到最好地实现。正是依靠不断地平衡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大价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才能经久不衰且充满活力。
六、关于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时间较晚,规定较为简略,发展并不完善,没能很好地实现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大价值的平衡。我国封建时期时间极为漫长,法治化思想并不完善,自古看重口供的传统和社会法治意识的淡薄导致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现象屡禁不止、时有发生。从近几年的冤假错案情况来看,赵作海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无一不存在着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身影,同时也都是因为证据疑点重重,诸位被告人均由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进而为日后翻案赢得了机会。鉴于刑讯逼供、违法取证仍然屡禁不止,人权保护工作形势严峻的社会现实,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程序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完善:
第一,立法层面,鉴于非法取证大多侵犯的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建议全国人大在宪法及相关基本法律中增加有关内容,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从立法层面提高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
第二,具体制度方面,我国应该详细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原则性的表述,详细规定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物证的排除规则,提高非法证据适用例外的标准。
第三,启动程序方面,依据我国目前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动议可以由公诉人、法官以及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但是依照目前实践情况来看,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动议权很难得到保障,建议庭审前单独设立一个庭前审,专门用来对于非法证据的审查,以此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同时进行非法证据审查的法官应不同于主持庭审的法官,以此保障审查和审判的公正性。
第四,审查时间方面,根据目前的规定,庭审之前的非法证据审查工作是由检察院负责,但是检察院也是侦查和公诉部门,如此安排的结果势必导致庭审前的非法证据审查形同虚设,笔者建议,非法证据的审查工作应该贯穿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并且庭审前的审查工作不应只由检察院独力承担,建议建立犯罪嫌疑人受询问时律师在场的制度,完善犯罪嫌疑人受询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且考虑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唯有这样才能保证“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的法定权利得以实现。
第五,惩戒制度方面,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涵盖了程序启动、动议主体、排除规范等各方面,但是唯独缺少了惩戒制度,没有惩戒的法律不能称之为完善的法律,对于国家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我们必须要确立严格有效的惩戒制度,使违法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较为严重的不利后果。目前,除了违法证据原则上不被采纳外,还应让违法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即使是可以被补正的非法实物证据,其采集人员亦应承担法律责任,以便彻底打消国家机关工作人非法取证的诱因。
第六,证人出庭作证方面,建议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针对我国目前证人出庭率偏低的现实状况,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经济、安全方面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切实严格执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这不仅仅是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的要求,也是诉讼参与人相互质证的需要,这样也更有利于及时发现非法言词证据,纠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
第七,律师方面,建议强化律师的监督、辩护、建议、会见等各方面的权利,使其可以充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利,使律师队伍成为证据收集合法化的强力监督者和法治建设的强力推动者,可参照美国等发达法治国家的做法,另律师可以出现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且法定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
第八,证明责任方面,建议加大侦查、起诉部门对于证据来源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不再只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提出证据来源合法化的证明,而是在每次庭审之前关于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庭前审中主动提交每项证据的来源合法性证明,以此来保证证据来源的合法性。
第九,监督机制方面,建议仍然要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使其足以不屈服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唯有完善的立法和独立的司法才是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真正的实现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的两大永恒价值,若不能实现这两大价值的平衡,那么无论法条制定的再如何科学详尽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国法治化进程起步较晚,立法水平相对落后,法制体系不尽完善,对于诸多法律价值的平衡与兼顾都未能做到尽如人意,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忽视近年来我们立法工作所取得的艰辛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非起源于我国,但是面对这一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理应借鉴相关国家的成熟做法,不断完善我国相关之不合理规定,通过不断地进步与完善,来达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这两大价值的平衡,进而达到推动我国法治事业和人权事业建设发展的最终效果。
[1]谢安平,郭华.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214-215.
[2]张英霞.刑事证据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3.
[3][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10.
[4]汪建成.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J].环球法律评论,2006(5):551-556.
[5]李步云,徐炳.试论我国罪犯在法律上的地位[N].人民日报, 1979-10-31(4).李步云.走向法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488-492.
[6]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2-123.
[7][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43.
[8][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94-195.
[9]杨宇冠.“毒树之果”理论在美国的运用[J].人民检察,2002 (7):57-59.
[10]张丽卿.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0:298-301.
[11][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册)[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
On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in View of the Balance between Combating Crimes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Mou Ruijin,Duan X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04)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re combating crimes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must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tasks.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refers to illegal physical and testimonial evidence,each of which entails different applicable standards,but serves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combating crimes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For the late establishment in China,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hasn’t been fully developed.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especially on the perfection of legislation, starting program,investigation period,cross-examine witness testimony,related personnel responsibility and several other aspects,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in China will get a qualitative leap and development.
combating crimes;protecting human rights;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DF731.3,DF48
A
1671-5101(2014)03-0001-06
(责任编辑:陶政)
2014-03-25
牟瑞瑾(1964-),女,辽宁丹东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法学、司法与人权。段旭(1990-),男,山东淄博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2013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以《警察法》的修改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