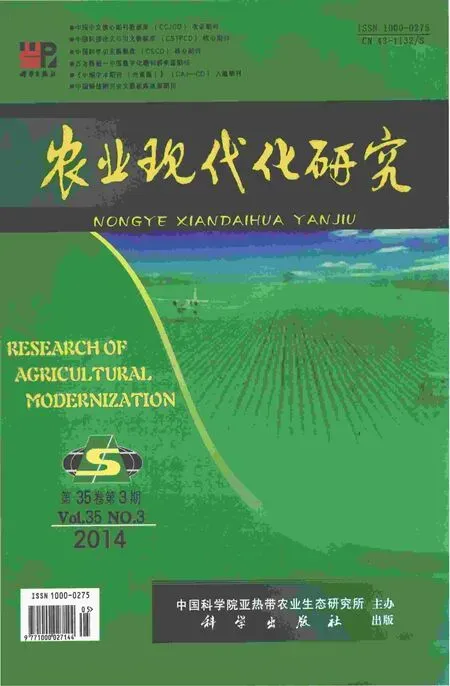灾害风险视域下避灾移民的迁移机理与现状及对策
何得桂 ,鄢 闻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陕西杨凌712100;2.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频率高、强度大、危害程度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其突发性、预测难度大的特点,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所引发的大规模灾害型移民(从时间节点上看,灾害发生后开展的移民活动通常称为“灾害移民”,而在灾害尚未发生之前主动规避灾害风险的移民活动属“避灾移民”的范畴。这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将它们统称为灾害型移民)愈来愈成为风险社会需要直面和应对的一道发展难题。在灾害仍无法有效规避的情况下,避灾移民搬迁的选址规划、资金来源、移民政策执行、生计发展与社会融入等一系列避灾移民安置和后续发展问题考验着现代公共部门的管理智慧。如何有效化解灾害风险、促进移民工程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各类移民工程的持续开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分析现有避灾移民工程实施状况,探寻避灾移民迁移的内在机理,为我国避灾移民工程提供理论援助和政策支持,既可为科学应对灾害风险提供有效根据,也有助于避灾移民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纵观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在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势下,Myers等的气候移民规模预测,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认可[1];施国庆等的适应气候、减缓气候变化观点,也充分表达积极探索气候移民的政策、途径以及进行有组织移民的必要性[2]。随着制度变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次生灾害,有学者发现,草原正面临着严重退化,随着牧民定居、草原分割和市场化,草原社区面对干旱呈现出严重的脆弱性,而这又加重了干旱的影响[3]。由于近年来自然灾害增多,与气候变化综合形成的泥石流、滑坡、洪涝等灾害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移民的主要动因。有学者发掘出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活动中的社会排斥机制[4],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和后续生计问题是避灾移民工程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逐渐增加,有学者基于风险视角的研究发现气候移民的迁移机理,总结现有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5]。这些已有研究均从科学客观的视野,根据特定的灾害风险对开展移民搬迁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操作性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充分论证,对本项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但是在以下方面还需加强:从研究对象上看,已有研究对生态移民、气候移民、工程移民等方面探讨的较多,而对于灾害型移民,特别是避灾移民的研究略显不足;从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尽管考察了灾害型移民与政策执行、移民可持续生计以及基本现状与深化路径等,但尚未有效揭示灾害型移民的内在机理与发展态势,研究内容有待丰富;从研究视野上,已有研究探讨了例如各类移民工程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还缺乏从灾害风险的视角进行系统论述,研究视野要进一步拓展。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灾害风险的视野对避灾移民迁移机理、基本现状与推进路径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深化灾害型移民研究,促进有关公共政策发展。
1 灾害风险的内涵与避灾移民搬迁的影响
1.1 灾害风险的基本内涵
不同学科对于由自然变化的不可抗力带来的灾害风险的内涵界定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自然灾害风险是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达到的灾害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自然灾害的危险性、暴露、承灾体的脆弱性或易碎性以及防灾减灾等多个因素相互综合作用形成区域灾害风险[6];通过对国际风险研究,有学者从灾害系统理论分析了概率条件、致灾因子两者是综合影响灾害风险的重要因素[7]。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风险研究不断深入,风险的概念一直被认为与概率和影响强度有密切关联,而纵观灾害学体系,随着灾害风险是“灾害活动及其对人类生命财产破坏的可能性”这一基本认识被普遍接受,科学定量分析不断发展和完善,灾害风险逐渐被认可为有害事件发生概率与发生后果的乘积:R(风险)=P(概率)×C(可能灾情)
灾害作为不确定事件以其可能发生的概率以及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带来的无法预知后果的严重程度,综合成为风险不可预知性的表现和反映。但结合实际情况,现实中存在扩大灾害本身危害的潜在干扰因素,承灾体的脆弱性、暴露情况、管理工作等时时刻刻影响着可能发生灾情的严重程度,影响因素多、潜在风险大,使得我们对灾害风险的认识和定义在提炼归结的基础上,要考虑更多的干扰因素。本文综合分析影响灾害风险的各种因素,认为灾害风险的认识应介入防灾减灾能力,用受灾体脆弱性的大小这一定量指标来表示不同程度的应对能力,将灾害风险表示为:风险(R)=概率(P)×脆弱性(V)
1.2 灾害风险与避灾移民
自然环境变化和气候的更替使得人类面临诸多考验和威胁。有学者发现,全球变暖等环境变化引致的诸如干旱、暴雨等异常天气的发生频率在增加,全球化过程引致各种灾害风险在全世界的扩散在增强,防范与科学应对已迫在眉睫[8]。地质灾害与异常天气,成为中国近几年威胁人类正常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据统计,2012年我国自然灾害受灾人口29,421.7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2496.20万hm2;2011年因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60亿元,因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28亿元,同比增长22.6%。一方面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威胁着现有生存境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存在大量易受破坏、环境恶劣、居住条件差的不适宜居住区也在加大灾害风险的可能性。未来自然环境状况和人类生活境况的不确定性表明化解不确定性,变被动为主动才是势在必行的科学之道。
在频发地质灾害和气候异常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我国重度干旱、毁灭性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呈迅速上升趋势。既危害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也逐渐摧毁赖以生存的家园。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受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不适宜居住区和环境恶劣地段在逐年扩大,政府不得不通过生态移民逐渐寻找新的居住地。受山洪、泥石流等严重影响的陕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导致陕西省政府从2011年开始对其展开大规模避灾移民搬迁工程,实现“挖险根”和“除穷根”的目的。随着避灾搬迁实践的不断深入,被动承受大自然灾害风险的传统做法逐渐失去其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而灾害风险的本身内涵也不可避免显示出受灾主体的脆弱性对灾害风险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增强潜在受灾主体的承受能力,科学应对和规避灾害风险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开发利用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保护养育原有家园日益成为规避风险的有效方式。当然,灾害多发性和难预测性带来资源减少等隐患,可适宜居住区的科学利用也将面临挑战。
2 避灾移民搬迁的形成机理
灾害是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二者综合而产生的能对人类赖以生存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的总称,而为避免或应对它的影响,灾害型移民由此产生。换言之,灾害移民是因自然灾害因素、社会灾害因素等胁迫导致的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重建活动[9]。自然灾害是人地耦合系统失衡的表现,灾害移民是在灾害因素诱导下产生的一种人口被迫迁移。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在逐渐适应自然发展规律,寻求和谐共处的生存之道,主要表现为受灾害风险胁迫下的科学防范与规避。
2.1 自然灾害与原始型人口迁移
环境变化在促使增强自身适应能力的同时,人类也不断地进行移动或辗转迁徙,即所谓由生态推动的原始型迁移(Primitivemigration)[10]。作为原始型迁移的灾害移民是人类面临自然灾害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和重要的一项生存策略[11]。受地区承载能力和抗灾水平的影响,人类逐渐通过对居住区生态条件的科学分析,将搬离不适宜区、开拓新家园作为新的应对大自然灾害风险的新方法,彻底摆脱任由自然主宰的命运,这种原始意义上的人口迁移更彰显出在大自然威胁下人类生存的智慧。
自然灾害的增加使得初始居住地在本身脆弱性较强的基础上显得更加不堪一击。据统计资料显示,2011-2012年我国因各种自然灾害引致的受灾人口达7万人次,严重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也破坏了居住区的可持续性。以陕西南部为例,受秦巴山区地质复杂、山区岩体较松的影响,加之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夏季强降水易发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每年因河道堵塞、排水不畅、居住区危险系数大等原因导致的死亡事件逐年上升,为彻底解决居民的安全隐患,2011年5月正式启动实施政府主导下的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通过移民搬迁,它已使受灾害胁迫的数十万山区居民摆脱了恶劣的人居环境,同时还促进当地城镇化快速发展,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应。2001年底,宁夏自治区共计搬迁安置4.42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后共计有15.7万人进行了异地移民搬迁[12]。这些受自然灾害影响的能动性搬迁不仅在短时间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生活水平较搬迁前也得到普遍改善。寻找新的适宜居住区,保护危险性地区的生态环境,恢复土地原始承载能力,为新生活持续发展扫除了后顾之忧。在意识到自身承灾能力差,不能循环往复进行以往的“受灾—救灾—受灾”模式后,主动测量当地承载能力、生态情况进行灾害预测,寻找可持续的生存之道为人类更好应对灾害风险变化与胁迫提供了可贵经验和有益教训。
2.2 社会灾害与驱动型人口迁移
由政治、文化、经济的变动所带来的灾害统称为社会灾害。社会人口、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是导致我国社会灾害脆弱性的3个主要因素,社会保障、医疗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也是决定社会灾害脆弱性的重要因素[13]。鉴于社会灾害更倾向于是制度政策设计和安排的不合理、指导思想的错误而带来重大的人为型灾害,“它具有自觉地能动性、最初时感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3个重要特征”[14]。
我国历史上因社会、政治等问题导致的为避免引发社会灾害而进行的移民不计其数。20世纪初,受自然灾害多发、经济困顿、生活窘迫的现实情况逼迫,一大批山东人开启了“闯关东”移民活动,这种“经济型”移民之后带动诸如“走西口”等大规模人口流动,逐渐成为当时躲避社会灾害、寻求新生活的主要方式。“九·一八”事变之后,由关内迁入的移民大幅度减少,但“七七”事变后山东沦为战场,难民又大部分涌向东北。这种政治型移民在战乱期间数量激增。“文化大革命”使一部分人受歧视迫害,为躲避政治变动,70年代后期大陆向香港的合法移民超过7万人。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成熟、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在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成为主要方式,社会灾害移民日渐减少。社会灾害带来的后果往往不易察觉和测量,但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会对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无论是政治型移民还是经济型移民,都是在受到一定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下而被驱动的移民活动,在面临社会灾害有可能带来的风险面前仍是有效防范和规避的重要手段。
3 避灾型移民搬迁的现状与趋势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呈多发、破坏性大的总体特征。它的科学预测与防范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变动的能力还有待提高。通常情势下,“受灾—重建—再受灾—再重建”的循环模式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随着社会发展,推进避灾移民搬迁工程作为可持续避灾方式逐渐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可。
3.1 整体性规划与集体性搬迁
避灾移民搬迁工程的主体是某一个地区所有因受灾害胁迫而无法继续生活的群体居民。当受灾地区生态破碎,无法再适宜人居住时,就要寻找规划新的居住区以供人类长期繁衍。例如,江西作为全国12个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地质灾害危害严重的省份之一,2011年以来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进避灾移民搬迁活动。最为典型的区域性重大避灾移民工程是:陕南地区2010年7月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至少夺走187条山区居民的生命,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重大自然灾害等因素对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陕西省计划在2011—2020年间对陕南地区3市28个县(区)居住在受灾害胁迫和交通不便山区中的60万户240万人进行区域内的大规模避灾型移民活动。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计划投资1000多亿元,移民搬迁类型涉及地质灾害移民、洪涝灾害移民等多种避灾移民搬迁。需要搬迁的村庄都予以纳入并全部进行移民搬迁。这些移民工程均以特定受灾或存在潜在灾害风险的地区为搬迁对象,政府统一规划搬迁方案,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在有效解决潜在问题、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原有社会结构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3.2 就近选址与异地搬迁相结合
移民工程搬迁地的选址规划在分析各种地理位置、生态状况等因素的同时,搬迁人数规模、资金的支配、社会融入情况等因素也不可忽略。现有移民搬迁工程,安置点选择主要有就近选址安置和异地搬迁两类,而这两种不同的避灾方式均是在仔细考虑搬迁工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决定的。不同地区根据受灾的程度、地质地貌的完整程度、生态的可恢复性以及民众的搬迁意愿、社会结构等因素综合考虑来决定避灾的主要方式,有效避免移民搬迁后有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例如,贵州省长顺县的南部因地处麻山地区,环境恶劣不适宜人居,地方政府通过开展移民移民搬迁,使他们迁移到条件较为优越的北部地区。而在陕南地质灾害多发区域,政府则将长期居住于山沟、山坡上等易受滑坡、泥石流灾害威胁的居民就近安置,在地势平坦、远离危险的地带建立避灾移民搬迁安置区,从而较为完整的保持了居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受土地资源等因素制约,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受人地关系紧张以及环境资源承载力有限的制约,也采取一定数量的异地搬迁安置方式,主要有跨乡镇、跨县域之间的移民搬迁活动,通过建立可吸收容纳周边多个乡镇或县域的避灾移民搬迁安置区以及鼓励搬迁户“进城”落户等方式促进异地搬迁。此外,它通过以集中安置为主,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确保避灾移民搬迁活动取得更大成效。
3.3 长期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避灾移民从开始的选址规划到最后的融入新环境,整体上呈现出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为科学规划移民工程和制定公共政策,初期评估迁入地的生态情况以及未来的社会发展情况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项目开发、资源配置、搬迁工作、后续配套安排无不是这个庞大系统中的重要环节。例如,甘肃、宁夏等地经过多年努力基本完成避灾搬迁工程;陕西省计划用十年时间分阶段式的将处于危险区的居民迁入适宜居住区,同时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搬迁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总体目标。避灾移民是把双刃剑,它在有效规避灾害风险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新的生活体系难以有效建立,社会融入度低等问题依旧是避灾移民工程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将系统性的观念贯穿始终,综合考虑所有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才是保持避灾移民工作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3.4 再次移民的或然性增大
灾害型移民是规避灾害风险的有效途径。对移民而言,彻底摆脱了担着风险过日子的生活,迎来新的生活契机。但移民工程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移民过程是一个使他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生产生活环境去适应陌生发展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物质财富、社会资源等将会受到显著损失和影响,而且其世代传承的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出现被遗弃到社会角落或消失的危险[15]。而当移民发现新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结构与自己格格不入或完全无法适应时,他们则会回到故土或者再次寻找新的移民点。对于搬回原来居住点的移民,公共部门基于社会公益和行政责任会对返迁的移民实施再次搬迁,灾害型移民于是呈现出“移民—返迁—再移民—再返迁”的往复性特征。另外,对于想再次寻找新的移民点的人来说,搬离最初灾害多发的风险区域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随着他们适应能力的提高和对条件更好的居住区追求,再次搬迁的或然性就大大提高。
4 应对灾害型移民及相关问题的路径选择
包括避灾移民内在的灾害型移民在国内外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伴随灾害变化异常概率的逐渐增大,避灾移民搬迁在其预测、规划、选址方面还存在不小的挑战。避灾搬迁科学化、系统化逐渐发展提升,灾害风险的预测分析成为移民工程规划考虑决策的关键因素,灾害风险中的致灾因子和脆弱性决定了科学预测防范灾害以及加强搬迁科学选址、寻找适宜居住区的重要性。
4.1 完善灾害风险预测和防范体系
“灾后治理”通常是以往应对灾害的主要方式,受灾体的脆弱性这一影响因素大都被忽略。灾害发生的风险可控性、预测性差,随着全球灾害发生频次增加,如何降低灾害风险成为科学管理的主要内容,即通过采取各种减灾行动及改善运行能力的计划降低灾害事件的风险,对灾害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16],最终把风险减至最低的过程。建立风险防范体系最终旨在减少或避免被迫的大规模人口避灾流动,以有效的预测和防范措施保证居住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周洪建认为中国要统筹考虑地区适应自然灾害的能力,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探讨积极的灾害移民方案,变“因灾移民”为“因险移民”[17]。
4.2 增强灾害多发区的承灾能力
在“建立适应辖区各种自然灾害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利用格局与产业结构,则是从根本上降低灾害风险的长远之策”认识的基础上,结合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受灾体的脆弱性2个主导因素对症下药。通过提高备灾能力以降低受灾体的脆弱性,提高社会救助能力以加快受灾体的恢复能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辖区的自然特征来达到提前预防和规避灾害风险,提高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终目的。陕南山区避灾移民搬迁进程中不仅要着眼于“搬得出”,还要注重和加强避灾移民搬迁户的社会保障,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进而增强抗风险能力。
4.3 提升灾害型移民的公共服务
灾害型移民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正常运行离不开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为确保移民工程的效用,要借鉴和运用社会脆弱性理论资源开展避灾移民安置点的规划选择,优先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升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这可降低灾害型移民搬迁的社会脆弱性,避免为后续发展留下“移民返流”等隐患。为避免搬迁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搬迁规划时移民的搬迁意愿、社会融入程度、安置点社会结构等因素都要被充分考虑,而在解决移民带来的后续诸如生计发展等方面政府应该设立完善的保障体系,在基本的搬迁保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进一步增强避灾搬迁的内在价值。
4.4 完善移民保护和发展政策法规
任何一项工程都离不开全局性调控和系统性协调。在当今灾害多发的风险社会环境下,避灾移民作为灾害风险的有效规避方式应得到规范化、体系化的政策保护。按照避灾移民的普遍性规律完善移民活动的法规和制度,为科学有效进行防灾减灾提供发展空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的避灾移民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所隐藏的潜在社会问题要引起重视。移民社会融入度不高、搬迁后生计问题解决难等均暴露出移民政策在解决后续问题系统上的缺失,而统筹全局、综合调控的系统性规划正是保障各项环节顺利完整进行的保障。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类似《避灾移民搬迁条例》等法规,提高政策执行力。加强对移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和生活境况的关注度,注重后期生存质量改善才是灾害风险下避灾搬迁的真正内涵。
5 结语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都时刻威胁着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的生存状态,虽然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消失殆尽,但仅有的科学技术也使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未知灾害风险。灾害型移民,特别是避灾移民作为积极应对灾害风险而形成的科学防范手段,有其选择的必然性。在有效改变恶劣的人居环境,改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等缺陷,有关避灾移民的科学研究与应对体系仍需发展,移民实践中的观念、方法和路径还需完善。未来随着国际社会对灾害风险、气候变化的关注,全球性灾害问题及其影响带来的避灾移民将不断增加,有关灾害风险管理、风险防范以及避灾移民等的深入研究或将进一步提高应对灾害风险的智慧、能力和手段。
[1]Myers N.Environmental Refugees:An Emergent Security Issue[C].13th ed Economic Forum,Prague,2005(5):73-79.
[2]ShiGuoqing,etal.Ready forClimateChangeRelated to Immigration[J].Science,2011,10(334):89-94.
[3]王晓毅.制度变迁背景下的草原干旱——牧民定居、草原碎片和牧区市场化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4.
[4]何得桂,党国英.陕南避灾移民搬迁中的社会排斥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2,35(12):163-168.
[5]曹志杰,陈绍军.气候风险视域下气候移民的迁移机理、现状与对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1):45-50.
[6]张继权,[日]冈田宪夫,多多纳裕一.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自然灾害学报,2006(01):29-37.
[7]施国庆,郑瑞强,周建.灾害移民的特征、分类及若干问题[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0-24.
[8]殷杰,尹占娥,许世远,等.灾害风险理论与风险管理方法研究[J].灾害学,2009(02):7-11.
[9]史培军,邵利铎,赵智国,等.论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模式——寻求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性对策[J].地学前缘,2007(6):43-53.
[10]Petersen,W.A generaltypologyofmigr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8(23):256-265.
[11]Hugo,G.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internationalmigration[J].InternationalMigration Review,1996,30(1):105-131
[12]刘 颖.避灾移民社会风险评价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3]葛灵灵,易立新.中国社会灾害脆弱性评价指标设计[J].安全,2011(5):1-4.
[14]姜超,赵华朋.社会工程视野下“社会灾害”的研究[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34-36.
[15]World CommissiononDams.Damsand CulturalHeritageManagement FinalReport[R].Beijing:DevelopmentCenterofStateCouncil,2000:8.
[16]Wilhite,Donald A,Hayes,M J,Knutson,Cody L,Smith KH.Planning for drought from crisis to riskmanagement[J].Journalof the AmericanWaterResourcesAssociation,2000,36(4):697-710.
[17]周洪建.灾害移民的未来动向:从“因灾移民”到“因险移民”[J].中国减灾,2011(21):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