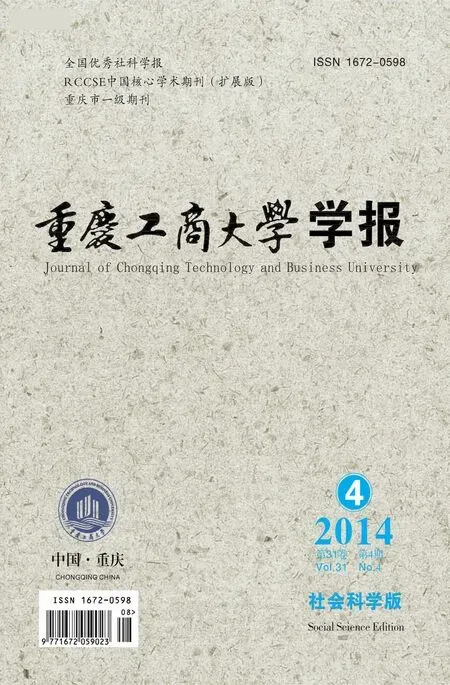巴赞纪实主义电影理论及其论述逻辑*
王家东
(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作为纪实主义电影美学的理论大师,安德烈·巴赞的理论通常被认为包括“电影影像本体论”与“电影语言进化论”两大部分。其论文集的名称《电影是什么?》是一个设问,而这两大理论部分实际上都是对这一设问的回答。“电影影像本体论”是对此问题的本体探讨;“电影语言进化论”是在其独特本体论的前提下的一个史学体系,[1]67一方面建构电影发展史中的电影语言进化论,另一方面这种语言进化论实际是这种本体论的体现,又构成了本体论自身。这个史学体系在研究电影语言的演化变革中,更多的指向其所认同的“景深镜头”理论,是其理论的落脚点,既是电影影像本体的体现,也是维护这种本体的电影语言手段。
巴赞的理论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其理论论述的完整构思性与系统性可能稍显不足,但是巴赞的电影理论内部却有着严密的论述逻辑。美国电影理论家尼克布朗评价巴赞:“论著作为一个整体,其主要倾向和主要活力在于批评方面和史学方面。巴赞思想体系之所以如此严密和如此有趣,是其复杂的美学立论、史学观和本体论信念加在一起的结果。”[1]68下面我们将结合巴赞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完整电影”的神话》以及《电影语言的演进》三篇文章详细论述巴赞的理论及其论述的逻辑框架。
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是由两篇文章《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完整电影”的神话》共同建构的,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1945年与1946年,虽不是整体构思的结果,却共同构成了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的逻辑框架。对于这两篇文章所构成的论述逻辑,我们大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造型艺术产生的心理学根源
巴赞对电影影像本体的论述基础是所有的艺术(尤其是造型艺术)的共通性起源。他把所有的艺术的共同起源视为人类的“木乃伊情结”。木乃伊可以视为古埃及的第一个雕像,从根本上讲是人类保存生命的本能的体现,“复制外形以保存生命”的心理动机成为众多造型艺术创作的因缘。
精神分析法追溯绘画与雕刻的起源时,大概会找到木乃伊“情意综”。古代埃及宗教宣扬以生抗死,它认为,肉体不腐则生命犹存。因此,这种宗教迎合了人类心理的基本要求:与时间相抗衡。因为死亡无非是时间赢得了胜利。人为地把人体外形保存下来就意味着从时间长河中攫住生灵,使其永生。妥善保存死者骨肉的完整外形,这曾经是天经地义的事。[2]6
从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出发,艺术摆脱了巫术,就成为人类想要降服时间以求不朽的本能在文明进步时代的一种升华,虽然生命延续的巫的意味淡去,但是其中依然有着深刻的“用形式的永恒克服岁月流逝的原始需要”[2]7。在巴赞的论述中,摄影与电影不过是造型艺术的延续,他们同样集成了造型艺术产生的心理学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的保存延续生命的动机的一种延续、一种完善,其根本上也是木乃伊情结的一种体现。电影从本源上看即是要创立一个符合现实原貌的理想的世界。从艺术起源的复制外形的心理学原因来说,艺术所要求的是写实,而且越像真实越好,电影也是这样。这是巴赞理论的第一点。
(二)绘画的矛盾与照相术产生的现实动因
巴赞并没将自己的论述仅仅停留在对电影起源的追根溯源的心理学的描述中,因为仅仅是木乃伊情结的观点并不能解释后世造型艺术以及电影艺术发展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解释绘画中存在的非写实的象征主义的问题。巴赞在其文章中进一步论述,摄影术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从造型艺术中发展而来的,其具体的现实动因又是什么。
《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最初发表在《绘画问题论集》上,这篇文章也可以视作一篇造型艺术史的论述。在论述了造型艺术产生的木乃伊情结之后,巴赞详细论述了绘画世界中所存在的形式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之间的冲突:
从此,绘画便在两种追求之间徘徊:一种属于纯美学范畴——表现精神的实在,在那里,形式的象征含义超越了被描绘的原形;而另一种追求是仅仅用逼真的摹拟品替代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这种追求幻象的要求一旦有所满足,便愈益强烈,以至于逐渐吞噬了造型艺术。[2]8
绘画世界中的这种矛盾,一方面是因为绘画想要虔诚于其产生的写实的木乃伊情结,这就产生了绘画中重要的写实技巧——透视法;另一方面,在绘画中表现精神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这就需要超越“透视法”的束缚,透视法就成为西方绘画艺术的原罪。造型艺术的发展急需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来承担绘画的写实主义的功能,照相术应时代要求而生。
这便是照相术产生的具体背景。照相术的产生,起到解放绘画的作用。“照相术既完成了巴洛克艺术的夙愿,也把造型艺术从追求形似的困扰中解放出来。”[2]10照相术与电影是造型艺术的延续,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写实主义的延续。照相术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造型艺术中写实主义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有了新的传承的力量,有了更好的表现手段,绘画也终于可以从木乃伊情结,从透视法的原罪中解放出来,去表现精神的、形式的、象征主义的东西了。
因而照相术的产生是在现实主义的呼唤下,造型艺术分化的结果,其最重要的作用便是继承造型艺术的写实主义传统。这是巴赞理论的第二点。
(三)摄影与绘画的区别以及摄影的美学优势
无论是电影产生的心理学根源,还是电影产生的现实需求,纪实性都是其重要的依据。巴赞进一步论述,摄影术的某些先天优势使得摄影术成为继承写实主义传统的最主要的艺术样式:
所以,从巴洛克风格的绘画过渡到照相术,这里最本质的现象并不是单纯器材的完善(摄影在模仿色彩方面还远不及绘画),而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欲望。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结果,而在于生成方式。[2]10
摄影创作,是完全依托于机械的复制,摄影的写实就具有了绘画写实无法到达的高度。摄影在客观性方面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
因此,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况且,作为摄影机的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而它们的名称就叫objectif。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2]11
摄影的这种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令人信服的魅力,这种技术的客观性使得我们更相信其所表现的对象是没有经过人为干预的真实对象;而绘画艺术无论其对现实表现得有多么真实,都因为其是以人为参与为基础的,在客观性方面,自然就没有摄影那么有力度。所以绘画对真实的表现只能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技巧,是复制手段的一种替代品。电影以其技术真实确保了对现实的尊重,电影的复制手段不仅是表现真实,更可以说电影就是真实本身。这是巴赞立论的第三点。
(四)完整电影的神话
以上的论述都是在文章《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完成的。巴赞从造型艺术的起源到照相术与电影的产生再到电影技术真实的优势三个方面,逐渐深入论述了:电影艺术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以上对电影艺术纪实美学本性的论述其实都集中于电影史中的前史阶段,所论述更多是电影产生之前的,作为电影先河的造型艺术以及摄影艺术。在《“完整电影”的神话》中,巴赞进一步结合电影的产生过程,说明在电影产生之初便已经包含着众多的写实因素,并且这些写实因素与现实一样是完整呈现在电影中的。
在起步尚难的物质条件下,大多数电影事业的先驱者便超越了各个阶段,直接瞄准较高的目标。在他们的想象中,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景。[2]19
在巴赞看来,电影中关于构成真实的所有必要的构成要素,如动作、声音、色彩,并不是电影发展史所呈现给我们的那样一步一步地进入电影中的,而是在电影产生之初,理论家对电影的设想中,便已经包含了如上的所有的因素,这便是所谓的“完整电影”的神话。从摄影术发展到电影术本身就是从静止的真实向运动的真实的跳跃。在声音与色彩还没有进入电影之前,早期的电影家们就已经尝试在自己的电影中增加进声音与色彩的因素,以便使其更像现实生活本身。而电影之所以在产生的早期并不具有完整电影神话的所有要素,纯粹是因为技术上的力不从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时人的观念中,没有以上的因素。
巴赞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上有着与爱因海姆完全不同的观点。作为一个早期电影理论家,爱因海姆的理论贡献更多集中在“电影作为一门艺术”。针对当时有人批判“电影是生活的再现,所以不是艺术”的偏见,爱因海姆对比了现实与电影艺术的不同,指出相对现实,电影所反映的是部分幻觉,但是观众可以依据格式塔架构完整的现实。“我力求详尽的证明:使得照相和电影不能完美的重现现实的那些特征,正是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一种艺术手段的必要条件。”[3]3电影之所以是艺术正是来源于电影技术的这种不足,因而爱因海姆公开反对所有使得电影更加逼真反映真实的技术进步,反对有声片,反对彩色电影。巴赞的不同,是时代的进步。在巴赞的时代,对于电影是一门艺术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这是电影艺术观的一种进步。
从整体来说,巴赞对电影真实与现实真实关系的论述是其理论的重要出发点。电影同其他艺术一样,是人类木乃伊情结的体现;其产生的现实说明其直接继承了绘画中的写实主义的风格;其技术真实确保其成为再现真实,体现真实客观性的最好载体;而在电影产生之前关于电影的设想都是一种“完整电影”的神话。以上四个论点,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奠定了其纪实主义的电影美学风格。
二、电影语言演进的史学框架
如果说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可以被看做是对造型艺术发展史的论述,那么巴赞的“电影语言进化论”,则是一个标准的电影史的论述。其在文章《电影语言的演进》中,巴赞详细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演进不是断裂的,任何一种电影美学观念总是有一种电影的语言形式与之相对应;长镜头的场面调度理论是电影语言发展的必然,也可以看成是电影语言的最高形式等。
在巴赞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在电影史的任一阶段,无论电影语言呈现怎么样一种封闭的特征,在具体的电影创作中,总是有纪实主义的作品存在。随着电影史的发展,纪实主义的因素被不断的发扬光大,最终构成了完整电影的形式。电影史发展的每个阶段总会有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使得电影离现实更进一步。
(一)无声电影时期的流派与语言形式
在巴赞那里,1920—1940年间的电影被分为对立的两种倾向,“相信画面”以及“相信真实”。在巴赞看来,所谓画面指的是“被摄物体再现于银幕时一切新增的东西,又可以分为画面的造型以及蒙太奇的手法”。[2]64造型,指布景与化妆的风格、表演风格、灯光以及构图等因素。至于蒙太奇,主要是源于格里菲斯镜头的组接方式,镜头的连接原则是按照一场戏的“实际逻辑”与“戏剧性逻辑”来分解事件。“无论是画面的造型内容还是各种蒙太奇手法,它们都是帮助电影用各种方法诠释再现的事件,并强加给观众。”[2]66巴赞又进一步把蒙太奇分为“平行蒙太奇”“加速蒙太奇”“杂耍蒙太奇”,而格里菲斯的作品显然是平行蒙太奇的代表,阿贝尔·冈斯的影片《车轮》体现了加速蒙太奇,爱森斯坦所开创的是杂耍蒙太奇。
在巴赞看来,“加速蒙太奇”与“杂耍蒙太奇”的形式绝对不是对事件的展示,而是对事件的暗示,影片意义的获得依靠的是所构成的元素而不是这些构成元素自身的客观内容,单个元素的内容不具有决定作用,叙事的内容从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之中产生,任何一个元素都有可能在关系中产生一种新的未预先包含的含义。
所谓相信真实是指那些作品中,蒙太奇只是起到必要的剪辑的消极作用,除此之外并不起任何作用的其他电影类型。这以弗拉哈迪、茂瑙、斯特劳亨等导演的作品为代表。
在默片兴盛时期就存在着和人们心目中典型的电影艺术截然相反的一种电影艺术,证明有一种语言,它的语义和句法单位绝不是镜头,在那里,画面首先不是为了给现实增添什么内容,而是为了揭示现实真相。[2]69
巴赞对早期电影的这两种流派的分析,其落脚点在电影中的声音在于电影的意义上。针对通常观念:没有声音的默片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声音的进入破坏了无声电影原有的完整性。巴赞以一直以来存在的相信真实的电影传统申辩:“无声电影实际是一种缺陷:现实中缺少了一个元素。”[2]69声音进入电影不是一种破坏而是使电影向现实更进一步。
(二)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电影语言
瓦解了无声电影的美学统一性后,巴赞进一步审视了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电影发展史。声音进入电影后,以经典好莱坞影片为代表,电影语言中形成了世界通用的表现手法,这些影片在内容与形式上呈现出某种独特的属性——类型。影片的分镜头形式也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库里肖夫实验在新的语言机制之下也会有新的表现形式,其对空间真实性的把握,对戏剧性与心理方面的考虑也是无声电影时期所没有的。而有声画面的组接进一步限制了电影中1920年代先锋派电影的造型性与苏联蒙太奇学派的“杂耍蒙太奇”的影响。“有声的画面不像视觉的画面那样容易随意处理,这就使蒙太奇向真实性方向发展,而愈来愈排除造型的表现主义和镜头之间的象征性关系。”[2]75
在电影发展的前声音阶段,巴赞以声音作为电影能否反映真实的重要标尺,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电影的语言像无声电影时期一样,又一次的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相对于默片时期,这种语言已经很大程度上靠近真实,进一步的排除“相信画面”的因素。但是在巴赞看来依然可能有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更靠近现实的电影语言存在,这种新的电影语言相对于有声片时期的经典电影语言离现实又靠近了一步。此时,被巴赞拿来作为标尺的就是电影的“景深”。
在1930年代,因为感光技术的革新,摄影机可以以小的光圈进行拍摄,从而使得电影的景深镜头成为了新的可能。技术的革新为新的电影语言的产生排除了障碍,下面所需要的实际是依托这样一种方法的独特的电影创作思维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是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以及导演威廉·惠特的作品,在他们的电影中所广泛采用的景深镜头对后世的电影创作尤其是纪实主义的电影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景深镜头理论
在通常的论述中,“景深镜头”理论、“长镜头”理论、“场面调度”理论,虽有所区别,但其指涉基本统一,都是与蒙太奇相对立的强调纪实的电影美学理论。实际上,巴赞的景深镜头理论并不排斥蒙太奇,蒙太奇带给电影语言决定性的进步应该是公认的,但是景深镜头的使用使得电影离现实又进了一步。景深镜头不仅影响着电影语言的结构,也影响着电影与观众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给观众更为客观、真实的感觉。
第一,景深镜头使观众与画面的关系比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更为贴近。因此,可以说,不论画面本身内容如何,画面的结构就更具真实性。[2]77-78
景深镜头是整体的,没有经过分割的镜头,镜头内部的因素都是非孤立的,是一个整体,因而所传递出来的真实感则更加强烈。这种画面的呈现形式自身就极具真实性。
第二,景深镜头要求观众更积极地思考,甚至要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场面调度。倘若采用分解性蒙太奇,观众只需跟着导演走,他们的注意力随着导演的注意力而转移,导演替观众选择必看的内容,观众个人的选择余地微乎其微。画面的含义部分地取决于导演的注意点和意图。[2]78
如果说蒙太奇依靠镜头的切换来引导观众的不同思考,那么景深镜头中导演拒绝控制观众的视点,在一幅大景别、高景深的画面中,多种要素共同呈现,提供给观众众多选择,观众只有积极参与场面调度才能理解意义。
第三,……蒙太奇由于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在分析现实时,要求戏剧事件含义单一……反之,景深把意义含糊的特点重新引入画面结构之中。虽则并非必然如此,至少也是一种可能。[2]78
蒙太奇关注单一事件,性质固定,长镜头则关注着同一个画面内部的多个因素,留给观众众多的意义选择的可能,而这种与现实一致的意义模糊,正是景深镜头真实性的体现,这也体现了导演的客观、不介入、旁观的纪实主义美学的方法与原则。
巴赞的电影语言进化论的主要依托是其电影纪实主义的本体论。电影语言的演进一方面体现了电影自身逐渐向电影本体靠拢的自律性,可以说是巴赞电影影像本体论的另一种论述策略。另一方面,电影语言演进的高等形态景深镜头理论则是确保电影纪实主义本体的重要语言形式。
总之,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与“电影语言进化论”共同支撑起巴赞理论的主干,分别以造型艺术史与电影语言发展史的呈现形式中,在自己独特的论述逻辑之下,详细解释了电影的本体以及电影本体与电影语言演进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成为世界电影理论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影响深远。[4]49围绕在巴赞身边的《电影手册》的同事们掀起的新浪潮电影运动把他的理论实践于银幕,为电影带来真实美学的新气息。虽没有电影作品创作,安德烈·巴赞依然被称为“电影新浪潮之父”,其理论在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也可见一斑。
[1]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2]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3]爱因海姆.电影作为艺术[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4]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