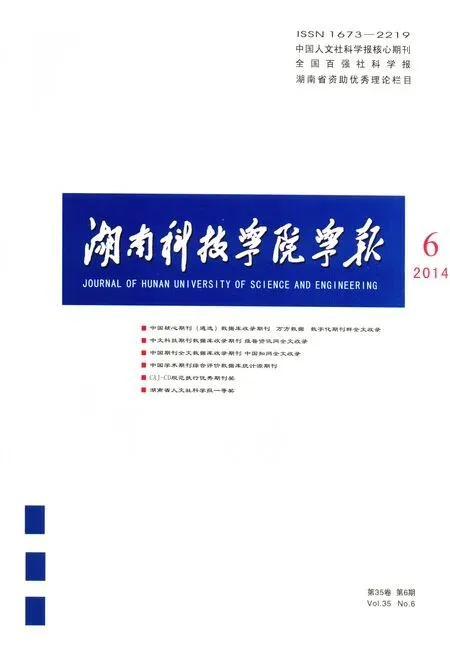温庭筠《华州参军》中的“史才”、“诗笔”与“议论”——以元稹的《莺莺传》为比照对象
李博昊
(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传奇》,讲述贞元年间,张生游于蒲州,居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子女路经蒲州,亦居寺中。兵士乘主帅之丧而扰乱,崔氏甚惧,张生与蒲将之友有交,派兵护寺,崔家得免于难。崔氏宴张生,始见其女崔莺莺,遂生爱慕,作《春词》二首,托莺莺使女红娘通意。莺莺端服严容,责其非礼。张生绝望。数日后,莺莺夜奔张生,与之结合。此后,张生两去长安。明年,张生考试不中,遂滞留长安不归。虽莺莺给张生寄去信物及长书,然张生终与莺莺决绝。[1]p80此后二人各自成婚,张生偶经莺莺居所,以外兄求见,莺莺终不为出,自此长别。《莺莺传》一出即广为流传,唐人王涣《惆怅诗》中言“八蚕薄絮鸳鸯绮,半夜佳期并枕眠。钟动红娘唤归去,对人匀泪拾金钿”,罗虬《比红儿诗》中曰“人间难免是深情,命断红儿向此生。不似前时李丞相,枉抛才力为莺莺”,均感《莺莺传》而发。鲁迅曾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李绅、杨巨源辈既各赋诗以张之,稹又早有诗名,后秉节钺,故世人仍多乐道”。[2]p53汪辟疆言此传流传最广的原因“一则以传出微之,文虽不高,而辞旨顽艳,颇切人情,一则社会心理,趋尚在此”[3]p140温庭筠受此影响,以《莺莺传》为底本,创作了《华州参军》,述说了一个生死契阔的爱情故事。华州柳参军乃名族之子,罢官后于长安闲游时遇容色绝代的崔氏女,心生爱慕,故赂其婢女轻红欲结之,轻红不受。不久,崔氏女病,其舅请为王生纳,崔氏女不乐,愿嫁柳生。其母应允,遂偷成婚约。居于金城里。王家寻觅崔氏女,弥年无获。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里赴崔母丧,为王生所见,遂讼于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于王。经数年,移其宅于崇义里。崔氏女使轻红访得柳生居所,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逃而同诣柳生,迁居群贤里。王生寻得后复兴讼夺之。后柳生长流江陵。二年,崔氏与轻红相继而殁。一日柳生于江陵闲居,轻红与崔氏女忽至,与柳生居二年间,尽平生矣。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亲见崔氏女与轻红,俄又失之所在。柳生与王生具言前事,又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见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赵彦卫《云麓漫钞》曾言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陈寅恪言“《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4]p120,温庭筠的《华州参军》所叙故事更为动人、所展诗笔更为含蓄、所发议论更为精深,较之元稹,皆有一定的突破。下详述之。
一
《华州参军》的人物勾勒、情节设计在借鉴《莺莺传》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造。《莺莺传》中的崔莺莺虽曾大胆追求爱情,最终却选择了放弃,她这样评价过去的自己:“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没身永恨,含叹何言!”莺莺钟情于张生,分别之后,虽“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寝之间,亦多感咽……幽会未终,惊魂已断”,却言“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当张生一去不返时,其传信曰“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幽愤所钟,千里神合……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言语之中满含关切。对于莺莺,张生这样评价:“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词之严,情之绝,令人生寒。对于张生“忍情”的行为,莺莺痛心之时感受到的是绝望,纵然其“万转千回懒下床”、“为郎憔悴却羞郎”,然当多年后张生请见之时,亦以“忍情”来回应:“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终生不复见。故事虽为悲剧,却因人为。如若张生重情,必不会有日后莺莺的垂泪。而温庭筠的《华州参军》则在一个超时空的背景下,展示出人在宿命中的挣扎。
崔氏女本着“人生意专,必果夙愿”的理念,执着于爱情,永不言弃。在初遇柳生之时,崔氏女“斜睨柳生良久”,在拒嫁王生时,其告母“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在第一次被判归王家时,其“使轻红访柳生所在”,“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赉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其死后,千里寻得柳生所在,言“已与王生诀,自此可以同穴矣”,爱人之心,如磐石般坚固。《古诗十九首》中描述过“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的痛苦,对于这种苦楚,崔氏女在接受的同时选择了努力改变,纵然道路长阻,衣带渐宽,仍旧无悔。汤显祖《牡丹亭题记》曾言:“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崔氏女一如杜丽娘般,其执着于柳生,实为一至情人,其与柳生未成眷属,亦乃悲剧。然《华州参军》的悲剧性远不止于此。王生“常悦慕表妹”,故其父相信崔母所言“吾夫亡,子女孤弱,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责打于他。但当他见到赴丧的崔氏女之时,“不怨前横”,与之生活数年中,轻红的“洁己处焉”亦表明其对崔氏的钟情。崔氏女后私离王家奔赴柳生,其多方找寻,“兴讼夺之”,崔氏“托以体孕,又不责而纳焉”,情深再现。崔氏女亡后,其“送丧,哀恸之礼至矣”。听闻崔氏尚在,即“命驾千里而来”,崔氏女确亡,其亦“入终南山访道”。王生是天下又一至情之人,明知崔氏女爱慕柳生之心,却仍就执着,这样的情感,可感动天地。崔氏女虽苦,毕竟和柳生拥有过幸福时光,而这样的时刻对于王生来讲,却只能是一种奢求。崔氏女拒嫁王生的时候曾说:“以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这句话几如谶语一般,左右着三个人的一生。崔氏女苦苦追逐着柳参军的脚步,王生痴痴钟情崔氏,这样的矛盾,终究不可调和。温庭筠在小说中屡屡表达命运的安排是那样的令人无奈与感伤,即使生命终结,化为幽冥,夙愿依然未尝。故事中柳生、崔氏女、王生之间的爱情,在艰难的人生中终未找到超脱的路径,整个悲剧的起因由“人心”转化为了“命运”,“求而不得”的悲慨,更为苍凉。
较之《莺莺传》,《华州参军》中主要人物的形象愈加立体丰满。对于次要人物,温庭筠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勾勒。《莺莺传》中的崔母在促使崔、张二人相见后,便再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无声地消失于作品之中。红娘的献策、传诗虽成就了崔、张之情,但其形象略显机械,亦缺乏思想性。此种不足在《华州参军》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弥补。崔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促成了崔、柳二人的婚姻。而在王家询问崔氏女下落之时,其泣云:“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极力为崔、柳遮掩,延续了二人的婚姻。其故去之时,崔、柳服丧为王生所见,又是故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个人物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较之《莺莺传》中的崔母,更为清晰。轻红亦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柳生初遇崔氏女,多方赂之以求结识,其不受。柳生悦其而挑之,轻红大怒言:“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其对柳生的一番教育是崔、柳恋情发展的基础。在王家“经数年,竟洁己处焉”,衬托出王生对崔氏女的至情。当崔、柳二人分开之时,又是她起到了青鸟传信的作用。崔母与轻红是柳生、崔氏女、王生之间联系的桥梁,她们的存在使得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矛盾更为突出,情节亦跌宕起伏。
二
《莺莺传》是中唐时的早期作品,虽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议论、叙事、诗词三体备具的特点,但作者续张生的《会真诗》有卖弄辞藻之嫌,显得冗长而无意义。[1]p87相比而言,温庭筠没有像元稹那般在小说中植入大量的诗句以炫诗才,他独特的诗笔展现在对爱情的描绘和对志怪题材的运用。那种生死不渝的情感本身就带有一种诗歌般的浪漫,小小情事却凄婉欲绝。而设幻之笔,亦是艺术表现中诗意性的一种展现。值得注意的是,温庭筠《华州参军》中某些场景描摹同其词作有着一致性,七首《南歌子》如若《华州参军》的诗化注释。崔氏女初见柳生“斜睨柳生良久”,同《南歌子》其一“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相形,不如从嫁与,作鸳鸯”所摹绘的场面、表达的心境暗合;其二“似带如丝柳,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同柳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后帘徐褰,见纤手如玉……女之容色绝代”,生“鞭马从之”一致。其三中的“为君憔悴尽,百花时”、其四中的“隔帘莺百啭,感君心”所描绘的正是崔氏女同柳生第一次被迫分开后的思绪。其五“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乃崔氏女携轻红奔柳生后的欢愉场面。其六、七中的“忆君肠欲断,恨春宵”,“近来心更切,为思君”又同崔柳二次被分开的心境相同。《华州参军》的“诗性智慧”与《南歌子》叙事性表达,展示出诸艺术类型的相通。
元稹的《莺莺传》一般认为是自传体小说,传中张生实元稹,以假语村言自叙艳遇。《侯鲭录》卷五王载王铚《传奇辨证》尝有辨,赵德麟作《微之年谱》亦借本传考元稹事迹。[5]p314或许囿于风流韵事的“实录”,《莺莺传》缺少大胆的虚构,整个情节与结构不够舒展,描写亦欠细腻。[1]p87但“忍情”论实代表了元稹对于爱情与仕途的看法。他对待崔莺莺,纵有爱怜,然当情感与现实冲突时,其毫不犹疑地选择了现实的利益,展示的是一个“极热衷巧宦之人”[4]p116的功利心态。而《华州参军》中的崔氏女和王生身上,则有温庭筠的影子。温庭筠一生仕途坎坷,于宦海之中苦苦挣扎,其参试、干谒、上启,却始终不能达到他想要的人生。小说中崔氏女对于柳生的执着,王生对于崔氏女的爱恋,终究和他的仕途梦一样,了无结果,求之不得的苦楚,难以言说。
《莺莺传》和《华州参军》所出时间相距不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皆有所反映。崔莺莺与崔氏女同是唐时显姓——崔姓,但二人虽有财产,却无父佑,纵为姓氏上的贵族,却非政治上的贵族。“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一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但明乎此,则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4]p116崔莺莺为张生所弃,遭遇虽令人唏嘘,亦属常见。崔莺莺自荐枕席与之后再嫁,折射出到元稹作《莺莺传》的贞元二十年(804),社会上所谓的礼法之风还不甚严格,当时唐人对于少女婚前的贞操亦不十分计较。崔氏女婚后另觅情人的行为,社会不认为是奇耻大辱,表明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侣的现象较为普遍。[6]p149-150但崔氏女虽“不乐事外兄”,私寻柳生,却不能与之解除婚姻关系。唐律规定男女双方如果姻缘不合,不相安谐,可和平解除婚约。而王生深恋崔氏女,不属此种情况。唐代法律还有“七出”之规定,却是赋予男子之权利,女子提出解除婚姻,不但不容易得到许可,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云溪友议》曾记“颜鲁公为临川内史……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饘臛不足,索书求离……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愚妻覩其未遇,遂有离心……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疋、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女子从法律上弃夫,终究不愿被社会接受。
温庭筠的《华州参军》虽是一篇较为优秀的小说,却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反响,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礼法之风渐趋浓厚。李唐原来胡化极深,与山东士卒迥然不同。如朱子《语录》所谓“闺门失礼之事很多”,但中唐以后山东士族在政治上重新抬头,礼法之风便开始浓厚起来,[7]p88-89失礼之举常为人不齿。所以在中晚唐小说《周秦行纪》中,太后让昭君侍寝的理由为“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垒若鞮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据《资治通鉴考异》,《周秦行纪》的创作目的乃为讽刺牛僧儒的母亲行为不检,“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绝矣,纪贵请以出母追赠。”[7]p84《周秦行纪》是牛李党争的产物,创作目的在于攻击政敌,既然以改嫁为羞,说明当时社会上对女子的婚姻管制较之前严格了许多。崔氏女这种既已为王家之妇,又屡屡私寻柳生,一女侍二夫的行为不为社会所提倡,亦不会被接受。此外,《华州参军》中的婚姻是不完满的,崔氏钟情于柳参军,终未能与之相守;王生钟情于崔氏,亦未得到崔氏的真心,故事以悲剧落幕。然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元稹的《莺莺传》屡遭修改,“张生和莺莺到后来终于团圆了”,而《华州参军》中的情感矛盾不可调和,后人亦不愿纠结于此,伤神改编,《华州参军》这样的小说,终究未能流传开去。
[1]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陈寅恪.读莺莺传[A].陈寅恪.陈寅恪集[C].北京:三联书店,2001.
[5]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6]高世瑜.唐代妇女[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7]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谈大型古装淮剧《马前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