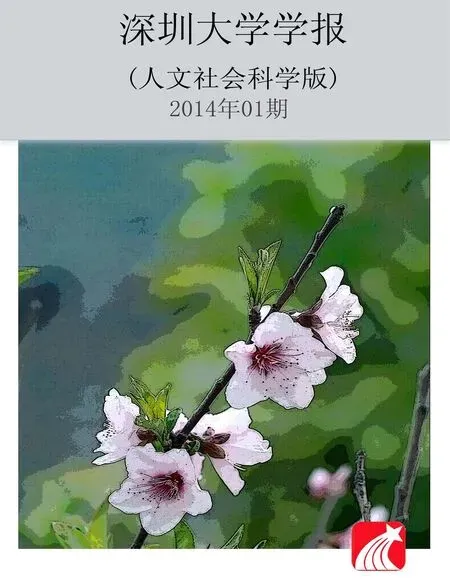中英文化的碰撞与协商:解读威廉·燕卜荪的中国经历
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中英文化的碰撞与协商:解读威廉·燕卜荪的中国经历
张剑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英国著名批评家、诗人威廉·燕卜荪是东西文化碰撞的一个实例,作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其经历反映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他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分析他在这个时期留下的文字资料,包括诗歌、小说、批评论文、书信、旅行笔记等等,将为读者展示他对文化身份、中西文化差异等问题的思考,从而展示文化间如何通过碰撞和协商以达到相互包容和理解。
燕卜荪;东方;身份;文化;协商
一、燕卜荪与文化问题
威廉·燕卜荪(1906~1984),英国著名批评家、诗人,《含混的七种类型》的作者,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在西南联大任教,随该校辗转湖南长沙和云南昆明,讲授的课程有“现代英国诗歌”和“莎士比亚”。钱钟书的《围城》和西方学者易社强的《革命和战争中的西南联大》都对这所流亡大学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土墙教室,日本飞机的轰炸,图书和教材的缺失,不断搬迁以逃避日军的侵略等等①。约翰·哈芬顿的《威廉·燕卜荪传》和燕卜荪的西南联大学生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扬周翰、赵瑞蕻、许渊冲、穆旦、杜运燮、郑敏、杨苡、袁可嘉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过燕卜荪及其特殊的人生经历。
许国璋曾经上过燕卜荪开设的“现代诗歌”课,他记得燕卜荪于1937年秋和1938年春在南岳和蒙自的课堂上朗读和背诵那些伟大诗篇的情景,“词句犹如从诗魔口中不断地涌出”[1]。李赋宁曾经上过燕卜荪开设的“莎士比亚”课,他记得学校没有教科书,燕卜荪 “凭超人记忆,用打字机打出了莎剧 《奥赛罗》”,以供学生们阅读[2]。赵瑞蕻记得燕卜荪嗜酒如命,常常喝得烂醉如泥,一天酒后他摘下眼镜,放进了[3]。了一只皮鞋里,第二天却忘掉了鞋里的眼镜,站起来后,他“才发觉一只鞋子内有异物”,结果眼镜踩破
燕卜荪的中国经历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他是一个西方人在异邦生活和工作的典型事例,异邦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与他自己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因此他感到了一种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或压力。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作品不仅记录了他的动荡生活,而且记录了他关于文化和身份问题的思考,记录了他的中国经历如何影响他的学术和批评观点。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以及对以上问题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西方的文化关系,理解文化间如何通过碰撞和协商达到相互包容和理解。
二、中国的炼狱
燕卜荪来到中国之时,正值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南方,组成了临时大学。冯友兰回忆说,“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4](P20)。燕卜荪的《南岳之秋》一诗就创作于湖南长沙的临时大学。该诗以南岳为背景,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临时大学的教学和生活画面。学校条件异常艰苦,教授都需要合住宿舍,燕卜荪与哲学家金岳霖被分配到同一房间。在没有暖气的冬天,燕卜荪穿着中国式棉衣,仍然患上了感冒。
文学院设在南岳半山腰韭菜园的美国圣经学院,没有图书,也没有教材。“课堂上所讲授的一切的内容 /都被埋在丢弃在北方的图书馆里”[5],因此燕卜荪只有凭着记忆去教学。回忆起来的文本有时并不准确,但是他认为“版本不同不妨碍讨论,/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条件虽然艰苦,但诗歌的“整个情调是愉快的”,不时还会有“幽默、疑问和自我嘲讽”[5](P207)。
诗歌围绕一个核心英语动词fly展开,对它的多义含混特征进行玩味和思考。该词同时表示“飞行”和 “逃亡”——燕卜荪乘飞机从香港飞往长沙的经历,与临时大学的逃亡经历交织在一起。燕卜荪1929年被剑桥大学开除,从而来到东方的日本和中国教学,对他来说,东方之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逃亡”。玩味“逃亡”的多重含义是典型的燕卜荪式诗歌批评方法,然而,这首诗并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个人怨恨的发泄,而是一首思考战争与中国未来的严肃诗歌。
“逃亡”是临时大学的生活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逃亡”就是中国的未来。学生和教授们可以埋头读书,在文学中找到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像坐上“太阳神的车”在想象中翱翔。另外,“虎骨酒”也可以让他们飞翔,像女巫骑着扫帚在天空游荡,但战争的残酷现实无法逃避——有一次日本战机误炸了婚礼,“炸死了二百条人命”,吃喜酒的宾客全变成了冤魂。因此,《南岳之秋》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深入思考。燕卜荪认为“诗不该逃避政治,/否则一切都变成荒唐”[5](P208)②。但另一方面,他也拒绝煽动性文学,拒绝“那种革命气概的蹦跳,/一阵叫喊,马上就要同伙/来一个静坐的文学罢工”。他认为这样的文学最多是一种“瞎扯”,毫无价值。
《南岳之秋》一方面是燕卜荪的自我辩护,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他将自己的中国之行视为一种“想去大事发生的城镇”的行动。作为诗人和学者,他并不想“招摇”或展示英雄气概,但他来到中国也不是“替代”那些不得不离开的人。他感到中国正在经受“炼狱”的考验,仿佛是钉在十字架上。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否意味着“重生”?像《金枝》里所说的那样?这是诗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最终我们没有得到答案。在诗歌结尾,临时大学又开始了迁徙,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三、文化冲击
燕卜荪与中国的相遇经过了“文化冲击”的几个典型的阶段:蜜月期、协商期、调整期、掌控期。一开始,他沉浸在一种异国情调之中,对所有事情都感到新鲜。他对佛教充满了向往,把南岳衡山视为 “圣山”,像信徒一样登上山顶去朝拜。“我所居住的这座圣山,/对于我读的叶芝有点关系”[6](P73)。他的心境有点像叶芝在《天青石雕》一诗中表达的那种对东方文化的敬意③。然而,这种兴奋感很快就被沮丧所代替,燕卜荪不断地碰到他感觉很奇怪的事件,对他自己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冒犯。可以说,他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一种突然被抛入不同文化环境所产生的困惑和不适。
与同在西南联大教学的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不同,燕卜荪不懂中文,而且“不能对这种语言产生兴趣”[7](P458)。他不理解中国饮食,觉得中国的晚宴“在结构上差点劲”。他不理解中国人的高声喧哗,认为“中国人的哈欠在一百英尺外都能听见。他们清理嗓门的声音像犀牛即将发起攻击一样”[7](P485)。他不懂中国茶文化,认为中国人不喜欢喝英国红茶,是犯了一种理想主义的错误,即“让绿茶的完美味道形成一种理念,然后在自己心里强加一种对红茶味道的讨厌”[7](P460)。然而,这些困惑和不适仅仅是细枝末节,真正意义上的冲击不是发生在日常生活,而是发生在课堂上,发生在师生共同面对文学和道德问题的时候。
《复杂词的结构》一书收录了燕卜荪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撰写的若干篇论文。与《复义七型》一样,它是对诗歌语义复杂性的研究,其中多次提到他在中国西南联大和日本东京文理大学教书的经历。这些教学经历不仅反映了英语语义的复杂性,而且突显了他本人特殊的文化身份。在他开设的“莎士比亚”课上,一名学生撰写了一篇关于《奥赛罗》的评论,将苔丝蒂蒙娜的死因归咎于她“软弱的性格”,她没有能够抵御凯西奥的诱惑,并且批评她的“思想开放、坦诚和过度的宽宏大量都会引来非议,特别是伊阿古。”这话使燕卜荪产生了不小的震惊,在他看来,这样的道德判断是建立在一种“完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它“击碎了整个西方的道德思考的传统”[7](P465)。
应该说,使燕卜荪吃惊的是学生评论中所中包含的这样一种暗示,即苔丝蒂蒙娜应该部分地为她的悲剧负责。在燕卜荪看来,她完全就是一个阴谋的受害者:她和丈夫奥赛罗都掉进了邪恶的伊阿古所设置的圈套。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对女性的贞洁要求更高,这位中国学生自然认为苔丝蒂蒙娜与凯西奥的关系过于密切,至少是导致她的悲剧的部分原因。这是文化传统不同导致的观点不同的一个例证。
在“英国诗歌”课上,一名中国学生针对英国民谣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民谣应该写得越简单、越通俗(vulgar)越好”。“通俗”一词刺激着燕卜荪的神经,他认为该词散发着“势利”的味道,隐藏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蔑视和不屑。这看上去是用词的错误,即“纯粹文字错误”,而实际上暗示了一种态度,一种“品味的错误”。在他看来,“通俗”一词不是一种客观描述,而是“暗示了说话人的审美或政治观点”[8]。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这样的观点并非“愚蠢”之举,而是因为“它来自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明”[7](P465)。换句话说,他不是简单地评价学生观点的对与错,而是深入思考这些观点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性。
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说燕卜荪的精细的语义分析使该词的涵义复杂化了。应该说,那位中国学生不具备燕卜荪的阶级意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所赋予的;那位中国学生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词背后的特别含义,但是他却将燕卜荪的注意力引到了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正如燕卜荪的传记作者约翰·哈芬顿的评论:“日本和中国学生不断地帮助他拷问自己的道德观念”;“帮助他证实了他在《复杂词的结构》一书中称为‘浓缩理论’基础上所作的批评分析”[7](P467)。因此,我们可以说燕卜荪对中国学生观点的不解,主要反映了他遭遇中国文化后所产生的焦虑。经过与西方视角和西方传统的比较,他逐渐意识到学生观点的不同,是因为来自不同的思想体系,从而促成了一种理解和宽容。
四、文明与文化
1938年日军占领长沙,临时大学迁徙至云南,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约250名学生从长沙步行前往云南,行程1600多公里,磨砺了斗志,宣示了抗日的决心[4](P20)。燕卜荪与他的同事们一起来到云南,在设在蒙自的英语系执教。在云南,燕卜荪接触到了中国的少数民族,了解到中国的地区差异,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从约瑟夫·洛克和C. P.菲茨杰拉德对纳西族和丽江地区的研究中,他看到了少数民族的服饰,认为刺绣和银饰相得益彰,体现出一种艺术美和民族特色。
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多数来自东部,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与云南当地人相比,他们更富有、更开放,受过更好的教育,特别是在爱情婚姻的态度上更加西化。有些学生甚至视云南人为乡下人或山民。对于云南来说,外来人口不仅造成了当地的通货膨胀,而且在当地人中间引起了不少疑虑,甚至引起了所谓的“文化冲突”[4](P104)。虽然燕卜荪很欣赏西南联大学生的才能和爱国热情,但是他并不认同他们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歧视,好像“野蛮的苗族人要吃他们似的”[7](P488)。
根据西方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一个民族的归属感主要来自这个民族的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独特性,这些合起来将在其成员中间创造出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9]。显然,燕卜荪认识到少数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对少数民族受到的所谓歧视感到巨大的失望,甚至认为他们中间存在着独立诉求和分裂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这些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汉族士兵一起流血牺牲,抵御外来侵略。显然他还没有理解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概念。
燕卜荪的《中国》(China)一诗反映了一个欧洲人眼里的抗日战争,以及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异性。赵毅衡说,诗歌暗示中国“龙”生出了一条日本“毒蛇”[10]。其实燕卜荪是想说,日本与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们像他们,犹如两颗豌豆”。诗歌的核心意象是一个复杂的玄学比喻:日本是肝吸虫,中国是肝脏,日本侵略中国恰似肝吸虫侵害肝脏。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肝吸虫的成长历程,我们将看到这个复杂的比喻实际上把抗日战争视为中日两个民族相互吸纳和相互同化的过程。肝吸虫幼虫是寄生虫,在蜗牛体内生长,“它们将变成一体”。换句话说,日本将被中国吞没,就像肝吸虫幼虫被蜗牛完全同化[11]。中国的战争苦难被理解为道家“以柔克刚”的智慧,燕卜荪在注释中写道:“释怀,才能增长智慧;退让,才能获得道路,就像在水中一样:这些观点在中国思想中有很长的历史”[6](P115)。
如果对于燕卜荪来说中国和日本很相像,“犹如两颗豌豆”,这可能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遥望中日两国的结果。对于欧洲来说,东亚都是建立在儒家和佛教思想基础上的文明。这个较大的图景展示了这个地区的国家拥有语言、宗教、风俗和思维方式上的一致性。然而,如果他们拉近距离,进入东亚仔细观看,正如燕卜荪在云南观察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就会看到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性。因此,燕卜荪视中国和日本为一个整体所暗含的矛盾性其实是一个观察视角的问题,视角的远近将会决定不同的世界图景。
五、东方与西方
燕卜荪在中国的身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但他也是英国政府的“基础英语”推广计划的成员,效力于大英帝国的语言政策。在他的导师I.A.瑞恰兹的鼓励下,他参与了“基础英语”的教材编写和师资培训。虽然他来到中国、供职于西南联大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无私援助,但是他每次来往中国都会经由英国殖民地香港,享受着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权。他会不会有一种他称之为“帝国建设者”的优越感或者负罪感呢?
在中国期间,燕卜荪留下了一篇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皇家野兽》(The Royal Beasts)。虽然小说没有完成,但是其情节大致已经清楚。“皇家野兽”是一个非洲部落,从外貌看,他们有人类的特征,但他们又有动物的尾巴,并且全身长毛。他们有语言和智力,但他们又像动物一样有交配季节。由于这个部落的领地上发现了黄金,临近的英国皇家殖民地和西罗得西亚开始了对这片领地和它蕴藏的黄金的争夺。“皇家野兽”部落更情愿归属英国,以换取英国对他们的保护。如果他们归属西罗得西亚,他们有可能沦为奴隶,而且他们的皮毛还可能招致大规模商业捕杀。
从这个简单的复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反映的是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入侵,这种入侵一开始是武力征服,后来变成了资源掠夺和文化入侵。有意思的是,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就是英国殖民者竭力教部落头领乌左说英语。语言能力是人性的主要体现,动物可能有一定限度的语言能力,但是它们不能表达抽象概念。皇家野兽的限定性的语言能力是他们的人性的表现,但是他们的毛皮和尾巴又显示,他们仍然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低级阶段。这些普遍人性问题的讨论充满了讽刺意味,但是它们拷问的是我们是否应该视非洲黑人为人?是否应该给他们宗教救赎?以及类似的问题。
燕卜荪通过人物的口,将该事件与美国南方的蓄奴制相比较,谴责南方政客和奴隶主将奴隶视为动物和财产的虚伪行为:“他们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还投票支持人人享有自由,说什么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12]。故事通过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掠夺,批评了欧洲人自认为在非洲传播进步和文明的幌子,暗示了东西方关系的某种张力,同时也影射了燕卜荪自己在中国的他者处境——他被北京的朋友们称为“乌左”[7](P472,P477)。
燕卜荪在中国,与中国人在西方一样,同样是另类。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对于欧洲来说与非洲人无异,因为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将欧洲以外的所有土地都视为“东方”。这暗示了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将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以便把东方视为西方的镜像。换句话说,如果西方是理性的、进步的、民主的,那么东方一定是非理性的、落后的、专制的——东方正好是西方的反面④。这个东方是西方的东方化建构,还是西方刻意将负面价值向东方的投射,这不是该文讨论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燕卜荪对西方殖民行为的批评,显示了文明之间的接触对他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正如他所说,在碰撞当中西方人才能逐渐认识到 “我们对异邦感情模式的强烈而批判性的好奇心,以及我们对异邦思维模式的坚固的同情心”[13]。
六、协商与调整
英国诗人罗德亚·吉普林 (Rudyard Kipling)于1890年代写道,“啊,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不会相遇,/直到天与地匍匐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这首诗名叫《东西方歌谣》,传统上被理解为东西方分裂的例证,或者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开脱。事实上这首诗讲述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英国殖民将领与一个印度的土匪头领之间的冲突和和解:通过协商与对话,最终两人的儿子盟誓成为朋友,肩并肩成为兄弟。吉普林评论道,“可是没有东,也没有西,没有边界、种族和出生的差异,/只有来自天各一方的两个强者相持不下,面对面站立。”吉普林的重点实际上不在于东西方的差异,而在于两个个人的友谊和团结,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种族、地域和社会背景。
传统上,东西方被视为对立面,双方由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被认为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具体地说,人们认为双方理解世界和现实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无法对接。有些概念和范畴只属于西方,而东方完全没有。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真理的概念,而在西方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的核心概念。然而,这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巨大误解。据张隆溪教授说,不仅古代中国就发明真理的概念,完全是独立发明,而且这个真理概念与古希腊的真理概念非常相似,因此也与从古希腊继承这一概念的西方哲学非常相似。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趋势是观察东西方的“对等性”,或者说双方理解和交流的共同基础[14]。那些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人可能只看到了吉普林诗歌的第一部分,而现在正是他们应该看到第二部分的时候。
吉普林不可能预见他的诗歌出版后一百年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意识到人类必须用国际法来规范各国的行为,用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分歧。吉普林也不可能预见到国际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开展,包括医疗、环境、消除贫困、疾病预防、反恐等。信息时代将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进了跨文化的理解。虽然在中东等地区,东西方仍然以怀疑眼光相互对视,但是目前的大趋势是接受对方的差异,甚至把差异视为文化多元性的一种表现。多元文化主义就是以承认他者权利、尊重不同价值体系为特征的、新的意愿和新的意识。哲学将他异性定义为正常的和崇高的,它帮助边缘化的思想获得了更多的认可,甚至帮助它们向中心移动,形成对主流思想的替代。不同文化的人们倾向于将对方视为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这种新的包容与和平共处的精神,是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战争与冲突的痛苦教训才获得的,也是经历了文化碰撞与协商的漫长历史才获得的,这种碰撞与协商教会了这个世界必须重视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
威廉·燕卜荪就是这种文化碰撞和协商的典型实例。他的四篇作品《南岳之秋》、《复杂词的结构》、《中国》和《皇家野兽》向我们展示,他在以不同方式对文化、身份和种族问题进行思考,文化差异是他在中国创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作品一方面增加了他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另一方面文化差异又迫使他反思西方人文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对文化差异的思考并没有强化他的西方视角,相反这使他能够认识到西方的思维方式不是唯一的、普世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他更加能够在东西方之间进行比较和调整、协商和接受。
注:
①《围城》,有时被称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小说”,描写一个
有才华但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在海外接受教育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回到中国,在一所流亡大学教书的经历。小说的背景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内地,反映了师生们不停迁徙的艰辛和困苦。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与燕卜荪的经历类似,反映了流亡大学生活的生动细节,包括偏远的校园、海归的教师、外籍教员、教育部推广牛津剑桥教学方式的努力、日军的蹂躏和中国军队顽强抗击的新闻、战时邮件的延误、对敌占区家人和亲属的担忧等等。
② 易社强记录了南京沦陷后报纸发表的文章,批评大学生在国家沦陷和人民涂炭之时仍然坐在教室无动于衷。激烈和充满爱国热情的文字呼吁大学生采取行动,保家卫国,而不是“逃避”,去获得学位,将来成为日本占领的国家的奴才。燕卜荪的诗歌呼应了这样的观点。
③ 叶芝的《天青石雕》一诗描写一尊17世纪的中国石雕,上面有康熙皇帝的铭文,表现一个和尚和两个随从爬圣山到山顶的情景。叶芝的诗歌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中国智者面对山下发生的悲剧和混乱所表现出的平和心态表达了极大的仰慕之情。
④在20世纪的文化批评理论中,自我认识来自与他者的对比。例如,萨特认为主体通过凝视和观看外部世界,将它收归意识之中,获得一种主控感。另一方面,他者的凝视迫使主体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从而催生一种自我意识。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被后来的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他们包括福柯、拉康、列维纳斯、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等。正如张隆溪所说,中国是一面镜子,在其中欧洲的自我认识到了它的负面自我。
[1]许国璋.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J].英语世界,1991,(4):4-7.
[2]李赋宁.人生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
[3]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A].离乱弦歌忆旧游[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45.
[4]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5]王佐良.王佐良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6]William Empson,Collected Poems[M].London:Chatto& Windus,1955.
[7]John Haffenden,William Empson:Voumel I.Among the Mandari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William Empson,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M]. Norfolk,Conn.:James Laughlin,1951.403.
[9]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London&New York:Verso,1991.5-7.
[10]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158.
[11]Christopher Norris,William Empson:Critical Achievement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81.
[12]William Empson.The Royal Beasts and Other Works[M]. ed.John Haffenden.London:Chatto&Windus,1986.147.
[13]Jason Harding, “Empson and the Gifts of China”,Some VersionsofEmpson[M].ed.Matthew Bevis,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7.
[14]张隆溪.异曲同工[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06.9-13.
【责任编辑:来小乔】
Britain-China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Negotiations: William Empson’s“China Experience”
ZHANG Ji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
William Empson,the famous English critic and poet,is a typical instance of East-West cultural encounter.His experience as a foreigner living in the Orient reflects the East-West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his anxiety about his identity.A close reading of his “China works”,namely the poems,short story and critical essays he wrote during this period,reveals his thinkings 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way his China experience influenced his academic and critical views.His experience will also show the way cultures try to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ccommodation by negotiations and adjustments.
William Empson;Orient;identity;culture;negotiation
G 04
A
1000-260X(2014)01-0025-06
2013-10-18
张剑,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英国现当代诗歌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