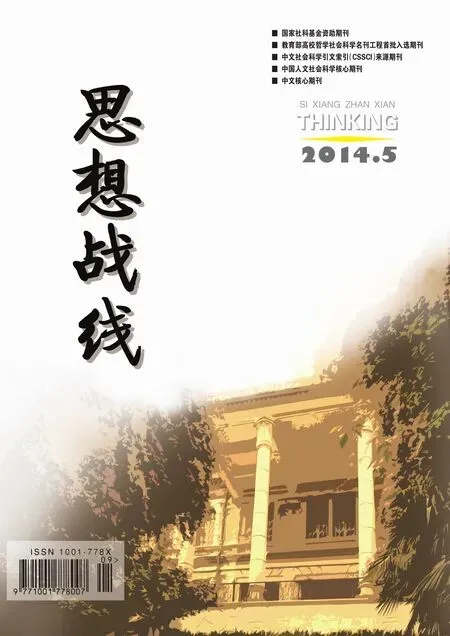近代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川教区的传教活动
马玉华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的传教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83年至1904年,创建昭通教会,主要在城镇的汉族地区传教;1905年至1915年,开拓石门坎,形成石门坎联区,转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教;1916年至20世纪40年代,扩大传教范围,发展到滇川黔边整个苗区,建立石川教区。
1883年,循道公会进入云南,在昭通、昆明等地活动,至1904年石门坎苗族到昭通求教为第一个阶段。1887年,该教会派遣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和弗兰克·邰慕廉(Frank Dymond)到昭通。柏格理曾在昆明工作了两年,毫无效果。1892年,传教团移住昭通。但昭通初期信教的人较少,1900年以前,教会仅有教徒30名。[注]古宝娟,饶恩召:《苗族救星》,汉口:中国基督圣教书会,1939年,第21页。
施医药和办学校是他们辅助传教的主要方法。19世纪末的昭通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又缺医少药。传教士用他们带来的少量药物,医治周围群众的常见病,抢救用鸦片自杀的人,为传教士树立了良好形象,并得到了当地官员的认可,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保护。后来教会开设福滇医院,通过减免医药费等办法,吸引人们入教。教会在昭通办有美会女校、宣道中学、小学、圣经学校等,从教育入手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外国传教士还采取与当地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建立友谊,邀请上门等方式传教,[注]刘鼎寅:《循道公会在昭通地区的早期传播》,《云南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利用当地人士的社会影响打开传教通道。他们先后与李国钧家、王玉洁家,以及昭通的龙、卢、陇、安等家族建立友谊,并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皈依基督教。传教士还请年轻人到家中,通过教认字、读《圣经》等发展教徒。这些早期的汉族教徒,有的被送到神学院读书,如李国钧于1898年由教会推荐到武汉华中协和神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牧师。教会再依靠这些当地的教徒或者传教士来传教,效果较好。柏格理曾说:“如果没有当地传教士的帮助,许多一直在进行的事务将永远不会被展开。在苗族运动初期,当时我没有一位固定的英国同事的帮助,多亏一些汉族基督徒英雄般的工作,若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注][英]塞缪尔·柏格理:《苗族纪实》,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在创建昭通教会的过程中,循道公会逐渐形成了基督教本土化的“昭通模式”。所谓“昭通模式”,就是以柏格理为首的外国传教士依靠本地汉族教徒,以关注人们的生老病死、日常生活为起点,慢慢渗透,从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介入中国社会,扩大基督教影响,以实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到1902年,柏格理等在城内集贤街购地,建立教堂,教会才在昭通站住脚。[注]萧耀辉:《昭通地区基督教调查》,《云南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近代,昭通一直是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办事处所在地,教区会议、教会的重要决定都在这里做出,昭通实为循道公会西南地区传教的中心和大本营。柏格理在昭通培养了一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信徒,他们成为了滇川黔边最早的传教士,为石门坎的开拓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昭通的学校和医院是教会各联区的主要依靠,为苗族学生升学和医药卫生提供支持。柏格理在昭通开始探索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途径,形成了昭通模式,为苗族教会的建立积累了经验,昭通也为后来石门坎苗族教会的开拓和石川教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904年7月12日,威宁石门坎的4位苗族同胞经安顺内地会牧师党居仁介绍,到昭通找柏格理。苗族的主动求教,与昭通布教的艰难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一个转折。此后,苗族络绎不绝地前往昭通,到1905年1月,已有4 000名苗族人到柏格理那里访问,[注][英]埃利奥特·甘铎理:《柏格理日记》,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05页。这促使了柏格理考虑建立新的传教地,最后选址在威宁石门坎。1905年春,柏格理带着昭通的汉族教徒王玉洁、钟焕然、李国镇(教名为李司提反)、傅正忠等开始在石门坎建堂办学校。5月,威宁苗乡的第一座基督教堂建起来。同年11月5日,柏格理为首批经过严格选拔的102位苗族施行了洗礼,[注][英]塞缪尔·柏格理:《苗族纪实》,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标志着石门坎苗族教会的建立。
1905年,石门坎建堂办校开始,到1915年柏格理去世为第二个阶段。教会的活动主要是建立石门坎联区,转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并向西发展到云南的东川、武定等地。1905年11月,石门坎小学开始招生。1910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成立,会址设在石门坎小学,石门坎成为循道公会滇川黔边苗族地区传教和办学的中心。1912年,学校更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同年,石门坎已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苗族学生毕业,柏格理留下一部分学生作布道员,同时选送学习成绩好的苗族学生到外地求学,由教会资助。随后,教会不断地送石门坎联区的学生到成都、贵阳、南京、昆明等地读大学,培养了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循道公会积极向石门坎周围的苗区扩大传教范围,较早建立的有彝良的咪洱沟和威宁的长海子两个教会。1906年10月,咪洱沟教堂几经周折终于建成,并开学招生。1906年6月,教会在石门坎东南部的长海子建教堂和学校。1907年11月,教会已“在71个村寨开展了工作,有1 412位接受洗礼的成员”。[注][英]埃利奥特·甘铎理:《柏格理日记》,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38页。此后,循道公会在威宁的大寨、论河、罗布甲、切冲、上海枯,云南彝良县的落尾坝、拖姑梅、青树林,永善县的老棚子,威信县的天池、后山、麂子坑等,镇雄县的沙木溪、发达等地先后建立了教堂和学校。
由于传教的重点转向少数民族地区,循道公会得到了较大发展,并开始向滇北和昆明传教。1906年,柏格理决定在武定洒普山建立教会,由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负责,石门坎派出了苗族布道员王胜模、王西拉、张道元、朱约翰、吴节等人协助郭秀峰工作。石门坎还派出苗族传道员到东川(今会泽)的苗区传教。[注]杨汉先:《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带苗族地区史略》,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南宗教研究——云南基督教史料专辑》,2004年编印,第21页。1915年,循道公会在滇川黔边已“有70多座新建或改作的小教堂,对于每一座(教堂)的建立,传教团协会平均资助为5英镑”。[注][英]埃利奥特·甘铎理:《柏格理日记》,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90页。柏格理去世前统计,“超过一万人可以被一般地认定为基督教徒。4 800人经过培训和通过会员资格测验后,接受洗礼,成为成年教会成员;900名青少年成员和5 000位为受洗礼正在接受考验者”。[注][英]埃利奥特·甘铎理:《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82页。
1912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成立,办事处设在昭通,先后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易理藩(A.Evans)、王树德(W.H.Hudspeth)、邰慕廉、马建忠等[注]颜思久:《云南宗教概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7页。担任教区长。西南教区组织较完备,教区有“共和年会”,年会下设四部三科,昭通部、苗疆部、东川部、东粟部,三科是:女学科、宣道科和医务科。1920年,增设昆明部。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因照顾生病的学生感染伤寒去世,苗族大规模入教的热情衰退,宗教信仰的大潮开始退潮。但在外国传教士张道惠、王树德和苗族布道员的主持下,苗族教会的工作依然有序地进行。
1916年至20世纪40年代,教会继续向滇川黔边的苗区扩展,发展到滇东北、滇中和川南等地,建立石川教区,这是第三阶段。1916年,石门坎派人到镇雄县的猪宗海、放马坝等地传教。1921年,派王正科到威信牛坡坎建教堂。次年,牛坡坎光华小学开学。此后,云南镇雄、威信、永善,四川筠连、珙县、高县、古蔺等地的苗族信教人数逐渐增加,一批教堂和学校在滇川黔边苗区建立起来。1925年以后,一批苗族传道员从石门坎进入云南的宣威、沾益和嵩明等地,循道公会随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教堂和学校。[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南宗教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6页。到20世纪30年代末,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苗区范围有2 590多平方公里,[注][英]埃利奥特·甘铎理:《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98页。已“有将近40个有组织的教会,拥有8 300名教徒和询问教义者,开设学校30余所,享受津贴的在校生1 400名”。[注][英]威廉·H.哈兹佩斯:《石门坎与花苗》,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5页。
1931年,西南教区下设各种委办会,有神学、宗教教育、医药、教育、妇女、产业、经济、文学、推广、差遣、接济、执行、地点、查账14个委办会,[注]《毕节专区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情况调查报告》,1955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8-2-102。并开办了教区神学院。这时的西南教区已包括五个分教区:即昭通分教区(原昭通部)、石川分教区(原苗疆部)、井宁分教区(原东粟部)、东川分教区和昆明分教区,而昭通的苗族教会划归石川分教区管辖。[注]萧耀辉:《昭通地区基督教调查》,《云南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1936年,以威信牛坡坎为中心成立川(四川)联区,下辖云南镇雄县的猪宗海、天星桥、雨洒河、发达,四川高县的铁厂,珙县的梧桐岩、王武寨、油榨坪、麻园,以及筠连县的小河子、长岩方等堂口。川联区归石门坎教会领导,合称为“石川联区”,管理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花苗和以牛坡坎为中心的白苗,联区领导机关设在石门坎,初期的教牧人员均由石门坎派遣。石川联区设联区长1名,由英国牧师担任,下设有专职传道员4、5名,全部由苗族老传道员担任。[注]张超伦:《记忆中的石门坎基督教会》,2008年,未刊稿。
1944年,川联区改称为牛坡坎联区,由镇雄县的杨明清牧师任联区长。1947年,牛坡坎联区再分为两个联区,即牛坡坎联区(又称川南联区)和王武寨联区(又称川北联区)。牛坡坎联区主要管辖威信和镇雄两县教堂,联区长是英国牧师张继乔;王武寨联区辖四川省高县、珙县、筠连三县的教堂,杨明清任联区长,实际上两个联区均由杨明清负责。这时,循道公会的石川教区跨滇、川、黔三省,苗族教堂或支堂有几十个。循道公会在滇川黔边苗族地区的传教,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首先,传播的方向,由滇东北的云南昭通往南传入威宁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派出苗族布道员向滇北和川南苗族地区扩展,向西传播到滇中一线直到昆明。
其次,宗教信仰的群体性。苗族几乎是全民族皈依基督教,根据张坦先生的统计,滇川黔边苗族85%信仰了基督教,[注]张坦著:《“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因此,在滇川黔边人们称基督教为“苗族宗教”。
再次,基督教的传播发展是始于苗族而及于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基督教首先在深受压迫的苗族中传播,教会培养的苗族传道再将基督教传播到西南地区的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因此,苗族在滇川黔边民族地区成为“引领民族”。
最后,早期苗族教会是少数民族群众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柏格理将传教的重点转向少数民族地区,引起了传教团内英国同事的讨论,只有少数人赞同他。而且当时差会的经费中没有少数民族工作项目,教会不可能提供经费支持。因此,早期的苗族教堂和学校,其实是当地的苗族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
二
对于循道公会在滇川黔边苗族地区传教的成功,基督教人士认为是“上帝之助力”和外国传教士柏格理等人的“穷年布道”之功;[注]1922年由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辑的《中华归主》上,记载了葛布内地会传教士艾萨克·佩奇(Isaac Page)的报告:“十五年前,基督教在苗人中布道颇有功效。当时全国宣教师几为一振,然此中实有圣灵之助力,潜移默化于无形,更加以积年经营不懈之工作,始克臻此,……不知即有亚当(Adam)及柏格理(Pollard)二人,抱大志、具远识,孑身独往,穷年布道,恃上帝之助力而功效立见,其工作始于安顺,推广及威宁而入云南,即今日彝家族中之布道运动亦莫不以是为导线。”参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76页。另外,《苗族救星》也有此意。社会学研究者用“短缺”的概念来解释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注]参见钱 宁《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 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还有学者从近代苗族的民族状况和阶级压迫剥削的角度阐述苗族信教的理由。[注]参见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然笔者认为:应该从循道公会的组织入手进行研究,循道公会组织的严密、制度的完善;“以苗传苗,以苗教苗”的本土化方针;苗族教会有计划的发展模式;外国传教士在苗区的努力工作等,是循道公会在滇川黔边苗区传教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卫斯理会(Wesleyans Church)的一个小教派。卫斯理会于18世纪创立,该教派提倡行事做人要循规蹈矩,被称为循道派或循道宗。1851年后,循道宗进入中国,从宁波和温州向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及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扩展。1907年,英国国内的卫斯理会几个教派联合组织成立“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1919年,该教派在华布道站有19个,传教士118人。[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1931年,圣道公会改组成为“循道公会”。
循道公会组织的严密、制度的完善在近代西南地区各基督教派中是有名的。其组织分为总教区、教区、联区、堂区。总会及远东委员会(亦名联省会议)设在英国伦敦的泰尔奔路25号,在中国的循道公会总部(原称中华循道公会全国会议)设在武汉,下辖7大教区,即华北、山东、天津、两湖、粤东、宁波、西南教区,昭通是西南教区办事处所在地。
伦敦总会权力很大,远东委员会专门管理远东教会,每年7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教区工作报告与请求举办的事项。中国各教区定于每年1月开会,全部材料均在远东委员会开会前送达伦敦,各教区一切重大问题,须于1月的教区会议上提出,经远东委员会通过,次年才能付诸实施。教区年会有牧师会议和代表会议之分,前者只有正任牧师、试用牧师能够参加,后者是全体会议,在某些问题上,试用牧师没有表决权。各教区设办事处,年会闭幕期间,由其执行决议。教区下设若干联区,联区经常负责人为联区长。联区下再设若干堂区,负责人为堂区执事。[注]《毕节专区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情况调查报告》,1955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8-2-102。
循道公会对于教牧人员的选拔和培养有严格规定,牧师分为:正任牧师、试用牧师、正任教区教士、试用教区教士、联区教士5种。牧师的选拔有严格的程序,先由联区提名(居留1年以上的平信徒)经教区会议通过,成为牧师候选人,经2年考察后,送神学院3年毕业,再由总会批准后,才能成为试用牧师。试用期4年,每年由教区按总会的规定举行考试,4年均合格,而且经过严格口试,经总会同意,始成为正式牧师。牧师10年以上,才能当选为教区主席。神学院毕业,可以做教区教士,由各教区自行聘请。循道公会对于牧师的资格要求甚严,任牧师者应具有高中或者同等学力,熟悉基督教经典,经过教区会议审核合格后送南京神学院,抗战期间则入湖北武昌神学院学习。3年毕业后,成为试用牧师,经过几年考试合格,方能成为正式牧师。另外,循道公会对于入教者的甄别和考察,联区学习的制度,[注]根据规定:石川联区每年冬季进行一次联区会议,会期为一周,所属各堂区的全体传道员、教师必须齐集石门坎。会议内容包括:学习时事,业务经验交流,人员工作地点的调动及进退安排等。联区有时还举办暑期读经、读书会等。工作的规范有序等完善的组织和制度,使得循道公会能够把居住分散的苗族群众有效的组织起来。
柏格理等人在昭通的早期岁月中,就开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形成了昭通模式。在昭通传教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苗区的实际情况,循道公会进一步探索出了在滇川黔边苗区的有效工作方式。
第一,有效的传教方式。除在教堂布道外,主要靠巡回传教,正是通过在苗族村寨中的不断巡回,传教士当面接触群众,才逐渐扩大影响。教会建教堂和学校同时进行,学校就建在村寨中,等于把教育办到了苗民家门口,正如专家所说:“苗胞大部分清贫,数百年之所以不感教育之需要,乃在其生活未渗入教育也。今教士们能从生活上予以教育,故学生日益增多。”[注]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第4卷,第9~12期合刊。另外,教会还利用医药布道、文字布道、赈灾和慈善事业等,吸引苗族群众信教。
第二,实行本土化发展方针,以苗教苗,以苗传苗,带动滇川黔边整个苗族的皈依。循道公会通过各种途径,为滇川黔边培养了一批苗族人才,1942年时,共计有大学生5名,高中毕业生10余名,初中生100余名,小学生3 000余人,特别培训了一大批传教士。[注]陈国钧:《石门坎的苗民教育》,载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他们先后被派到石门坎周边地区和石川教区进行布道和教学,成为了苗区布道传教和教学的骨干,还有人参与了云南东川、寻甸,武定洒普山与川南教会的工作,特别是“花苗人本身成为水苗人的传教士”。[注][英]威廉·H.哈兹佩斯:《石门坎与花苗》,东人达译注,载《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5页。
第三,苗族教区有计划的发展。石川教区常有所谓“五年计划大纲”发表,如1936年石门坎教区拟定的《石川分教区五年运动计划大纲》提出:从1936年7月1日起至1941年6月30日止,教会将用5年时间开展建设,制定了宗教、教育、生活改进、风俗改进、慈善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计划。[注]石门坎循道公会:《石川分教区五年运动计划大纲》,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2-1028。1941年,教会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运动计划大纲,内容仍然包括宗教、教育、生活改进、风俗改进和慈善事业等5个方面。[注]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边政公论》第4卷,第9~12期合刊。
第四,教会采取许多优惠政策,鼓励苗族入教和读书。如初期上学免费,治病免费,远处来做礼拜供给食宿,苗族毕业学生帮助传教给予津贴,成绩优良的学生由教会资助读中学或送出国外留学等。[注]陈国钧:《石门坎的苗民教育》,载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教会还利用小恩小惠引诱群众入教,柏格理开始时在石门坎发救济盐,后来说不发了,却又在黑板上写:“盐巴照发,到学校去拿”。不识字的苗族群众没有拿到盐巴,大家发现不识字吃亏,[注]《毕节专区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情况调查报告》,1955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8-2-102。因此群众就积极送子女入学校读书。
第五,以柏格理为代表的早期外国传教做了大量值得肯定的工作。柏格理在中国传教28年,在石门坎工作11年,走遍了昭通和石门坎周围的大小苗寨。他学习汉语和苗语,穿苗服和草鞋,与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尊重苗族群众。柏格理的妻子毕业于昆明护士学校,结婚后在石门坎主持药房工作,为苗族同胞看病,同时在光华学校任教。[注]谭佛佑:《威宁县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威宁文史资料》第5辑,2006年,第30页。这些都为基督教在苗区的开拓打下了基础。1915年柏格理因照顾病人不幸染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正是他“打开了苗族传道之门,奠定了苗族教会的基础”。[注]古宝娟,饶恩召:《苗族救星》,汉口:中国基督圣教书会,1939年,第1页。
1906年,张道惠夫妇与柏格理共同主持石门坎工作。柏格理去世后,张道惠主持在石门坎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开凿猴子崖通往昭通的小路、修建游泳池、建立医院、麻风病院和孤儿院等。这些早期传教士以其努力的工作和人格魅力获得了苗族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使得基督教在滇川黔边苗区得到广泛传播。
1951年,中央访问团的报告中说:外国传教士“放弃了安适的物质生活,远渡重洋,来到生活最艰苦,生命有威胁的异族人中去居住,言语不通,风俗互异,而泰然居住下来,用了最大的耐心,报着诚挚的同情,为这些落后的少数民族服务,千方百计来求谋解除群众的痛苦,提高群众的生活,满足群众的要求,甚而牺牲生命,亦无所不顾,在主观上虽或有企图,但在客观的努力和服务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注]中央民族访问团调查资料:《教会在贵州的西北角》,1951年,贵州省档案馆藏:47-1-43。不过,这样的评价只适用于循道公会早期以柏格理、张道惠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后来的外国传教士大都不会讲苗语,已很少长住在苗族教区。
三
要探讨苗族大规模信仰基督教的原因,需要从当时苗族的历史处境中进行考察。西南边疆历来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制定了有关的边疆政策,如羁縻政策、移民垦殖、土司制度等,以实行有效管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流官,使西南边疆地区“土流并治”,这种政治统治到民国时期仍然保留。清末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既受流官统治,也接受各民族土司的管辖,前者一般实行间接的统治,后者则是直接的管辖。因此,近代滇川黔边的苗族既受政府官吏的统治,又受地主土目的压迫。在贵州西北部的威宁,虽然经过了1726至1735年间的清朝改土归流,但土司土目的统治势力到民国初年没有受到削弱,人民群众所受的剥削还是很深重。
近代,滇川黔地区仍然是封建领主制,土地为彝族地主土目所有,“在领主经济下,苗人集体在彝族地主土地上无偿劳动,按期纳贡,并由领主指定的苗人寨老管理苗人事务。这种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有存在”。[注]费孝通:《关于贵州威宁苗族不安心情况的反映和意见》,1956年4月28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259。“苗族佃农除向彝族地主交纳地租外,还要交所谓的牛租、马租、羊租、鸡租,甚至有最残酷的人租。苗族生育的子女,都属彝族‘诺’的私产,故需交纳人租。……地主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苗族农民处于无权和受着残酷压迫的悲惨地位”。[注]杨汉先:《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苗族地区传教始末》,《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年。
滇川黔边苗族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及与丘陵相接的过渡地带,所居之地平均海拔在一两千米或者以上。他们所居之地,土壤既薄,范围又狭小,土地利用受到限制,生存环境恶劣,自然条件艰苦。他们居住的区域主要是山区,地力不佳,需要轮流耕种,形成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主要粮食为包谷杂粮。[注]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
总之,当地的苗族群众经济、文化落后,政治地位低下,加上自然条件艰苦,苗民生活艰难而贫困,苗族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处在国家、彝族、苗族三重结构的底端。当他们接触到基督教平等博爱的宣传后,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传教士的关爱和帮助让他们感到亲切和温暖;教会的特权和资源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庇护。[注]张慧真:《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第156页。所以,苗族大规模信仰基督教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基于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的网络诈骗行为研究
——以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