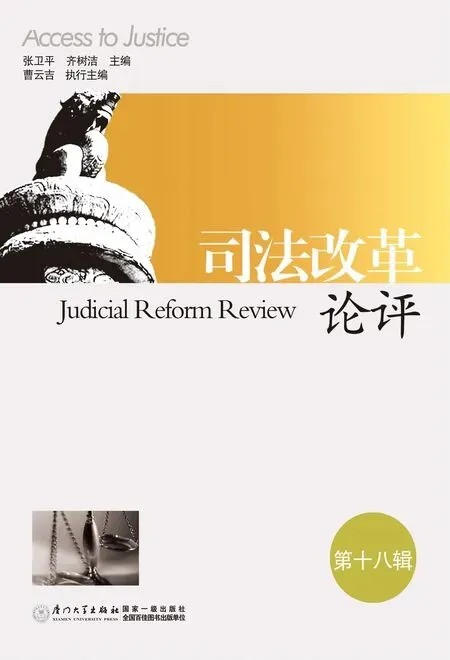司法改革之司法的去政治化
张卫平
司法改革之司法的去政治化
张卫平
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改革目标。例如,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其相对具体的措施或原则性方案就是要实现法院、检察院在省级以下人、财、物统管。之所以要人、财、物统管,其目的就是要实现所谓的“司法去地方化”。
司法的去地方化也是若干年前学界多数人所一直主张的,其要旨在于防止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权势及受其他关系的影响,导致司法机关无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机关不能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则作为以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为宗旨的法治也就必将落空。
除了司法去地方化之外,作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或目标还包括所谓的司法去行政化、去非职业化(等值的提法是司法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去封闭化(等值的提法是司法的公开化),以及笔者提出的司法去社会化(“司法的社会化”这一概念有着特定的含义,是指司法机关被广泛地融入社会之中,参与政府主导的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各界保持着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司法的社会化也是司法非独立的一种表征,尽管这一表征不是从权力结构关系的视角来认识的。司法的去社会化是要保持司法机关与社会的适度隔离,以保障司法机关不受社会各种关系的侵蚀和干扰,以便独立地行使司法权)。虽然法院与检察院两个系统有各自的特点,笼统地针对两个机关谈去上述“几化”还过于简单和粗疏。司法改革在具体的措施上还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实施不同的改革方案。司法改革除了去上述“几化”之外,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方面,还应当加上去“政治化”,而且去政治化可能是最重要的。司法如果不能去政治化,则司法不能成为实现法治的工具,司法不能成为现代的司法,也无法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司法的政治化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常常受到政治泛化因素的影响,无法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这种情形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我国的司法运行过程中。司法的泛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将政治口号直接作为司法的依据加以适用,导致司法在政治口号之中空转,使得法律适用技术化被政治口号消解。例如,像“司法服务于大局”这样的政治口号,对于宏观政治层面的要求而言,司法当然应当做到服务于政治要求,如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政治稳定等,但对于司法机关在具体的司法过程而言,只能根据既定的法律来操作,因为立法者已经将政治的大局、政治要求规定在了具体的法律之中,司法者只需要执行法律即可,虽然有时我们会觉得这样显得过于单纯(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单纯,法律将无法得以贯彻)。如果现行的法律没有适应政治发展和要求,则是法律应当修改和完善的问题,修改和完善法律以满足政治要求是立法者的任务,而不是司法者的任务,是政治层面的作为,立法、修法从来与政治有关。作为司法者就只有服从法律,如马克思所言,法官之上、上帝之下唯有法律,对于法官而言只有法律至上,没有其他可以置于法律之上的。法官不可以不服从法律,而服从法律之外的大局。大局是政治家、立法者所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要求司法者在法律之外考虑所谓的大局问题,就完全有可能违背法律。如果强调司法服务于大局就可能因为大局已成为权力者手中的魔杖,正为地方权力者所任意诠释,一旦满足这样的大局,司法机关无疑会堕落为权力的附庸、奴婢。其二,司法的泛政治化还表现为司法者对政治的过于敏感。原本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法律程序加以解决的问题,但却因顾及政治因素而放弃严格的适用法律。例如,对于有些案件完全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受理的,却基于所谓的政治影响,而不予受理,置法律的规定于不顾。其三,人为地将政治作为司法运作的最高要求。在意识上沿袭传统的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的思维定式。习惯于政治思维,而不是以法治思维思考法律问题,解决法律争议。看似是司法机关,但由于政治思维方式的原因,往往是用政治的方式和方法解决争议,法官成为政治家,法院成为政治机构。以法律思维、法治方式辅以一定的具体事实,按照法律适用的规律解决纠纷,从而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从对司法的传统领导和管理组织机构以及专门大学的称谓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定式的强烈影响。其四,司法机关在政治上依然被视为是实现阶级专政的工具,为特定的阶级服务,这可以从司法机关特定的修饰语看到它的政治性。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提出了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这样的口号,还提出了要注重政治效果的口号。无论是注重社会效果、还是注重政治效果,都是试图逾越法律。
司法的泛政治化不是传统司法中完全独立的一个方面,而是与传统司法的其他特征彼此联系,彼此强化,相互牵扯的。司法的政治化直接强化了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非职业化、非公开化和社会化。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非职业化、非公开化和社会化是司法泛政治化的结果。因为政治化,就要求司法权力在外部和内部被行政化,以便实现权力的集中,这正是特定政治形态的要求。司法的政治化自然要讲究权力位阶的高低、大小,这与司法的行政化是天然契合的;因为政治化,地方化成为必然。地方权力作为地方政治的核心必然要求司法归顺、服从于地方的权力;因为政治化,司法也自然地排除了职业化或专业化,职业化可能使得权力干预受到阻碍,这是政治化所不能认可的,政治化就要求权力没有制约,无论这种制约来自哪一个方面,政治化与职业化是天生相互排斥的。在强化政治化的时期,也就必然发生司法机关的一把手可以是非法律专业出身,没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有知识、有经验的法官可以随意调离法院到司法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其他机关的干部可以任意地调入法院;司法的政治化使得司法会尽量避免其公开化,因为政治化强调的是政治诉求、政治利益的实现,讲究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对于政治而言,程序、形式都是次要的,政治从来讲究实质理性而非程序理性。公开化恰恰是手段、程序的正当性要求,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这显然与政治化是背离的;司法的政治化也必然导致社会化,政治讲究的是普遍联系和一体化。政治化程度越高,社会化程度也越高,泛政治化本身就意味着打破所有隔离,也就不可能强调司法机关的非社会化,反而会要求司法机关广泛融入社会,甚至走进社区,与社会发生广泛的联系,淡化司法机关本身的特性。司法的社会化必然使得司法机关难以与社会隔离,免受社会各种关系的侵蚀和干扰,无法做到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虽然从法社会学、法政治学以及后现代法学的角度,如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法哲学家昂格尔所言,法律与政治就是一回事,司法就是一种政治现象。但毕竟法律与政治有所不同,法律虽然不能与政治割裂,例如在制定法律的层面,甚至在有的情形下,司法也不可能完全离开政治,政治也必然会时刻纠缠着司法,但由于法律调整的范围还是相对清晰的、确定的,司法的规律、范畴与政治的规律、范畴毕竟不同,因此,我们应当尽量让司法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遵循司法自身的规律,避免政治的干扰和侵蚀,因此司法的去政治化是必要的,必需的。司法的政治化对于实现司法的公正,实现依法治国、法治社会是一种极大的妨碍,因此,司法的去泛政治化是司法体制改革所必须作为的事项。笔者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司法的泛政治化对于其他“几化”有着强化、甚至本源的作用,而司法的泛政治化又最不容易,或难以让人们意识到。
司法如何去政治化使司法回归于司法,要比司法去地方化、行政化、非职业化、非公开化、去社会化也许更难,因为去政治化的作业更多的不是组织、结构的硬件调整,更多的是意识、观念、理念上的,属于形而上层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更难,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调整予以配合。司法的去政治化还需要从政治入手,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人们政治观念、意识的转变。司法的政治化是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泛权力化的结果,因此,必须寄希望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去泛权力化、泛政治化。当然不是说,司法的去政治化需要等待整个社会的去政治化。既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那么司法的去政治化也可以作为社会去政治化的一个切入口,并由此推进社会去政治化,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往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也不时提出要进行、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但却没有触及司法的去政治化,因此,其司法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还发生了倒退,以至于司法不仅没有去政治化,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化,走向了反面,这是我们所必须吸取的教训。
写于2013年圣诞节,清华近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