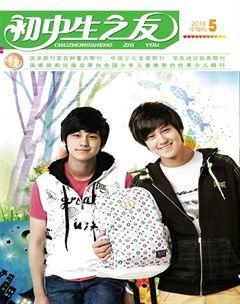“读书”主题阅读(二则)
(一)墓园里的读书人
○毕飞宇
法国人对图书的热爱我是知道的。大概在三四年之前吧,上海领事馆的法国总领事郁白先生来到南京,吃饭的时候闲聊,他告诉我,他就要离开中国了,最近刚刚买了一些中国书。我问他买了多少,郁白先生想了想,笑着说:“两吨。”
一个买书的人用“吨”来做他图书的计量单位,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这可能就是法国人了,做事和说话都要不同寻常。但是,就在不久前,我在法国参加了他们的第二十四届图书沙龙,终于发现了法国人最平常的一面,最自然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对图书的喜爱。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手捧书籍的法国人,地铁、街头、公园、咖啡馆、酒店的大堂,一句话,一切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们捧着书,神情是专注的、忘我的,但同时又是悠闲的、家常的、自足的,像呼吸一样,也可以说,像咀嚼一样。我在中国同样看到过许许多多的读书人,撇开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不说,我们的读书人大多是一些临近高考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些攻研或攻博的年轻人。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脸上都带上了“最后一搏”的庄严,是总攻,是全力以赴,是迫在眉睫,仿佛赌徒手中最后的一个筹码。筹码压出去之后,便放下图书,立地成佛。
不用不好意思,必须承认,从总体上说,我们的阅读要功利得多。关于图书,我们的汉语不是有一个最形象的比喻么:敲门砖。敲门砖,说得好。砖头是有用的,但是,面对“砖头”,我们缺少了一样最简单的东西,那就是日常的感情。
我还记得克罗德·巴彦先生带我去游玩的那个下午,克罗德先生六十多岁了,他把我们带到了贝尔拉雪兹公墓。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有阳光,却很冷。公墓非常辽阔,肃穆而又冷清。克罗德先生兴致勃勃,他把我们带到了巴尔扎克的面前,带到了普鲁斯特的面前。克罗德拿着地图,一次又一次为我们寻找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那同时也是刻在我们心中的名字。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石头下面那些“不朽的人”,不是。是公墓里头那些活着的人,是那些普通的市民,准确地说,是那些读者。他们坐在公墓的长椅上,安安静静地读他们的书。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他们有七十多岁了吧,也许还不止。他们的年纪让他们无限地安详,一句话都没有,他们就坐在很冷的阳光里,戴着手套,一个人的手上拿着一本书,坐得齐齐的,正正的,用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常说的话说,“很乖”,“很听话”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是枯寂的还是幸福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呢?是巴尔扎克还是普鲁斯特?是《长寿秘诀》还是《怎样安度晚年》?我不知道。我多么想知道。是怎样的一本书让他们如此的寂寞,如此的安详,如此的满足,如此的幸福?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我多么希望在我百年之后有一对年老的夫妇静坐在我的墓前,捧一本莫言的书,捧一本苏童的书,或者,捧一本我的书。我希望那本书是我的。我想我会微笑。
(选自《读者》2012年第4期)
赏析:毕飞宇不愧是一位眼光敏锐、善于思考并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大作家。他从法国总领事郁白先生在离开中国时买书“两吨”之事谈起,谈到他在异域见到的法国人热爱读书的震撼人心的情形,进而引起他对当今中国人读书现状的深刻思考。读后引人深思,促人警醒。
(二)“书虫”父亲二三事
○刘永红
父亲今年已届72岁高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
父亲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习惯——“读”书。只要手中有书,必定旁若无人,口随眼动,振振有声,抑扬顿挫。时常,还能听到他长时间“读”书而出现停顿吞咽的声音。看他戴着黑框老花镜,一字一句从口中读出,那种痴痴的样子,我极为不解。有时候忍不住在父亲“读”书正酣之时打断他:“人家都是安静地看书,您却总是大声朗诵,不口渴吗?不觉得累吗?不怕吵着人家吗?”可他总是煞有介事地答道:“读书就是要大声‘读,不读出声还能叫‘读书吗?”弄得我无言以对。回味着他的话,或许还真有些道理,想想我们每次临考之前,哪次不是通过大声朗诵以增强记忆呢!
记得小时候,姐姐从省城捎回一本《宋氏三姐妹》。父亲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地念了一遍又一遍。夏夜纳凉之时,父亲经常为我们娓娓讲述书中的精彩情节与点滴趣闻。可是,这段好景在我以优异成绩考入镇重点初中之后便结束了。入初中没多久,适逢学校打算组建图书馆。由于经费非常紧张,学校无力添置藏书,便发动学生自愿捐书,多多益善。作为积极分子的我,回家后翻箱倒柜,竟然也“搜刮”出近二十本。其中自然包括父亲最喜爱的《宋氏三姐妹》。为此,三年初中生涯,我没少听父亲的念叨与埋怨。我很是后悔和自责,可脸皮儿又那么薄,终于没敢找老师把书要回来。
后来,我顺利地进入大学,继而读研、读博。在外求学期间,虽然跟父亲的相处时光甚少,然而,偶尔回家还会感受到老人家对《宋氏三姐妹》的念念不忘。谈起其书其事,竟然还是如数家珍。博士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人民出版社,经济上不再如学子时候那般囊中羞涩,于是就琢磨着给父亲买一本《宋氏三姐妹》。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宋氏三姐妹》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出版社正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我很幸运地从责编老师那里获赠了一本市面上早已售罄的《宋氏三姐妹》。抚摸着熟悉的封面,心情既激动又喜悦!我当即把书给父亲寄了过去,随寄的还有一个放大镜。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收到书,小心地捧在手上,口中喃喃道:“就是这本书,就是这本书……”我顿感欣慰,心底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
前两年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无意之中,我听到父亲与我那刚上初中的侄子的一段谈话。大意是父亲让侄子跟他的同学好好说一下,先还一本书,另外一本书过两天看完了再还。我心头一怔一乐。“怔”的是想起了自己刚上初中的时候把父亲的书捐给了学校,而现在侄子也上了初中,却是替他借书;“乐”的是,这么多年来父亲阅读的习惯还完美地保持着。后来,我那颇感无辜的侄子告诉我,自己经常跟同学换书看,每次,只要被老父亲发现,必定会打一个书“劫”,等他看完才还。毕竟已是古稀之年,父亲“读”书的进度慢了下来,常常延期还书,害得侄子经常要颇费口舌跟同学解释。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书虫”。我常常想:若非幼时家境贫困而过早地走上了为家庭生计而奔波的艰辛之路,或许,父亲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
(选自2013年4月30日《光明日报》)
赏析:这是一篇写人的散文随笔。作者撷取父亲与“书”有关的生活琐事和特定情景,生动而形象地刻画出父亲这一“书虫”形象。文章语言质朴,文句流畅,对父亲的敬佩和赞美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有很强的感染力。
(荐文与赏析:向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