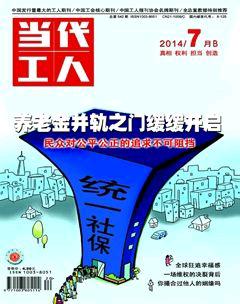执着于工业遗产保护的人们(三)
初国卿
在著名的纪录片《铁西区》“工厂”结尾部分,轧钢厂开始拆除设备,推平厂房,巨大的钢架被电焊枪切割下来,在钢架轰倒的刹那,积存七八十年的灰尘,瀑布般落下。现实里,人们不知灰尘散尽的铁西会是个什么样子。
10余年间,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建设之前,铁西工业遗产保护最早建成的是“两馆”,即铁西工人村生活馆和铸造博物馆。 2007年5月,当在建的铸造博物馆5号展馆“铁西工业展示区”里,原车间的一面南墙厚厚的灰尘也如“瀑布般落下的时候”,砖墙外上个世纪70年代抹了一层水泥的黑板报也开始脱落。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斑斑驳驳的脱落处,竟露出了彩色壁画。当时在现场具体指挥建馆的区文体局党委书记侯占山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展品。于是带人一点一点清除那层水泥黑板,最后露出壁画的全貌。这幅作于1968年的大幅壁画是用当时的广告颜料所绘。画面近景为高悬的两只大红灯笼,灯笼下的花丛中,左面是一位擂鼓的女工,右边是一位手中展开喜报的男工。女工穿着红色上衣,双手举着鼓槌在奋力擂鼓,神情激昂,连红色的上衣都欢快地舞动起来。男工则一身工装,脖子上扎着白毛巾,脸上漾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远景则是大地上一排排高炉和电塔。画面上方写着“1968第二季度先进生产工作者”,女工旁边写着“革新能手”,男工面前写着“质量能手”。这幅车间壁画正是那个“火红”年代里工人们不忘“革新”,不忘“质量”,“抓革命,促生产”的生动写照,是那个特殊时代里的真实记录。最终这幅壁画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壁画的来历经过两年多的查询,终于在2009年3月30日找到了当年的作者。他叫潘维华,1997年退休,退休前始终是铸造厂的吊车工人。当年创作这幅画时是1968年,他27岁,风华正茂。铸造厂车间搞节约标兵和铸件能手竞赛活动,按工会领导的指示,他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了这幅“欢欢喜喜送喜报”的壁画。如今这幅壁画旁放上了潘维华的照片和创作背景介绍,已经成为博物馆里一件生动的展品。
铁西有一大批像侯占山这样从官方到民间对工业遗产悉心保护、着力研究的人,才使铁西的工业遗产保护做出今天这样的成就。这些人中有区委书记,有局级干部,还有普通的工人和民间自主谋业者。他们在为铁西的工业遗产保护认真规划、精心选项,甚至奔走呼号。
2002年12月,时任铁西区委书记、区长的谷春立,上任伊始第一次召集的会议就是新区规划定向讨论。会是在区政府食堂二楼召开的,时间是下班以后,参加会议的人有相关的局长,还有同济大学的专家。这样的会召开过多次。最后在2003年出台的《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发展规划设计咨询》中的“改造及调整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汇总表”里,一共列了90个改造地块,其中的15块明确定为“保留”,这15个保留地块主要是作为工业遗产保护的。
2006年以后,谷春立的继任者李继安上任之后首先落实的就是工业遗产保护,并且创意和落实了三件事:一是接收了原在沈阳植物园的老火车头,于铁西体育场附近建立了蒸汽机车博物馆;二是保留了原铸造厂的翻砂车间,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铸造博物馆;三是建立了工人村生活馆,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工人生活情态。三个项目的完成,铁西的工业遗产保护即初见成效。
铁西区规划无疑是在生产与文化建设之间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体现了那个时期的领导者登高望远的筹谋。
铁西区有一位叫宋敬泽的沈阳市劳动模范,原来就是沈阳重型机器厂的职工,后来离职做平面设计工作。但他心里却有着割舍不断的工厂情结和对工业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工业遗产保护志愿者。哪家工厂拆迁,他就会去看一看,先是拍照,留下了大量的铁西老工业的照片资料,许多需要老铁西照片的人都去找他;再就是寻找有价值或带有历史文字或文化符号的当作废铁处理的老物件。听说沈阳重型厂要拆除了,他觉得最有历史特点与工艺流程的几个老车间,还有那些最有价值的老物件都应保留下来。如日伪时期的天车、铸有“1936”字样的铸铁管、“回字形”砖甬路、改作出钢提示钟用的航空炸弹头等等,都是极为难得的工业文物。他为此找有关部门寻求对这些物件的保护,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就给区委宣传部长汪诚的手机发短信,请宣传部长支持他的想法。汪诚接到宋敬泽的短信后,大为感动,同时又深感工业文物保护的紧迫性。于是马上给区委书记李继安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尽快组织人力物力抢救如重型等搬迁工厂的工业文物。区委书记当即在她的报告上做出批示,最终使一大批工业文物抢救下来进了博物馆。
工业遗产保护队伍中还有一位商国华,是在铁西长大,曾担任过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城建局局长、建委主任、教育局长、人大副主任,三十年来坚持以诗歌写铁西,写铁西的大工业。他在《工业文化遗产是沈阳长线发展的根脉与城市再生的魂魄》一文中说:“如果我们认为旧建筑影响了市容,都去与高楼林立做比较,那我们沈阳还有什么个性呢。比楼房,我们比不过上海;比园林,我们赶不上苏杭;比古城,不能跟西安同日而语;比水乡文化,又不及周庄;比红色旅游,我们又比不过江西、湖南。我们比什么呢?那些大量的不能复制的老厂房、老生产资料都是不可再生的凝固语言,是我们沈阳的独特历史资源,是我们与其他城市比较中,能够引为自豪的得天独厚的元素。工业文化是我们的个性,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应该向其他城市传达的精气神。”有人主张将铁西的工业铁路专用线全部拆掉,他急了,利用一切机会,找领导谈,找专家谈,在不同的会议上谈,尽情地阐述保留铁路专用线的理由。主张将这些铁路专用线利用起来,既可做景观,也可将来做为社区交通或是旅游设施。铁西的大部分铁路专用线保留了下来。
工业遗产保护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尤其是在当下,工业遗产的保护是与土地出让,与财政收益,与GDP,与短期的民生需求相矛盾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利益的博弈。要远比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保护北京古城墙时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
当年建铸造博物馆时,高大而宽敞的翻砂车间成为1号展厅。厅里曾悬挂着160多面厂旗,那是铁西当年最有名的大企业的标志。这些企业如今大部分已搬迁,有的已经不在了。每一个到博物馆里的参观者都会仰头凝望这些厂旗,那是一部工业铁西的创业史、血泪史和光荣史。这个厂旗集中悬挂的创意就出自建馆现场指挥侯占山,他为此付出了许多精力。侯占山曾一家一家地走访,没有厂旗的他督促设计制作出来,企业不在了的厂旗就到民间寻找,或是请老工人回忆当时的厂旗是什么样子的,进行重新复制。就这样,经过努力,使今天的铸造博物馆有了160余面厂旗飘扬的壮观与震撼。
那些日子里,侯占山带领一班人每天脑子里想着的都是铸造博物馆,都是工业文物的搜集。早春的一个傍晚,侯占山下班回家,在暮色之中,他隐约看到路边一个人正在修理拖拉机,职业般的敏感让他趋前细看,正是博物馆所没有的两轮手扶拖拉机。于是他异常兴奋,帮着修车的老农动起手来。修好后,他说明身份,请求老农将这台拖拉机卖给博物馆。老农为侯占山的诚恳所感动,几天后就将拖拉机开到了铸造博物馆里。
刘放原是铁西区档案馆馆长,当年建铁西区工人村生活馆时就是她具体负责。为了建好工人村生活馆,她带领档案局全体职工在工人村及附近走访了3000多个家庭,从而才有了现在工人村生活馆里13户不同层次典型人家的再现。在搜集生活馆展品的那些日子里,刘放每天都领着人起早贪黑逛旧物市场、动迁市场和古玩市场,着迷一般搜寻工人村老物件。如今,谈起工人村生活馆里的每一件展品,她都会如数家珍般地说出它们的来历和背后的故事。 “那时候,人家都称我们是‘破烂王。但现在想想,这个‘破烂王做得很值。”是啊,正是因为有了她们这样一群“破烂王”满世界地寻找,才使今天的工人村生活馆丰富而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原生态,为铁西的工业遗产保护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立体资料。
现任铁西文化馆书记的高巍,当年在筹备铸造博物馆时也像一个收破烂的,不过她主要收“旧钢铁”,因为她当时负责征集车辆。为了将铁西当年工厂里的车辆尽量丰富地征集上来,她特意在报纸上做了一批小广告:收旧车。于是许多人就同她联系,于是通过这样的渠道找到了许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铁西生产的车辆。除此之外,她们还开着大卡车,扮作收废铁的,到抚顺、法库等地寻找展品。就这样,她们找到了11辆不同时期的从东方红牌到白山牌的自行车,还有200余辆各式拖拉机、农用汽车、推土机、吊车等,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展品。
前面说到的给宣传部长发短信的劳动模范,是一位敦实而淳厚的年轻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2009年8月沈阳高温35度的那几天,他几乎每天都在重型厂里,看着那几件他认为有价值的老物件,唯恐拆迁的人不知道将它们装上卡车当废铁拉走。他说这些东西如同我的命,如果它们不保,就如同我失了魂一样。问他为什么这样执着于工业遗产保护,他说:“起初我自己也问我自己,是不是因为我感情用事,是不是我太偏激了,但是,通过跟许多老工人、老领导交谈,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我相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厂子的历史价值确实十分重要,如果就这么拆了,不要说沈阳,就是全中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工业文化遗产了。”
在铁西,像宋敬泽这样热爱和自觉保护工业遗产的年轻人还有许多。他们聚集起来,一起搞工业遗产摄影,一起为工业遗产保护奔走呼吁,还在“沈阳网”的“新闻快报”版上开了一个保护铁西工业遗产的专题,发表了许多颇有见解的观点以及大量图片,并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