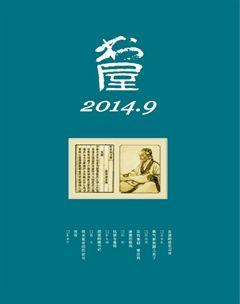“老苏”的江湖
秦颖
我不记得为什么或什么时候起开始称他“老苏”,肯定不是带有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说的“时代味道的一种称呼”,对我来说通常是平等随意谈得来的都会如此称呼。老苏名福忠,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现已退休。
记得是2000年上海的英国文学年会上认识了老苏。第一印象是为人颇热情,又有些大大咧咧的老哥;对会上讨论的英国文学文化的话题,他都有自己的看法,会上说得不多,会下跟我们倾囊而谈,可惜我却听不太懂,他的语速快,山西口音还重。之后去北京,总会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坐,会会熟人,自然要去看他,但这时候我们的来往并不多,倒是听有人说他这人不好好工作,尽干些私活,还在自己编辑的丛书里夹带私货。
后来一位师长推荐我看一篇文章:《我认识的肖乾》,并说极妙!作者苏福忠。我找不到,直接写信给老苏讨要。难得读到这么过瘾的文字:语言性情,细节丰富,特别是那时不时出现的农民视角的观察入木三分,既亲切亦复可爱,我仿佛看到了背后那个性兀立、快意恩仇的老苏。在肖乾先生去世后,写这样的文章,需要相当的勇气。那之后,我们好像自然亲近了起来。我的影像札记开笔之后,老苏曾建议放开来写,不要太多顾忌,“人做事情,实话实说、真事真做,是最有底气的,也是比较省麻烦的方法”。但我却是达不到他这种境界。
后来我们渐渐熟络了起来。到北京组稿,与作者聚餐时,我会邀他出来聊天,他也多次邀我去他家吃他亲手做的山西手擀面。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邀吃“苏式面条”,可是特殊待遇。我曾一度想在外国文学名著上出出新,搞插图本(不是一般的点缀,有点左图右史,图文互证的味道),四处搜罗插图。他说贾辉丰家里收藏有大量的插图本原著,介绍我们认识。我张罗现代作家、学人的大家小集,版权联系困难重重,他又给我推荐吴学昭老师。若有一阵子没联系了,打电话给他,他会说把我忘了吗,没电话,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对于我迟迟没有应邀到家里吃面,也许他有些想法。当我知道他与牛汉、绿原住在一栋楼里时,尝他的手擀面的机会才水到渠成了。可他也是嘴不饶人:要不是老牛他们跟我打邻居,你什么时候才来吃我的面条呢!他就是这么个一片热心、心直口快的人。
在我看来,这辈子老苏只做过一件事:做编辑,做外国文学编辑,做英语文学编辑。其他的一切都附着其上,是副产品。他曾说:“编辑有为人做嫁衣裳之嫌,但只要有心,完全可以有很不错的沉淀。”
老苏编辑的书小至《黑狗店》,大到《伍尔夫文集》和《莎士比亚全集》等,简至《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早上》,繁到《外国戏剧百年精华》和《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等。对项星耀《米德尔马契》译稿的反复掂量,几乎是挽狂澜于既倒,颇能反映他的认真、敬业和水平。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还做翻译。在谈到他为什么做翻译时,他说:做外文编辑,好稿子看了不少,从中获益匪浅;差稿子也看了不少,从中汲取了不少教训。看好译稿,舒服,令人兴奋;看差译稿,别扭,生气。“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绪转换中,翻译的活而渐渐地进入了我的业余时间”。他的译著有《索恩医生》、《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瓦尔登湖》、《红字》、《爱德华庄园》、《兔子富了》、《1984》等。他还有三本著述:《译事馀墨》、《席德这个小人儿》和《编译曲直》。前一本是编辑翻译作品的积累和翻译经验的总结,后一本是他的外国文学评论集,第三本是对编辑工作和翻译行为的看法,以剖析实例为主。
《译事馀墨》不但功夫深(几十年的卡片积累),而且颇有见地。如严复“信达雅”,他认为无关理论,而是标准;关于意译和直译,“‘意译之说早已不能成立,更不能成为标准。‘硬译如果是指‘信,但说无妨;如果就是字面意思,也难成立”。里面充满着翻译实例和编辑家的真知灼见,这种意见的表达也是充满了自信:“目前不少人把莎剧当作典雅的译事来做,把莎士比亚的语言当作优美的文体,以为只有用诗体翻译他的作品才能接近莎士比亚,这是一种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看法,无知得不能再无知的观点。”
《席德这个小人儿》取名很调皮,作为一本厚实的外国文学评论,也许换个书名更好些。对外国文学文本的熟悉是老苏的看家本事,也是让人敬畏的功力。我很喜欢用作书名的这一篇,姑且看作他观察人性的学术文本;莎士比亚系列他挑战的是中国莎翁研究崇拜多于剖析研究的浮躁之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长短”体现了他从文本出发,不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等等。然而,这一切在一开始时并不容易。他三十六七岁时,为编辑的一本特罗洛普中篇小说集写的前言压了一年多后,改为后记,书才得以出版的遭遇,并没有让他止步。“想明白了,就不想听之任之,哪怕面对被尊为什么老权威的人。所以,一旦有机会写个前言或者评论文章,我是绝不放弃的,不管能否发表。在文化问题上,不是你镇压我,就是我镇压你,但是谁更接近真实,谁就更强大,更持久”。“要生存,就得有环境。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写点什么,自然还是为了提醒自己别懒惰,别人云亦云”。这么一头倔强的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我佩服。
农民出身和英国文学似乎是老苏这辈子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而它们又可用一个词串联起来:生存。这是我跟他交往、读他的书和文章留下的印象。他在《随笔》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恒产者的文化沉淀》,他通过一本书的评价和自己早年的经历得出了无产者无文化,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心才能沉淀积累文化的结论。虽说观点并不新鲜,但从自己的经历和家乡的人文历史来谈,具体、丰富、深刻而好读。
2006年,去山西参加一个传记文学的学术会议,遇上老苏,会后他邀我去老家晋东南走走。事后来信,想听听我“对那里的众生在这个体制下的作为,有什么感受”。他说:“人的生存弹性太大了,五六十年代那么大的政治高压竟也可以承受,如今环境这么宽松,也不知如何爱惜;好像百姓只能跟着洪流走。”他始终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家乡,始终不能放下他的家乡,想写一写他熟悉的人和事,以及他的思考。他认为家庭背景的不同,决定文学写作的绝对质量,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刻性跟他的家庭“从高位跌落到低位面对社会和人性看得透彻”相关。其实从社会底层往上奋斗的人,对人性,对世态也会看得更透。老苏很多的文字,都透露出这种敏锐和深刻,同时保持了一股子山野之气:endprint
“托尔斯泰年轻时‘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要客观得多。人老了经历丰富,吃盐比年轻人吃粮多,抛撒起沉积肚里的盐来,那可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劲头了。”《托尔斯泰VS莎士比亚》
“那时候没有一点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我看事想事还是一副直肠子。老萧的话在我的肚子里七上八下窜动了一十五次,还是捉摸不明白,就还是按农村人的习惯寻思:这个人怪呀不怪?……按我老家的话说,这不是只让你烧香敬佛爷,不让你翻书念真经吗?”《我认识萧乾》
我一直感叹他的文字的直率,本真。对此,老苏自己有一个解释:“到了五十岁,我才对自己的性格、脾气等很个人化的东西回想了一下,感觉是三分天意,七分成长环境吧。本质上很自由,可能源于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父亲从小管理太宽松,因此对妨碍自由的东西感觉早,研究早,又正好和英国文化鳔上了,那里是现代自由观念的发源地,和那里的文化很合拍,这对我写点东西很管用。自由的前提是独立性格,这也是我强项,让不少人不习惯。”
好一个“和英国文化鳔上了”,依我看是跟莎士比亚鳔上了。他给我的信中说:“关于莎士比亚,恐怕是我今后持续不断的活儿。”这些年,他业余研究莎士比亚,颇有成绩,已经结集,准备出版。集子分四个部分:莎士比亚面面观,深观莎士比亚,莎剧翻译观,莎剧的背景与提要。我有幸先拜读了他的序言。一上来,他就说“怎么才能尽快地接近莎士比亚呢?学习英语。只要坚持学习英语,莎士比亚这个词儿迟早会遇上,一旦遇上,就不单单是一个单词,很快会变成一种文化。”这是在写他自己。“莎士比亚成了我衡量文学与比较其他作家的标尺,也成了我认识人生的经历的纲领。”对人性的复杂多面的观察批判,是他这一辈子体验甚多、也关注甚深的一个方面,这一点,他在莎士比亚这里取得了共鸣:“莎士比亚最擅长的就是把人类缺陷中最深层的东西往外扒拉,越私密越好,越隐蔽越深刻。人这种东西很复杂,好的地方怎么赞扬都不过,坏的地方怎么批判都不解恨。”
我特别喜欢他在序言里讲的他寻访莎翁故乡斯特拉福镇的故事:“一绺白云从远处升起,越升越高,越升越直,像一根飘动的旗杆在和那教堂尖顶一争高低。渐渐地,那根悬挂天空的旗杆头变得很尖很尖,不远的下方几丝白云飘飞起来。我正纳闷儿横空出来一杆晃动的红缨枪,莎士比亚的名字就跳了出来。尽管那时阅读莎士比亚的剧本还只限几个著名的悲剧,但是因为觉得他的名字奇怪,我查过字典,也读到一些资料,知道它有‘晃动的枪之意。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心脏有一点跳动,两腮觉得热热的,望着那块形状怪异的白云的目光一刻也不想离开,生怕转眼之间它会幻变成另一副模样。”
“快意恩仇”的评价,老苏不一定认同,把他的独立性格打上了江湖气的标签,有些随意。但江湖气是我推崇的风格,我理解为敢作敢当。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说,他的江湖气并不是没有原则,他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勇气。这一点,在他纪念牛汉的文章中就有表现。他很敬佩牛汉,但不客观、欠准确的吹捧夸赞,即使是应景的场面话,也是不能苟同的。
似乎说得太多了。我不知道我的这篇东西是不是有主题先行之嫌:江湖气。草根出身的他,凭一己的努力,在编辑出版、翻译研究、散文随笔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的学问,见识,爽直,无城府大概是吸引我,跟他越走越近的原因吧,我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