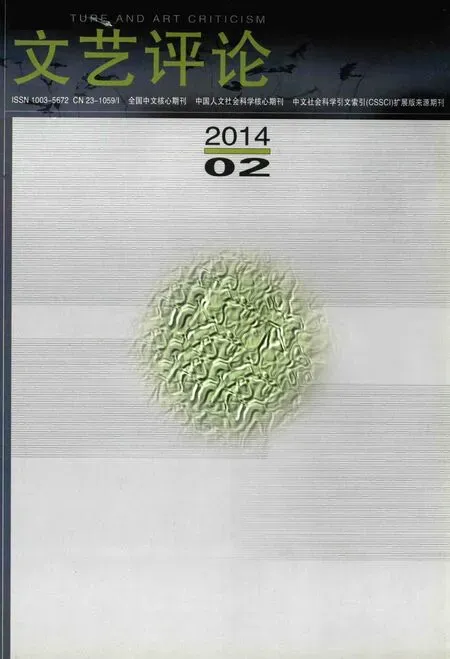论《周书》中的孝观念
罗 山
《尚书》所存篇章真假不一,然历代学者对其《周书》部分向无多大疑义,王国维认为《周书》的全部篇章“皆当时所作也”①梁启超也认为:“从《牧誓》到《秦誓》叫做《周书》,真伪绝无问题,年代可照向来的说”,可看做是周代的作品。②因此,对周代思想观念的研究来说,《周书》显得弥为珍贵。本文即以《周书》为据,对其中的孝观念进行探究。
一、《周书》中孝字释义
首先,本文对《周书》中的孝字进行文字上的梳理,以此来弄清其大概的涵义。传世《周书》除去伪古文,《康诰》、《酒诰》、《文侯之命》四篇中有“孝”字出现。③《文侯之命》为东周时期的作品。《康诰》、《酒诰》所记为西周初年之事。对《周书》中孝字的考察,主要就集中这两处。其中之一在《康诰》中: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以词类来看,孝友连文,在西周早期金文中也出现过如《历方鼎》:“孝友唯型”。唐兰断此器为“此器以书法论,必为康王无疑。”④康王是继成王之后第四位周王。两者相对来说相隔不远,以此来看《康诰》中“孝友”于西周早期已经存在。
“不孝不友”句后,周公对此进一步解释了一番。传统的解释皆以《说文解字》“善事父母”的观点来立论,以为“不孝”针对父母。仔细阅读可以看出,文中“不孝”指的是子不“祇服厥父事”而伤了其“考心”。此外,“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与上句并列,再参考《康诰》中不友的内容,此句应该是指不孝之行为:父不能字(慈)其子,也视为不孝。不孝的对象是祖考,也能解释得通;父对子的慈来自于对祖考的孝。无论在世的子还是父,其不孝的后果是针对逝去的祖先而言的。
以“考”为父死后之专称者,现在所能见到的解释最早出现在《礼记·曲礼下》之中:“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嫔。”《尔雅》释“考”也以此为据。古来学人对此都有异议,如清代的邵晋涵在《尔雅正义》中对“考”有一番辨析。“古者父母,考妣不以存殁而有异称,……汉人犹知雅训,自汉以后遂以为存殁之殊称矣。”⑤明辨以“考”专称逝去的父亲,是汉人受《尔雅》的影响之后的事情。笔者认为,“考”虽然在先秦时期并不是对逝去父亲的专称,但在这仍是针对祖考而言。根据就在“子弗祇服厥父事”中的“服”与“事”上。
“服”杨树达言:“古文‘服’字皆为职事之义,故旧诂多训为‘事’。此‘事’当如今通言谋事之‘事’。”⑥《尔雅》“服,事”;《大雅·荡》“曾是在服”,毛《传》释“服,服政事也”。金铭文中也常见此“服”字,如西周早期的《周公簋》就有“王令荣眔内史曰,匄邢侯服。”杨树达解释为“此王命荣及内史与邢侯以职也。”⑦也用于继承祖或者父职之事,如西周中期的《趩觯》“更氒祖考服,赐趩织衣。”即继承“考服”,父之职位。
再回到《周书》,“服”字也有职事之义,有:《大诰》“大历服”;《康诰》“乃服惟弘王”,“乃大明服”;《酒诰》“越在外服”,“越在内服”,“惟服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召诰》“王先服殷御事”;《多士》“亦惟尔多士攸服”。亦有作动词的服字,为奉行和从事,有的与职事有关,有:《多士》“有服在百僚”,“有服在大僚”;《无逸》“文王卑服”。有的与天命有关,有:《康诰》“明乃服命”;《召诰》“兹服厥命”,“有夏服天命”,“王乃初服”,“知今我初服”。此外,《康诰》“服念五六日”,服释为“念”;《顾命》“相被冕服”指的是衣服;《吕刑》“五罚不服”,“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服通也,治也”。⑧以上是《周书》西周文献中除了《康诰》“子弗祇服厥父事”和《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两处外,服字的解释。服的基本意义就是“职事”,作为动词也基本上也是就职事而言。吕祖谦言:“为子职不敬顺其事,反大忧伤其父之心。”⑨上半句的解释就正切合服所代表的涵义。《尚书纂传》也解释道;“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业。”⑩将“服”的内涵揭示出来了:“服”针对的“事”,并不针对父而言;服的对象并不是以后孝所常言的“善事父母”,指的是父的“职事”,伤的是“考心”。
“事”也有特殊的涵义。《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洛诰》“予惟曰‘庶有事’”指的就是祭祀之事。《周书》中其它“事”字,其中以“御事”词组作官名者常见于各篇,不一一举例。作官名的有:《立政》“作三事”,指的是三事大夫。此外有通“士”者,有:《金藤》“乃问诸史与百执事”;《酒诰》“有正、有事”,“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矧惟尔事”,“弗蠲乃事”。再泛指职务、职事者,有:《多方》“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尔惟克勤乃事”;《洛诰》“我惟无斁其康事”;《立政》“乃克立兹常事”,“立事”;《立政》“尔惟克勤乃事”。有指“王事”者:《大诰》“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洛诰》“及抚事如予”,“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君奭》“故一人有事于四方”。除这些外,与战事有关:《大诰》“我有大事”;《康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汝陈时臬事”⑪;《多士》“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康诰》“惟曰未有逊事(指臬事)”;《梓材》“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还有,《牧誓》“今日之事”指的是伐商之前的军事舞蹈,亦与战事有关。与祭祀相关的有:《金藤》“不能事鬼神”;《立政》“以敬事上帝”。以上对事字的统计,基本上有三种意思:一是与“职事”有关;一是与战事有关;二是与祭祀有关。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观念相吻合。那么“父事”之事,也不出此范围。具体指哪一个,再看《周书·酒诰》中另一则材料。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酒诰》指出“用孝养厥父母”,实际上“孝养”词组不见于其他的西周文献与铭文。铭文中中常出现“用享用孝”、“用孝”的句式,“孝”与“养”分开。“用孝养厥父母”可以句读为“用孝,养厥父母”。金文词句与《周书》词句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因此以金文作参考,《酒诰》中以“用孝”为词组是行得通的。
“养”在西周也并不限于父母,如《小雅·黄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谷”马瑞辰训为“养”。⑫对象是妻子。《小雅·我行其野》“尔不我畜,复我邦家”。“畜”也有“养”的意思,对象也是妻子。此外“厥父母庆”其“庆”也有深意。如:
《小雅·楚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
《小雅·甫田》:农夫之庆,报以介福。
《小雅·裳裳者华》: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大雅·皇矣》: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大雅·烝民》:庆既令居,韩姞燕誉。
《鲁颂·閟宫》: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
诸“庆”字皆与祭祀有关。“厥父母庆”以往常释为“其父母喜庆”⑬并没有揭示出,“庆”所具有宗教意蕴。下一句为,“自洗腆致用酒”。《酒诰》是周公下的戒酒令,据《尚书正义》解释“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挈厚,致用酒养也”。⑭《酒诰》引文王的教谕“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祭祀时饮酒才被允许。如以《尚书正义》的解释,就与文王的话有矛盾。“自洗腆致用酒”可以解释为“子涤器,陈献丰盛酒食,以之祭祀祖先,祭祀后父子与祀者一同畅饮”⑮所以,综合考察《酒诰》中的这一段,“事厥考厥长”,这个“事”落脚点是与祭祀有关。
“养厥父母”之观念在西周即有之,但在当时并没有视为孝行,与养其他人一样,只是某种公认的行为规范,与后世有特定伦理涵义的“孝养”不同。“用孝”在当时指祭祀活动。《酒诰》中“奔走事厥考厥长”,这里的考与长并列,指生父。其“事”应该是“戎与祀”中的“祀”,“用孝”指的是祭祀祖先;再则,“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祭祀用酒,更是祭祀之“事”的具体行为。
总之,《大诰》中“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的“考”是指死去的父亲或者祖先。“服”指向的是“事”,不是“父”。而“事”,结合《酒诰》的分析,主要是祭祀之事。不做好祭祀,所伤的是祖考之心,这应该是“不孝”在《周书》中的涵义。《周书》以“不友不孝”为罪大恶极,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中国封建社会以“不孝”为十恶之一,涵义与《周书》原意有很大的差别。
二、孝观念的提出与殷鉴思想。
上面从文字的梳理揭示《周书》孝观念的基本涵义。孝是周人原创的观念,而为什么周人会提出这样的观念呢?在《周书》中能找到一些线索和启示。
笔者认为《周书》的创作和编撰者是政权的持有者,是王官文化以及史官文化的代表。其经历和地位影响到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具体的经验教训。《康诰》中“不孝不友”的提出,并不如后世的思想者那样专注于人性的辨析,或是从报本反始等情感中体味出来的;其源起来自于历史教训。探寻《周书》提出孝观念的缘由,可以从“殷鉴”思想出发。
《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周之际的历史剧变和社会动荡,激发了周初统治者们的感叹和思考。亲身经历了殷周之际社会剧变的武王、周公、召公等政治家,对殷亡周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殷之乱败成为他们活生生的教科书,就如周公对召公奭所言的:“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殷)乱明我新造邦”(《君奭》),《周书》中的《康诰》、《酒诰》、《召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都讨论过夏商兴衰成败的历史。《酒诰》言:“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周公引古人言,人可以从水中获取自己的形象,但更应该是从人民中去了解。周公发展了这样的观点,提出要以商殷的失败为监,即借鉴。
鉴于殷商的失败,周人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如殷末风气奢靡,纣王放纵淫乐,酗酒乱德,骄奢淫逸等,在周人看来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周书》中周公反复提出要戒酒无逸、要修德勤政,其举的反面典型就是“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哪一篇)郭沫若总结甲骨文“田游”专类时议论道:“每日一卜,或隔三日一卜,而所卜者皆为田猎之事。殷王之好田猎,诚足以惊人,《无逸》谓殷自祖甲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了从之。’足见并非溢恶之词。”⑯从这一方面来看,《周书》举殷末之恶习是有所根据,也是有所针对。
以此看《周书》中“孝”的提出,是否也具有殷鉴的意味呢?特别是《康诰》所提出的“不孝不友”是否也是如此?《牧誓》中有一段武王的话: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结合其它的史料,商王受的罪行可以归纳为:宠爱妲己,听妇言;放弃了对祖先的祭祀;抛弃了父系和母系亲族,而重用外人;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这些武王站前的动员,都具体的指出了商王失去天下的原因。“以史为鉴,人们必须首先集中注意于历史上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越是真人真事,活灵活现,可供后人借鉴的内容也就越丰富。”⑰在战前这一段控诉就以活生生的事实来激起人们对商王的痛恨。《牧誓》这部分内容,实质上指责商王纣没有处理好族群内部的事务,选用的不再是父系和母系亲族内部的人,而选用了“多罪逋逃”;前者是与殷王同族或者“婚友”(《商书·盘庚》),后者却是商王纣自己的亲信。
笔者认为,“不孝”的提出正是针对于“昏弃厥肆祀弗答”;“不友”针对的则是后面诸事。商纣王“昏弃厥肆祀弗答”,即指商纣王废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这与商代先王“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理解《周书》中的孝观念,也与上面文字释义相合。孝最基本行为是祭祀祖先;而友所涵盖的范围就要大得多,通过联姻,基本上众多的氏族都可以纳入友的范围。
以史为鉴,周人不仅对夏商的历史进行反思;西周初年发生的叛乱也提供了更为现实的教训。武王灭商之后,封纣之子武庚,而武庚却企图恢复殷王室,与管叔、蔡叔联合起来举兵叛周。周公作《大诰》,出征平叛。平叛后迁殷民,作《多士》、《召诰》。周公针对殷遗民中与周为敌者,重申天命,处处以天命压制殷人。自家兄弟的反叛,给周公敲响警钟。军事的镇压只是暂时征服,而一个稳定的秩序需要王朝上下共同遵行基本原则。传说中周公制礼乐正是在平定叛乱之后。《康诰》提出“不孝不友”为元恶大憝,成为西周时期宗族中非常重要的原则。
三、孝观念的推行与天命观的改变。
以祖先为对象的西周之孝,在思想领域还与天命观的改变有莫大的关系,这一点在《周书》中也有体现。从思想源起来看,天命观的转变和历史观的转变应该是相辅相成。《周书》中周公常常感叹“田棐枕”(《大诰》)、“天难谌”(《君奭》),纯粹的天命难以揣测,使得周人转向他们亲身经历的领域——周族兴盛的历史过程。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周人有天命不可靠的认识,是以史为鉴的结果。另外越是感到天命不可靠,就越要从人事上寻找成败得失的契机,从而越发重视以史为鉴。”⑱
从《周书》来看,周公对本族人谈话常常是感叹天命难知;而对于殷商遗民,周公对天命的论述可谓斩钉截铁。以《多方》为例,文中控诉夏商之灭亡不是天命所能左右“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一切都是夏商咎由自取,“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闲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天命丧邦是因为人的行为,而天命兴邦也取决于人的因素。殷人多年的统治亦在于君王之勤勉:“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酒诰》)周人革殷之命,是因为“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多方》)在周人眼中,殷初几位商王皆勤政惠民;对商人历史回顾中,也褒扬商时的几位贤王。周人用自己的天命观来重新构建殷人的历史。对历史的建构支撑着周人对天命轮回的判断,归根到底还是在宣扬自己受天命,以证明自己,说服殷人。
而从甲骨文的卜辞来看,真正的商人迷信天命,天命的意志是无法捉摸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讨好天帝。商王纣在即将灭亡的时候还坚信“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无视自己所作所为引起的后果,迷信天命有助于自己,最后被灭亡。作为征服者周人却理性地认识到,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天命,天命意志的根源实际上就是统治者的行为:他们之所以能得到天命,一方面是“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多方》);另一方面是“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康诰》)。周人祖先发奋图强成就周民族大业的历史,成为《周书》说服殷人接受天命转变的重要论据,同时周人自己也坚信这一点。
以史为鉴,一方面吸取了商王纣不祭祀祖先的教训;新的天命观为祭祀祖先注入了新的东西。商人对于至上神“帝”的感情是畏惧,“殷人创造的上帝并不单是降福于人、慈悲为怀的神,同时也是降祸于人、残酷无情的憎恶的神。”⑲从宗教学的意义上看,殷人的早期崇拜和信仰本质上属于自然宗教的形态;在宗教情感经验上来说,殷人对帝、对祖的情感体验是一样的。对他们的崇拜行为的作出亦仅仅是基于恐惧和对现实生活的需求。神与自然界一样,对殷人来说都是难以捉摸的。从殷商卜辞中我们能看出,对于所问的问题,答案只有简单的两种极端之间的回答。没有理性的解释和根据。祭祀者所能做的就只是尽量通过祭祀来讨好神灵,影响他们的情绪、行为。在殷人沟通神意的占卜方式是用龟甲、牛骨,烧烤后根据裂纹进行占验,卜问的对象很不确定。而且占卜这一过程完全凭借偶然性。这样的占卜更具有巫术的神秘交感性质。他们生活在一种怀疑、恐惧社会气氛中,《礼记·表记》说殷人的社会心理是“荡而不静,胜而无耻”。一些偶然的自然现象就会引起很大的心理动荡。如《尚书·高宗肜日》所记载“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庚祭祀武丁时,一只野鸡飞到鼎耳上,就使他害怕起来。
这样的恐惧不仅仅出现在宗教生活中,也反映在其族人之间和被统治部落之间。殷代宗族与家庭内部及其之间的关系维系在于神灵威力。通过对殷人奢侈的祭祖仪式和频繁的占卜活动,以此为自己谋求庇佑。他们与祖灵之间存在一种赤裸裸的交换关系。祭品的多寡被视为换取庇护的必要代价。这样的利害关系,无疑与西周人对祖先的热情赞美和称颂有很大的不同。对外族,殷人更是赤裸裸地威胁和杀戮。刘起釪先生指出,《尚书·盘庚》主要思想确实是商代的,全文突出的一点就是,处处以上帝的旨意来威吓人民,“不奉上命的就是奸诈邪恶,就要斩尽杀绝,不让留下一个孽种”⑳。
周人对祖先有着比较理性的认识,而理性的认识来至于真实的历史,这不仅是天命观发生改变的缘由,更成为了祖先之所以被崇拜的基础。《周书》推行孝观念,是推行建立在对祖先功业体认基础上的祖先祭祀。一方面,祖先的功业是周人获得天命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对族内以及异族的奖赏和分封的重要依据。在新的原则下,祭祀祖先不仅仅是宗教的需要,更关系着现实的政治功利。祖有功德者,通过某种仪式活动来反复颂扬,不仅仅人们感情上的宣发,也是昭彰其所以可以世享权力和领地的资本。
西周统治者以孝观念来昭彰建国守业的依据,也可以用来明确各个阶层境遇差别。《召诰》言:“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周天子是天命的接受者,同时也与天的儿子。相对殷王来说,周天子与“天”有了血缘的关系。而通过联姻和分封,统治阶层也形成了血缘结构。这样的政治结构是宗教、宗族一体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灭商的开始,西周王朝就对本族内部以及异族进行重新地整合。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顺我者,以功业而立足,成为获得改朝换代的利益所得者;而逆我者,则以此成为被统治的对象甚至被驱逐和消灭。直至上一辈,即父辈的所作所为都可以成为其考量的对象。统治关系与亲属关系时相重合的。孝和友就可以涵盖所有的关系之间的。对祖先不孝,就是否定了其安生立命之根本;而对兄弟不友,也就破坏了现实统治的团结。这是“不孝不友”为元恶大憝的真实含义。
总之,笔者认为在《周书》的思想体系中,周人提出和推崇孝观念与其殷鉴的历史观以及天命观的转变密不可分。殷人失去天命的历史,周人针对性地提出“不孝不友”的批评;而周人显扬祖先,团结族人和姻亲也需要孝友的观念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