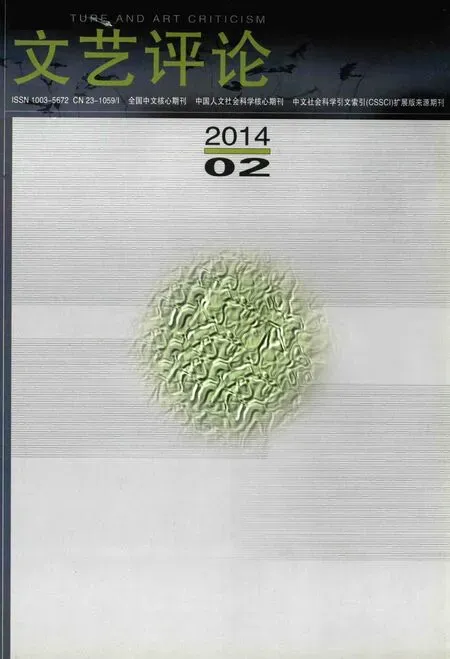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人物新考
孙 植
岑参的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题中的武判官究竟是谁,历来的唐诗选本对此给予的注解都付诸阙如,不可考证①。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按图索骥,梳理归纳,试图对此给出答案。
一、武判官其人初考
天宝十五载(756)八月武判官东归,照理应该是因公而行。因为当时中原战事正紧,皇帝出奔在外,返乡处理家事的可能性极小,况且“中军置酒饮归客”亦意味着是公事送行宴。像安西、北庭这样的幕府判官公事东返,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作幕府信使向京城报告军国重事,一是皇帝或吏部更有新的任命而被召还。武判官东归应该属于被召还的情况。那么会是一个什么任命呢?
天宝十五载(756)八月前后,当时围绕唐肃宗一系列重要的国家军事与人事中,给人印象最为显著的是李岘被恩授为扶风郡太守。《旧唐书·李峘传》后附李岘传:“至德初,朝廷务收才杰,以清寇难,岘召至行在,拜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一:“李岘天宝末为京兆尹,著声绩。杨国忠恶其不附己,出为长沙太守。肃宗至德初,朝廷务收才杰,以清寇难,岘应召至行在,拜扶风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师,拜礼部尚书,守京兆尹,复兼御史大夫。”扶风郡即凤翔郡。《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凤翔府扶风郡,赤上辅,本岐州,至德元载更郡曰凤翔,二载复郡故名。”唐肃宗李亨至德元载(756)七月甲子于灵武即位,《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七月辛酉,上至灵武,……是月甲子,上即皇帝位于灵武。”肃宗即位后当月即敕改扶风为凤翔郡。《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云:“(元载七月)敕改扶风为凤翔郡。”而唐肃宗灵武即位后诏拜李岘为“扶风太守”,可见其时亦在至德元载(756)七月,李岘任扶风郡太守没有几天即改任凤翔郡太守。
李岘被唐肃宗任为扶风郡太守是一件大事。扶风郡是长安西面和北面的门户,是阻止安禄山西北追击老皇帝唐玄宗、新皇帝唐肃宗的第一道堡垒,其重要性堪比潼关。当时唐玄宗在长安听到潼关失守,不几日便怆惶西幸,而敌军尚未进逼到长安。如扶风再不守,唐肃宗等大概只能北逃荒漠、西窜吐蕃了。由此,接受这个任命之重大责任可想而知,获得任命者被唐肃宗倚为心腹亦是毋庸置疑。
乱事之秋,百端无绪。受命之日,李岘当然要千方百计网罗得力干将。在李岘所招揽的人物当中有一个姓武名就的人。检《文苑英华》巻八百九十七《职官五》,有权德舆撰《赠吏部尚书武就碑一首》,全称为《故中散大夫殿中侍御史润州司马赠吏部尚书沛国武公神道碑》②(以下简称《武就碑》),复检《全唐文》,亦录有《故中散大夫殿中侍御史润州司马赠吏部尚书沛国武公神道碑铭(并序)》一文,撰人同。两篇文章内容完全一致。《武就碑》云:“公讳就,字广成,沛国人。……李梁公岘之守右扶风也,表为兵曹掾。”由《武就碑》文可知李岘受诏为扶风郡太守,时在至德元载(756)七月,则武就受辟之时亦当为至德元载七月。武就七月被李岘荐举为扶风郡兵曹参军,朝命八月应该到达北庭。皇命在身,不能拖延,武就应即于当月东返。事发突然,然中原多故,则又是情理中事。岑参与诗友情深意长,自然不免作歌惜别。僚友、诗友们相继东返,而岑参却远留茫茫西域,国事之悲,家园之念,伴随着凶猛冷酷的大风雪,一齐向诗人袭来。于是,寄寓满纸沉郁悲愁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就呼之欲出了。由上所述,从李岘受诏,到武就受辟,再到北庭送别,时间上可谓丝丝入扣,事理上可谓在情在理。当然,这些还只是若合符契的观点的提出。
二、武就其人及其与岑参关系
《武就碑》云:“周室之兴,本于忠厚;赵王之裔,厥有勋贤。元魏步兵尚书,雁门、朔方、云中、马邑四郡太守,洽启封晋阳,田禄益大,生国子祭酒受阳公讳神龟。受阳四叶至太原王讳华,太原生鄼国节公讳士逸,节公生河间郡王讳仁范,河间生颍川武烈王讳载德。代以文武上才,为将军二千石。识芒砀之气,密赞皇图;承沙麓之祥,分封戚里。颍川生考功员外郎修文殿学士讳甄,字平一,以字行于时,未弱冠有重名,闳览博学,为人文龟玉。在天后朝,累征不起,以公族好爵为惧,常晦其明,与桑门大士修无生法。中宗复辟,甫践周行,载笔论思,特盛渊云之选,赋诗感激,必以昌霍为诫。虽位有陟降,而道无磷缁,丛滋后昆,纂服遗烈。公即考功府君第三子也。”武氏家族在武则天一朝占尽了荣华富贵,但其中亦有些当福不享之辈,武就的父亲武平一就是这种人。“累征不起,以公族好爵为惧”,在崇尚功名利禄的时代,能抱有这样一颗平常心,一般人看来真可谓匪夷所思。除此《武就碑》外,我们其他能见到有关武就的历史资料可谓少之又少,零星的还有下面几处。《旧唐书·武元衡传》云:“(元衡)祖平一,善属文,终考功员外郎、修文馆学士,事在逸人传。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贵,追赠吏部侍郎。”《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武就集》五卷,元衡父。”《嘉定镇江志》卷十六:“武就,为润州司马(宰相世系表)。”《新唐书》卷七十四上《宰相表四上》:“就,字广成,润州司马。”《元和姓纂》卷六:“平一,考功员外郎,生集、备、就、登。集,梓州刺史。备,殿中御史。先元衡,门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登生儒衡,殿中御史。”关于这则资料,《元和姓纂》在其后的“备殿中御史生元衡”条校记较为详备地阐述了武就生武元衡的问题。兹录其文如下:
罗校云:“案‘先’,金石录唐赠吏部尚书武就碑引作‘生’。又案就碑、唐表并以元衡为就子。”余按金石录二九云:“右唐武就碑。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载平一四子,集、备、就、登,备生元衡。今此碑与唐书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为就子。姓纂,元和中修,是时元衡为宰相,不应差其世次,岂余家所藏本偶尔脱误乎?当俟别本校正。”是赵氏见本已误作“备生元衡”,今本又误“生”为“先”也。旧书一五八元衡传:“父就,殿中侍御史。”(新表则云润州司马。)今备亦殿中侍御史,历职相同,宜乎易于脱误矣。据就碑,尝为殿中侍御史,终润州司马,卒贞元六年,年七十八。传举京朝官,重内也,表则举其终官。
《武就碑》亦云:“(就)亦既戾止,俄然化性,时贞元六年冬十一月,享年七十八。”由贞元六年(790)上推,可知武就当生于开元元年(713)。岑参生于开元七年(719)③,比武就仅小去六岁,两人年龄相仿。
不仅年龄相仿,岑参和武就还差不多同时中举、登科。《武就碑》云:“始以方闻之士,对诏策,佐宫卫。”这里是说武就最初以制举登科,授官为宫卫僚佐,进入仕宦之途。“方闻之士”,博洽多闻之士;“对诏策”,指制举登科。武就应皇帝制举登科当无疑,只是究竟是什么制科,“方闻之士”是否即意味着是博学宏词科,这些还有点不好说。据徐松《登科记考》,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曾有过一场博学宏词,之后除了天宝元年、二年、四年均有博学宏词科考试外④,直到大历十四年才又开始有博学宏词的记载。王勋成先生在其《唐代铨选与文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一样,都是吏部为“格限未至”、“选未满”的人设置的,其一诞生即归属于吏部科目选,制举从来就没有此二科⑤。不过,我们的倾向性意见认为,武就应当是在天宝元年、二年、四年中的某一年制举登科,这次制科考试名目可能是博学宏词科,也可能是其他类似的科目。因为吏部的博学宏词科目选“试文三篇”,“文”与“策”终究还是不同的,而武就则是“对诏策”的,所以我们并不好简单地认定武就参加的制科名目肯定是“博学宏词”。要知道,所谓制举,本来是皇帝随心所欲而设,何时举行,并无定例。
岑参是天宝三载进士,武就天宝三载左右制举登科,他们二人科举成功的时间一致。据《武就碑》,武就初入仕途是“佐宫卫”,此官职与岑参释褐时的情况也最为近似。据《岑嘉州诗集》序,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转右威卫录事参军”。如此看来,武就、岑参两人不仅年龄相仿,差不多同时中举、登科,而且还是差不多同时解褐为官,踏上仕途,初任官职性质又很相近。
按唐时官制,上州兵曹参军品级为从七品下。扶风郡属“赤上辅”,是当然的上州,武就其时官阶即升为从七品下。《武就碑》文中,交代武就自“佐宫卫”至“为兵曹掾”,其间并没有其他官职经历,当然亦无在西域封常清幕为判官的行迹。唐代,判官是节度使幕中的重要佐官。“唐代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皆得自选中级官员,奏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掌文书事务。中期以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均设有判官,由本使选充,以备差遣。其权极重,几乎等于副使。”⑥有人不免要问,这样一个“其权极重”的判官之职在综述墓主生平的碑铭中却一字未提,原因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楚有唐一代的职官观念。
从文献资料看,唐时节度使的佐官往往“由本使选充,以备差遣”,一般都是没有品秩的。《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节度使”条云:“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无员数也。随军四人。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节度使直属军队的军职和使府内的文职,大多数是自行任命的。规定的文职有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等,其中任要职者也可以代行节度使职权。次一等的,可以委派代理州县职务。这些名为幕职的差遣官,无官阶,故此种人必须带有郎官、御史等头衔。幕职不限出身,文士不论是否中进士,都可以应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推荐到中央任职。事实上,唐代中期以后的文士,很多都以幕僚作进身之阶。”⑦因此,在有关“人物简历”中,这方面的情况不作清楚的交代,并不奇怪,而且是非常正常甚至是非常之规范的事情。如前引杜甫等人《为遗补荐岑参状》,虽然其时岑参在西域时已位至伊西北庭支度副使,但杜甫荐状却仍只称“宣议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岑参”,并未说明岑参已曾任职伊西北庭支度副使一事。李岘将武就“表为兵曹掾”,其上表中应也不会去罗列武就曾任职北庭判官事,而只称其佐宫卫的官职与品阶。岑参由宣议郎(从七品下,散官衔)、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升职为右补阙(从七品上),从品阶而言,亦是很自然的升迁。同样,武就任职为从七品下的兵曹参军,之前其“佐宫卫”的官品一般亦当在八品甚至以下。武就、岑参从西域东返后又均官升一级,至此他们两人的初期官历基本差不多,其中岑参似乎发展得还要略为好一些。
三、李栖筠与武就
长安沦于安禄山之手,好在茫茫一片西域诸镇尚在中央政权的牢牢控制之中⑧。西域诸镇此时就如大唐的兵库,源源不断地向东方战场输出军将人才。武就到了李岘麾下,是作出了许多忠诚贡献的。《武就碑》云:“宣皇在岐,供待有劳,改永乐令,历河中府户曹。毂下求吏,转万年丞。建陵复土,推择充奉,拜醴泉令。朝廷嘉其才,擢为殿中侍御史。”我们所知道的,除了武就,武就的同僚李栖筠几乎同时也加入到了李岘麾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七月)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旧唐书·李栖筠传》亦云:“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擢殿中侍御史。”
李栖筠,天宝七载(748)进士,亦是岑参在北庭幕府的同僚兼诗友。《全唐诗》李栖筠小传云:“字贞一,世为赵人。吉甫之父。举进士高第。调冠氏主簿,太守李岘视若布衣交。擢殿中侍御史,为李岘三司判官。三迁吏部员外郎、判南曹。累进工部侍郎。元载忌之,出为常州刺史。以治行,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拜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寻为御史大夫,力抗权邪。卒赠吏部尚书。栖筠喜奖善,而乐人攻己短,为天下士所归,称赞皇公,诗二首。”按,李栖筠虽曾在西域为幕府判官,后又供职为“摄监察御史”、“行军司马”,然在这则小传中,“冠氏主簿”到“殿中侍御史”之间亦未有交代判官事,其与前述岑参、武就的情况相同。《新唐书·李栖筠传》云:
擢高第。调冠氏主簿,太守李岘视若布衣交。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摄监察御史,为行军司马。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擢殿中侍御史。李岘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贼者,表栖筠为详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胁污者,轻重以情,悉心助岘,故岘爱恕之,誉一旦出吕諲、崔器上。三迁吏部员外郎,判南曹。时大盗后,选簿亡舛,多伪冒,栖筠判折有条,吏气夺,号神明。迁山南防御观察使。会岘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众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阳,高其才,引为行军司马,兼粮料使。改绛州刺史,擢累给事中。是时,杨绾以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诏群臣议,栖筠与贾至、李廙以绾所言为是。进工部侍郎。关中旧仰郑、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硙利且百所,夺农用十七。栖筠请皆彻毁,岁得租二百万,民赖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载忌之,出为常州刺史。……以治行进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赐一子官。人为刻石颂德。……会平卢行军司马许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窥江、吴意,朝廷以创残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图之。……以功进兼御史大夫。……引拜栖筠为大夫。始,栖筠见帝,敷奏明辩,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无所屈。于是华原尉侯莫陈怤以优补长安尉,当参台,栖筠物色其劳,怤色动,不能对,乃自言为徐浩、杜济、薛邕所引,非真优也。始,浩罢岭南节度使,以瓌货数十万饷载,而济方为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载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决。会月蚀,帝问其故,栖筠曰:“月蚀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怤等皆坐贬。故事,赐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顐杂侍,栖筠以任国风宪,独不往,台遂以为法。帝比比欲召相,惮载辄止。然有进用,皆密访焉,多所补助。栖筠见帝猗违不断,亦内忧愤,卒,年五十八,自为墓志。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献。”
其他历史载籍中有关李栖筠的情况大致有下面几种,或多或少可补《新唐书》李栖筠传之缺失。《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记载肃宗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事云:“辛亥,以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諲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栖筠多务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岘独得美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诏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议。”《唐会要》卷八十九“疏凿利人”条:“至广德二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硙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六》:“广德二年,户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硙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唐语林》卷一:“广德二年,春,三月,敕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碾硙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岁收稻二百万斛,京城赖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强御,故用之。”《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大历三年)二月己卯,以常州刺史李栖筠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西团练观察使。……(六年八月)丙午,以苏州刺史、浙江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八年春正月)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吏部侍郎徐浩。……(十一年二月)辛亥,御史大夫李栖筠卒。”
李栖筠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仕途发展比较顺利,为官声望亦很高。唐肃宗驻灵武时,栖筠认真安排安西精兵七千余人奔赴行在,救了肃宗军源不足的燃眉之急,李栖筠的名字在肃宗脑海中从此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不久他即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加上肃宗的左右手李岘对他青眼有加,李栖筠很快就又成为了李岘处理繁杂政务的得力助手。上引《新唐书·李栖筠传》云:“李岘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贼者,表栖筠为详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胁污者,轻重以情,悉心助岘,故岘爱恕之。”其实,李栖筠受到李岘看重事出有因,其因在二人相知甚早。同前引书云:“(栖筠)擢高第,调冠氏主簿,太守李岘视若布衣交。”
李栖筠有子名吉甫,李吉甫为宪宗元和时著名宰相;李栖筠又有孙(李吉甫次子)名德裕,李德裕为武宗会昌间著名宰相。李吉甫给文史学者最耳熟能详的印象是《元和郡县图志》。谈到李栖筠、武就,我们发现他们的下一代——李吉甫与武元衡的关系相当好。《旧唐书·武元衡传》:“始元衡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宰相。及出镇,分领扬、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数,若符会焉。”又《旧唐书》卷十五上《宪宗本纪》:“(元和二年)己卯,以户部侍郎、赐绯鱼袋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与武元衡年龄相当,同日为相,等等诸多一致之事,足以让人叹奇。一般而言,思想常有矛盾之时,政见总有抵触之处,同室办公者往往表面和睦,内里交恶,更遑论都是大权在握的宰相。不过,李吉甫与武元衡二人看来是很珍惜天造地设的这一段缘分的。《北梦琐言》卷一“李太尉英俊”条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
《新唐书·李栖筠传》附李吉甫传云:“始,吉甫当国,经综政事,众职咸治。引荐贤士大夫,爱善无遗,褒忠臣后,以起义烈。与武元衡连位,未几节度剑南,屡言元衡材,宜还为相。”《旧唐书·令狐彰传》:“元和中,宰相李吉甫奏(进令狐通)……宪宗念彰之忠,即授通赞善大夫,出为宿州刺史。时讨淮、蔡,用为泗州刺史。岁中改寿州团练使、检校御史中丞。每与贼战,必虚张虏获,得贼数人,即为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李吉甫与武元衡之间这种良好关系甚至有点让宪宗“不满”起来,很可能是两人间政事往往彼此迁就,大概是武元衡办事,李吉甫总无意见;而李吉甫办事,武元衡总无意见。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皇帝用意制衡。于是宪宗竟然采取了一个措施期望改变如此局面。《新唐书·李栖筠传》附李吉甫传:“帝亦知其专,乃进李绛,遂与有隙,数辩争殿上,帝多直绛。然畏慎奉法,不忮害,顾大体。”既然是皇帝安排,武元衡不便多言,却好做起和事佬来。《旧唐书·武元衡传》:“时李吉甫、李绛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于上前。元衡居中,无所违附,上称为长者。”
子辈有如此紧密的关系,与身为父辈的李栖筠和武就二人打下的交情基础密切相关。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找到岑参和李栖筠在西域共事时的和诗,却没有发现李栖筠和武就两人之间当时的和作。因为载籍遗佚,《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虽录有《武就集》五卷,而今天我们却看不到武就的一篇作品,哪怕是他的一个句子;李栖筠在西域就常常有诗“即事见呈”于岑参,其喜爱吟诗作赋亦是可以想见的,可《全唐诗》仅仅收录李栖筠诗二首。历史是无情的,几世几劫下来,过去的遗存就像冰山之一角,大部分如烟似雾,随风而去,令人慨叹!
四、张谓、刘单等与武就
张谓,天宝二年(743)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天宝二年(743)“进士二十六人”条下有张谓(本年状元为刘单),考云:“《唐诗纪事》:‘张谓登天宝二年进士第。’”是。《唐诗纪事》卷二十五张谓条:“谓,登天宝二年进士第。奉使长沙,尝作长沙风土记云: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七集前张谓小传云:“张谓,字正言,河南人。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历间官至礼部侍郎,三典贡举。诗一卷。”《全唐诗》录张谓诗一卷,其中多有他人诗作羼入,其卷数在卷一百九十七,紧接其后的就是岑参诗四卷,这似乎亦能从另一角度体察到张谓与岑参二人之间的关系。
同前述岑参、武就、李栖筠一样,《全唐诗》张谓小传亦不交代其曾在西域入幕的经历(张谓入幕西域详见后述)。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张谓生平事迹记载,时间最早而又较为具体的,大概要算是元人辛文房所撰的《唐才子传》。《唐才子传》卷四有张谓小传,传云:
谓,字正言,河内人也。少读书嵩山,清才拔萃,泛览流观,不屈于权势。自矜奇骨,必谈笑封侯。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亭障间稍立功勋;以将军得罪,流滞蓟门。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为礼部侍郎。无几何,出为潭州刺史。性嗜酒简淡,乐意湖山。工诗,格度严密,语致精深,多击节之音。今有集传于世。
后来讲述张谓生平者,往往以此为据。
傅璇琮先生曾在《唐代诗人丛考·张谓考》一文中对《唐才子传》的说法提出了全面质疑,认为“经过对有关材料的考证,可以证明《唐才子传》的这一记载主要部分是错误的,应当予以订正”。其中,关于张谓早期生活的记载,傅先生认为真实性很有问题——张谓不是在东北方的营、朔,而是曾在西域从军入幕,所入为封常清幕。证据一是元结《别崔曼序》曾经清楚地叙述张谓任潭州刺史以前的经历:“张公往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开境千里,威震绝域,宠荣当世”;二是,《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五载张谓文八篇,当中有三篇明显为西域所作,即《为封大夫谢敕赐衣及绫彩表》、《进娑罗树枝状》、《进白鹰状》。特别是其中的《为封大夫谢敕赐衣及绫彩表》为人们提供了张谓从军西域写表的具体时间,即天宝十三载(754)秋或十四载(755)秋。⑨
熊飞先生在《唐代诗人张谓生平事迹考略》一文中则又力挺《唐才子传》,认为元结和辛文房记载得都有根据,反映的是张谓早年生活的不同两个阶段,一在后而一在前,相互衔接,即先受辟于营朔,后又曾在西域从军。关于张谓西域从军的经历,熊先生认为他曾两入西域,首次是开元二十八年(740)春至天宝元年(742)初入安西都护田仁琬幕,第二次是入安西兼北庭都护封常清幕,同时推测第二次在西域甚至于还可能起于入高仙芝幕。
《唐代诗人丛考·张谓考》和《唐代诗人张谓生平事迹考略》是张谓研究中的两篇重要论文,虽然二者持论颇异,但是对于天宝十三载(754)秋或十四载(755)秋张谓在西域,却有认同一致的看法。
陶敏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补正“张谓”下指出,《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七张谓《送青龙一公》:“事佛轻金印,勤王度玉关。不知从树下,还肯到人间。楚水青莲净,吴门白日闲。圣朝须助理,绝莫爱东山。”而卷一百九十八岑参《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略云:“久交应真侣,最叹青龙僧。弃官向二年,削发归一乘。……往年仗一剑,由是佐二庭。于焉久从戎,兼复解论兵。……”这个归一上人“原与张谓、岑参因在封常清北庭麾下,后削发为僧,故二人同以诗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岑参与张谓在西域时交往很深,大概他们西域时诗作往来频繁,以至于人们竟分不清谁是谁的作品了。这种版权纠葛,现存《全唐诗》中,即有两次,是为二人重出诗两首。岑参集中《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谿宴》,张谓集中题作《早春陪崔中丞浣花溪宴得暄字》,两诗全同;岑参集中《题金城临河驿楼》,张谓集中题作《登金陵临江驿楼》,两诗全同。
岑参与张谓、武就等人交往之多,至此也可以有个清楚的印象了。就这三人小圈子而言,还能拿出张谓与武就关系密切的证明么?这里就有一个。前举《武就碑》云:“(就)尝与张礼部谓、元容州结歌诗唱和,著文集五卷,自有涂中之适,异乎泽畔之词。”碑文谈论武就的文章密友,只列举张谓和元结,可以想见,张谓与武就的友好关系不仅在西域如此,而且终其一生。张谓约卒于大历十年(775)⑩,武就逝于贞元六年(790);张谓官终礼部侍郎,早武就十五年而卒。
唐代科举有一个现象很值得重视,这就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中第登科者虽然可能与主考官素不相识,从未聆听其训示或教导,但这一层师生关系却是异同寻常地牢固的。师生关系既然有这样的认同,同时的中第登科者们大概亦是很乐于互称“同门”的。这一层“同门”关系其牢固程度并不比师生关系逊色许多。史上有诸多事例,其中如白居易和元稹,他们同年参加科目选而登科,后来两人结成的亲密关系可谓后世文友典范,他们事业上相互支持,文学上彼此唱和,开“元白体”诗一派。综合考量岑参的交游,我们发觉,其不少诗友或同僚均为其“同门”或“同门”之邻。其中,岑参军旅西域期间联系紧密的就有不少,除了上文所称述的武就、李栖筠、张谓等人,再可举的还有一个就是刘单。
刘单,天宝二年(743)进士科状元。《全唐诗》无其诗。《元和姓纂》卷五“诸郡刘氏”条下:“礼部侍郎刘单,岐山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九天宝二年进士二十六人首列一人即状元刘单。考云:“《元和姓纂》有礼部侍郎刘单,岐山人,当即此人。《旧书·杨炎传》:‘元载自作相,尝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恐《姓纂》作侍郎误。”《元和姓纂》的意思是刘单官终礼部侍郎,这应该是正确的结论(详见后述),而徐松《登科记考》却以为官终礼部郎中。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亦以《元和姓纂》不误,并认为刘单于大历六年任礼部侍郎,放春榜。我们以为,刘单既然是元载所引“将以代己”为相者,那么其官位则不当低至郎中。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大历六年上都知贡举者作礼部侍郎刘单,校正了徐松《登科记考》误作张谓的失误。其引陈补云:“徐《考》定本年上都为张谓知贡举。按《唐语林》卷八谓知六年、七年、八年贡举,《唐诗纪事》卷二五则以为‘典七年、八年、九年贡举’。本有歧异。《纪事》卷三六云阎济美‘大历九年春下第,将出关,献座主张谓诗六韵。’是谓知九年举可得证实。徐氏以六年至九年四年间皆作谓知举,实非是。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以为本年刘单知举,所证有:一,《太平广记》卷一七九引《乾子》云阎济美:‘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是刘单在谓前任礼侍。二,《元和姓纂》卷五:‘礼部侍郎刘单,岐山人。’是单终于礼侍任。三,《旧唐书·杨炎传》云:‘初,(元载)引礼部郎中刘单;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郎中为侍郎之误;薛邕以大历八年五月由吏侍贬出,则单为礼侍卒必在稍前;又邕自元年为礼侍,至五年迁吏侍,单为礼侍应在邕后。严氏考刘单以五年迁礼侍,知六年春贡举,是年卒官。其说较为可信。”不过,《旧唐书·杨炎传》讲元载引人之所以有“礼部郎中刘单”之误,很可能亦有原因,这就是刘单官礼部侍郎之前极有可能是礼部郎中。《郎官石柱题名》司勋郎中里即列有刘单之名⑪,刘单应是由司勋郎中迁转为礼部郎中,再升迁到礼部侍郎。史籍里不仅有刘单“礼部侍郎”和“礼部郎中”的异文,而且还有其为“礼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的异文。检《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七:“(元载)初引领吏部侍郎刘单,单卒,又引礼部侍郎薛邕。”要辨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薛邕相关官历。《新唐书·徐浩传》:“召拜吏部侍郎,与薛邕分典选。”《新唐书·顾少连传》云:“顾少连,字夷仲,苏州吴人。举进士,尤为礼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补登封主簿。”《唐语林》卷八“补遗”条:“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薛邕四,大历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唐摭言》卷十四“主司称意”条:“至德二年,驾临岐山,右初阙兼礼部员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后至大历二年,拜礼部侍郎,联翩四榜,共放八十人。”《全唐文》卷四百十一常衮撰《授薛邕吏部侍郎制》:“中散大夫守尚书礼部侍郎兼集贤殿学士判院事上柱国汾阳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薛邕,含和保真,莫见其际。雄词秘学,德行之馀,信厚可亲,朝之英达。往者润色鸿业,焕发丝言之美,又与五经诸儒,质正石渠之论。擢以公望,贰於秩宗,岂惟人神之和,兼举孝秀之目。鉴裁高朗,加以直清,进退可否,归于精实。慎乃服命,五年如初,择吏辩言,宜当慎选。无易前政,副予得人。可守尚书吏部侍郎,余如故。主者施行。”《唐语林》讲是薛邕四年累为主司,《唐摭言》称薛邕大历二年起“联翩四榜”,《全唐文》则说薛邕“守尚书礼部侍郎”是“五年如初”,可见,薛邕官礼部侍郎应该前后总历五年,实放春榜四年,于大历五年放完春榜后迁转吏部侍郎。《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大历八年)二月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吏部侍郎徐浩。丁卯,幽州节度使硃泚加检校户部尚书,封怀宁郡王。徐浩、薛邕违格,并停知选事。……五月乙酉,贬吏部侍郎徐浩明州别驾,薛邕歙州刺史,京兆尹杜济杭州刺史,皆坐典选也。”《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载、王缙之党。”《新唐书·李栖筠传》:“……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载所厚,栖筠并劾之。”薛邕大历五年转吏部侍郎后,至大历八年与吏部侍郎徐浩等人并为李栖筠所劾而左迁。由此可知,《册府元龟》中刘单的“礼部侍郎”误作“吏部侍郎”,薛邕的“吏部侍郎”误作“礼部侍郎”,正因为薛邕先为“礼部侍郎”,后再作“吏部侍郎”,导致行文讹易。结论是,刘单在大历五、六年间任礼部侍郎之时为元载所称引,薛邕则在大历七、八年间任吏部侍郎之时为元载所称引(大历九年后为元载称引者则是吏部侍郎杨炎,非本文所论)。又《新唐书·杨炎传》:“载当国,阴择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礼部侍郎刘单,会卒,复取吏部侍郎薛邕。”此与《元和姓纂》卷五有关记述相同。综上,刘单官终礼部侍郎应为确论。
刘单进士及第后,曾在西域从军入幕。这有两个证据。其一,《旧唐书·高仙芝传》云:“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婆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詧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又谓刘单曰:‘闻尔能作捷书。’单恐惧请罪。”天宝六载(747)之前高仙芝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尚未做到安西节度使。正是天宝六载(747)的这场大胜仗让高仙芝真正成为一方大员。《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徵灵詧入朝。”《旧唐书》卷一百四:“八载,入朝,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仍与一子五品官。”既然武功可以获得官位名禄,高仙芝这类边将就很自然地热衷于东征西战了。《新唐书·高仙芝传》:“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九载(750)讨石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石国王车鼻施已经约降,可是高仙芝照样将其作为战俘献阙,邀功请赏。而唐玄宗已成好大喜功之主,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只一声令下问斩,彰显大唐国威。大食、波斯、石国本有贡献于大唐,《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外臣部·朝贡》:“(开元十二年)三月,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识匿国王遣使献马及金。……(天宝六载)五月,大食国王遣使献豹六,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石国王遣使献马。……八月,十姓突骑施遣使来朝,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石国王子远恩来朝。”特别是天宝六载(747)高仙芝讨平小勃律国,可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极大地树立了大唐帝国在西域的统治威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仙芝约王降,遂平其国。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旧唐书·李嗣业传》:“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款塞朝献,嗣业之功也。”然而,所谓经营难,毁坏易。高仙芝的失义之举一夜之间激起了西域诸胡的强烈反抗,惨痛的失败随之而来也就是顺其自然的了。
岑参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一首,此为刘单进士及第后于西域从军入幕证据之二。诗云:
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夫子佐戎幕,其锋利如霜。中岁学兵符,不能守文章。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西望云似蛇,戎夷知丧亡。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置酒高馆夕,边城月苍苍。军中宰肥羊,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望君仰青冥,短翮难可翔。苍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
此诗即作于天宝十载(751)五月高仙芝出师西击大食之时。闻一多先生《岑嘉州诗系年考证》云:“据《新书·方镇表》,天宝十载王正见代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十一载正见死,封常清代之,常清居此职,至十四载始迁平卢,是十载以后,仙芝不复在安西也。《武威送刘单》诗称‘高开府’,又曰‘安西行营’,则作于天宝十载无疑。公作《送刘单》诗之年为天宝十载,而作诗之地,乃在武威。”《旧唐书·高仙芝传》云:“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其载(十载),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刘单天宝六载(747)就曾为高仙芝草告捷书,此天宝十载(751)又以判官身份从河西武威出发赴高仙芝安西行营。从上可见,刘单一定是岑参在安西幕府的同僚兼重要诗友。
由以上所论岑参、武就、刘单、李栖筠、张谓、青龙归一上人等人的关系情状之中,我们可以大致清晰地勾勒出当年北庭幕府一个文士圈子的印象。这些人有不少相似的特点,一是出处雷同——多为同时或同门登科,二是年龄相仿——往往在三、四十岁的有为之年,三是仕历相同——多由八、九品官进入边幕,四是志趣一样——长于以诗会友,多文人雅兴。因此,我们讨论武就为武判官,是在一个深厚而宽广的史实背景之下展开的。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云:“奉使三年独未归,边头词客旧来稀。”至德二载(757)初春时节,诗友们都已陆续东返,失去诗友们的精神世界,对岑参而言,无异于这苍茫绝域,变得一无所有,诗人只好由衷地感叹“自怜弃置天西头”了!
综上,我们认为《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题中的武判官即为岑参的僚友兼诗友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