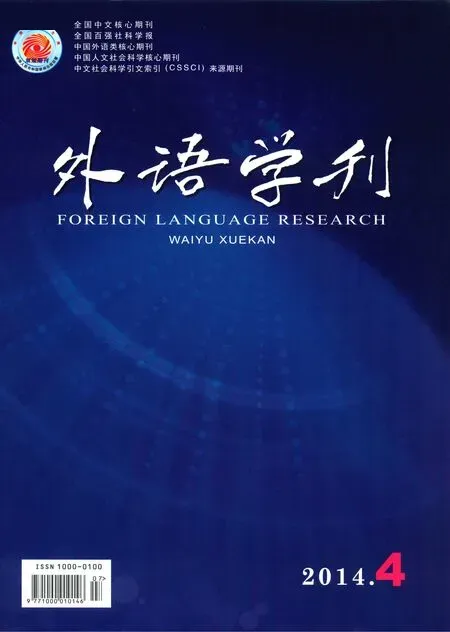涵泳其中 放宽著心
——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
皮德敏 何正兵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
涵泳其中 放宽著心
——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
皮德敏 何正兵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
郑燕虹教授的著作《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启发于张隆溪先生关于中西理论对话的建议和庞德的诗人论诗之妙悟,将雷克思罗斯的诗作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中,以符合文学运动规律的“整体研究”和“明澈细节”的独特视角,钩沉隐没在历史、文化、知识、心理背景之下的诗学要素,实现对文本的独特理解和还原,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研究空白,更在于从文本阐释中引申出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得出符合实际的理论思考,修正学界“理论先行”的局限。这种极具朴学色彩的研究旨趣既具有从跨学科理论的套用返归文学本质研究的意义,又具有融汇中西、升华传统的开拓性价值。
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学术价值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美国诗歌的译介与研究从原来的宏观视域转入针对重要诗人的个案视域,对一批大牌诗人如埃兹拉·庞德、托·史·艾略特、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加里·斯奈德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出版郑燕虹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又是一项颇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下面,从该书的选题立意、研究视角、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4个方面进行评述。
1 独具慧眼、得鱼忘筌之选题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 1905-1982)在美国当代诗界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许多方面很像庞德,他做诗、写评论、搞翻译,还是个具有领袖风范的组织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雷克思罗斯是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被称为“垮掉派之父”。他曾经创办诗歌中心,帮助并影响一批年轻诗人,金斯堡、凯鲁亚克和史耐德等都曾受他影响。他热爱中国文化,被誉为美国现代诗坛中推介中国文化成就卓著的诗人,他翻译出版4部中国诗集:《汉诗百首》( 100PoemsfromtheChinese,1956)、《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LoveandtheTurningYear: 100MorePoemsfromtheChinese,1970)、《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TheOrchidBoat:WomenPoetsofChina,1972)和《李清照诗词全集》(LiCh’ing-chao,CompletePoems,1979),其中后两部与中国学者钟玲合译。他也写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文章,如《宋朝文化》(Sung Culture)、《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绘画中的道》(TheTaoof Painting)、《中国古典小说译本》(The Chinese Classic Novel in Translation)、《老子,<道德经>》(Lao Tzu,TaoTeChing)、《司马迁,<史记>》(Ssu-ma Ch’ien,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ofChina)、《杜甫,诗歌》(Tu Fu, Poems)等。雷克思罗斯不仅翻译介绍中国文化,还在诗歌创作中吸纳佛家、道家思想,模仿中国古诗的一些创作技巧,成为美国当代诗坛中吸收、介绍中国文化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文坛的地位与学界的地位有时不一定有必然、直接联系。文坛如雷贯耳,学界可能雨声很小,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艾略特和叶芝的作品早就进入大学讲堂,庞德较少被人提及,但现在对庞德的崇高地位已毫无置疑,对他的研究依然如火如荼。雷克思罗斯目前也面临庞德当年类似的尴尬情况,他还没有得到应得的地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唐纳德·古铁雷斯曾分析其中原因:(1)早在1927年,雷克思罗斯就移居旧金山,远离培养名人的文化中心纽约;(2)尽管雷氏活跃在西海岸的社会文化界,但他与东海岸的学术权力中心的重要人物关系疏远,坚持己见,不随意附和主流的文学批评主张;(3)雷氏性格独立不羁,不易相处,这也使他失去一些学术圈里的盟友(Donald 1992:142)。此外,郑燕虹认为,其政治主张也是他被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雷氏是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经常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活动。雷氏的政治倾向使他遭到政府排斥,也给他的学术地位带来不利影响。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从来没有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他在美国诗坛一直遭受冷遇,对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近乎空白。
郑燕虹以雷氏诗歌为研究对象,可谓独具慧眼、得鱼忘筌。作者抛开西方学界的陈见,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去拓展雷克思罗斯的诗歌风景线,倡导一种可资操作和极具远景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通过个案分析以支撑大幅度的诗学探索。因此,这部著作在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研究领域对中美学术界皆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该书除了选题新颖外,其本身的学术研究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并富有启发意义。
2 整体研究、诗史互证之视角
本书作者选取的研究视角深契于中外经典学术传统。作者认为,“这种融抽象的理论玄思与具体的作品文本、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沉浮命运相结合的整体研究经过时间的检验是比较符合文学运动的规律的”。该书的论题是“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文化”的定义在学界种类繁多,论争纷纭。作者取法英国文化批评学家雷蒙·威廉斯关于文化定义观点。威廉斯认为“文化”关乎人的整体的生活方式,是指总体的思想形态或习性,与人类完善的理想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对雷克思罗斯的影响关涉其诗学观乃至他的人生理想。书中全面系统地探讨了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雷克思罗斯孩提时常常随母亲去芝加哥的一所剧院看广东大戏,戏中色彩艳丽的戏服和演员婉转缠绵的唱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作者敏锐地指出,雷克思罗斯小时随母看中国戏,固然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喜爱中国文化的种子。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不仅仅源自幼时的爱好,更主要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及其诗歌艺术探索过程中观念革命的结果。书中针对雷氏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的动因有深刻挖掘。书中的主要篇章是结合雷克思罗斯的翻译、诗学观与文化批评,来研究他与道家思想、禅佛思想以及中国古诗对他创作的关系。这些研究视角不是单方面的叙述,而是常常联系雷氏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作家的个人经历以及整个诗歌浪潮,并将理论思考与具体文本结合起来分析与研究。
同时,该书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不把某些概念和方法当做万应的灵丹一样应用到任何文本上去,“无意事先规定运用某种外国文学理论来贯穿整个的研究,但各种相关的外国文学理论(譬如“新批评”、“历史主义”、“影响研究”、“文化误读”理论等)所提供的概念、范畴、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无疑对该书的研究有一定借鉴和指导作用。”如在第一章中论及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作者对照庞德、德莱顿、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对雷克思罗斯提出的“诗歌翻译是一种‘契合’的行动过程”、“诗歌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同化”、“诗歌翻译能给诗人带来灵感”进行了解读,这种分析不是与中外名家的观点做简单的比附,而是深入到雷氏的翻译理论与翻译作品进行剖析与挖掘,并指出其对当代诗歌翻译的借鉴价值。对雷克思罗斯翻译的中国古诗是否忠实原文,译界存在争议,有人将其化为不忠实翻译、有人将其列为“创作式翻译”或者“创意翻译”。例如,钟玲教授将庞德和雷克思罗斯等人的翻译作品划为“创意英译”,她说,“我把庞德、韦理、宾纳、雷克思罗斯等翻译的中国诗歌称为‘创意英译’,有别于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译的诗歌……这些学者的译作当然以忠实于中文原文为其翻译的原则”(钟玲 2003:41)。郑燕虹在全面考察雷克思罗斯的译作基础上,对其译作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提出自己的主张:“仅用‘创意英译’来概括,恐怕过于简单。他的汉诗英译情形比较复杂,也值得深入研究。首先他英译的中国诗数量多,涉及的诗人多,并影响了一批年轻的诗人。其次,他的翻译实践,可以划分两个时期,前期阶段他基本上参照其他译本,独自进行翻译,此阶段主要作品有《汉诗百首》和《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后期阶段他与钟玲合作完成译作《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和《李清照诗词全集》,这两部译作从翻译的忠实层面讲,显然较前阶段强,因为有中国学者在准确性方面把关”。因此她将雷克思罗斯的翻译分为3类:“我们将一首诗中绝大多数诗句是释译,偶有拟译的译文称为‘较忠实’的译文;将一首诗中既有释译又有拟译,释译多于拟译的译文称为‘次忠实’的译文,而拟译多于释译的译文称为‘不忠实’的译文”。书中还就雷氏英译杜甫诗歌3种类别进行例举分析。
3 涵泳其中、明澈细节之旨趣
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深入调研雷氏的作品诞生过程、作品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其他诗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探讨雷克思罗斯的英译中国诗歌时,作者对雷克思罗斯所译的全部诗歌进行了细致爬梳和分类,并对其中某些诗歌的翻译过程还朔本清源。例如,在《汉诗百首》中,雷氏选译了梅尧臣的13首诗,其中有6首是梅尧臣悼念亡妻之作。梅氏的悼亡之作,情感真挚,深受雷克思罗斯的喜爱。作者认为雷氏选译这些诗亦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雷氏的结发妻安德莱·雷克思罗斯(Andrée Rexroth)聪颖过人,擅长绘画。她与雷氏志趣相投,婚后幸福美满,但不幸的是安德莱 38岁时英年早逝,他深感悲痛,写了多首诗悼念她。梅尧臣的悼亡之作自然会引起雷氏的共鸣,雷氏在翻译梅尧臣的诗时,把自己的情感和经历也糅合进去。作者以例为证,结合译诗和创作的诗歌进行比较和解读,从而得出结论:“人的情感是相通的,雷氏改译的灵感正是其所谓的诗歌翻译情感‘契合’行为过程的结果”。在该书的“雷克思罗斯的中国文化情节”一章中,作者首先调研美国19世纪以来一些重要作家的中国观,爱默生虽敬重孔子,但对中国怀有鄙视与怨恨。在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作品中有关中国人和中国事物常常是负面意象。而庞德、赛珍珠、斯奈德、雷克思罗斯等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持肯定态度,他们的作品借鉴了中国的情景以及文化,以此来匡正西方的时弊和革新现代文学。该书可贵之处不是简单地对雷氏下定义说他热爱中国文化,而是从他小时候与中国文化的渊源着手,并进而调研他阅读过《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以及有关宋朝的诗词书画艺术著作,得出“雷克思罗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不仅仅源自幼时的爱好,更主要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及其诗歌艺术探索过程中观念革命的结果”。
4 立足文本、入乎其内之方法
美学家贝尼季托·克罗奇认为,“语言活动并不是思维和逻辑的表现,而是幻想、亦即体现为形象的高度激情的表现,因此,它同诗的活动融为一体,彼此互为同义语。这里所指的就是真正、纯粹的语言,就是语言的本性,而且即使在把语言作为思维和逻辑的工具,准备用它作某种观点的符号时,语言也是要保持它的本性的”(贝尼季托·克罗奇1992:41)。可见,语言与诗歌精神(诗歌语言的“本性”)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但是在学术界,大多数时候诗歌是作为客观语言材料进入研究视野的,语言与诗歌精神的内在联系难以得到充分阐释。郑燕虹独辟蹊径,其研究方法立足于文本,透过语言材料,入乎诗歌精神之内核,勾勒出中国古典文论中对诗歌意象和诗歌意境的历史叙述,并依此对雷氏诗歌中展现的不同的诗境进行分析;还结合雷氏的诗歌文本揭示他对中国诗歌创作技巧的吸收和运用,挖掘出其中蕴含的道家思想;作者充分运用诗人般的领悟力和感知力,捕捉雷氏诗歌的深刻意蕴来源于他对“空”的理解和感悟,研究雷氏吸收禅宗公案的语言形式来进行诗歌创造的特征,揭示出其诗歌特有的禅定时的宗教体验和禅佛意蕴。这种研究的学术效果正如叶维廉所形容的:“以美学考量为中心”,使研究对象“意境重现”,直接参与“创作的经营”与“趣味”,并且阐释效果不会“喧宾夺主”(叶维廉1994:9)。众所周知,中国诗学历来以禅、道思维为理论源泉,究极于天人之际、物我之间的诗学体验,其与西方的逻辑研究方法差异巨大,导致在国际学术界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在国内亦是如此,“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在汉语文化圈轮番上演的历史”(曹顺庆 李天道 2001)。在这种情况之下,郑燕虹教授所弘扬的治学路数无疑具有先导性和创造性,其意义不仅在于确立中国诗学的文化身份,更在于挖掘出中国诗学的某些普适性,并运用于对西方文学的话语分析,其意义是最终达成中西文学、文化的互相理解。本质上讲,这是一场基于文化自信的诗学对话,这种自信并非凭空虚托,而是渊源有自,深具传统学理基础。作者在开篇绪论引用张隆溪先生的话:“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而应该把理论还原到基本的‘原理论问题’,在有关语言、表达、理解、解释等许多方面,去看中国和西方怎样表述和处理这类问题”(张隆溪2009:52)。在全书的论证过程中,作者始终贯彻这一对话立场。例如,在论述雷氏诗歌翻译讲究“情感契合”之时,作者认为雷氏所谓的“同化”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引《七缀集》和雷氏论文比照分析,在追溯诗歌翻译本质的同时,研究翻译对创作的意义在于其为创作提供灵感之源泉,从而由此展开对雷氏诗歌中东方诗学要素的研究。又如,文章在梳理一系列中国诗学要素如“心”与“物”、“意”与“象”、“情”与“景”的关系时,最终以王国维的观点为旨归:“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周锡山 2004:26)。作者以此为学理基础,从“显景隐情”、“借景抒情”、“移情入景”3个方面,通过中外文本的比勘,详尽论述了雷氏诗歌翻译与创作中的情景关系。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学术界不乏关于这方面的一般性理论探讨,但始终缺乏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个案研究。郑燕虹教授立足文本、入乎其内的个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和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形成不同于学界以西方理论为先导的诗学研究景观。从作者所引立论根据可以看出,其秉承着源自先辈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等人的经验与眼界,承袭他们文哲互见、文史互证、多重证据等治学路数,实现融汇中西、升华传统的学术价值。
5 结束语
郑燕虹结合雷克思罗斯早年经历、个人知识背景,又结合马克思观点、现代派文论、古典文论和自身对佛道经典的独到理解,详论雷氏的诗学观念,通过个案视角,为中西文化与诗学融合开启一扇门——导向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视角。其学术影响不仅体现在对雷氏诗歌的阐释,还以“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灵活视域,达到一种促进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双向的“文化反观”与“诗学反观”的效果;其治学方法的价值在于促成文学与哲学、体认与推理、具体与抽象的学理融合。作者在论及雷氏的文学影响时说,“雷克思罗斯的艺术探索不仅构建了自己独立的诗歌艺术世界,为美国诗坛贡献独特的诗歌形式,而且还为其他诗人提供宝贵的诗歌创作经验,成功地勾画出一道中美文学交汇融合的风景线”。同样,这本研究雷克思罗斯诗歌的学术专著,也成功勾画出一道融汇古今与中外的学术风景线。
贝尼季托·克罗奇.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曹顺庆 李天道等.汉语批评:从失语到重建(笔谈)[J].求索, 2001(4).
钟 玲. 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张隆溪. 比较文学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周锡山编校.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Donald, Gutierrez. Kenneth Rexroth: Poet, Radical Man of Letter of the West[Z]. Northwest Review 30.2 (1992).
【责任编辑孙 颖】
ABookasaCross-culturalLandscape— Comments onKennethRexrothandChineseCulture
Pi De-min He Zheng-bi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Inspired by the poetic views of Ezra Pound and the opinions about the methods coping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which is proposed by Mr. Zhang Long-xi, Professor Zheng Yan-hong takes a specific view both on the whole and detailed levels, and puts Rexroth’s poems into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o investigate the poetic elements which exist deep in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intellectual and psychological contexts. Finally the author achieves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Kenneth Rexroth’s poetry and restores its valu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work lies not only in the uniqueness of its topic but also in the universality which is concluded by analyzing the texts and their surrounding elemen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More significantly, to some extent it has broken through the academic constraints of popular notion of ‘theories first’. With the spirit of Pu Xue, a Chinese traditional textual criticism school, this book promotes a kind of retur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ure application of non-literature theories. In such a way, it achieves the goal of bringing together the west and the east culturally and innovatively.
Zheng Yan-hong;KennethRexrothandChineseCulture; academic value
I206
A
1000-0100(2014)04-0155-4
2013-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