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教育情结
管谟贤
莫言在《虚伪的教育》一文中说:“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的确,他最初是以一个小学五年级肄业的实际学历踏上文坛的。对于莫言的成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对中国教育的讽刺。莫言如果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肯定没有今天的成功,甚至成不了作家。这话说重了,有失偏颇。作为他的长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莫言的成功,除了天资聪颖、勤奋刻苦之外,也得益于中国的教育,尤其是“文革”前的教育。莫言虽然只上了五年小学,但这五年培养了他的阅读能力,使他掌握了阅读的工具(识字)和写作的 A、B、C(作文)。他的散文集中关于教育的篇什也有不少,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对文革前17年教育的向往,对1958年之前中学《文学》课本的推崇。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莫言对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十分向往,十分关心,有着浓厚的教育情结。
殷殷求学梦
莫言是1961年上小学的,到了三年级,就因作文写得好,受到老师的喜爱。其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甚至被附近的农业中学拿去让学生学习。他小时候活泼、调皮,还爱唱两声茂腔,所以经常登台表演节目,自编唱词搞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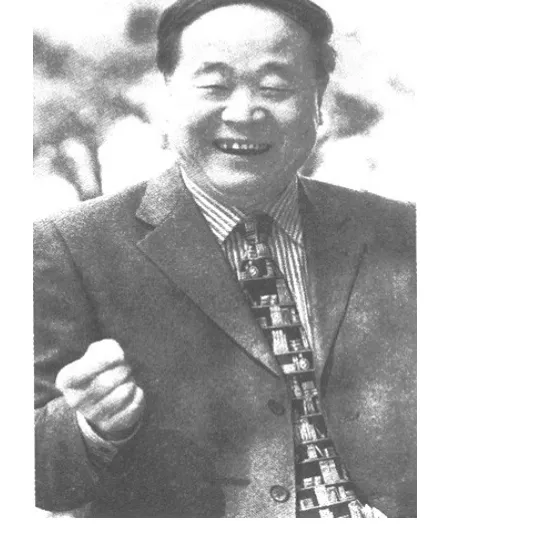
1966年“文革”爆发时,莫言正在读五年级。翌年初,上海、青岛等地开始夺权。我从上海回家探亲,带回一些造反派散发的传单。莫言看后,受到鼓动启发,便到学校造反。他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撕掉了课程表,成立战斗队,写大字报。还同小伙伴一起去胶县串连,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跑回来了。为此,学校就不想要他了。之后,贫下中农组织“贫宣队”进驻农村学校,管理学校一切事务,搞“斗、批、改”,学生上中学也要贫下中农推荐。莫言因揭露了“贫宣队”一个女队员的下流行为,所以该队员以莫言“出身上中农”为理由,坚决反对莫言上中学,莫言就此辍学,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名小社员。我家的家风,可以用我家每年过年时贴在大门上的一副对联概括,那就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要忠厚诚实,要好好读书,不读书就会糊涂一辈子。因此,莫言从小就喜爱读书,从学会拼音开始,就查着字典读了不少课外书籍。—下子失学在家,看着昔日的小伙伴一个个背着书包去上学,自己每天只能背着草筐去放牧牛羊,莫言心里很不是滋味,求学上进之心更加迫切。当时我已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莫言老盼望着有一天能“像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一直读到大学。为了满足自己读书的欲望,莫言曾经帮人推磨换书看,曾经因为躲进猪圈、草垛读书而被马蜂或蚂蚁咬过。实在无书可读了,他就把我留在家里的全部中学语文、史地课本都看完了,连我的作文也读了一遍,甚至去读字典,把一本《新华字典》翻得稀烂。“那时中国的乡村普遍贫困,能借到的书很少,自家拥有的书更少。我把班主任老师那几本书和周围十几个村子里的书借读完后,就反反复复地读我大哥留在家里的那一箱子中学课本。”(《杂谈读书》)莫言读字典是认真的、用心的,他着重了解字词的含义和用法,所以他比同龄人掌握了更多的字词,为自己以后的创作奠定了较好的文字功底。
那时,求学成了莫言的一个梦,读书使他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后来,他回忆对读书乐趣的体验时曾说:“我童年的时候,书很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书,就如获至宝,家长反对我读这样的‘闲书’,牛羊等待着我去放牧它们。我躲起来不顾后果,用最快的速度阅读,匆匆忙忙,充满犯罪般的感觉,既紧张,又刺激,与偷情的过程极其相似。”(《杂谈读书》)
莫言在农村生活了整整20年。这20年,可以用贫穷、饥饿、孤独来描述。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混乱不堪的形势下,莫言的求学梦总也圆不了。看到报纸上说工农兵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张铁生交白卷也上了大学的报道,莫言曾经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写过信,要求上大学。他还真收到了教育部的回信,但信中让他安心农业生产,等候贫下中农的推荐。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又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诉说自己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得到回音。
1976年,莫言当了兵。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国家发展逐渐走向正轨,高考得以恢复。1978年1月,领导通知莫言,让他报考河南郑州的一所部队院校,莫言喜出望外,但也压力很大,连续三天吃不下饭。因为他知道,自己除了作文好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而当时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最后还是决定考。”(《我的大学》)当时全家人都支持他、鼓励他,把我上学时用过的教科书全部给他寄去。他自己更是夜以继日地学习,恶补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但是到了6月,领导却告诉他名额没有了,莫言的大学梦又一次破灭。
1983年,莫言到北京延庆工作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他报名参加了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半年时间,四五门课程考试均以优良成绩通过,眼看一张大专文凭就可到手。1984年夏天,他又得到了另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凭着“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的成绩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真正地踏进了大学校门,圆了自己的求学梦!在这里,莫言受到了系主任徐怀中及许多国内著名作家的教诲,学到了大量的国内外文学知识,“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的大学》)
学习期间,莫言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等小说,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在中国文坛站稳了脚跟,并逐步走向世界。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作家创作研究生班,莫言报考并被录取,两年后,他获得了硕士学位。莫言自己说:“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我的大学》)他总以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基础教育为憾。
浓浓教育情
莫言虽然没受过系统、完整的基础教育,但却十分关心、支持教育。多年来,莫言经常出国,尤其是到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去讲学时,都要到人家的中小学去看看,给那里的学生做报告,和学生座谈。1986年,他为了创作中篇小说《欢乐》,专门去山东高密二中听语文课。近十几年,他还与山东大学教授合作招收研究生。他对学生进行辅导时,十分认真坦诚,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2008年,他应邀去北京十一学校参加“名家大师进校园”活动,给学生做报告,与学生座谈。2009年,莫言受聘担任高密一中名誉校长,被潍坊学院文学院聘为名誉院长。到目前为止,莫言已被国内外众多院校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讲座教授;他亲自为学生上课、做学术报告,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莫言的作品中,长篇小说《十三步》是专门写教育的,中篇小说《欢乐》是写高中复读生参加高考的。在这些作品中,莫言关注着当时教育界存在的教师地位低下、学生负担过重、“应试教育”盛行、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热点问题。而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飞鸟》是赞颂有一技之长的右派教师和揭露“文革”对教师的迫害的。在莫言的散文中,直接或间接谈到教育问题的有:《童年读书》、《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我的老师》、《虚伪的教育》、《陪考一日》、《漫长的文学梦》、《杂谈读书》等。在这些文章中,莫言对教育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阅读,尤其是课外阅读非常重要。
莫言说:“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虚伪的教育》)我觉得这话是很对的。任何作家都是要先当读者,才能成为作家,一个人母语写作的能力,主要是通过阅读、朗读形成的。因之,莫言说:“语文水平的提高,大量阅读非常重要。”(同上)“我上学时不是个好学生,但读书几近成痴的名声流播很远。我家门槛上有一道光滑的豁口,就是我们三兄弟少时踩着门槛,借着挂在门框上那盏油灯的微弱光芒读书时踩出来的。那时我额前的头发永远是打着卷的,因为夜晚就着灯火读书,被燎了。”(《杂谈读书》)
其二、语文教学首先要有好教材,有了好教材,还得有好教师。
莫言认为,“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虚伪的教育》)。莫言对前些年通用的中学语文教材是不太看好的。他认为,建国以来,编得最好的一套中学语文教材就是1958年以前使用的那套《文学》课本。那时中学语文分《文学》和《汉语》。那套《文学》课本,文学性强,古今并重,十分吸引人,可读性强。莫言说:“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大哥的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当然,“有了好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令莫言忧虑的是,现在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不愿意报考师范院校,因为教师的地位、收入仍然偏低。“文革”前的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家庭困难的学生还会得到人民助学金。现在,这些优惠条件基本都取消了。如果有朝一日,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都争着抢着去当中小学教师,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上去了。
当然,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重要,莫言曾说:“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我的老师》)莫言这里说的好坏,主要是指师德。据我所知,莫言在仅有五年的小学生涯中,碰到过很多有知识、有能力、有善心、有爱心的好老师,如孟宪慧老师、于锡惠老师和王召聪老师等,有的老师还教过我,一直受着我的尊重。“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我的老师》)他也碰到过个别人格低下、品德较差、打骂学生,像“狼”一样的老师。现在的教师队伍中仍然存在个别害群之马,道德败坏、实为人渣者也屡见不鲜,对此,有关部门实在应该花大力气加以整顿。
其三,作文教学,应该鼓励学生讲真话,要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好奇心和创造力。
莫言说:“语文成了政治的工具。于是我们的孩子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不说‘人话’。”(《虚伪的教育》)他还说:“欣赏奇才,爱听奇人奇事,是人类好奇天性的表现……只有好奇,才能有奇思妙想;只有奇思妙想,才会有异想天开;只有异想天开,才会有艺术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创新也就是社会的进步。”(《读书杂谈》)我们现在的作文教学,事实上是受高考指挥棒指挥的。这些年来,高考的语文试卷也实行了标准化,作文命题也以“给材料作文”居多,这种作文实际上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什么时候,高考科目设置合理了,命题科学了,我们的素质教育才会有真正落实的希望。
其四,高考是必须的,但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更公平。
莫言在陪女儿高考时,看到有的考生生了病还被人架进考场,感到“高考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陪考一日》)。他说:“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公平,但比当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公平得多了。对广大的老百姓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自主招生,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同上)这真是一针见血!莫言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纯洁的高考,对于高考门类和学科的设置,则主张一定要合理,一定要有利于人才的选拔。莫言的女儿是爱好文科的,但由于客观原因,她不得不选学理科,参加了理科高考,到了大学,又改学了文科英语。一个学生,如果高中阶段就能放手学习自己喜爱的学科,那么到了大学,其专业知识水平该有多高!
莫言的教育情结,承载了太多的梦想与责任。他的教育梦,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梦想,也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莫言只是一个作家,并非教育专家,他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对我们搞教育的人,却不无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