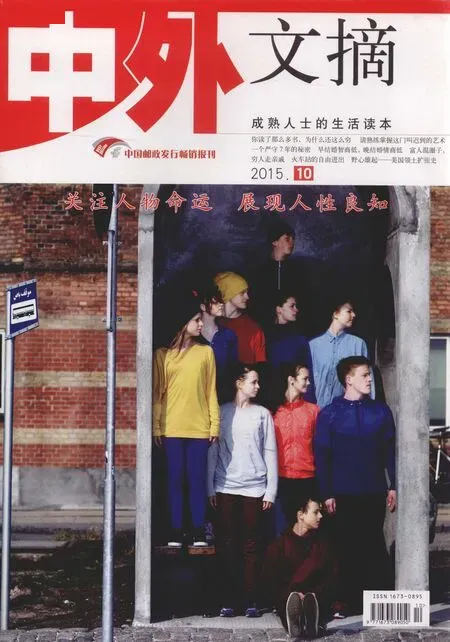间胶囊里的国革命史
□ 华 锐
间胶囊里的国革命史
□ 华 锐
2015年伊始,麻省州议会出了大事。勤劳的水管工们在州议会大厦古老的奠基石里发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铜盒。闻风而至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它是大名鼎鼎的第四任麻省州长、美国独立运动领袖塞缪尔·亚当斯两百多年前留下的时间胶囊。
从各地赶来的古物收藏家们很快就失望了,盒子里只有几张1795年的波士顿报纸和23枚锈迹斑斑的硬币。不过考古学家迈克尔·卡姆还是激动万分。他看着盒子里的州长之印热泪盈眶,“这就是我们波士顿人可触可感的共同历史记忆啊!”
在波士顿这座时间胶囊式的城市里,头上脚下到处都有这样的革命陈迹。哈佛大门外不远处有一座不起眼的墓园,细读墓碑铭文,里面安葬的是独立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死难将士。再往前,有个街心岛,远看貌似公交车站,走近才发现,原来是300年前殖民地先驱南下波士顿的歇马处。
有意思的是,厚重的历史在这里一点都不沉重。怀旧的波士顿人乐于纪念历史,纪念方式或多或少带着喜感。
在举世闻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故地,有个倾茶博物馆。波士顿人把当年三艘运茶船里的一艘从海湾里捞出来修好,做成了大革命角色扮演游戏中心。老少游客们看过革命历史教育宣传片,马上现学现用,戴上羽毛,穿上伪装衣,在等比例复原的市政厅大声发表反殖民演说,然后一哄而上,把塑料制的茶箱模型扔进大海。头戴三角帽的“船长”大喊,这些塑料茶不怕水淹,你们尽管扔个痛快。
哈佛也不甘落后,一周5天都有穿着17世纪燕尾服的绅士挥舞着手杖,带游客参观学府风光。最受欢迎的“景点”当然是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大人的塑像。不过绅士导游很快就会操着殖民地口音告诉你,塑像的真身不是哈佛本人,而是20世纪初某位好事又有钱的哈佛本科生。校方也不避讳,就让这个山寨创始人风光了一百多年。每到期末考试,同学们还要去摸摸这位师兄的脚,求不挂科。
波士顿的早期历史当然不是这么轻松愉快的。莱克星顿、邦克山的金戈铁马不说,当年保皇党人和独立派之间的斗争也是针尖麦芒,搞不好就会丢了身家性命。两百多年后,历史还是历史,革命还是革命,但戾气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兴高采烈的集体纪念,剑桥市的一条街还大张旗鼓地写着,“我们这条街以前住的就是保皇党人!”
兴高采烈,但并不虚无。波士顿人天天生活在历史里,有人自然反思起了这段美国人的“共同记忆”。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这是每个孩子都背得滚瓜烂熟了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杨考证了一下倾茶事件,发现从1773到1830年这五十多年,“倾茶事件”这个说法根本就不存在。现在看来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在当时看来不过小事一桩,只是在倒放电影式的历史回忆里,才变成建国功臣们的不世功勋。
不过这种学究式的反思也许没有《波士顿环球报》对时间胶囊事件的追问有现实意义:“亚当斯当年埋下时间胶囊,是想让早已不知报纸和硬币为何物的未来人回想起先人筚路蓝缕的艰辛。但现实却是,成千上万的波士顿人今天就花几枚硬币买来一张报纸,然后读着硬币和报纸被发掘出来的特大喜讯。”
“还好亚当斯没有看到时间胶囊的出土,”这位作者戏谑道,“不然他该多么失望啊。”玩笑归玩笑,老城波士顿的忧患意识也在这里:“现代”已经开始两个多世纪了,我们到底前进了多少?一成不变的旧日革命理想,如何能撑起今天的改革大业?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7期)

倾茶博物馆,当年的三艘运茶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