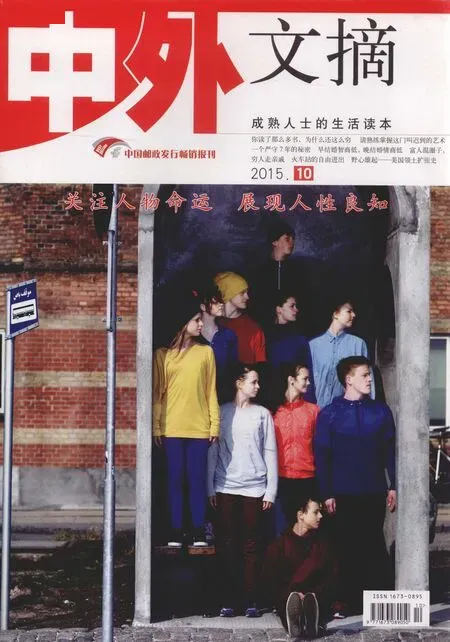思念
□ 石 峰
思念
□ 石 峰
我的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他就像茫茫林海中一颗无名的小树,在这个世界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座山、是一棵大树,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依靠、最重要的力量支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我的父亲叫石新根,字丙武。父亲的名字寓意很好,新的根,预示着未来、预示着希望,是家族兴旺的期待。父亲出生于农历壬子年8月20日,换算成阳历,2012年9月30日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今年这一天正好是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前后,我和夫人与我大哥大嫂正在江西宜春温汤镇小住。这里是全国著名的国家森林公园明月山风景区,传说是嫦娥奔月的地方,有“月亮之都”的美称,在这里过中秋赏明月,自是别有一番情趣。
中秋节晚上我们四人住宿在明月山书画院,这是一处十分优雅的山中院落,坐在屋里都可以观景赏月。不过我们还是来到了一处相对空旷的地方,这里四周没有大的树木,更没有房子,却有一个小小的明月湖,也不知是天工之作还是人工打造,山形、皓月尽收一湾湖水中。当夜幕降临,这里静得有些让人紧张,有节奏的各种昆虫的叫鸣,反而又增添了夜空的寂静。好在我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经历得多了,心里倒也坦然。月亮从山那边慢慢爬上来,让人有豁然的感觉。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据气象部门观测,今年是十五的月亮最圆,也最大、最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是能寄托思念的。我走到明月湖边,水中的月亮好像要与我对话。我用树枝轻轻地点了一下水中的月亮,平静的湖水荡漾开来,月亮笑了。我的思绪也随之荡漾,我仿佛从荡漾的月亮中看到了父亲那眯缝着双眼的笑脸,勾起我对九泉之下父亲的思念。

1962年的全家福
我的父亲是1977年10月2日逝世的,算起来整整35年了。记得那是我出差调研,从杭州到广州,路过义乌顺便回家探望父母,他们都特别高兴。那时我父亲患半身不遂,且已第三次复发。我很担心父亲的病,那天晚上与他聊了很多。他反复嘱咐我说,像我们这样家庭的人,你能在国家机关工作,不容易,要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不要担心他的病。因为是路过,第二天我就要走。我走的时候,父亲艰难地送我到路口。我走远了,回头看到父亲还站在那里,心中阵阵酸楚。据妈妈后来告诉我,我走了以后父亲在路口站了很久,一直到看不见我的身影还不肯回家,暗自流泪,当天晚上病情就加重了,第三天就不行了。那天我正在科普出版社广东分社座谈,广东省出版局人员告诉我噩耗,我愣了,急忙往家赶。我真的一直很后悔,一次匆匆的探望竟成永别,要是我那天不回家呢……
还有一件事我对父亲心存愧疚,就是我没能接父亲到北京来玩玩。我父亲有点文化,我知道北京在他心目中是怎样的分量。我能在北京生活,而且在国家政府部门工作,在他心里有多荣耀。我每次回家他都会问我很多北京的话题,他很想来北京看看。可是当时家里正在盖房子,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知道他舍不得那几十元路费,但他嘴上还不承认是钱的问题,总是说以后再去。他得病以后,来北京又多了一层困难,最后他带着遗憾走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憾事,我后悔极了。我不能原谅自己,现在想起这件事,心里还很不是滋味。父亲的遗憾也成为我的终生遗憾。
我父亲一直在义乌苏溪镇做商业工作,打得一手好算盘。苏溪离家有30多公里,那时回家一趟都得坐火车。他平时至少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有时几个月回不了家。父亲每次回家,妈妈的第一件事是忙着生炉子烧水泡茶,这既是家乡迎接亲人的礼俗,又是母亲对父亲的一片深情。满屋烟雾腾腾,一家人弥漫在烟雾中,其乐融融。父亲回家只能住两三天就得回去,因此我们父子相处的时间很少。我上学、工作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从我记事算起,我这一辈子与父亲直接相处的时间也许只能按天计算,这是多么让人心酸的事。所以我们特别珍惜每次相见。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了,家里急着用钱,妈妈就让我到父亲那里去一趟。当时我也十四五岁了,可那是我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当我找到父亲工作的商店时,父亲惊讶得不得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嘴里不停地说,“大人了,大人了”,那亲热温暖的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由于父亲常不在家,父亲每一次回家我们都十分期待。尤其是过年,父亲是肯定要回来的,而且总是年三十很晚才能到家,因为他要等商店打烊后才能往家赶,而家里一定要等父亲一起吃年夜饭。父亲在官塘车站下火车后还要走将近十几里路,我们兄弟几个会早早地到距家有3里路的江边渡口去等他。接到父亲后我们都会抢着背父亲的那个帆布包,包里面装有我们过年的希望,或吃的,或穿的。父亲到家了,我们这个家的年味就有了。每年初二随父亲到外婆家拜年,是我兄弟几个孩提时最美好的记忆。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而且抽得很凶,但总是抽最便宜的烟,因此他常常咳嗽。他抽烟没有一点浪费,每个烟头都会与新一支烟对接后抽完,对接手法十分娴熟。那时候农村很多人都抽自制烟,我也曾经试着给父亲做卷烟,方法很简单,用一支铅笔就可以做,但我做得不好,而父亲却特别高兴。年轻时候只是觉得好玩,现在回想起来却成了一件难忘的事了。
1966年我从金华师范学校毕业,1967年7月分配到家乡的稽亭中心小学当老师,我和家里人都很高兴。那时当兵是青年人的理想和向往,1968年初征兵工作开始,我和我弟弟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就报了名,而且两人体检都合格。当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特意从苏溪赶回家,见到我时他没有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什么,但看上去心里却不平静。我知道这时父亲的复杂心情。我工作以后,虽然每月只有三十几元工资,而在当时农村也算是不少的收入,可以为父亲减轻一点家庭负担。我当兵一走,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很清楚。但送儿子去当兵他有自己的认识,我大哥当兵,我二哥也当过兵。我记得他身边有一张我大哥穿着军官军衔服装的照片,他经常给人看,他很自豪。因此他不反对我去当兵,但还是把我弟弟留下了。当我穿上军装时,他很兴奋,特意带我到我的母校——大成中学——门前与我合影留念。我要集合出发了,他把他的东风牌手表送给了我,什么也没说,默默的眼神里透露出信任和期待。
我的婚姻是我大哥大嫂牵的线,当时我父亲正在南京,他很高兴。1974年1月我们结婚时,双方的父母都没有参加,婚礼是在南京我大哥部队的招待所借住的房间里举办的,参加婚礼的总共只有10个人,简朴得现在年轻人都难以想象。但在老家为我们结婚做了很多准备,为我们定制了一张架子床,定做了一床8斤重的棉被,说是北京天冷,被子上还用红棉线做出了我们俩人的名字。我二哥还从10多公里外的山区扛回来一个棕绷床垫,足有二三十公斤。这些都是全家人对我们俩的深情厚意,我们很珍惜。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我爱人还真有点缘分。我们完婚以后回家,先到上海我爱人家,然后回义乌。那时候通讯联系不便,只写信告诉父亲大概到家的时间,没想到我俩竟在同一列火车同一节车厢里遇见了父亲,他一见我们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父亲后来告诉我:我一看小刘就像我们家的人,真诚、善良、俭朴、勤快,不像印象中的上海姑娘。
俭朴,是我们家的家风,是父母亲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现在我们兄妹几个都成家立业了,家境都不错,但我们的生活都很俭朴。至今在我们脑海里对父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勤俭持家,村里人也这么夸我们家。我们兄妹5人,小时候生活困难,全家主要靠父亲每月三十几元工资生活。母亲除了操持家务,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所得工分抵不了口粮,每年还得给生产队交钱。每到生产队分粮食,如果欠生产队的钱没交齐就很尴尬,人家都高高兴兴地把粮食拿回家了,我们得在那里等,听候发落,有时候给了,有时候只能空手回家,那种屈辱感让人刻骨铭心。因此,只要妈妈手头有钱,首先把生产队的钱还上。每到新学期开学,筹措我们几个孩子学费也是一件难事,我是到8岁才得以上学的。我们兄弟几个的衣服总是大的穿过改小的,破了补了再穿。父亲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拿回家来,母亲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平心而论,我小时候的生活算不上幸福,但在父母的呵护下,也没有吃太多的苦,生活还是快乐的,每到过年还总能穿上新鞋或新衣服。家中的一切困苦都由父母亲默默地承担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蓝天。
节俭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美德。节俭成为我们这个家族为人为业的传家宝,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概括:上联“为谋家业任劳任怨,苦也无言,累也无言”;下联“恩泽后代遗风犹在,家也安然,业也安然”;横批“馨德相传”。
一片祥云飘来,渐渐遮住了明月的生辉,也挡住了我的思绪……
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中秋之夜,明月为我架起一条时空隧道,让我与九泉之下的父亲在这里相约。父亲就像我心中的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虽然不那么明亮,但给我做人的方向、做事的力量。
回到北京,我从办公室的书柜里拿出父亲的小镜框,细细端详父亲那眯缝着双眼的笑脸,慈祥、善良、温暖。父亲的笑脸深深地嵌在我的心里。
天涯海角有尽时,唯有思念无穷处。
父亲是我心灵永远的支撑。
2012年10月于北京
(摘自中国书籍出版社《书人书事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