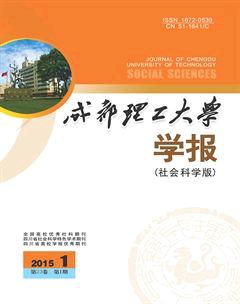环境美学与日常自然审美
崔晓艾
摘要:卡尔松明确提出环境美学涉及的两个重要问题是“欣赏什么”和“怎么欣赏”。结合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日常自然审美经验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人们在选择自然审美对象时不仅需要敏锐的身体感知,而且也受其情感、经验、知识等因素的影响。审美方式并不是单一的静观无功利模式——对象模式,而是混融性的审美模式,包括景观模式、参与式的自然欣赏模式等。明晰了“欣赏什么”和“怎么欣赏”的理论实质,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日常自然审美行为既体现出人类获取美感的合理性,同时也蕴含着影响生态环境的某些危险性。我们应该吸收借鉴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更应审慎地选择我们欣赏的对象和欣赏的方式。
关键词:环境美学;日常生活;自然;审美模式
中图分类号: B83-0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1006905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人们一直试图寻找与环境和解的恰当途径,使人类能够在和谐美丽的环境中悠然持续地生存下去,因此,环境美学这样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科,愈来愈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但环境美学毕竟仍然处于开端时期,所以,很多学者就环境美学的概念、审美方式以及与伦理学的关系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争论的重点涉及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然的审美。现代美学观,如张玉能的实践美学,明确提出了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审美关系”,显然,这种观点承袭了西方美学长期以来的习惯。对艺术的审美方式大多认可的是“18世纪现代美学确立以来所倡导的审美模式,它的典型特征是无利害的静观。”[1]而且,这种审美方式进而被放大到了对所有美的事物的欣赏,包括对自然的审美。这种静态的审美模式遭到了众多环境美学家的反对,他们提出了多种审美模式,如卡尔松、柏林特的自然环境模式、参与模式等。这些美学家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探讨自然审美问题,但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是如何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呢?本文尝试从自身的日常自然审美经验出发,还原到日常生活中,了解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是如何观察自然的,同时结合相关环境美学理论进行分析,或许我们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一、什么走进了“我”的审美视野
刘成纪老师曾这样界定环境,他认为:“环境这一概念虽然指涉自然对象, 但这里的自然明显以人为中心, 以人的可居性体现其价值。即环境是自然对作为主体的人的环绕, 是周边的自然为人建构的生存之境。”[2]这里的环境被局限于为人存在的自然,虽然环境并不单指为人存在的自然,但从中可以得出的信息是,自然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环境中的自然是环绕在人的周围,为人存在的。卡尔松则在《自然与景观》中认为“欣赏什么”是有关自然审美的重要问题之一。那就来看看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日常的“我”在一个清晨看到了什么。
“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出家门,清爽的微风拂过,空气洁净而又新鲜。虽然才7点钟,可街上已是熙熙攘攘的了。勤快的人们趁着凉爽锻炼身体,买菜,学生则三三两两结伴上学……”(1)
“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的环境被营造了出来,城市环境离自然似乎很遥远,人们见到的大多是经过人为矫饰的环境,日常生活充满了随意性和偶然性,而我偶然经验到了什么呢?
“到了目的地,身上也微微出汗了。看看时间,离开车时间尚有十几分钟,我信步走到远离校车的地方……”(1)
此时,我把目光停留在了一片草坪。
“这是一片荒芜的草坪。因许久没有工人的光顾,它失却了往日的平整柔嫩,但却平添了错落有致的繁茂生机。清风中摇曳在最上面的是野外随处可见的狗尾巴草,它们参差点缀在草坪上,依偎在它们身旁的是曾经低矮的小草,小草们摆脱了剪草机的戕害,肆无忌惮地舒展着惬意的臂膀。狗尾巴草生机勃勃地伫立着,它们俨然是这片草坪上出类拔萃的强者的象征。放眼望去,狗尾巴草似麦穗大小的花束英姿飒爽,一阵微风吹来,轻盈的身姿左右摇摆,似乎在跳着灵动的舞蹈。”(1)
在这个纷乱的环境中,狗尾巴草凸显了出来,引起了“我”的关注。桑塔耶那曾指出:“自然景观是一个无定形的对象:它几乎经常包含着充足的多样性,使得我们的眼睛有极大自由区选择、强调以及组织其元素。”[3]23正是在这种“无定形”的环境中,在“我”的视觉可以自由选择的支配下,狗尾巴草才走进了“我”的视野。人类在营造城市景观的时候,并不会把狗尾巴草作为欣赏的对象,它在景观设计者那里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很多所谓的自然都被人们经过改造成为景观,以使其符合人类的审美习惯,居于城中的人们目之所及,尽是被规训过的“自然美”,所以,在城市环境中,这种草或许才是真正的纯粹的自然。问题是,为什么微不足道的狗尾巴草能走进“我”的审美视野?在一个老农,或建筑工地上的工人眼中它是不是审美的对象呢?显然,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小草兀自生长在那里,如王阳明所说,“我”“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似乎这草是为我存在的,因我而显现。而“我”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让这花“显现”呢?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敏锐的审美感知,另一个是对象选择。
罗丹曾说,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可见,在对美的欣赏过程中,是需要敏锐的审美感知觉的。如果我们的身体深陷功利性的日常感知,终日忙于“禄位田宅妻子,数米计薪”,脚步匆匆,他是不能“兴”的,不能体悟到狗尾巴草的美。按照传统的审美态度解释,“涤除”才能“玄鉴”,“心斋坐忘”才能感知到美,这里都是在强调审美者要持无功利的心胸。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卡尔松所说,是“怎么欣赏”的问题。另外,审美者之所以能对这样的事物审美,跟他的选择有关。面对雪花,岑参写出了千古佳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背后能左右他选择的是统觉。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统觉是一种自发的活动,它受心灵中已存在的内容的影响。具体到个体,则表现为审美者自身的经验、知识、兴趣等影响其作出审美选择。赵红梅则提出了“自然全美——一个令人置疑的环境美学观念”,她从自然全美的概念、内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自然并不全美,并用众多例证表明自然“归根结蒂是人的审美活动使自然之美展现出来。但人类并不是将所有的自然都归结为审美对象,并不是所有的自然都可以被人化为审美对象的,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必须是肯定人的生存、生活、人的情感的那部分自然。”[4]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自然都美,只有特定的自然在“我”的眼中才会美,同样也从侧面说明了对象选择在审美经验中的重要性。endprint
由此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在面对环境中的自然时会有所选择,除了自身拥有敏锐的审美感知觉外,他们选择的结果必然是与自己情感契合的审美对象。因此走进“我”的审美视野的是狗尾巴草,而不是它旁边的人工草坪,更不是正在建造中的高楼大厦。
二、什么审美模式左右了“我”
当我们确定了要审美的对象,也就是知道了自己要“欣赏什么”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卡尔松所说的“怎么欣赏”的问题了。关于如何欣赏,传统美学认为要持无功利的态度静观审美对象才能获得美感。让我们来看一下,当狗尾巴草走进我的审美视野后,“我”是怎么对它审美的。
“……我静静地凝视这个可爱的小东西。这棵狗尾巴草羸弱的身体支撑着对自己而言略显庞大的脑袋,此时茎的柔韧作用凸显出来,它的身体虽纤细,但却韧性十足,当承受不了重负的时候,它会左右摇摆转移上天给予它的担子。……狗尾巴草柔韧的茎支撑着硕大的花穗,花穗从外观上看分内外两部分,内部像是盔甲一般,排列着结结实实的籽粒,像是在无声地告诉你它是多么坚不可摧。细看,有些籽粒上还残留着枯萎的黄绿色花朵,而看似十分密实的籽粒中间竟然萌生着状如麦芒的东西。这些芒状的东西均匀地覆盖在狗尾巴草墨绿色的戎装之外,恰似身披一层轻柔的霓裳羽衣,这不就是刚柔相济的绝好印证吗?我把它放置在前面靠椅的背面,土黄色的缎面背景,衬上一棵如此淡雅的狗尾巴草,中国画虚实相生的意境跃然而现。”(1)
从“我”的细致描述来看,这正是遭受一些环境美学家批判的传统审美模式——无功利的静观。卡尔松在《自然与景观》中把它命名为“对象模式”。他认为这种审美模式“面临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无论我们将对象从其环境中移除出来还是让其置于原处。”[3]27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我们静观某个单独的审美对象,就相当于在想象中把这个对象从环境中移除出来,得到的审美属性会因为被确定而打折扣,但是,如果没有在想象中被移除,就不能实现对它的审美。总而言之,在这种审美模式里,审美对象是僵死的、静态的,是为人而存在的客体,所持的立场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且得到的是有限的审美经验,因此他们提出了新的欣赏方式,如自然欣赏模式、参与模式等。在这里,“我”把狗尾巴草当做静态的艺术品来看待,它本来是环境的一分子,但在“我”的静观下,被“我”从周围纷杂的环境中移除出来,周遭的环境被“我”在想象中隐去,而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对象,被“我”无意识地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艺术审美的法则进行观照。这样欣赏的结果是,我能对面前的审美对象进行深入细致地欣赏,对审美对象的体验更加深刻独特,不被纷纭的其他自然景物所迷惑,从而避免了最终一无所获或者得到的是模糊的印象,而且这种审美模式能让“我”得到与匆匆一瞥所不一样的审美经验与心灵的触动:
“在繁华喧嚣包裹的城市中,狗尾巴草静静地偏安一隅,表达着属于自己的美丽。或许它们伫立的地方不久会被人类的堡垒占据,在新落成的堡垒缝隙里,也会有新绿填补,可丝毫不炫目,又不易驯服的狗尾巴草,注定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即使偶尔有几棵倔强地生存着,又有多少人会把目光停留在它们身上呢?有些生命就是兀自存在着,它不去想是否有人能够发现它的辉煌,只要自己曾经绽放过,来过这个世界,这就足够了。”(1)
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更能时常经历到这样的自然审美情景,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再比如“我”对家乡桂花树的观察:
“每到八月十五前后,一年一度的桂花开始绽放自己的绚丽。热热闹闹的淡黄色小花你拥我挤地点缀着高大的桂花树,仿佛一个素朴的美人云鬓上散落着细小的珍珠。我总要走近它,细细打量一朵朵可爱淡雅的小花。桂花柔嫩的花瓣犹如涂了蜡一般,托着几个米粒样的花蕊,在轻风中微微颤动,淡淡的香气霎时盈满胸怀 ……”(2)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卡尔松所反对的传统审美模式——“对象模式”,同样也能让审美者经验到自然的美,因为在这种审美模式中,即使“不起移情作用,虽分明觉察物是物,我是我,却仍能静观其形象而觉其美。”[5]而且这是更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它能使人超脱于生理快感,沉浸在审美情境中,带给人审美愉悦。
景观模式也是卡尔松反对的审美模式之一,在他看来,景观模式“过于关注其艺术和风景的特征,却将自然维度予以忽视。”[3]27简而言之,是拿艺术的眼光来欣赏自然,而自然却是活泼泼地呈现的,有区别于艺术的独特性,这种欣赏模式同样限定了自然审美的特质,而且,关键的是,“自然是自然的,而非艺术,也不是我们的创作品。”[3]30这告诫人们自然并不是人类随心所欲的对象,人类也不应该在自然的面前以傲慢的主体自居。现实中,即使在较少工业文明侵袭的乡村,自然环境虽然并没有大的改变,但经受工业文明洗礼的人们在自然审美中也往往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如“我”对故乡的这种审美经验:
“黄河的南岸,往常都掩映在烟波浩淼的绿色中,现在却可以一览无遗。几个村庄错落有致地散在山脚下,以前灰秃秃破烂不堪的房屋大都变成了暗红色的楼房,上面均是人字形的瓦房顶,瓦房顶是蓝黑色的,像是给红色的楼房戴上了一顶顶顽皮的小帽,冬天乏味的田野顿然有了一丝生气。”(2)
在这种审美经验中,虽然“我”也是在描述乡村的自然环境,但客观上已经给周围的环境限定了范围,我站在山顶这样一个定点,由此看出去,一切都在我的视力范围之内,这种情境显然是把自然对象框定在一个框架中作为一幅风景画来欣赏,自然中的美丑是按照“我”的取舍来判定的。在我的眼中,“灰秃秃破烂不堪的房屋”是不美的,而经过改造的“暗红色的楼房”则似乎更美一些,因为它使“冬天乏味的田野顿然有了一丝生气”。由此看出,景观审美模式一方面能让审美者体会到类似于艺术的美感,另一方面,这种美感确实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规定自然的美丑,结果是,我们认为不美的自然在人类审美感知觉的筛选下会逐渐变得“美”起来,但同时,真正的自然正在离我们远去。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人情化后的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已经不再是原生的自然,它已经变成了一面镜子,一面镜照人类自身的镜子。”[4]这是在说,纯粹客观的不为人存在的自然无所谓美丑,自然美是为人而存在的。因此,在自然审美中,人类更应该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带给自然什么,会使之发生什么变化,或许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会更加融洽。endprint
一些环境美学家认为景观模式除了有以上诟病之外,它还会“将自然物体和欣赏者两者从它们应当属于并在其中能够实现适当欣赏的环境中生硬剥离出来”。[3]31因此,卡尔松和柏林特提出了另外的审美模式:参与式的自然欣赏模式。柏林特在对参与式美学进行解释时说:“无边无际的自然世界不仅只是环绕着我们,它还刺激着我们 ……在此情形下,审美的标记就是全身心地参与,一种在自然世界之中的感官沉浸。” [3]31这种观点强调审美者在自然环境中要调动尽可能多的身体感官参与到周围环境中,它在对审美者提出要求的同时,也看到了自然环境对审美者的刺激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参与美学是一种在反思传统无利害的、静观美学的基础上,注重审美体验的完全综合的生态美学观,它追求一种包容性的审美参与模式。”[6]但是,这种观点在卡尔松看来也有弊端,因为这会导致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体验将只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侧重点的‘生理感知的复合”[3]32。所以卡尔松又进一步提出了自然欣赏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审美者要拥有关于自然环境的常识与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审美者获取最佳的审美效果。事实是否如此呢?让我们再来看现实中另外一个自然审美的例子,这是乡村的自然环境:
故乡的山,其实丘陵而已。……秋日的阳光在五彩缤纷的枝叶上起舞,小路旁,殷红的酸枣在丛中若隐若现。我迫不及待地拨开荆棘,轻轻地摘下一颗。分明是一颗相思红豆! ……我含在嘴里,酸中微甜,薄薄的果肉里裹着硕大的核。没了果肉,我仍然久久地把核含在口中,恋恋不舍秋日的馈赠。
……路边,黄的紫的野花星星点点,幽幽地散发着苦香,毕竟是野花的味道,不同于城市花圃里鲜花的甜香。有一丛野菊花含笑拂我,我禁不住把脸凑到跟前,亲近柔嫩的花瓣……(3)
在这个审美经验中,“我”并没有对自然环境中的某个单一对象进行静观审美,而是沉浸在包绕周身的环境中。山、秋日的阳光、枝叶、果实、野花等都成为了“我”感知的对象,而且审美者并不是只限于视觉,味觉、肤觉等感觉也参与其中,“我”调动了最大限度的身体感知觉参与到了自然环境中,这种审美模式类似于参与审美模式。这种审美经验使“我”获取的审美效果似乎更为全面,而且在这种审美模式的影响下,人俨然是环境的组成部分,他并没有站在冷静客观的一角,而是用主体性的视角来打量自然,人与自然更加亲近和谐了。同时,审美者并没有刻意地从自然环境的常识与科学知识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自然,就像柏林特描述的那样,周遭的环境在刺激着我们,触动我们去感知,去体验。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恰恰在于,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得到的是整体性的感知,在某种程度上获取的审美效果不及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带给人的审美体验那样深刻。因为“作为对主客二元模式的突破,这种参与模式有可能混淆人们的审美辨别能力,使其难以区分肤浅的鉴赏与严肃的鉴赏。后者必须考虑到鉴赏对象及其真正本质,然而前者通常只是涉及对象偶然带给经验的东西。”[3]31所以,它可能适应于某些自然环境的审美,并不能适应于全部自然环境的审美。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的日常自然审美中,我们用敏锐的审美感知觉去欣赏自然,会凭自己的喜好选择审美的对象,而且在对自然审美的时候会无意识地运用多种审美模式,例如对象模式、景观模式、参与式的自然欣赏模式等。在自然环境的审美中,欣赏什么,怎么欣赏直接关系到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而在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环境美学的理论探讨显得尤为重要。赫伯恩的《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在引发人们对自然美关注的同时,客观上也促成了环境美学的兴起。借由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审视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审美经验,能让我们明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去欣赏什么,怎么欣赏,关键是我们欣赏的对象和方式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人类的行为在怎样影响着与我们休戚相关的自然环境。正如柏林特所说:“美学并非是逃离道德领域的一个乌有之乡,它将引导和实现伦理。”[7]结合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我们明晰了城市或乡村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审美实质,这使我们懂得,当人类在对自然审美时,一方面可以享受自然带来的美感,但另一方面,人类的自然审美行为会影响到生态环境,甚至会因为人类的一意孤行而危及到生态环境的平衡,所以,我们在对自然环境的审美中,应该更审慎地选择欣赏的对象和欣赏的方式,这对于人类来说也许是最为重要也最为现实的维护生态环境的手段之一。
注释:
(1)选自本文作者的随笔《遭遇狗尾巴草的美》。
(2)选自本文作者的随笔《微雨飘香》。
(3)选自本文作者的随笔《那山,那人,那狗》。
参考文献:
[1]彭锋.环境美学的审美模式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21-125.
[2]刘成纪.自然美:一个经典范畴的当代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06-108.
[3][加]卡尔松:自然与景观[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3.
[4]赵红梅.自然全美——一个令人置疑的环境美学观念[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8-32.
[5]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6]李晓明.参与美学: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审美观[J].山东社会科学,2013,(5):44-48.
[7][美]阿诺德·柏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