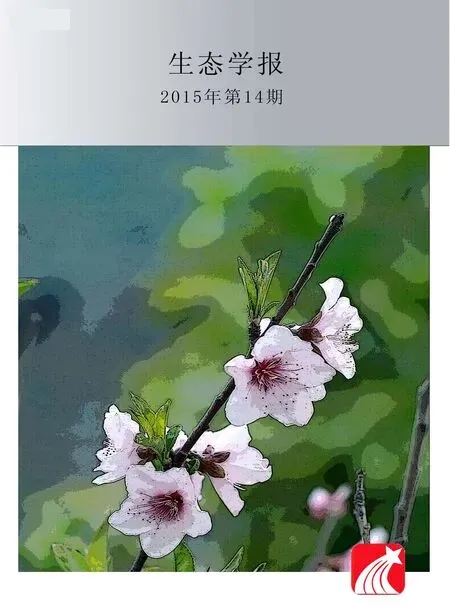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的影响
——以苏锡常地区白鹭为例
吴 未, 张 敏, 许丽萍, 欧名豪
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的影响
——以苏锡常地区白鹭为例
吴 未*, 张 敏, 许丽萍, 欧名豪
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生境网络对于物种更具有生态意义。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的影响,对破碎景观中种群的扩散和迁徙至关重要。研究结果有助于区域生境网络的恢复和完善,从物种的角度而非景观结构的角度优化生态网络。以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利用变化明显的苏锡常地区为研究区域,优势湿地鸟类白鹭为代表物种,构建物种生境斑块约束条件概念模型,提出按照物种生活习性特征划分、选择生境斑块的方法,并从斑块和网络结构两个视角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0年研究区白鹭生境的适宜地类总面积虽有所增加,但主要由于大量新增线性人为干扰致使白鹭生境网络质量下降;(2)白鹭生境网络在研究区不是全区覆盖的回路,基本由宜兴—溧阳片、无锡滨湖片、苏州吴中片和苏州阳澄湖片4个小片网构成,其完整程度按照宜溧片、滨湖片、吴中片、阳澄湖片降次排列;至2010年,宜溧片破坏最为严重,滨湖片和吴中片次之,阳澄湖片受破坏程度相对最弱。总体上,白鹭生境境况在10年间恶化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朝着不利于白鹭持续生存的方向发展。
土地利用变化; 适宜地类斑块; 生境斑块; 生境网络; 白鹭; 苏锡常地区
生态网络是保护生态学、景观生态学[1-2]、环境生态与园林生态[3]、城市规划与设计[4]、土地利用规划[5-6]等众多领域的研究热点。生态网络在功能上是物种生境网络的集合,是物种在不同生境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的重要空间保障[7-8],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的急剧变化会改变生物生境和资源的时空分布[9],削弱物种的适宜生境[10],影响物种的生境网络。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的影响,有助于区域生境网络的恢复和完善,加深对生态网络从生态过程上的认知。
目前有关网络的研究多集中在生态网络方向,将其作为一种规划手段,通过识别斑块、廊道等要素以及测度网络连接度等方法,实现对网络的构建[11-13]、评价[1,14-17]及优化[1,18-19];而有关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区域景观格局变化[20]或生态环境效应方向[21]。以生境网络为对象,考虑到时间因素,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造成影响的研究还较少。
鉴于此,本文选取了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利用变化急剧的苏锡常地区为研究对象,湿地代表性鸟类白鹭为研究物种,回答问题:(1)如何利用影像图遴选生境斑块、构建生境网络?(2)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生境斑块和网络结构)的影响是什么?
1 研究区概况

图1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苏锡常地区(苏州、无锡、常州)位于江苏省南部太湖之滨(图1),属长江冲积平原。区内地势平坦,河湖众多,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1092.4 mm,年均气温15.3 ℃。境内物种丰富,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200多种,鸟类为优势野生物种。
苏锡常地区总面积1.75万km2,其中水域面积占32.47%;地区以占全省约17%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实现了约40%的GDP和地方财政收入。2000—2010年地区农用地比重从56.69%降至44.41%、建设用地比重从14.71%增至27.82%,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2 数据与研究方法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中国科学院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2000年、2005年、2010年三期TM遥感数据、DEM数据(30 m×30 m)[22];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矢量数据[23]。空间数据通过ArcGIS 10.1和Fragstats 4.1进行了预处理。
2.2 研究方法
2.2.1 选择物种
通过代表物种选择适宜生境是研究生境网络的常用方法和手段。代表物种一般选择国家或当地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苏锡常地区野生物种以鸟类居多,加之水网密布、地表水资源丰富,为优势湿地鸟类,如鹭科(Ardeidae)提供了大量栖息地。区内主要分布有白鹭(Egrettagarzetta)、夜鹭(Nycticoraxnycticorax)、池鹭(Ardeolabacchus)和牛背鹭(Bubulcusibis)四种鹭鸟[24]。白鹭作为优势物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名单,适宜作为区域代表物种。
2.2.2 构建生境斑块约束条件模型
影响湿地鸟类生境形成的因素通常包括:(1)自然地理因素:土地利用类型、高程与坡度、植被类型与盖度、气候与气温、斑块形状与面积等;(2)生物因素:觅食半径、水深、底栖动物密度、种群密度等;(3)人为干扰因素:距建筑区和道路的距离、鱼类捕捞等[25-27]。据此可构建出一般意义上的物种生境斑块约束条件模型:
Hi=Fi(Gi,Bi,Di)
(1)
Gi=fi(Li,Ei,Sli,Vi,Ti,…)
(2)
Bi=fi(Ri,Fdi,…)
(3)
Di=fi(Bdi,Rdi,…)
(4)
式中,Hi为物种i在一定区域内的生境斑块,Gi、Bi、Di分别为影响物种i生境形成的自然地理、生物和人为干扰因素;Li为土地利用类型因素,Ei为高程因素,Sli为坡度因素,Vi为植被因素,Ti为气温因素;Ri为觅食半径因素,Fdi为底栖动物密度因素;Bdi为距建筑区的距离因素,Rdi为距道路的距离因素。式中省略号表示其它影响因素。
白鹭在太湖地区的生境斑块约束条件为:(1)自然地理因素:栖息地海拔5—70 m[28],主要在沼泽、稻田、湖泊或滩涂地以及乔木林树冠上层,主要栖息树种包括马尾松(Pinusmassoniana)、香樟树(Cinnamomumhupehanum)、麻栎树(Quercusacutissema)、榆树(Ulmusprmila)和杨梅树(Myricarubra)[24]等,受较好保护的临界面积在10 hm2以上[29];(2)生物因素:繁殖季节以湖泊和鱼塘为主要觅食生境;觅食生境水深通常不超过50 cm[30];觅食半径多在10 km左右[24];(3)人为干扰因素:包括惊飞距离(flushing distance)、距城市中心距离、平均噪音、城市化综合指数等[31]。本文选择城市区和主要对外交通用地人为干扰的缓冲距离(400 m和300 m)为主要因素[32]。
2.2.3 划分地类,选择适宜地块
生境斑块地类在很多研究中直接采用沼泽滩涂、河流湖泊、林地、草地等[4],或在此基础上细分[19],或在同一地类(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内细分[33-34]。上述考虑忽略了物种生境的多样性和变化的多元化特征。如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域内会因生活习性变化而出现生境斑块地类变化,造成在分析生境斑块过程中出现简化、遗漏等现象。可以通过以下3个步骤修正完善:(1)依据物种生活习性差异,把研究区细分为亚区,构建与亚区相对应的生境斑块约束条件;(2)依据约束条件,制定亚区地类划分方案;(3)选择适宜地类,构成亚区生境斑块。亚区生境斑块集合即区域生境斑块。生境斑块地类在亚区之间不能互换。如长三角地区,夜鹭(Nycticoraxnycticorax)和牛背鹭(Bubulcusibis)在太湖地区主要栖息地为间插在湖泊坑塘的有林地,主要筑巢树种为马尾松(Pinusmassoniana)[24];在杭州市区(不含余杭、萧山)特别是至市中心距离5—15 km的郊区[35],多栖息在到主要水源距离较近、具有灌木丛的行道树带(街巷用地、公园与绿地或其他城市建设用地)中,筑巢树种包括法国梧桐(Platanushispanic)、香樟(Cinnamomumcamphora)、槐树(SophorajaponicaL.)和杨树(Populussp.)等[36]。
本文设定白鹭在同一生活习性区,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乔木林地、沼泽滩涂、湖泊水库、对外交通用地、住宅工矿等城乡用地、其他用地六类。其生境斑块为符合以下4个基本约束条件地块的集合:(1)乔木林地为筑巢地,沼泽滩涂、湖泊水库为觅食地,筑巢地与觅食地相距不超过10 km;(2)面积不小于10 hm2;(3)高程在5—70 m之间;(4)至城市区和主要对外交通用地距离不小于400 m和300 m。
2.2.4 构建生境网络

图2 生境网络构建示意图
生境网络是彼此距离很近的生境斑块集合,在它们之间物种个体可以较自由地跨越扩散[37],即生境斑块与迁移廊道的集合。
生境斑块面积不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过程的影响和限制程度便不同。生境斑块功能上依次分为过小斑块、MVP(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斑块、小斑块和关键斑块四类[38]。对于大多数物种而言,许多斑块相对MVP斑块来说太小,故本文将生境斑块按面积分为500 hm2以上、100—500 hm2、50—100 hm2和10—50 hm2四类,分别对应一、二、三、四级生境斑块。
白鹭(鸟类)的迁移廊道通常是直线,觅食半径不超过10 km。借鉴图论[6]方法, 在ArcGIS中通过Feature to point工具将生境斑块转换为节点;借助TIN和Conefor工具得到两两距离不超过10 km的迁移廊道,构成生境网络(图2)。
2.2.5 选择指数
生境网络的变化与生境斑块面积和空间布局的变化休戚相关。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的影响可以从对生境斑块和网络结构的影响两个方面入手。
(1)斑块 选择包括斑块总面积(CA)、斑块密度(PD)、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AWMSI)、平均最近距离(MNN)、聚集度指数(AI)5个类型水平景观指数和蔓延度指数(CONTAG)、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两个景观水平指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斑块的影响[39-40]。
(2)网络结构 网络的复杂性可通过闭合度、线点率以及网络连接度等网络结构指数描述。选择α、β、γ3个网络结构指数,分别反映网络中回路出现的程度、每个节点的平均连线数、所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16-17],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结构的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境斑块选择结果
图3是苏锡常地区2000、2005、2010年满足白鹭筑巢地和觅食地条件的适宜地类斑块分布情况。把整个太湖作为白鹭的潜在生境,与实际情况不符,故剔除从其边界沿纵深10 km以外的部分。符合生境斑块约束条件、并经划分等级的生境斑块分布情况(图3)。

图3 满足白鹭筑巢地和觅食地条件的适宜地类斑块及经约束条件限制和等级划分的生境斑块分布情况
2000—2010年,受约束条件限制,白鹭生境斑块在面积和范围上比适宜地类斑块明显偏小(图4)。分区上,苏州境内的适宜地类斑块和生境斑块都最多,无锡次之,常州最少。适宜地类斑块向生境斑块转换过程中,常州的变化最明显,主要是境内适宜地类斑块中的长荡湖、滆湖以及茅山风景区等均在10 km范围内没有相应的筑巢地或觅食地,未达到生境斑块条件被剔除。太湖是区域最大的生境斑块,占总面积的95%以上。

图4 2000—2010年苏锡常3地及研究区总的适宜地类斑块及生境斑块面积变化情况
生境斑块等级上(表1),高等级斑块数量少于低等级斑块:一级生境斑块数量很少,除太湖外,斑块间面积相差很小;二级生境斑块总面积从与三、四级生境斑块相差不明显(面积比为2.36∶1∶1.93)变化至明显(8.29∶1∶1.75);三、四级生境斑块总面积都很小,相差不大。总体上,一、二、三级生境斑块数量接近且偏少,明显少于四级生境斑块数量。
生境斑块空间分布上(表2),高等级生境斑块多在苏州、无锡的一级生境斑块数量最少、常州没有二级生境斑块。变化趋势上,苏州2000—2005年,一、二、三级生境斑块数均有增加,但四级生境斑块数减少了;2005—2010年二级生境斑块数增加了,其余等级生境斑块数都减少了。无锡仅有的1块一级生境斑块(宜兴国家森林公园)到2010年降至二级;三级特别是四级生境斑块减少明显。常州一级生境斑块集中在天目湖周边,数量稳定;三、四级生境斑块数则先增加后减少。

表1 2000—2010年各等级生境斑块数量及面积变化情况

表2 2000—2010年各等级生境斑块空间分布/个
太湖作为一个斑块处理,归并到苏州除太湖外,区域白鹭生境斑块面积偏少、苏锡常3市分布不均,低等级生境斑块面积持续减少。尽管适宜地类斑块总面积有一定增加,但仅对白鹭单一物种而言,生境斑块总面积减少了,生境环境在恶化。
3.2 对生境斑块的影响分析
一级生境斑块数量很少且占总面积比重很高,需要单独分析。2000—2010年,区内有4块一级生境斑块发生了显著变化:(1)2000—2005年,金鸡湖区出现了适宜白鹭筑巢的乔木林地,在金鸡湖—独墅湖—阳澄湖周边形成了1块一级生境斑块。由于历史资料不足,无法校核解释乔木林地新增原因。(2)2005—2010年,宜兴国家森林公园周边路网密度明显加大,特别受长深高速公路、昆承湖周边苏虞张公路及锡太一级公路、阳澄湖周边苏绍高速公路及京沪高铁建设等影响,3块一级生境斑块破碎降至二级。
类型水平指数中(图5),(1)2000—2010年,二级生境斑块面积>四级生境斑块面积>三级生境斑块面积,并且二级生境面积持续增加,三、四级生境面积持续减少。(2)2000年,四级生境斑块密度高于二、三级生境斑块密度,2005年起差距不断缩小;二、三级生境斑块密度较接近且变化稳定。(3)三类生境斑块形状都趋于规整,且高等级斑块形状复杂程度高于低等级斑块。(4)三类斑块的平均最近距离情况差异较大,二级斑块从约500 m增至约10000 m后又降至4000 m,三级斑块从15,000 m降至10000 m后激增至25000 m,四级斑块从2000 m缓慢升至5000 m。总体上,四级斑块分布最密集,二级次之,三级最稀疏。(5)三类斑块聚集度指数变化趋势都基本缓慢增加,但二级生境斑块>三级生境斑块>四级生境斑块。景观水平指数中(图5),蔓延度指数2000—2005年变小,至2010年变大且超过2000年水平,香农多样性指数表现为与之完全相反的变化。2010年,留存生境中高等级生境斑块优势明显,不同等级生境斑块间的差异性变弱。事实上大量新增建设用地特别是国家及区域性大型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线性人为干扰)的修建,对区内各级生境斑块进行了普遍分割。原有高等级斑块出现降级,原有低等级斑块因不能达到最小门槛面积被剔除;区内高等级斑块数量减少,但占斑块总数比重反而增加。说明新建线性人为干扰对地区生境斑块的影响甚于新建团块状人为干扰;线性人为干扰致使区内各级生境斑块面积普遍减少降级;网状线性人为干扰的负面影响作用最为明显。

图5 2000—2010年二、三、四级生境斑块不同景观指数的变化情况
3.3 对网络结构的影响分析
图6为图3各时期生境斑块所对应的生境网络。苏锡常地区白鹭生境网络大致由四个破碎不完整的部分组成:斑块与廊道最为密集的宜兴—溧阳(宜溧)片、次之的无锡滨湖片、苏州吴中片以及苏州阳澄湖片。2000—2010年,(1)宜溧片的破坏最为严重,被割裂成彻底孤立的溧阳和宜兴2小块,构成宜兴块的2个环仅靠2个四级生境斑块间的1条廊道维系连接。(2)滨湖片的破坏程度次之,被割裂为彻底孤立的、长度均不足20 km的2小块廊带。(3)吴中片由太湖北部和中部2小块组成,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湖北块破坏严重,被分割成彻底孤立的2个单环;湖中块内的生境斑块普遍降级,廊道密度明显降低。(4)阳澄湖片受破坏程度相对最弱,斑块间带状连接基本没有受到破坏。

图6 由生境节点和迁移廊道所组成的白鹭潜在生境网络变化情况
网络结构指数中(表3):(1)α指数2000—2005年时大于1,网络回路较多、环通度较好,可供白鹭在宜溧、滨湖、吴中3片区各自内部自由迁移;2010年降至不足0.5,网络回路明显较少,环通度很差。(2)β指数2000—2010年从4.59降至1.88,虽然个别小块保持了较好的连接度,但节点对外连接的实际状况恶化严重。(3)γ值2000—2010年从1.58降至0.65,说明近半生境斑块被割裂孤立了,与β指数分析结论一致。节点和廊道数量变化上,节点减少了46%时,廊道数降至不足原来的23%,劣于节点减少情况,意味着一些连接型节点(如图7中的节点1、2、3)的失缺(节点重要性由实际连线数决定,连接线数越大,重要性越高)。即土地利用变化对苏锡常地区白鹭生境网络破坏重点是,造成了连接型节点所对应的生境斑块的失缺。
节点等级与生境斑块等级相对应,反映生境斑块及连接不同等级生境斑块廊道在重要性上的差异。廊道两端连接的节点在等级上有3种情况:高—高等级节点连接、高—低等级节点连接、低—低等级节点连接。重要性通常依次下降。但图7中,2000—2010年在宜溧片生境网络体系中,有若干位置型节点(如图7中的节点4、5、6),它们的等级不高、连接的廊道数也不多,但在维系整个生境网络的整体性时,它们存在的位置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超出了比自身更高等级斑块及其所构建的高等级廊道。说明土地利用变化对白鹭生境网络的另一破坏重点是破坏位置型节点造成生境网络整体性下降。

表3 2000—2010年苏锡常地区白鹭潜在生境网络结构指数变化情况

图7 宜溧片节点与廊道等级分布情况
4 结论
本文以苏锡常地区白鹭为代表性物种,构建了物种生境斑块约束条件的概念模型,提出按照物种生活习性特征划分和选择生境斑块的方法,从斑块和网络结构两个视角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0年苏锡常地区白鹭生境的适宜地类斑块面积虽有所增加,但主要由于线性人为干扰的增加造成了白鹭生境网络质量的下降,土地利用变化实际朝着不利于白鹭持续生存的方向发展。白鹭生境网络在苏锡常地区不是覆盖全区的环路,仅为4个小范围的片网,境况在10年间不断恶化。
白鹭生境约束条件较为复杂,本文选择了部分重要条件作为选择生境斑块的依据,对水深、水质等未细分,设定直线路径为白鹭(鸟类)迁移廊道也较为粗略等,需要不断完善。虽然鸟类为苏锡常地区优势野生物种,但兽类、两栖爬行动物与鸟类迁移特性不同,更容易受到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其研究有待加强。白鹭生境网络与区域适宜地类斑块变化情况更进一步反映出区域生态网络中必须加强对生态过程的研究。
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是长三角地区的典型代表。苏锡常地区白鹭生境网络变化情况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乃至我国经济活跃、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其他地区,仅对高等级(生境)斑块重点保护是不够的,低等级(生境)斑块也需要保护;识别并恢复已消失的但重要的低等级(生境)斑块,更切合实际;要有选择性的增设一些具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的斑块,贯通斑块间的生态过程,优化完善生态网络。这种分析思路和方法,为深入研究生态网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尺度问题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及核心问题之一。多尺度角度研究生境选择[26]、生境保护[2]、生境网络及生态网络优化,更能够全面反映出斑块、格局之间的生态过程;不同幅度上实现空间和功能上的合理镶嵌,真实反映物种的生态过程,才能真正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对线状人为干扰因素的影响很大,只有分辨率小于线状人为干扰因素最小宽度时,才能避免线状要素的消失或出现断点现象[41]。
[1] 孔繁花, 尹海伟. 济南城市绿地生态网络构建. 生态学报, 2008, 28(4): 1711-1719.
[2] 赵振斌, 赵洪峰, 田先华, 延军平. 多尺度结合的西安市浐灞河湿地水鸟生境保护规划. 生态学报, 2008, 28(9): 4494-4500.
[3] 鲁敏, 杨东兴, 刘佳, 裴翡翡. 济南绿地生态网络体系的规划布局与构建.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0, 18(3): 600-605.
[4] 尹海伟, 孔繁花, 祈毅, 王红扬, 周艳妮, 秦正茂. 湖南省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 生态学报, 2011, 31(10): 2863-2874.
[5] Marulli J, Mallarach J M. A GIS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application to the Barcelona Metropolitan Are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5, 71(2): 243-262.
[6] Vasas V, Magura T, Jordán F, Tóthmérész B. Graph theory in action: evaluating planned highway tracks based on connectivity measures. Landscape Ecology, 2009, 24(5): 581-586.
[7] Jongman R H G, Bouwma I M, Griffioen A, Jones-Walters L, Doorn A M V. The pan European ecological network: PEEN. Landscape Ecology, 2011, 26(3): 311-326.
[8] Opdam P, Wascher D. Climate change meets habitat fragmentation linking landscape and biogeographical scale levels in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4, 117(3): 285-297.
[9] 欧阳志云, 郑华. 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机制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2009, 29(11): 6183-6188.
[10] Palomino D, Carrascal L M. Habitat associations of a raptor community in a mosaic landscape of Central Spain under urban development.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 83(4): 268-274.
[11] Vuilleumier S, Prélaz-Droux R. Map of ecological networks for landscape plann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2, 58(2-4): 157-170.
[12] Gurrutxaga M, Lozano P J, Barrio G D. GIS-based approach for incorporating the connectivity of ecological networks into regional planning.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2010, 18(4): 318-326.
[13] Weber T, Sloan A, Wolf J. Maryland′s green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land conservatio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7(1-2): 94-110.
[14] Cook E A. Landscape structure indices for assessing urban ecological network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2, 58(2-4): 269-280.
[15] 滕明君, 周志翔, 王鹏程, 徐永荣, 吴昌广. 景观中心度及其在生态网络规划与管理中的应用. 应用生态学报, 2010, 21(4): 863-872.
[16] 王海珍, 张利权. 基于GIS、景观格局和网络分析法的厦门本岛生态网络规划. 植物生态学报, 2005, 29(1): 144-152.
[17] Linehan J, Grossa M, Finnb J. Greenway planning: developing a landscape ecological network approach.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3(1-3): 179-193.
[18] 宋晓龙, 李晓文, 张明祥, 杨殿林, 张黎娜, 张贵龙. 黄淮海地区跨流域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网络体系优化. 应用生态学报, 2012, 23(2): 475-482.
[19] 傅强, 宋军, 毛锋, 吴永兴, 姚涵, 唐剑波. 青岛市湿地生态网络评价与构建. 生态学报, 2012, 32(12): 3670-3680.
[20] 万荣荣, 杨桂山. 太湖流域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演变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2005, 16(3): 475-480.
[21] 周启星, 王美娥, 张倩茹, 任丽萍, 王如松. 小城镇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分析. 应用生态学报, 2005, 16(4): 651-654.
[22]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2013-07-01].http://www.gscloud.cn
[23]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 [2013-07-01].http://www.geodata.cn
[24] 阮禄章, 张迎梅, 赵东芹, 董元华, Mauro F. 白鹭作为无锡太湖地区环境污染指示生物的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2003, 14(2): 263-268.
[25] 葛振鸣, 王天厚, 施文彧, 周晓. 长江口杭州湾鸻形目鸟类群落季节变化和生境选择. 生态学报, 2006, 26(1): 40-47.
[26] 曹铭昌, 刘高焕, 徐海根. 丹顶鹤多尺度生境选择机制——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学报, 2011, 31(21): 6344-6352.
[27] 董超, 张国钢, 陆军, 侯韵秋, 乔龙巴特尔, 昂秦. 新疆巴音布鲁克繁殖期大天鹅的生境选择. 生态学报, 2013, 33(16): 4885-4891.
[28] 张迎梅, 阮禄章, 董元华, 龚钟明, 李运东, 王辉, Mauro F. 无锡太湖地区夜鹭及白鹭繁殖生物学研究. 动物学研究, 2000, 21(4): 275-278.
[29] Hinsley S A, Bellamy P E, Newton I, Sparks T H. Habitat and landscap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 breeding bird species in woodland fragment. Journal of Avian Biology, 1995, 26(2): 94-104.
[30] 辜永河. 白鹭的栖息地与取食行为的研究. 动物学杂志, 1996, 31(3): 23-24.
[31] 王明春, 杨月伟. 城市化对繁殖期白鹭的影响. 曲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 33(4): 90-94.
[32] Palomino D, Carrascal L. Threshold distance to nearby cities and roads influence the bird community of a mosaic landscape.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7, 140(1-2): 100-109.
[33] Luan X F, Qu Y, Li D Q, Liu S R, Wang X L, Wu B, Zhu C Q. Habitat evaluation of wild Amur tiger (Panthera tigris altaica) and conservation priority setting in north-easter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1, 92(1): 31-42.
[34] 张爽, 刘雪华, 靳强, 李纪宏, 金学林, 魏辅文. 秦岭中段南坡景观格局与大熊猫栖息地的关系. 生态学报, 2004, 24(9): 1950-1957.
[35] 陈水华, 郑光美, 丁平, 诸葛阳. 杭州市湿地水鸟的分布与多样性研究. 生命科学研究, 2000, 4(1): 65-72.
[36] 王彦平, 陈水华, 丁平. 杭州城市行道树带的繁殖鸟类及其鸟巢分布. 动物学研究, 2003, 24(4): 259-264.
[37] Verboom J, Foppen R, Chardon P, Opdam P, Luttikhuizen P. Introducing the key patch approach for habitat networks with persistent populations: an example for marshland bird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1, 100(1): 89-101.
[38] Jongman R H G, GIori a IPungetti. 生态网络与绿道——概念. 设计与实施//余青, 陈海沐, 梁莺莺,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46-49.
[39] 布仁仓, 胡远满, 常禹, 李秀珍, 贺红士. 景观指数之间的相关分析. 生态学报, 2005, 25(10): 2764-2775.
[40] 陈文波, 肖笃宁, 李秀珍. 景观指数分类、应用及构建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2002, 13(1): 121-125.
[41] 吴昌广, 周志翔, 王鹏程, 肖文发, 滕明君, 彭丽. 基于最小费用模型的景观连接度评价. 应用生态学报, 2009, 20(8): 2042-2048.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habitat network: a case study ofEgrettagarzettain Su-Xi-Chang Area
WU Wei*, ZHANG Min, XU Liping, OU Minghao
CollegeofLandManagement,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Habitat network as part of ecological networks is very important for species.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the impacts of land use change on habitat network as well as the dispersal and migration of species, especially in current rapid urbanizing cond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rebuilding and optimizing regional ecological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es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process, but not only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as most previous research did.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find out: (1) how to map out the habitat network of a certain species from TM images in a grid pattern? (2) How land use change affected the habitat network of the species, especially from the views of habitat patch and network structure? The Su-Xi-Chang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was selected as case study due to its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changes. In this research, theEgrettagarzettawas selected as a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species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reasons: (1) marshland birds are the superior species among wild animals of the study area; (2)Egrettagarzettais the superior species among marshland birds which is on the list of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3) the data related to living and hunting habitats ofEgrettagarzettain the study area are easy to ge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Egrettagarzettahabitat, we developed a Conceptual Constraint Model of Species Habitat Patch (CCMSHP) and a method to select habitat patch properly from different land types. In CCMSHP,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forming of species habitat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oarsely, which are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human disturbances. In each category, main specific constraints were obtained from previous results and transferred suitably from the calculation supported by the ArcGIS software. Based on the identifiedEgrettagarzettahabitats, their habitat networks were accordingly developed. Then, landscape metrics and network structure indicator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he mapped-out habitat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area of patches suitable forEgrettagarzetta′s living and hunting was increas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10; however, the quality of the habitat network was decreased seriously due to the strong negative effect of newly-built constructions, such as expressways and high-speed railways. (2) The habitat network ofEgrettagarzettai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whole area which consists of four separate fractions. They were Yixing-Liyang Part, Binhu Part, Wuzhong Part, and Yangchenghu Part and ranked down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ir conditions of 2000. During the recent ten years, these fractions have been seriously destroyed. Among of them, Yixing-Liyang Part was in the worst condition and then following by Binhu, Wuzhong and Yangchenghu Part. In a summary,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the condition ofEgrettagarzettahabitat environment was becoming worse; and the land use change has affected the survival ofEgrettagarzettabadly. We suggest that the protection both of high and low-level patches in hierarchy is importan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and rebuilt those disappeared low-level patch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abitat network.
land use change; suitable patch; habitat patch; habitat network;Egrettagarzetta; Su-Xi-Chang Area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90451220); 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0003592)
2013-12-11;
2014-12-08
10.5846/stxb201312112930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ww@njau.edu.cn
吴未, 张敏, 许丽萍, 欧名豪.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网络的影响——以苏锡常地区白鹭为例.生态学报,2015,35(14):4897-4906.
WU W, ZHANG M, XU L P, OU M H.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habitat network: a case study ofEgrettagarzettain Su-Xi-Chang Area.Acta Ecologica Sinica,2015,35(14):4897-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