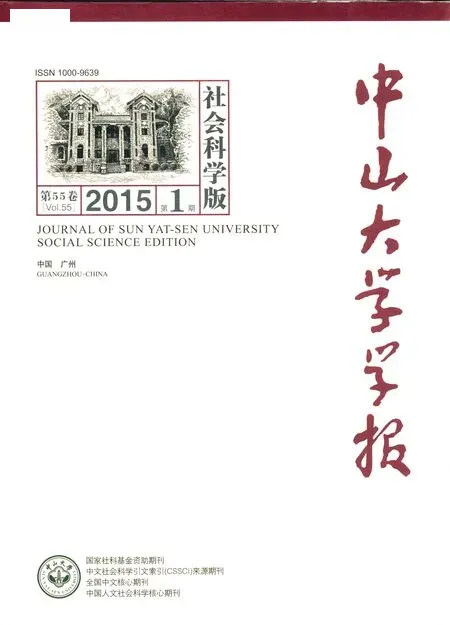事件·文本·社会*
——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历史事件与文学形象的考察
高翔宇
事件·文本·社会*
——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历史事件与文学形象的考察
高翔宇
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关于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广告,引发了多重场域的反应与互动。唐群英率众将报馆捣毁,酿成了一场官司诉讼。在历史事件中,唐群英本人因“英雌”动武的行为,不仅于法庭审判中败诉,同时被公众扣上了“女德有缺”的帽子。而文学作品的介入,更使得唐、郑“婚变案”颇具戏剧化色彩。事实上,透过案件结局与文学形象中唐群英的遭遇,恰可瞥见“英雌”话语的内在困境以及民初女性面临的诸多社会生态。
唐群英;《长沙日报》;历史事件;文学形象;英雌话语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阳人,民国初年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袖人物①学术界对于唐群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领导的民初女子参政运动方面,代表性论文有,严昌洪:《唐群英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李细珠:《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陈家新:《辛亥女杰唐群英与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等。此外,亦有学者关注唐群英的家世生平、女子教育、诗词成就、人物交往等,参见罗湘英主编:《唐群英研究文集》,衡阳市妇女联合会刊行,1998年。。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刊载了一条关于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广告,遂引发了唐率众捣毁报馆的“暴力化”行动。该事件经当时报刊的披露,无论作为案件的审判抑或是文学作品的书写,均为公共视野所追踪②目前关于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事件的研究,仅在颜浩:《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中“英雌大闹参政权”一节略有提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4—167页),但叙述较为简单,尚未充分挖掘该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而案情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唐、郑婚姻关系的简单释义,恰可作为解析民初女性与社会的个案,细加揣读。
一、案发现场:婚变广告与诉讼风波
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馆经历了一场被捣毁的飞来横祸。肇事者正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英雌”唐群英。“祸水”源头便是《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关于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告白启事:
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当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湘省,拟重登花烛,以乐慈帏。因误会少生家人之变动,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殊不知儿女英雄,凡事皆出人一等,同志亮诸。郑师道、唐群英
同启。①因报馆被唐群英捣毁,故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已失传。该广告原文被当时诸多报刊转载,可参见《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新闻报》1913年2月26日,第2张第1版;《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之详闻》,《神州日报》1913年2月26日,第3版;《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之祸胎》,《申报》1913年2月28日,第6版;《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大公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等。
据悉,唐群英见到该广告后情绪异常失控,当天下午三时便来到《长沙日报》编辑部,“大肆咆哮”,并“打碎玻璃、窗、茶、碗、椅子等”。报馆人员表示可对广告纠误,且将“更正稿”交由唐本人阅目。唐群英对此本已“毫无异词”,但因稍晚印行的“修订稿”竟将唐、郑结婚的日期添改为“十二月四号”②《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广告最初关于唐、郑结婚日期的表述,确为“二月四日”,但更正版修订为“十二月四日”,少数报刊转录的是修改后的版本。见《公电·长沙日报来电》,《民立报》1913年2月18日,第3版;《唐群英也闹报馆(湖南)》,《正宗爱国报》1913年2月20日,第5版等。另,法庭对唐群英的第二次预审中间,唐群英的代理辩护人丁云龙亦对日期添改问题质疑,见《唐群英案第二次预审详情》,《申报》1913年3月7日,第6版。,故在其女友张汉英的鼓动下,于晚间八时三十分,又“忽统率男女三十余人来馆”。她们取去“门首招牌两块”后,“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长沙日报》只得发出停刊通告,并“报知警署”以清理现场,且拟“提起诉讼”③《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新闻报》1913年2月26日,第2张第1版。。唐群英发表通电,声称郑师道为“浙江极无赖之人”,与之撇清关系,又斥责报馆滥登广告,“损人名誉,毫无道德”,且请谭延闿都督“将郑拿办”及取消该报。女子参政同盟会亦来电为唐群英助威呐喊④《唐群英通电》,《时报》1913年2月27日,第4版。。郑师道则理直气壮地坚持请社会各界“力主公论”⑤《公电·长沙日报来电》,《民立报》1913年2月18日,第3版。。
郑师道,浙江人士,同盟会会员。在与唐发生“婚变案”之前,郑曾在临时参议院的某次大会上,于胸前捆绑“鸡蛋两枚”充作炸弹,扬言欲与共和党人“同归于尽”⑥《参议院纪要·石破天荒之炸弹》,《申报》1912年7月3日,第2版。。又曾因调停沈佩贞与《亚东新闻》的冲突未遂,反被殴打⑦《沈佩贞大闹亚东新闻社》,《申报》1912年12月19日,第3版。。在宋教仁的追悼大会上,郑还因挑动“南北感情”的激烈发言,搅得全场“秩序颇为纷乱”⑧《社会党追悼宋钝初大会》,《申报》1912年4月15日,第10版。。故时人多将郑看做“亢进性精神病患者”⑨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页。。民元旧历之冬,当唐群英返湘筹建“女子参政同盟会支部”时,追求唐素来已久的郑恰得“湖南调查盐务委员”身份,便尾追来湘。不料,《长沙日报》却刊登了“新人物之面谱”——郑认为男面上题的“无耻委员”与女面上题的“多情学士”,影射了他与唐群英的关系。殊为难堪的郑师道决定通过刊登与唐结婚的广告,以挽回些许颜面⑩《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一)》,《民立报》1913年2月28日,第10版。故,郑所登广告内容中有“……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等语。。
2月18日下午一时,长郡地方检察厅对《长沙日报》被毁诉讼案进行第一次预审。原告《长沙日报》总经理文斐、被告郑师道均到案,而被告唐群英则拒绝出庭。法庭经讨论认为:一因广告为郑送予刊载,故郑应对唐负责,与报馆无涉。二因报馆本是“据事直书,有闻必录”,故唐应对《长沙日报》负责,并赔偿对方损失九千元。三因唐、郑婚姻关系属民事纠纷,故其不在该庭讨论范围内⑪《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二)》,《民立报》1913年3月1日,第10版。。
该案件本属私领域范畴内的男女关系问题,但由于法庭的介入,上升为一场关乎法律信用与法律适用的论争。在法庭上,郑师道主动为唐申请“无罪辩护”称:“中央违法之处甚多。如大总统杀张方案……赵秉钧封闭北京某报。总统总理既可违法,则唐群英亦系革命有功之人,自应原谅。”原告文斐反击,得到了审判厅长的支持:至于郑所称,系北京审判厅自行放弃责任,“湖南审判厅不得援以为例”①《唐群英打毁长沙报馆之讼案》,《神州日报》1913年3月2日,第4版。。
第一次预审结果已颇为尴尬,而唐接连“拉虎皮做大旗”的行动,更使其深陷被动。一是唐“以女界全体名义”召开大会。会上某两女士威胁称:“如不与唐恢复名誉,各处女学即一律停课。”且唐称:“准备三手枪与文、郑二人相见于法庭。”如确有结婚证据,即以手枪自击②《唐群英之对付文斐》,《新闻报》1913年3月5日,第2张第1版。。随后,一纸题为《长沙日报主任文斐之罪状》的印刷物在群众中间散发开来。其中牵扯到所谓去岁湘省光复时文斐“惨杀焦陈”一节,立刻点燃了舆论的沸点③关于文斐“十大罪状”的全文内容,见《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五)、(六)》,《民立报》1913年3月6日,第10版;3月7日,第8版。当谭延闿杀害焦达峰、陈作新之际,文斐正在都督府部署军事。随后文与谭的靠拢,亦使其与此案似难脱干系。参见柳无忌、殷安如编:《南社人物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53页。。二是唐偕亲密姊妹七八人赴都督府,扬言不愿与该报在法庭对质,如该报再行出版,“即要再打,非达取消之目的不止”,并“请予通饬各署将郑严拿究办”④《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新闻报》1913年3月4日,第2张第1版。。三是《女权日报》附和唐的口诛笔伐,“以攻击《长沙日报》及其总理文斐之事为多”⑤《湘中女权消长谈》,《申报》1913年3月19日,第6版。。
唐群英上述“反击”将湖南舆论界搅得风生水起。批评《长沙日报》的“少数派”认为,报馆违反了唐之前在《长沙日报》刊出“凡往来文牍,嗣后若未盖有私用图记,请作无效”启事的原则⑥《唐群英启事》,《长沙日报》1913年2月4日,第9版。,且“郑之疯狂,尽人皆知,该馆不应听其污蔑女界”。而责备唐的“多数派”认为,因“广告系营业性质”,报馆本不负责任,且该馆对唐已“格外通融”⑦《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新闻报》1913年3月4日,第2张第1版。,故与其说唐是女界之豪杰,毋宁说其为“女界中之败类”⑧《长沙日报与唐群英诉讼详志(续)》,《时事新报》1913年3月2日,第3张第1版。。
事实上,民初“英雌”插足社会,肆行无忌之怪态,早在男性中引起了骚动与不安。如唐群英大闹参议院、揪打宋教仁、干涉胡瑛娶两妻、用铁条穿弟妾头部等行径皆为时人侧目⑨参见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20—25页;范体仁:《桃源胡瑛生平》,政协湖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十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3—194页;《倡平权迁怒弟妾》,《申报》1912年12月24日,第6版。。沈佩贞大闹参议院、亚东新闻社,对追求者熊载扬的表白还以鞭打等野蛮面目亦让时人嗤之以鼻⑩参见《沈佩贞大闹亚东新闻社》,《申报》1912年12月19日,第3版;钝根:《心直口快》,《申报》1912年10月16日,第10版。。男性在肃清女界风气方面苦于寻求一个适宜的时机,恰好唐大闹《长沙日报》之“暴动”为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男性遂以此事为开端,以批判“女子无德”为名义,论及女性“国民之母”形象尚且欠缺,自然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女国民”,既然“女国民”做不成,则女性不配拥有参政权。换句话说,当人们一旦在“女德”与“女权”之间建立起联系,以“女德”缺失为由,质疑女性拥有参政权——这一逻辑便自然而生。
3月14日,《申报》发表了《女权与今日》,讨论女德、女学、女权三者的关系。“女学实今日中国之急务,而女权者实今日世界之缓图……女德不张也,女权适足以亡国”,女同胞“苟欲言女权,吾请再言女德……吾非谓唐、沈诸女士之女德有缺,吾特恐继唐、沈诸女士之芳躅而继起,以滥用女权者,尚复大有人也”。故培养女德必先兴女学,女学为女权之根本问题⑪曼倩:《女权与今日》,《申报》1913年3月14日,第1、2版。。3月22日,某作者在《大公报》发表的《论女权》中指出,先进之英国尚且难免女子参政党人之纷扰,“我凡百草创之中国”之流弊恐更难言。返观“近日唐群英之捣毁《长沙日报》”及其“种种不名誉之事”层见迭出者,“为吾人所不忍言”。唐、沈等辈“以光怪陆离之异彩,炫幼稚之国民……吾且为女权呼冤矣”①《论女权》,《大公报》1913年3月22日,第1、2版。。
与此同时,《长沙日报》一方面致函各处斥责唐群英“蛮不论理”,比“乡井无知识之强悍妇之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今欲图女学发达,希望女子参政,“非力去此种害马”不可②《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3版。。另一方面还以对于醴陵县某邑为李氏、何氏等六百余贞孝节烈之人建筑祠坊,并“复合贞裔纂修谱牒”事迹的歌颂,给予“女德有缺”的唐群英不点名的批评③《阐扬贞孝节烈》,《长沙日报》1913年3月9日,第10版。。经理文斐除了痛骂唐、郑二人为“奸夫淫妇”④《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还摆出一副患有“唐群英恐惧症”的可怜模样,称恐唐“真来打闹”,请调“警察多人在馆守卫一天”,又请“木工制短棍多根、绳索数件”,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⑤《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四)》,《民立报》1913年3月4日,第10版。。
此外,女界在对唐群英的评价问题上也出现了分化:不仅有“将唐劣迹印刷宣布者”,还有人批判唐,其捣毁《长沙日报》馆且用女界全体名义遍发传单及开会,“犹不自愧”。甚至湘中部分女校学生“以唐群英辱人贱行,耻与为伍”⑥《郑唐之案·转录长沙寄来之印刷品》,《新闻报》1913年3月11日,第4张第1版。。
舆论对唐、郑“婚变案”的渲染,已经使得唐在湘省建立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支部卷入风波,“以致湖南妇运一度颇受影响”⑦吴剑、段韫晖:《湖南妇女运动中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66页。。唐自己还闹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笑话。女子参政运动的另一位领袖王昌国,对于其与国民党元老谭人凤结成“奇缘”的绯闻,曾登报“誓抱柏舟主义,决不再醮”。唐为了与郑在男女关系上划清界限,便仿效王,宣称“矢志柏舟”。唐虽为寡妇,但非同王为丈夫遗弃。故“闻者皆为之捧腹”,一时间“湘中女界以‘柏舟’二字为最近之新名词,竟相率以为口头禅语”⑧《湖南女杰风流案之余闻》,《神州日报》1913年3月9日,第3版。“柏舟”二字最早见于《诗经·邶风·柏舟》、《鄘风·柏舟》,“柏舟”在古义中为妇人遭受遗弃,为群小所欺,但坚持正道,不甘屈服。另,需要说明的是唐的寡妇情况:1889年,唐群英被父亲许配与湘乡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1891年与曾正式完婚。1894年唐生一女,1896年此女夭亡,1897年唐的丈夫猝然病故。见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8—10页。。此外,郑在法庭上为唐乞求原谅本已使人们“窃窃不解”,其到处宣扬拥有一大包含有“相片、信札、婚约等件”的“结婚证据”⑨《唐群英凶毁长沙日报馆始末记·长沙日报之报告》,《时报》1913年3月3日,第4版。,更使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面对“第二次预审”的催讯,唐群英依旧“托病不到”,邀请丁云龙为其代理人。并且,或是出于唐的频繁“控诉”,或是基于“郑不离湖南,则风潮将不止”的社会共识,最终湘省巡警厅还是给郑师道下了“逐客令”⑩《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七)》,《民立报》1913年3月9日,第8版。。2月25日下午二时,第二次预审已无被告郑师道的踪影。然而,尽管丁云龙雄辩称:报馆何以不顾郑为精神病患者的事实,而擅登广告和篡改日期?文斐为何大骂唐、郑为“奸夫淫妇”?在法庭上为何不以唐、郑婚姻的事实问题作为解决该案的关键?但经过两小时的辩论,仍无法挽回唐败诉的趋势。审判厅厅长宣布,“诉讼成立”,唐群英、张汉英“须亲行到案,否则当照法律作为缺席裁判”⑪《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
纵观预审全过程,仅就法律审判的层面而言,唐群英在法庭上处处被动,是文斐“恶意为之”、法官“偏私袒护”、谭延闿的“姑息纵容”互相配合的结果。文斐所称的“九千元”赔偿要求确有些过分,因“字架不过推翻两三架,原物尚存,仅费手工而已”①《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四)》,《民立报》1913年3月4日,第10版。。审判厅长亦未能贯彻“公平”的原则:一是认为郑为精神病患与否,文斐难辨别,且其所登者不出法律范围。二是声称“修改稿”确为郑亲笔经手。三是认定文斐骂唐、郑“奸夫淫妇”纯属唐理屈词穷后所编造的谎言。四是对于唐、郑的婚姻关系问题,完全回避不论②《唐群英第二次预审详情》,《申报》1913年3月7日,第6版。。而就“法律事实”而言,唐、郑的婚姻关系确为“凭空捏造”。民国二年二月四号,唐已抵长沙筹办女子参政同盟会湘支部建立事宜,民国元年十二月四号,其办《亚东丛报》,“并未出京”。据此可知,唐、郑在天津白屋旅馆举行婚事,皆纯属子虚乌有之事③《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六)》,《民立报》1913年3月7日,第8版。。审判厅长也不避讳其故意整饬女界之用意,“唐群英、张汉英、周意绶辈,遇事干涉,肆行无忌。不挫其锋,殆有不可收拾之势。此次唐群英本属无理取闹,故欲乘机而推翻之”④《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此外,都督谭延闿面对唐及女界的迭次控诉,要么“一笑置之”⑤《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新闻报》1913年3月4日,第2张第1版。,要么给出的均是“官样文章”的批示⑥《唐群英大闹报馆之余波》《新闻报》1913年3月15日,第2张第1版。,这在某种程度上确是收到了姑息助奸之效。
此前,唐便邀各报馆主笔及政、学界多人调处,但对热心人士提出的“送招牌于《长沙日报》,并致书道歉”一节坚决不受⑦《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四)》,《民立报》1913年3月4日,第10版。。随着案情进展,唐知绝无“转败为胜”的余地。恰逢国民党湘支部“黎君尚雯等为唐女士保护名誉起见,邀集同志从中调处”⑧《唐群英与长沙报交涉之结果》,《申报》1913年4月9日,第6版。,才使双方就此罢休。案件的结局反倒颇具“雷声大,雨点小”的味道:由《长沙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结此案的“本报特别启事”⑨《本报特别启事》,《长沙日报》1913年3月31日、4月1日,第2版。,唐对报馆付出二千元洋银的赔偿。考虑唐女士自尊,报馆招牌由调停人送回⑩《唐群英与长沙报交涉之结果》,《申报》1913年4月9日,第6版。陶菊隐在《记者生活三十年》一书中有对案件结局的回忆:“事件发生后,唐、傅二人同时投诉于都督谭延闿之前,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一个要赔偿报馆损失。谭调停无效,只得动用公款二千元赔偿报馆损失,此案遂以不了了之。”经笔者考证上述表述是错误的,见该书第9页。。谭延闿亦以都督名义为唐的名誉“辟污”:
当时有人通信各埠及南洋群岛各馆,污唐□君及女界多名,实属无聊痞徒臆造捏诬。延闿等知唐君等有□,用特代为剖明,以彰公道而释群疑。⑪《为唐群英等女界辟污致各报馆电(1913年4月2日)》,周秋光等编:《谭延闿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0—391页。
虽然调停人的介入与谭延闿的“公电”给了唐群英一点面子上的安慰,但唐在法庭上的“败诉”及其“女德有缺”的形象在公众中已经定型。伴随此案的余波,还有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冲击着唐的“英雌”形象:3月17日唐及湘省第一女子中学校学生、女子自由党强行闯入长沙城董事会“大肆滋闹”⑫《长沙通信·董事会战胜女学生》,《民立报》1913年3月28日,第8版。。4月10日前后,唐及张汉英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名义与湘省“女国民会”展开关于秋瑾女烈士祠的争夺战⑬《抗争秋烈士祠产》,《神州女报》月刊第3号,1913年5月,第86—87页。。5月27日,张汉英等因泄愤于“女国民会”,率众捣毁“黄泥墩三育女学校”⑭《湘省风潮一束》,《申报》1913年6月6日,第6版。。上述滋闹之举,与唐大闹《长沙日报》一同被反复提及,强化着人们对于“英雌”闹剧的负面记忆⑮《女国民会之捣毁》,《申报》1913年6月11日,第7版。。俟11月袁世凯勒令解散“唐群英组织之女子参政同盟会”⑯《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申报》1913年11月24日,第6版。,唐便从此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而郑师道亦于1913年4月16日被捕入狱,后为浙督朱瑞所杀⑰《郑师道被捕之详情》,《顺天时报》1913年4月24日,第4版;《密探唐群英》,《申报》1913年9月16日,第6版。。
就某种程度而言,唐群英等“英雌”以及其所领导的《女权日报》与《长沙日报》、文斐、谭延闿等人均属于国民党派别,其对“民主共和”的坚守以及反对袁氏政府的基本立场具有相对一致性。文斐等人借助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风波大做文章,内中牵扯不少唐、文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①参见《唐群英大闹报馆之原因》,《大公报》1913年3月7日,第5版;《唐群英之对付文斐》,《大公报》1913年3月10日,第3版;《唐群英大闹报馆三志》,《大公报》1913年3月17日,第5版等。综合以上材料,唐、文关系素来不和主要有:一是唐对《长沙日报》所登插画不满;二是两人关于办报宗旨意见不合;三是两人先前因私人问题结怨已久。。该案亦是国民党人内部种种矛盾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历史场域中,一件本来微乎其微的“婚变案”传闻,经公共领域的介入,竟成了关乎法律信用、女德与女权,甚至为唐群英“英雌”形象定性等复杂问题的讨论。尽管民初的法律尚处于缺失的阶段,但男性一方抓住这场诉讼风波中唐群英的“软肋”,利用“法律”、“道德”等关键词,肃整唐群英个人、攻击女权运动、否定女性参政资格的用意,异常明显。而该事件在舆论传播中的变形以及随着文学作品的介入,使得唐、郑“婚变案”在文学场域中被赋予了更为传奇的色彩。
二、文学叙事:被讲述的“艳史”与“丑史”
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一案,尽管以唐作为负面形象谢幕,但使得唐的名气在省内更加传开②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8页。。唐“抗传不到案”,郑“为唐作无罪辩护”,基于先前唐、郑的交往经历,唐、郑的婚姻为事实与否,郑被逐离等事件,使二人的暧昧关系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其一,在唐揪打宋教仁一事中,郑师道奋勇质问主席“何以新政纲将‘男女平权’一项削去”,是否为唐增加了信心和后盾③《国民党成立大会纪略》,《时报》1912年9月1日,第3、4版。?其二,地位一般的郑积极为唐创办的《女子白话旬报》、《亚东丛报》撰写祝词,是否有向唐献媚之意④分别参见《郑师道祝词》,蒋薛主编:《唐群英诗赞》,衡阳市育新印刷厂印行,1997年,第21页;郑师道:《祝词(十)》,《亚东丛报》第1期,1912年12月。需要指出的是,为唐题写祝词的人,或为社会名流,或为唐家的亲朋好友。?其三,郑自行发结婚广告在先,为唐作无罪辩护在后,是否为其对唐穷追不舍的执着?总之,唐、郑“婚变广告”引起的“蝴蝶效应”并未随着法庭判决而终止。相反,唐、郑关系在舆论传播中逐渐变形,加之各类文学作品的广泛介入,使得“文学想象”距离历史现场渐行渐远。
“唐群英流行病”气候的形成,与民初的媒介环境、文学生态、文化消费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阅读市场逐渐从“精英阅读”向“大众阅读”转型。以《申报》、《新闻报》、《时报》为代表的上海报界纷纷创设副刊⑤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80—483页。,《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也不时选登“逸史”、“谐文”、“画史”、“酒令”、“艳史”等体裁的“游戏文章”。民初报刊出现了一种“谐趣化”的现象⑥参见杜新艳:《论民初报刊谐趣化现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客观上也为社会营造了一个恣意抒发政见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初的风靡流行,同样为唐、郑故事的“再创造”提供了广阔舞台。
新闻媒体对唐大闹《长沙日报》事件的报道有客观性陈述,当然也免不了记录者的臆断猜想。
其一是人们关于唐、郑在北京时期“暧昧关系”的想像:唐在京起先“颇利用郑师道为记室”,日后两人“至为密切”,且常同室“通宵达旦”,并已允郑之求婚,双方数宿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俨然夫妇”。其二是人们对唐群英回湘原因的求索:唐此次回湘主要是“为备办与郑结婚事”,且召来女友张汉英帮忙“说服”唐母与唐兄。但张抵湘稍迟,唐、郑二人已走向“决裂”。其三是人们对唐群英于湘拒见郑师道原因的猜测:唐、郑于汉口分道扬镳后,郑至湘谒唐皆遭拒绝。郑情急之下,于《长沙日报》登广告,反惹来唐的勃然大怒。亦有人称,唐偕郑回湘,将郑先“匿之小西门外金台旅馆”,欲得母、兄同意婚事后,再领其面见家人。可郑自行“以庚帖诣唐宅”,惹得唐兄、唐母以死相抗。唐只得“力辩其诬,且捏称郑为疯子”。对此,金台旅馆主人附和,确有“唐先生者,曾与郑在该馆共宿数宵”①《唐群英捣毁长沙日报之余谈》,《神州日报》1913年3月5日,第3版;《潇湘风流案》,李定夷编:《民国趣史》,车心吉主编:《民国野史》卷4,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13—116页。。其四是人们对郑师道被驱逐离湘内幕的讨论:郑出省“并非由谭都督一纸公文”之故,而是唐派遣张汉英持手枪“亲至金台旅馆郑师道寓所,迫令其立刻出省”②《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七)》,《民立报》1913年3月9日,第8版。。亦有人称,当郑到达岳州之后,唐托张蕙风姊等叮嘱郑暂避风头,“仍许结婚”③《长沙通信·唐群英大闹长沙报(八)》,《民立报》1913年3月15日,第10版。。还有人称,唐请张汉英赠郑“白金二十元,嘱其回京稍待,不必太急”。不料郑登载广告之过激行动,酿成了两人不欢而散的结局。其五是人们对郑师道手中“结婚证据”真伪的关注:郑逢人便信心十足地称“与唐结婚之证据甚多”,故唐所谓的“以枪见郑”,难免有“欲先杀之,以为灭口计”之用意④《唐群英捣毁长沙日报之余谈》,《神州日报》1913年3月5日,第3版;《潇湘风流案》,李定夷编:《民国趣史》,第114—116页。。亦有人称,郑临行时,仍指唐与其为正式夫妻⑤《湘中女权消长谈》,《申报》1913年3月19日,第6版。。
唐大闹《长沙日报》一案,除了在新闻传播中间产生了扭曲变形,在文学场域,同样成为被讲述的“艳史”、“趣史”,乃至令人发指的“丑史”。
“英雌”作为晚清的新生“流行语”,就构词方式而言,是与“英雄”相对而出现的。在清末种族革命话语下,“英雌”形象通常作为“爱国、尚武的女英雄典型而备受礼遇”⑥黄湘金:《“英雌”的陷落——关于沈佩贞的历史与文学形象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作为“英雌”的代言人,唐大闹《长沙日报》表现的英雄气概,的确令社会上一部分男子欣赏。论者将唐群英看成是专为妇女打抱不平的“女豪杰”。有人谈及清室小朝廷“仍循旧例选秀女”的恶习,深望唐“帅娘子军,握无情棒,直捣黄龙,以与鞑靼从事也”⑦钝根:《游戏文章·选秀女感言》,《申报》1913年4月24日,第10版。。唐群英还被塑造成为讨伐社会上“薄情”男子的领军人物。有作者戏拟《为娘子军讨薄情郎》启事,称有“薄情郎”追求某女士之初,以“鸳鸯比翼”盟誓,然未久“反目无情”。今若女界在唐群英的带领下,必可“大夺眉须之气”⑧莽汉:《游戏文章·为娘子军讨薄情郎檄》,《申报》1913年6月19日,第10版。。又有论者以嘲讽郑师道,反衬唐群英“英雌”形象的大放光彩:郑“乃敢妄想天鹅肉,捏登同婚广告”,盖其“神经病”程度实在不可救药矣⑨默:《杂评二·唐群英大闹长沙报》,《申报》1913年2月26日,第6版。。郑“又想请朱都督替他在西湖上盖房子,享清福”,其“一张面皮倒可以卖给制革厂……发一注大财”⑩《自由谈话会》,《申报》1913年4月22日,第10版。关于郑师道回浙后,向朱瑞索取住房事,可参见《郑师道被捕谈》,《申报》1913年4月19、20日,第3版。。
然而,就唐大闹《长沙日报》一节的文学形象而言,唐被完全当成“正面教材”而书写的文字并不多。或许是“湘女多情”传说经久不衰的魅力使然⑪“湘女多情”之传说古已有之,该传说的来龙去脉可参见肖甫:《湘女多情》,《通讯(湖南)》第7卷第1期,1947年,第69—70页;善之:《湘女(随笔)》,《石门月刊》第16期,1947年,第22—25页。,唐作为“多情”湘女的代表,与郑演绎的缠绵悱恻之“艳史”,更为读者津津乐道。
1913年3月12日,《民立报》“笔词墨舞”之专栏刊登了署名“雄郑”的文章,似为投稿者假郑师道名义向唐群英求爱的文字:“天下多情,惟使君尔……有某痴子者,家傍西湖,名标东阁。”“时下英雌鹿鹿,狮吼神州”,本人为先生才华所折服,不甘庸为“筹边使之头衔”,深愿与汝结成连理,比翼齐飞⑫雄郑:《笔词墨舞·警大舞台》,《民立报》1913年3月12日,第12版。。该文对唐、郑关系的“书写”,尚有清末民初“自由恋爱”的新旧之间“依违离合”的痕迹。此外,以“露骨”的方式讲述的亦不在少数。海吴虞公在《唐英雌之趣谈》中称,郑师道与唐群英女士仅有数面之缘,但唐对郑“偶假以辞色”,使郑“情丝空袅”以至“妄有缱绻之思”,遂做起了赴《长沙日报》刊载结婚广告的“白日梦”①《唐英雌之趣谈》,海吴虞公:《民国趣闻》,车吉心主编:《民国野史》卷4,第486页。。亦有文人刻画了郑被逐出湘省之后,唐、郑“难舍难分”的情境:当郑踏上离湘的小船时,唐忽然匆匆赶来,奈何“光阴不再……此行此时万分焦灼,如坐黑暗”②《艳史·郑师道之新婚别》,《新闻报》1913年3月11日,第4张第1版。。当郑抵岳州时,有人戏拟“郑师道致湘中旧识者书”,称“此次离湘,乃群英令其暂时避地,并无毁约之意”。又有人续拟“郑师道致谭延闿书”,表达了其对“长沙情深,湘水不意,满庭佳话,几酿悲观”的无奈③《湘江逝水楚云飞·民国艳史之一》,《时事新报》1913年3月21日,第4张第3版。。至郑为朱瑞枪毙,有人戏拟“唐女士祭郑师道文”,其中“望空洒泪,致祭于未婚夫郑君之灵”,回想“人人以君为有神经病,唯我独赏君之磊落”,浙督“竟请君为鬼,而使我为嫠”等缠绵之语,流露出唐对郑的悲切和爱恋之情④剑秋:《游戏文章·戏为唐女士祭郑师道文》,《申报》1913年9月2日,第13版。。
除了对唐群英“多情”形象的刻画,游戏文章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作者也随心所欲地展开对唐“功利”、“虚伪”、“无情”等面孔的塑造。
把唐打扮得最为“功利”的当属“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作者把唐说成仅是“母大虫”一只,“连字都认不了几个”,但“偏会办报,偏会做论说”。唐为了利用郑助己办报,不惜在肉体上与其“有了些结合”。而“书呆子”郑师道误以为拥有了“纯粹的爱情”,便向唐提出结婚的要求。唐虽顾虑结了婚“便得受人拘束,行动不得自由”,但觉得郑尚有利用的价值,故暂给郑“一纸没有证人的婚约”,计划着“到不用他的时候,再托故回绝了他就是”⑤平江不肖生:《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留东外史》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05—506页。。
唐群英的“虚伪”面孔也为文人所“洞察”。有人戏拟《长沙之新竹枝词》两首,其一曰:“结婚何事大荒唐,海誓山盟枉一场。省识销魂滋味苦,从今怕过便宜坊。”其二曰:“天津倭馆认双栖,珍重还将密约题。留得鸳鸯红印在,任他化水与沾泥。”⑥《民国艳史中之绝妙文章·二竹枝词》,《时事新报》1913年3月22日,第4张第3版。前者说的是唐、郑二人已凭盟友订盟于北京便宜坊,后者则述唐、郑二人同居天津白屋旅馆,并携有结婚印约。另有人仿照《诗经》笔法,题写“新诗经”三首,讲述了唐、郑婚约引得唐母、唐兄以死相逼,以及唐叮嘱郑勿登报,免食可畏人言等事⑦寄:《趣言·固一世之英雌也》,《新闻报》1913年3月9日,第4张第1版。。上述作品皆“肯定”了唐、郑结婚确有其事,暗指唐群英对于婚约“不虞反悔”,为批评唐背信弃义张本。
唐群英等“英雌”外表冷淡、内心蠢蠢欲动的形象也为笔墨者捕捉。王钝根在《观春柳社新剧十姊妹》中刻画了春柳社剧中所演十个“自命为新中国女豪杰”、不畏“唐群英之皮鞭”的女子。她们平日以“无夫主义”相互牵制,但当闻悉“世家子弟”褚士俊登报求婚,便演绎了一场为争嫁褚士俊,大乱彩票场,捣毁报社的闹剧。后经教育会长调停,十姊妹遂与褚士俊等十人同日结婚⑧钝根:《剧谈·观春柳社新剧十姊妹》,《申报》1914年10月7日,第13版。。该剧情显然以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为摹本。
文人墨客在描绘唐群英的“薄情寡义”时,更倾向将郑师道打扮成“无辜”、“可怜”的样貌。有文人称,当郑被唐“坐逼即行”之际,还“涕泪满衣”地致予对唐深深的眷恋:“我最亲爱之妻唐女士,汝不过因醉后暴动。我二人两方面爱情决不因此而稍减也。”⑨《潇湘风流案》,李定夷编:《民国趣史》,车吉心主编:《民国野史》卷4,第122页。有“游戏作者”仿写《西厢记》,在谈及郑时感叹:“你有心争似无心好,吾多情早被无情恼。”⑩东埜:《自由谈话会·好一齣新西厢》,《申报》1913年5月17日,第13版。当郑师道入狱,有人戏拟《郑师道狱中上唐群英书》,以郑的口吻表达了对唐“深情似海,眷属疑仙”,也为唐在婚姻广告纠纷中明哲保身的做法难以释怀。郑泯然心痛自己深陷牢狱时,唐竟与“男女同志,欢然一室”,故制造“幸得狱吏女解意”的“三角恋爱”,以期与唐破镜重圆⑪东埜虚拟:《游戏文章·郑师道狱中上唐群英书》,《申报》1913年5月4日,第13版。。亦有作者撰写《戏拟某女士致浙江都督书》一文,与上篇文字遥相呼应:郑虽误解了唐的“假以辞色”以致“顿起妄想”,但法庭上唯有“师道于众论摇撼之时,乃甘冒不韪”,力排众议,故恳请朱都督网开一面,否则娘子军将“于西子湖边与贵督一决雌雄”①率:《游戏文章·戏拟某女士致浙江都督书》,《申报》1913年5月4日,第13版。。巧妙的是,该作者以郑师道的无辜和唐群英在娘子军中的“缺场”,强化了唐“不念旧情”、“冷酷无比”的狰狞面孔。
除了“多情”与“无情”的“艳史”讲述外,文人还杜撰了作为“泼妇”的唐群英演绎的“丑史”。但“游戏文章”或“自由谈”中整体仍持中立温和的态度,“直接指涉时事,特别是批评、讽刺、笑骂某些人”的尚属少数②参见杜新艳:《“自由”与“游戏”:民初〈申报·自由谈〉的自我表达及其旨趣》,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有作者戏拟《代湘督谭延闿复郑师道书》,诉说谭对唐群英“撒泼”的无可奈何,使唐“横行乡野”的形象变得谐趣化:唐“横扫弱男子之队,孰敢不弃甲曳兵?”宋遯初“辄受掌责而不辞,某何人斯敢蹈覆辙?”③懦夫:《游戏文章·代湘督谭延闿复郑师道书》,《申报》1913年3月25日,第13版。另有批评者谈笑风生:“余欲新增报律一条曰:泼妇有打毁报馆之权。某英雌其赞成否”④《自由谈话会》,《申报》1913年3月26日,第13版。?有附和者亦调侃谓,若创办一《女量报》,专登“悍妇命令”、“撒泼新闻”、“歪缠新闻”,以“注重平权、自由离婚”等为宗旨,而将“阐扬女界打报馆、健词讼诸美德”,悉皆列入,以辅助唐当时主持的《女权报》,并选购钢制印刷机,“以免男界冲打时不致受毁”,不知唐女士意下如何⑤罢了:《游戏文章·拟办女量报章程》,《申报》1913年4月4日,第13版。?此外,有人戏拟《巴拿马赛会进行社征求物品通告》讽刺道,不妨将“唐女士捣毁长沙日报之摄影”、“沈女士饷亚东新闻社记者之竹杠”、“溥仪所戴之红缨大帽”等“民初劣迹”一同送往“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⑥瘦蝶:《游戏文章·巴拿马赛会进行社征求物品通告》,《申报》1913年6月27日,第13版。。亦有作者仿“关公战长沙”故事,戏拟“唐群英、郑疯子、文斐合演战长沙”之传奇,称唐打报馆,堪比关公当年之勇⑦热庐:《滑稽戏评》,《申报》1913年3月23日,第13版。。
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则将唐“蛮横无理”的形象推向了高潮。郑每谈及婚事,唐均支吾应付。但当郑送刊结婚广告时,唐呵斥郑“专制”,且“带了一群女打手”,摘取报馆招牌,打入排字房,将铅字一盘盘扳下洒了一地后,又把字盘踏得粉碎。作者以夸张手法描述了唐大闹后的丑态:“母大虫虽然凶勇,无奈上了年纪的人,到底精力不继,接连捣了两处,实在有些气喘气促,不能动弹。”作者还以反语讽刺:“你看他们女国民的威风大不大,手段高不高?”⑧平江不肖生:《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留东外史》上,第506—507页。
在历史场域,唐群英本已是“女德有缺”的代表人物。在文学视野下,唐不仅以“功利”、“虚伪”、“无情”的姿态与郑上演了一段风流韵史,而且其在大闹《长沙日报》中的“野蛮”、“泼辣”,也违背了女性“贤淑良德”的优美品格。“面目可憎”的唐群英打破了男权社会的“禁区”,使得“牝鸡司晨”的恐慌很快在男性社会中蔓延开来。署名“丹翁”的作者称,沈佩贞大闹《亚东新闻》“未逾期年”,今唐故伎重演,是有“猛牝”群起之危险趋势⑨丹翁:《讽辞·唐群英捣毁长沙报馆》,《新闻报》1913年3月1日,第4张第1版。。不如由唐“联络京师沈佩贞,结成攻守同盟,与中原男子大战几十万合”,以此一决雌雄⑩丹翁:《异言·郑师道不负唐群英》,《新闻报》1913年3月6日,第4张第1版。。亦有作者称唐面呈“克夫相”:“夫教仁以两颊之故,晦气上身,至遭极惨之祸。师道以诟谇之故,红鸾未照,便成白虎,至有牢狱之灾。”⑪立:《戏言·痴心女子负心汉》,《新闻报》1913年5月11日,第4张第1版。
综上所言,在文学场域,“游戏文章”的作者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受到历史事件在媒介传播中变形的灵感驱动,加之出于迎合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考虑,利用手中的笔墨尽情挥洒对唐群英的“文学书写”。他们或是将唐塑造成具有十足正面意义的“英雌”代表,或是将唐、郑二人的关系“想象”成为一代风花雪月的“风流艳史”;或把唐打扮成一个“多情”的湘女,或把其丑化成为一个“薄情”、“功利”、“虚伪”的角色。实际上,“艳史”不仅作为一种叙述模式,亦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特殊“期待”。这既体现了民初“男女边界”较晚清时期的某种突破,也表露出人们对于“性爱情感”、“自由恋爱”的朦胧渴望;唐等英雌以“武力”向男性“说话”的“泼妇”行为,引发了男权社会对“牝鸡司晨”回溯的惶恐。无论是唐对于“性”与“情”的释放,抑或是对于男性“霸权话语”的挑战,在时人看来均乃“离经叛道”的行为。由此也不难理解,唐群英在文学叙事中的“境遇”,同其在法庭中的“败诉”相似,一并遭遇了“陷落”。
若要在“历史现场”与“文学叙事”之间做一比较,其不同之处在于:在历史事件当中,唐、郑二人“婚姻事实”的真伪不在公共话题的讨论范围内——此或许与法庭审判官对原告一方的“偏袒”有关。但在文学创作中间,唐、郑二人的“暧昧关系”则得到了反复书写;其相同之处在于:两个场域均不回避对于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的“道德批判”,换句话说,作为“英雌”的唐群英,历经了双重领域“陷落”的命运。而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并非一则简单的故事,投射到她身上的是一个时代镜像的缩影:以上“历史事件”与“文学形象”双重场域的互动过程,折射出了民国初年“英雌”话语的内在困境,以及女性生存面临的诸多社会生态。
三、时代镜像:“英雌”话语与民初女性的社会生态
(一)被“英雌”误解了的逻辑
在晚清“种族革命”及“民族主义”话语的感召下,传统社会中涌现出部分女性——尽管是极其少数的,随同男性一道加入革命队伍中间出生入死。她们以“英雌”自居,力图作为四万万同胞另一半的代表,追求并展现其性别角色的建构。辛亥年间,诸如唐群英与张汉英来沪组织“女子后援会”①《女子后援会筹募军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0页。,参加“女子北伐队”,驰赴金陵作战等壮举不为罕见②陈婉衍:《女子北伐队宣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457页。。进入民元,女子参政团体的成立、女报的创办、女学的开设蔚为奇观。“英雌”亦受到相当高的“礼遇”,如唐本人即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并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还获得“二等嘉禾章”③《唐群英年表》,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编:《唐群英史料集萃》,衡阳市妇女联合会刊行,2006年,第16页。。
就唐群英等女性看来,作为“英雌”的自己,在革命中“尽义务”之余,“享权利”乃当然之理——共和胜利的曙光升起之际,便是“女界革命”、“男女平权”梦想成真的时刻。于是,女界关于争取参政权运动的上书一次次地递到参议院议员们的手中。唐在《女界代表张(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中呼喊:“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④唐群英:《女界代表张(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妇女时报》第6期,1912年5月,第21—22页。然而,这一切却遭遇了来自“另一半”的阻力:其关于“男女平权”的要求或被参议院一一驳回,或在《临时约法》中被漠视,即使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也被“无情”地删除。
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反对女子拥有参政权的终极目标,他们同样希望能将两性在革命中间建立的合作基础保持并延续。而采取何种方式更好地协助女性从传统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成为了当时男性精英不得不着力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唐群英等“英雌”毕竟在二万万女性中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则是未能在历史书写中留下声音的妇女大众。据包天笑回忆,在他主持《妇女时报》期间,当时的妇女“知识水准不高,大多数不能握笔作文,因此这《妇女时报》里,真正由妇女写作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二三”⑤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62页。。另一方面,即便是“英雌”们的知识素养与经营能力也值得怀疑。据仇鳌回忆,民元年间,在唐群英等结队多番请愿女子参政权的过程中,“每次呈文都是由我代笔”⑥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0页。。陶菊隐亦称唐参与创办的《女权日报》“营业不振”⑦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8页。,遂不得不由何步兰“呈请都督拨给公款,并常年津贴,以资接济”⑧《维持女权报》,《申报》1913年3月19日,第6版。。
故而,在男性同盟者的眼中,采用一种温和的、渐进的、符合现实的方式,引导女性逐步参与到“女权”行动中来,或许更为妥当。孙中山称:“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①孙中山:《复南京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8页。宋教仁虽然代表国民党全体,向女界表达了否决女子参政权的决议,但仍为唐创办的《亚东丛报》题写发刊“祝词”②宋教仁:《〈亚东丛报〉发刊祝词》,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0页。。刘揆一在办报问题上同样对唐给予支持③刘揆一:《〈亚东丛报〉发刊祝词》,饶怀民编:《刘揆一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何海鸣在《求幸福斋随笔》中亦称,若“有数辈脑灵心敏、志高胆壮之女子投身社会,使知世故而增阅历……苟一觉悟,即以身作则,启迪后来之女子以正轨,其收效必至大矣”④何海鸣:《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求幸福斋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然而,上述的“苦心孤诣”并未得到“英雌”的理解。相反,在唐群英等人的内心中,瞬间涌起一股“失落感”:先前男子应允的“女界革命”、承诺的“女权”,竟然不过是“海市蜃楼”,“英雌”的标签亦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身份”而已。当参议院讨论《临时约法》之际,唐群英等人“擅入议事厅”,“坚执议员衣袂”,将议院的“玻璃窗击破”,并把阻拦的警兵踢倒在地⑤《女子参政同盟会力争参政权》,《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582—583页。。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面对举手赞成“男女平权”的男子寥寥无几,唐群英便“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⑥《专电·国民党昨日在湖广馆开成立大会》,《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第2版。。逐渐地,唐从希望的幻灭,走向失望的低谷、绝望的深渊,以致到达愤怒的沸点。一方面,《长沙日报》刊登的一则子虚乌有的“婚变广告”点燃了唐群英蓄势待发的情绪。另一方面,唐大闹报馆一事与其此前的行径有所不同,内中涉及不少唐个人“霸蛮”性格、其与郑师道之间男女私情,以及国民党人内部矛盾等复杂因素。但若将此事同其之前的“故事”放在同一脉络中考察,便不难想像,她想凭“英雌”的身份,用暴力的行动,争取各界的关注及女界的拥护,以重新觅回自认为理所应当的“女权”。
(二)被“妖魔化”了的“英雌”形象
社会由两性组成,男女之间并非作为对立的两极存在着,而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当两者处于和谐并生的共同体之下时,社会才能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而一旦某一方的性别意识过于强烈,或至极端膨胀时,必将导致平衡的破裂⑦参见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8—269页。。就此意义而言,唐群英等追求“英雌”话语的传递、凸显性别身份的愿望过于鲜明,以至于有意或无意间将自己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唐群英揪打宋教仁那“清脆可听”的耳光声音,反复地回荡在男性的耳边。其砸毕报馆后“高坐吃烟”的傲慢姿态,也永远地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其在参、众议院用烟卷盒扔议员的做法还被其他女性效仿⑧傅文郁:《在北京参加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英雌”们同时透露出欲与男子“一刀两断”的决心。某作者在《女子白话旬报》的一篇文章中,赤裸裸地谩骂男子:“就是怕女子有参政权……夺了男子的饭碗……我们女界……不可说有了男子赞助我们,巴不得将自家的担儿减轻些,这种依赖的劣根性,千万要铲除净尽才好。”署名“开云”的作者语气更不容商榷,“参议员剥夺女子的选举权,便是看待女子和罪犯一般了……我女界当视为公敌,一个个用手枪炸弹对付他”⑨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34—37页。。此外,“英雌”们不仅伤害了赖以合作的男性伙伴,也殃及了女性同盟者。《长沙日报》风波初平,唐群英、张汉英复大闹“秋瑾女烈士祠”。这次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女界自身——“女国民会”⑩林受祜:《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旧事》,《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十五),第9页。。事件虽因祠产纠纷而起,但不免让人叹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笔者将秋瑾与唐群英加以比较:秋、唐婚后皆生活在湖南湘乡,且很早就有过交往,二人皆组织过女子团体和出版报刊、皆经历过革命的洗礼①参见陈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3页;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9—20页。。然而两人身后的社会评价却大相径庭。民国元年,作为“女革命家”的秋瑾迎来了一场自湖南至浙江的“迁葬运动”,其作为“共和大业的缔造者”、“女界革命的先驱”、“双重党派身份的拥有者”,被纪念者赋予了极为崇高的历史地位②参见拙作:《秋风秋雨返秋魂——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民元秋瑾迁葬》,《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85—98页。。而作为“女界参政运动领袖”的唐群英进入民元之后,则何以广受诟病且不为见容?
唐群英等“英雌”采取的激进化、暴力化、极端化的斗争方式,使其最终陷入到“自我孤立”的绝境。就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本身而言,“自以为是”带给她的灾难,完全超乎了最初的估想。除了经济上的赔款、法庭上的败诉、文学形象的“陷落”,最为重要的是,男性对其“女德有缺”的批判,以及对其拥有“女子参政权”能力的进一步怀疑,甚至是对其作为“英雌”资格彻头彻尾地否定。最终,唐在那个她曾经闪耀过的舞台上永远地“销声匿迹”了。二次革命后,唐被安置到回家乡从事“女学”事业的坐标上——这既是女子“自觉”的起点,也是“英雌”回归的终点③关于“二次革命”后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办理女学的概况,参见谭长春、杨端云:《融心化血破世顽——唐群英在衡山创办女子学校的情况》,《一代女魂——衡阳文史》(第12辑),政协衡阳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等编印,1992年,第88—91页。。
在时人的笔下,唐群英等“英雌”的行为张力,某种程度上被冠之以“妖魔化”的形象,因有“三千年未有之活剧”之讥④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1912年8月25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唐群英“丧失女德”、“泼辣蛮横”的“泼妇”面孔已不必赘言。沈佩贞“英雌”标签的背面,同样隐藏着一副“女流氓”的模样。国民党元老仇鳌回忆称,沈被问及与唐绍仪的绯闻时,竟笑答“我不过想利用他一下罢了”⑤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0页。。沈因1915年在北京醒春居与伙伴“以嗅女子脚为酒令”被《神州日报》披露后,聚众大闹报社的野蛮行径,亦深刻在时人记忆中⑥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94页。。其时,尚有沈每以“裸体者仰卧”待袁世凯召见之传闻的流布⑦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页。。陶寒翠在所著的《民国艳史演义》中,以沈佩贞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孙贝珍”在来访的议员面前大张八字式大腿,脱褂在净桶上方便,并大谈关于治脚气的方法等种种怪态⑧陶寒翠:《民国艳史演义》,上海:时还书局,1928年,第96—108页。。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干事傅文郁的形象亦在“英雌”与“娼妓”之间摇摆。1913年,傅文郁到河南建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豫支部时,不仅在开封“明妓暗娼荟萃之处”时常出没,还在金台旅馆与男友赵显华及其他妓女一同上演了一出“泼醋迁居”的放荡丑剧⑨《傅文郁之风流艳史》,《长沙日报》1913年3月24日,第8版。。直至十余年后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交流中还批评唐、沈之流组织的女子团体无任何事业建设,不过是“‘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对于她们这群人“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⑩《鲁迅全集·两地书》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7页。。
造成“英雌”形象“被贬抑”的原因,固然与女性在塑造其“英雌”身份中自我形象定位的“迷失”与“模糊”不无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英雌”——虽然是二万万女性中的“另类”,但她们的“无所适从”所导致的“变异化”的行为模式,无意间构成了对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这一性别规范的冲击。换句话说,“英雌”们的过度“表演”,使得男性对其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角色颇为堪忧。遂有男性转而以“对立”的眼光去打量这批“英雌”的惊骇之举,并将“少数者”不由自主地加以“放大”,以至于在他们的价值概念中生成了一种“被摇撼了秩序”的警觉⑪191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女子参政运动均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可参见《列国女子选举权考》,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年9月,“内外时报”,第21—22页。。
(三)“英雌”话语构建中的“困境”
唐群英等在追求“英雌”话语中呈现出的激进主义的态势,不仅惹得男性一方“放大化”了的反感,即便在其他的女性同胞看来,亦未必认同。女界同仁王达三认为,唐群英之所以遭受《长沙日报》“婚变广告”的污蔑,与其“锋芒太露”而招引太多的忌恨者不无关联①《来函·王达三女士函》,《申报》1913年4月4日,第11版。。若干年后,唐本人回忆时,也觉自己当初的行为有些“过火”②唐寿春:《回忆陶姑》,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编:《唐群英史料集萃》,第155页。。其时绝大多数女性的观念是:既要做“国民母”,又想成为“女国民”;既须在家庭中相夫教子,又应在战场上随同男子赴汤蹈火。将自己视为男性从属者的角色,既是社会分工的内在要求,也是女性自觉的性别认同。
总体而言,在“英雌”话语的诠释问题上,她们的困惑恰巧在于,“性别表演”强烈的动机与审视自身条件后的清醒。换言之,关于“女权”与“女学”孰者优先,“英雌”们也并非真正不解。唐群英在《女学界之障碍》中指出,唯有养成“完全的学识,高尚的人格”,才有资格与男子“立于平等的地位”③《女学界之障碍》,《女子白话旬报》第3期,1912年11月,第30—31页。。这也是《女子白话旬报》、《亚东丛报》、《女权日报》三份女报诞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唐群英从大闹《长沙日报》的风波中冷静下来后,便从长沙回到北京,继续着女报的改良事业④《本京新闻·女报改良》,《顺天时报》1913年5月2日,第5版。。吴木兰也自觉地放下了鼓吹“女子参政”的号角,以研究“男女教育平等”的进行方法为宗旨⑤《男女教育联合会开会预备会》,《顺天时报》1913年5月8日,第9版。。
诚然,我们无法排除部分男性持有“功利主义”的两性观:他们或将“女界革命”、“女权运动”作为一种鼓吹女子参与革命的动员话语,或将之以为某种政治功用。此种印记在袁世凯的身上得到了体现。1912年4月,面对唐群英等“英雌”来京请愿“女子参政权”,袁致电唐绍仪:请从速阻止南京女子的北上行为,“以免种种窒碍”⑥《致国务总理唐绍仪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9页。。然而,在“洪宪大典”筹备的语境下,“女子请愿团”便成了袁对帝制合法性的论证依据之一⑦黄毅编述:《袁氏盗国记(选录)》,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在袁政府充作“幕僚”、且自诩为“大总统门生”的沈佩贞⑧《洪宪女臣》,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4页。,则成为了袁“功利主义”的牺牲品。“二次革命”后,女子参政同盟会被解散,社会人士希望保留一位“英雌”去完成“救亡”结束后女学的“启蒙”任务。沈一度活跃在“提倡内国公债大会”、“救国储金运动”中,且其作为“女界代表”,极具煽动力的演说尚有可圈可点之处。闻者赞叹“演说家必有悲惨激昂之声,借题发挥者,乃独沈佩贞有此精神”⑨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1915年5月9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然而,沈未能吸取唐群英等“英雌”的教训,继续“我行我素”。其因大闹《神州日报》一案,遭受了入狱的下场。先前在她身上贴有的“英雌”、“总统府女顾问”等标签,突然遭受了来自袁以及各界的矢口否认⑩《本案之结束》,饭郎编:《沈佩贞》,新华书社,1915年7月,第6—7页。。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道出了其中的实质:“袁氏欲操纵伟人,一切豢养皆属诱致作用,沈氏虽女流,性颇伉直,探以党中暗幕,辄肯相告”,而一旦“党人之势堕败,了无足患”,沈便失去了“利用价值”。等到沈“骄纵嚣张”地大闹《神州日报》,引起了社会“公愤”之际,袁便仿效两年前公共舆论界对唐群英的打击方式——以“女德有缺”为名,进而否定其女子参政权——结束了他对沈佩贞的招抚与褒嘉⑪《女伟人》,许指严:《新华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149页。。在众目睽睽之下,沈“仍照通常送人犯惯例,乘大厂车……道经商市,异常羞愧”⑫《沈佩贞之下场》,《香艳杂志》第10期,1915年10月,“女界新闻”,第5页。。
(四)“贤母良妻”的游移与复归
无论是男性渐进、温和女权理念的失败,抑或是持有“功利主义”性别观者的别有用心,或“英雌”在追求性别话语过程中行为模式的“变异”……诸多因素交织,使“英雌”群体在清末民初犹如“昙花一现”。与其将“英雌”的陷落看成是近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从“女权论”向“贤母良妻论”)①参见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9—132页。,不如说此为“贤母良妻”形象的“游移与复归”。“英雌”从她们战斗过的“社会”,返回到了最初生活过的“家庭”与“校园”。“英雌”不再受到宠爱,而“贤母良妻”成为了民初人士心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
民国初年,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整饬女界不良风气、培育“女子道德”的言论。有论者建议创立“尊孔女塾”以“昌正学而明经术”②《女子也受头巾毒》,《民立报》1913年3月2日,第11版。。1915年3月,某作者在《大公报》上发表言说:近世以来,“女子道德之知识,日渐澌之,忠孝节义之义理,无复闻问”,而“维新派轻佻之妇女,遂有女子平权、女子自由之声浪……纵恣肆狂,四维不张,国几灭亡”。“贤母良妻”角色的规范,“由个人而及于众人,由家庭而及于国度,社会恶俗,荡扫净尽,则国家富强可企望”③朱济美:《论国家欲转弱为强当注意积极进行普及女子教育》,《大公报》1915年3月26日、27日,第1、2版。。教育总长汤化龙亦称:“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④《教育总长汤化龙谈女子教育(节录)》,《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712—713页。1914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治安警察条例》,禁止女子“加入政治结社”及“政谈集会”。同月袁世凯又制定了《褒扬条例》,给予“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匾额及金质或银质褒章⑤《公布治安警察条例令》、《公布褒扬条例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5卷,第396、472页。。“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李定夷因在《湘娥泪》中塑造了具有传统美德的女主人公,亦领取了教育部颁发的“甲种褒状”⑥《教育部通俗教育会小说股原评》,李定夷:《湘娥泪》,上海:国华书局,1914年,第1页。。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妇女报刊也出现了从宣传“英雌”向褒扬“节烈”,直至塑造“贤母良妻”的回归潮流。1914年12月创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杂志,鼓吹“男子可以多妻,可以放纵”,要求妇女遵行“礼义廉耻”,并设有“家政学”专栏,以“介绍妇幼卫生保健知识和家庭生活常识”。1915年1月创刊的《妇女杂志》,其宗旨亦为使“一般之女界勉为良妻贤母”,将提倡女学作为“昌明女权的必备条件”,且有“家政”和“学艺”两个栏目的设置⑦《女子世界》、《妇女杂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2—309、351—359页。。同一时期的《中华妇女界》、《女子杂志》等妇女期刊,也体现了上述表征⑧《中华妇女界》、《女子杂志》,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3卷·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21—1531、1554—1556页。。然而,此时宣传的“贤母良妻”教育与传统社会的要求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其中既体现了“传统道德”的抬头,又显示出“新文化、新思想”的萌芽;既有“英雌”向“贤母良妻”的回流,又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革命”的余波荡漾;既有告别“旧式女性”的难分难舍,又有迎接“新女性”曙光照耀的从容等待;既展现出“英雌”们从家庭、校园走向社会的困惑歧途,也彰显出女子人格从“依附”走向“独立”的某种预示。或许,从唐群英等“英雌”角色重置的这一课题出发,恰可瞥见民初中国妇女特定的生存语境,即“挥手晚清,拥抱五四”。
(五)“发乎情,止乎礼”的男女边界
最后需要讨论的一点是,在文学场域,唐群英“艳史”的“被发现”,也为我们观察民初中国男女限界“发乎情,止乎礼”的特征,打开了一扇窗口。
辛亥革命后,社会关注的热点除政治问题外,在西方“自由结婚”、“文明结婚”思想影响下,表现男女情爱的文学作品也引起了读者的特别兴趣⑨参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3页。。“英雌”们的个人情感均是文人墨客们乐此不疲的话题。然而,由于传统伦理道德在时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故人们在欣喜地尝到“艳史”的新鲜后,不自觉地再度与“艳史”划清界限。如,有评论者“特致书于傅文郁,谓如再任意妄为,定下逐客之令,免使中州一片干净土,留此污点”①《艳史·傅文郁在汴之艳史》,《新闻报》1913年3月13日、14日,第4张第1版。。
当“英雌”们真正面对外界对其“艳史”的指责时,也不得不与之绝缘。如唐群英为了与郑坚决地撇清关系,大声向世界告白,郑师道只是“精神病”一个,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向都督府请愿——非将郑师道驱离湖南不可。她拒绝出庭,不仅是不敢正视法庭对其“英雌”身份的审判,更是不敢接受庭审观众对她“风流韵事”的拷问。她砸毁报馆的暴力行动,既是其作为“英雌”自以为是的体现,同时也是为证明自己在感情问题上的“清白”,以及“英雌”性伦理不容玷污的一种行为模式。就某种意义而论,唐群英以“礼”的方式,即大闹《长沙日报》,以为自我辩诬,驱逐郑出湘,与之分道扬镳——拒绝了郑师道的“情”,即“婚变广告”的表白;在“文学场域”中,“多情”湘女唐群英与郑师道演绎的“艳史”,或以唐“泪洒”郑而收场,或以郑欲与唐“重叙旧缘”的痴情无望而终止。其间透露出的“悲剧”情怀,亦是“情”与“礼”抗争的归宿。而唐的“寡妇”身份作为一种潜在的语境设定,亦暗示了作为“张力”的“情”,在民初语境下,最终不得逾越作为“限界”的“礼”这一框架。那么,“根乎道德,依乎规则,乐而不淫,发乎情而止乎礼”便成为了当时男女感情的普遍选择②双热:《孽冤镜·自序》,《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孽冤镜》,第222页。。徐枕亚在《玉梨魂》中便讲述了一种不为礼教所容的恋爱③参见徐枕亚:《玉梨魂》,《民权素》第一、二集,上海:民权出版部,1913年,第148—150页。。
综上所述,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一案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或“文学叙事”。透过唐及其女友前后的历史活动及命运,我们不仅得以瞥见“英雌”话语构建中的内在困境,也可以认知民初女性面临的诸多社会生态:在种族革命话语的感召下,女性被动员参与到其中,并开始了其“英雌”角色的表现历程。当共和告成之际,男性从谨慎的视角出发,更希望以一种渐进而平稳的步骤,引导广大女性实现女权享有者这一目标。然而男性的逻辑为“英雌”们误会,相反她们以激进暴力的手段对待同盟者,以致在社会人士眼中被放大为“妖魔化”的形象。“英雌”在构建性别话语中间的困境,一方面表现在其在声势上要盖过男子的夸张“表演”,另一方面则是当她们衡量“女学”的水平后,对于作为“辅助者”性别身份的自觉安置。此外,她们还面临着持有“功利主义”话语者对于民族国家性别秩序重构的挑战。于是,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男女双方在革命中间形成的合作基础亦随之破裂。与之直接相关的是,“英雌”们在历史事件和文学形象中,皆遭遇了不可避免的“陷落”。当“英雌”消逝以后,取而代之的便是社会对于“贤母良妻”形象的重塑。但此时的“贤母良妻”却与往昔不同,在她们的身上,可以望见“新旧杂糅时代”的曙光。此外,“英雌”及大众对于“艳史”即若即离的态度,展现了民初“发乎情,止乎礼”的时代镜像④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夏晓虹教授开设的“晚清女性与社会”课程给予笔者诸多启发,深表感谢!。
四、余论:拟态环境下人物形象的重构
从李普曼的传播学理论出发,“拟态环境”不是对“真实环境”的完全再现,而是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加工、重构⑤参见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一百年来,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及其人物形象,在“拟态环境”中不断变迁。民国初年,唐撒泼的“历史记忆”为时人刻骨铭心。俭父在小说中以唐、沈大闹报馆的故事警告主人公实甫,不可轻率曝光名人女子酒后颜色等丑闻,以免重蹈《长沙日报》的覆辙⑥俭父:《笔谈·金风铁雨楼随笔》,李定夷主编:《小说新报》第五年第十期,1919年10月,第4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杨尘因的小说《神州新泪痕》中,“新派人物”冯世新等将唐群英塑造成“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妇女解放”的代言人;而“保守人士”周桐荪、辛觉盦则以“女流氓”的目光打量着唐,并据此反对“新女性”话语的诞生①尘因:《神州新泪痕·第三十五回》,徐枕亚主编:《小说季报》第四集,1920年5月,第1—2页。。唐群英作为“超贤母良妻主义”人物的代表还为胡适所征引。他虽以对从事三十年社会事业的美国女子“Jane Addmas”的称赞,批评唐行为模式的失策,但实际上也认同了唐的“自立”精神②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第218页。。直到1920—1930年代,唐群英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才被各类作品广泛书写。但是人们对于唐群英的评价仍持谨慎的态度,即虽然唐群英有较大的历史功绩,但或是其斗争中间的改良色彩过于明显③纯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资料》,《中国青年》第7卷第5号,1927年2月,第113页。,或是其斗争目标过于狭隘——“仅为个人利益而斗争”④《北伐军抵湘前后的湖南妇女(湖南通信)》,《中国青年》第6卷第23号,1927年1月,第614页。,或是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不过沈佩贞、唐群英几个女士而已”⑤李三无:《妇女参政运动研究》,《改造》第4卷第10期,1922年9月,第24页。,或是其斗争方式过分激进——以至于被社会加上了“‘叫嚣’、‘猖獗’的徽号”⑥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前锋》第二号,1923年12月,第55—56页。,最终导致其斗争结果不彻底。但是,唐群英对于鞭策妇女运动,仍具相当的激励作用⑦文央:《悼唐群英女士》,《妇女生活(上海)》第4卷第11期,1937年6月,第30页。。新中国成立后,唐群英作为妇女运动“领袖人物”的身份得以奠定。唐的历史地位被无限制地“拔高”:1979年,邓颖超将唐群英与秋瑾并列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界”的两大英雄人物;1991年,康克清亦赞其为“一代女魂”⑧《邓颖超论及唐群英》,李天化、唐存正主编:《唐群英年谱》,第1—2页。。以湖南衡阳为中心,关于纪念唐群英的“文集”、“专著”、“诗赞”纷纷出版⑨《各地编印唐群英专集、专著一览(1985—2006)》,衡阳市妇女联合会编:《唐群英史料集萃》,第217—223页。。在共和国的语境下,关于唐大闹《长沙日报》这一问题的阐释,无论在回忆者的叙述中,还是在文学作品的书写里,甚至是在学术论文的创作上,均被叙述成“唐群英领导广大妇女,反击《长沙日报》对女权运动的诋毁”——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⑩参见吴剑、段韫晖:《湖南妇女运动中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65—466页;中共衡山县委员宣传部编:《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5—209页;蒋薛、唐存正:《唐群英评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146—150页;曾启球:《唐群英思想之形成和发展》,《衡阳文史》(第12辑),第169—170页;冯湘保:《简析唐群英男女平等思想的实践》,罗湘英主编:《唐群英研究文集》,第156页;饶怀民、阳信生:《唐群英女权思想析论》,饶怀民、范秋明主编:《湖南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7页等。。
唐群英本人及其大闹《长沙日报》的风波,经历了“五四”前后的民初中国、1920—1930年代国共两党关系运动下的“革命年代”、新中国建立直至今日——这一跨越了整整百年的时代穿梭。无论是其人物形象,还是事件传播,均在时代语境下不断变迁。这些后来者的叙述,早已与最初的“历史现场”以及昔日的“文学叙事”,渐行渐远,甚至“面目全非”。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张慕华】
K258
A
1000_9639(2015)01_0104_16
2014—08—20
高翔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