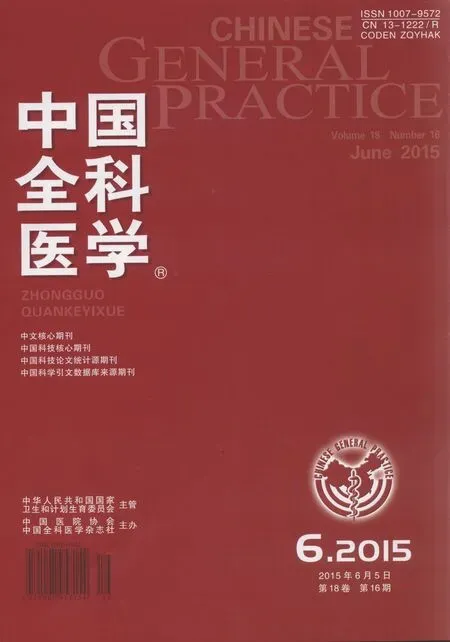网络疑病症:概念界定、影响因素与干预方法
丁佳丽,杨智辉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将近中国人口数量的一半,互联网普及率为45.8%[1],如今互联网使用已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关联。网上可获得的健康、医疗相关信息的增加,以及中国频频出现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问题,雾霾等空气质量问题等使得中国人对健康的担忧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使用网络搜索健康相关信息。2010年一项来自12个国家 (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含12 262人的研究发现,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中60%的人会利用网络搜索健康、医疗、疾病相关信息,56%的人会利用网络健康信息做自我诊断[2]。在2010年,约80%的美国互联网使用者在网上搜索过健康信息,且62%的被试是在调查的最近1个月内搜索过[3]。基于中国网民数量之大及对健康的担忧,且网络搜索信息量大、快捷方便、隐匿性高的优点,在线搜索健康相关信息的人会越来越多。当有健康焦虑的人为了使自己放心在网上搜索健康相关信息后,会产生两种结果:焦虑程度增加或者降低。焦虑程度增加了的人如果仍然选择继续搜索,这种情况则被称之为网络疑病症 (cyberchondria)。研究发现约40%的人在线搜索健康信息后焦虑程度会增加[4],因为人们倾向于关注严重的、罕见的疾病信息,或者把普通的症状扩大化或进行消极的非合理的解释。它使人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上,且使人遭受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困扰。那么深入研究网络疑病症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以减少人群患上网络疑病症的可能性,并对已患上网络疑病症的人群进行有效干预。网络疑病症已经在国外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重视和心理学界的关注,但一切都还在探索和起步阶段,且在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本文介绍了网络疑病症的概念界定、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和干预方法,最后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1 网络疑病症概念的界定
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这个词源于“cyber” (网络)和“hypochondriasis”(疑病症),可以追溯到 1999年 Ann Carrns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互联网上疾病猖獗,疑病症患者的担忧”[5],提到网络健康信息会增加信息搜索者对疾病和健康的担忧和焦虑。网络疑病症作为一种新的病症开始被重视是在2001年,发表在英国《独立报》上的文章“新的障碍,网络疑病症,席卷互联网”使网络疑病症几乎成了一种正式的诊断[6]。
网络疑病症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不同的研究者对其下了定义,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由在线健康搜索产生的过度健康焦虑”[7]; “基于对网上搜索结果和内容的查看,对普通症状的担忧毫无根据的扩大化”[8]; “利用网络搜索健康和医疗信息增加了对健康相关的害怕”[9]。对于网络疑病症的定义,研究者们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种行为是和在线搜索健康相关信息有关的,且这种行为是过度的 (重复,花费时间);第二,这种行为有负面的影响,使人不愉快和更焦虑。基于此,网络疑病症可以被定义为:出于对健康的困扰或焦虑,在网上过度或重复搜索和健康相关的信息,结果扩大了这种困扰或焦虑的症状。
网络疑病症在词语来源和概念上与疑病症、健康焦虑相联系,网络疑病症存在健康焦虑和疑病症的某些特征。网络疑病症目前在国内外都还未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另外,如何与健康焦虑、疑病症相鉴别,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关于疑病症(hypochondriasis),是指患者相信或担心自己患有一种或多种躯体疾病,因而反复就医,尽管检查结果呈阴性及医生解释其并没有患该病也不能打消其顾虑,常伴有焦虑或抑郁。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 (修订本)(DSM-IV-TR)对疑病症已做出了明确的诊断标准[10]。健康焦虑 (health anxiety)一词是由认知-行为理论的研究者们提出的,目前还没有分类和诊断标准,是指个体由于对自身躯体感觉或症状的错误解释而存在对健康大范围的担忧[11]。疑病症和健康焦虑并不是同义词,在国外,最近几年疑病症有被健康焦虑一词替代的倾向[12-13],通常疑病症被认为是健康焦虑的严重形式[14]。但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V)中,疑病症一词已被疾病焦虑障碍 (illness anxiety disorder)和躯体症状障碍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两种障碍替代[15]。在疾病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中,有一条是“个体表现出过度的健康相关行为,如在网上搜索信息以寻求健康保证”。从网络疑病症的表现症状上来看,主要是由于对健康的过度焦虑而上网重复搜索相关健康信息,从而进一步导致更为难以控制的焦虑。因此,网络疑病症与DSM-V中的疾病焦虑障碍在概念和症状表现上更为接近。另外,网络疑病症和网络成瘾[16]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均是过度反复使用网络,停止或减少使用网络会出现某些精神和躯体反应。关于网络疑病症的诊断标准还有待相关专家的制定。
2 网络疑病症的产生
患有高水平的健康焦虑或疑病症的人在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健康保证时,会有短暂的心理缓解,这种缓解会强化寻求保证的行为,从而保持了健康焦虑或疑病症。但是,健康焦虑个体为了寻求健康保证或使自己安心而在网上搜索健康相关信息时,搜到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对健康的保证,因为搜索结果是不可预料的,有时可以使人安心,有时不能。有研究发现,在线搜索健康信息的人群中约50%的人健康焦虑水平降低了,约40%的人焦虑水平增加了[4],这种不同的结果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
网络搜索使健康焦虑增加或者降低之后又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健康焦虑降低后继续在网上搜索健康相关信息;第二种,健康焦虑增加后不再选择继续搜索;第三种,健康焦虑增加后仍然选择继续搜索。这三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是不同的,见下。
第一种情况,由于患健康焦虑或疑病症的个体在网上寻求到了令人欣慰的信息,因此他们的担忧和焦虑水平降低了,但是他们在下一次寻求安心时会回到网上搜索,希望再次体验这种欣慰[17]。按照我们对网络疑病症的定义,这种情况不属于网络疑病症的范畴,而是受前一次在线搜索降低了的担忧和焦虑的驱使。
第二种情况,健康焦虑个体在网上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信息,因而变得对自己的健康更加焦虑、担忧和害怕。尽管他们可能会再次回到网上搜索健康相关信息,以期望使自己安心或降低焦虑,但是他们获得的信息仍倾向于增加他们的焦虑和担忧[18]。有了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很多这样的个体就回避在线搜索有关他们症状或疾病的信息,甚至回避去看医生,回避和他人讨论健康状况,以致后来,尽量回避任何能增加他们对健康担忧的事情。这也不属于本文网络疑病症的范畴。
第三种情况,患健康焦虑的个体在线搜索健康相关信息后,增加了对健康的焦虑和担忧,但是仍然选择继续搜索。这属于网络疑病症。为什么个体最初在网上并没有获得令人欣慰和安心的信息,甚至获得了更多的焦虑和害怕之后,仍然会选择继续在线搜索,并且不顾多次搜索后的失望,这似乎很难让人理解。是什么因素强化了他们的搜索行为吗?或者在搜索的过程中,有什么可以使他们感到安慰的东西存在?那么,研究那些保持网络疑病症的影响因素,以及进一步深入探索它的发生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3 网络疑病症的影响因素
3.1 健康焦虑 对自己身体症状的错误解释而导致自己对患严重疾病的担忧,这就是健康焦虑。有健康焦虑的人为寻求健康的保证会不断重复查看医疗信息使自己安心。许多刊登医疗信息的书、杂志、期刊以及临床观察均表明,健康焦虑患者正在逐渐增加利用网络作为健康信息的来源[19]。研究显示,高水平的健康焦虑会使人更频繁地在网上搜索健康信息,持续更长的时间,并且引发更多的焦虑和担忧[18]。Baumgartner等[20]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搜索的增加相关,有健康焦虑的个体从搜索中体验到更多消极的结果,不过研究也发现只有从信任的网站访问,有健康焦虑的个体比无健康焦虑的个体才会有更高的担忧。由此,可以得出健康焦虑会增加网络疑病症发生的可能性。
过度在线搜索健康信息也可能导致健康焦虑的发作[8]。现有的研究指出大多数获得健康信息的方法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个体关心的症状,但是搜索非特定的症状会提供不相称的大量严重和稀有的医疗解释信息,而70%刚开始搜索普通、无害症状的个体会逐渐发展成搜索稀有的和更严重状况的信息[18]。这些结果表明,使用搜索引擎作为诊断工具很可能会使个体暴露在严重的、慢性的和危及生命的疾病信息中,这很有可能加剧健康焦虑。同时由于网上包含大量不受监管的健康信息,健康网站上提供的信息存在准确性和完整性上的问题,因此利用网络作为健康信息的来源也使得个体暴露在冲突、混乱的信息或者不可信的、不准确的、过时的信息中,而个体则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加以辨别。这也会导致个体担忧和焦虑的增加。
3.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 IU是个体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进行感知、解释和反应的认知偏差,它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研究发现,高水平IU唤醒度的人可能对于未来发生的消极以及压力事件持有消极的态度并且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感到十分焦虑[21]。在网上搜索健康信息,超大的信息量可能会导致个体更高水平的不确定性,而对于不确定性忍受力低的个体会增加他的焦虑水平,因而强化网络疑病症。有研究表明,IU在搜索健康信息频率和健康焦虑之间起着调节作用[22]。虽然通常认为信息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但有可能正好相反,网上模糊的医学术语、复杂的图表、不同的医学解释等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驱使高水平IU个体继续在线搜索,为了找到真相,因为害怕不确定性和未知,不能忍受不确定和模糊性[23]。不确定性对网络疑病症的保持作用和在健康焦虑、疑病症人群中高水平IU的发现相一致[5]。基于此,高水平的IU个体由于在线搜索健康信息可能会经历健康焦虑的增加,同时增加了网络疑病症发生的可能性。
3.3 完美主义特质 观察和研究发现,许多患有疑病症的人存在完美主义特质和强迫性人格障碍的其他特征[24]。面对网上大量的信息,有完美主义特质的个体希望搜索到一些信息可以解释一切或者提供完美的解释,因此会不顾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焦虑而持续寻找这种信息。由此,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疑病症产生或强化了。
3.4 知觉到信息的可信度 由于网上很多与健康相关的信息都存在不准确、误导、不完整和过分简单化的问题,有健康焦虑的个体可能会花大量时间在辨别信息的来源及信息本身是否可信任上,希望通过尝试找到一个可信任的网站,在上面找到可信任的且自身需要的信息。在非临床样本中,关于知觉到的信息的可信度与健康焦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只有从可信赖的网站获得信息,有健康焦虑的人比无健康焦虑者在搜索后才有更高的担忧,而非信任信息则没有发现这个结果[20],但也有研究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关系[18]。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因为知觉到的网上信息可信度不同,且信任对于健康焦虑人群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确信的是,知觉到的信息可信度是网络疑病症的一个影响因素,但是如何影响还有待发现。
3.5 认知偏向 在对焦虑相关障碍 (尤其是广泛性焦虑障碍和社交焦虑)的研究发现,焦虑障碍患者或者焦虑易感人群普遍存在消极的认知偏向,包括消极注意偏向、解释偏向、记忆偏向、心理意象偏向、评价偏向等[25-26]。对于网络疑病症患者,在搜索健康相关信息时,相对于普通症状,更倾向于注意严重的、稀有的疾病;对于模糊、不确定的症状或诊断信息,倾向于解释为消极的、严重的[8];在搜索完之后,个体倾向于记住和回忆出那些严重的、消极的健康信息。总之,研究发现,在线搜索健康信息有潜在的可能使个体在解释普通症状时,将症状扩大化,而不是寻求合理的、理智的解释,这加大了个体对症状的担忧和焦虑。
3.6 在线搜索技术 研究发现互联网用户通常会点击排名靠前的搜索结果,也更容易相信排名靠前的信息,从而保持了该网站的排名[27]。但是至少75%的用户在某个时间混淆了健康相关搜索结果的排名和患特定的疾病的可能性[8],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搜索结果排名越靠前,患该种疾病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搜索健康信息的个体倾向于关注严重、罕见的疾病信息,因此增加了这些信息的点击率,从而这些网站排名靠前,而普通症状信息排名靠后。这意味着严重的、消极的健康信息由于排名靠前再次增加了其点击率,用户查看后增加了其焦虑水平,导致其为了寻求使自己安心的症状解释再回到在线搜索,这就陷入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即保持了网络疑病症。
4 网络疑病症的干预方法
目前,国内外还罕见专门针对网络疑病症的干预研究。但是针对健康焦虑和疑病症的治疗方法研究非常多,而网络疑病症和健康焦虑/疑病症在影响因素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如 IU、完美主义倾向、消极认知偏向等。而网络疑病症作为健康焦虑/疑病症的一种特殊表现,对它的干预,可以在健康焦虑/疑病症的干预整体框架之下,但是又需要具备针对性,不可忽视网络疑病症的独特性。
对网络疑病症的干预,最终目标是使个体能够在大体上掌握和处理在线健康相关信息,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恐慌,以致重复搜索。总的来说,针对网络疑病症的干预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是网络技术层面的干预;第二是用户阅读教育层面的干预;第三是个体心理层面的干预。通过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保持网络疑病症的因素主要有IU、完美主义特质、知觉到信息的可信度、认知偏向、在线搜索技术等。因此,可以从以上几个因素入手,制定出针对以上几个因素的干预方案,从而间接地达到干预网络疑病症的目的。
首先在网络技术层面上,主要是健康相关信息的搜索排名、信息的质量、准确性等问题[8]。如果搜索引擎能够改变网络搜索结果的排名,那么由信息导致的焦虑和担忧发生的可能性也许会降低。搜索引擎的排名规则一般是采用特殊的算法,通常根据搜索的关键词的匹配性、搜索的频次、链接数量、内容质量、人工干预等进行计算,得出排名等级,反馈给用户,但是当前时常存在搜索引擎作弊行为[28]。因此如果能将医疗信息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加入算法,所得结果可能更加合理。另外,对网站进行监管,建议网站提供更加精确、不模糊、友好的医疗信息,或者开发科学的健康咨询系统。
其次,在用户教育层面,需要提高在线搜索健康信息的用户对于健康信息的阅读能力[29],教育用户如何客观地评估健康信息,解释在线搜索结果,以及如何将检索到的信息运用于他们自身的健康问题和个人状况。
最后,在心理层面上,主要是用认知行为疗法对其进行干预。首先,需要将个体暴露在网络健康相关信息中,治疗师对其进行关于在线搜索技术和它对以后搜索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心理教育,改变个体对信息不合理的认知和信念。治疗师会关注强化网络疑病症的影响因子,然后将个体的注意力转向这些因子,每次只矫正一个因子,如消极解释偏向,然后便用认知行为疗法中专门针对解释偏向的干预方法对其进行矫正[30-31]。有研究证明,在线认知行为治疗对严重健康焦虑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针对健康焦虑的保持机制,通过降低个体知觉到的疾病风险、减少对身体症状的关注、增加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显著降低了个体的健康焦虑[3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也有良好的效果,在团体心理干预的几个阶段,设置不同的干预内容,如介绍治疗原理、焦虑情境暴露、提高不确定性忍受力、放松、冥想训练等,干预效果是理想的[33]。另外,在治疗焦虑时,所采用的认知偏向矫正方法对矫正临床焦虑障碍个体和焦虑易感个体的消极注意、解释偏向具有良好的效果[25,34]。认知行为疗法是否对网络疑病症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对网络疑病症的干预,需要多个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如信息技术专家、公众健康专家、健康心理学专家和健康管理专家等。在选择用何种干预手段之前,我们需要考虑个体差异,即个体的网络疑病症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人格因素、情境性的,还是心理层面的,然后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法。
5 国内网络疑病症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还罕见针对网络疑病症的专门研究,近似空白状态。虽然一些文献中已出现过网络疑病症这个术语,用来形容基于网络搜索健康信息而产生的医疗恐惧和焦虑[35],但是国内对网络疑病症的定义还不规范且不一致,因此存在用词不恰当的地方,如把由于在网上看到某种疾病信息,觉得和自己的症状很像,因此怀疑自己得了该病的现象,称为网络疑病症[36]。而国内现有的和网络疑病症关系密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网络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健康焦虑/疑病症的,而其中有的文献会简单提到网络疑病症。有研究认为,网络健康信息搜索行为与健康焦虑和躯体症状相关,有健康焦虑的个体在线搜索健康信息,会增加他们的焦虑;而无健康焦虑的个体搜索健康信息,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35]。余春艳等[37]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在线搜索健康信息的内容和频率与健康危险行为、性别、上网时间长短、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还有研究发现,个体与健康有关的互联网使用行为能够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这两个中介变量对其健康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而对健康信息的信任程度具有调节作用[38]。此外,国内对健康焦虑/疑病症的研究已比较多,对其评估、影响因素、临床表现、治疗方法等已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39],给网络疑病症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6 网络疑病症研究现有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国外有关网络疑病症的研究虽然已有了一些进展,但是文献数量不多,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如:(1)网络疑病症的诊断,目前还尚未有诊断标准。 (2)网络疑病症的测量,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测量工具,因而无法检测网络疑病症的严重程度。以往研究大多是用自编的调查问卷或者一两个简单的问题来让被试回答,没有做过信效度的检测。(3)网络疑病症的影响因子。虽然目前已发现健康焦虑、IU、知觉到的信息准确度等因素会影响它,但还尚未有研究发现或证明的因素,如认知偏向、人口学因素等,且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哪些是直接影响因子,哪些是中介因素,哪些是调节因素,有无交互作用等都有待研究的证明。(4)网络疑病症的发生机制。在线搜索健康信息的人群中,有些会演变成网络疑病症,有些不会,这是否与在线搜索的动机、个人健康状况和人格特质、平时上网习惯相关?在线搜索的过程中,什么保持了个体的继续搜索,什么强化了网络疑病症?(5)网络疑病症的干预方法。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是否对它有用,其他疗法的干预效果如何等。这些不足亟须研究者们的探索。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以上未解决的问题入手,设计相应的研究。如该领域的专家制定网络疑病症的诊断标准;编制网络疑病症量表,对其进行心理测量属性的检验;设计研究对影响网络疑病症的相关因子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和分析;运用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认知疗法或其他疗法对存在网络疑病症表现的重点人群进行干预,探索各个疗法对其的疗效等。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2014-3-16].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fOiko_KY6wYYNtiSJk4cwR7Uoot-A9lMgsypri7I1 hID10RB2bqXjIWtmZPfkwANdocGGdN2_rDEfhZ16_sIj2tr8oOek0vfj17MAlm-Zim.
[2] McDaid D,Park AL.Online health:untangling the web[DB/OL].[2014-03-16].http://www.bupa.com/media/44806/online_20health_20-_20untangling_20the_20web.pdf.
[3] Aikens M,Kirwan G,Berry M,et al.The age of cyberchondria[J].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in Ireland Student Medical Journal,2012,5:71-74.
[4] White RW,Horvitz E.Experiences with web search on medical concerns and self diagnosis[J]. AMIA AnnuSympProc,2009,2009:696-700.
[5] Starcevic V, Berle D.Cyberchondria: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xcessive health-related Internet use[J].Expert Rev Neurother, 2013, 13(2):205-213.
[6] Valley P.New disorder, cyberchondria,sweeps the Internet[DB/OL].[2014-03-16].http://www.nzherald.co.nz/technology/news/article.cfm?c_ id =5&objectid=18542.
[7] Harding KJ,Skritskaya N,Doherty E,et al.Advancesin understanding illness anxiety[J].Curr Psychiatry Rep,2008,10(4):311-317.
[8] White RW, HorvitzE.Cyberchondria:studies of the escalation of medical concerns in web search[J].ACM Trans Inf Syst,2009,27(4):23.
[9] Recupero PR.The 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J].J Am Acad Psychiatry Law,2010,38(1):15-26.
[10]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M].4th ed.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2000.
[11] Fergus TA,Bardeen JR.Anxiety sensitivity and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evidence of incremental specificity in relation to health anxiety[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3,55(6):640-644.
[12] Braddock AE,Abramowitz JS.Listening to hypochondriasis and hearing health anxiety[J]. Expert Rev Neurother,2006,6(9):1307-1312.
[13] OlatunjiBO, DeaconBJ, Abramowitz JS.Is hypochondriasis an anxiety disorder?[J].Br J Psychiatry,2009,194(6):481-482.
[14] Hart J,Björgvinsson T.Health anxiety and hypochondriasis:description and treatment issues highlighted through a case illustration[J]. BullMenningerClin,2010,74(2):122-140.
[1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M ].5th ed. 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2013.
[16] Gao WB, Chen ZY.A study on psychopat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of internet addiction[J].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6,14(4):596-603.(in Chinese)
高文斌,陈祉妍.网络成瘾病理心理机制及综合心理干预研究 [J].心理科学 进 展,2006,14(4):596-603.
[17] Salkovskis PM, Warwick H.Morbid preoccupations,health anxiety and reassurance:a cognitive-behavioural approach to hypochondriasis [J].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1986,24(5):597-602.
[18] Muse K,McManus F,Leung C,et al.Cyberchondriasis:fact or fiction?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xiety and searching for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J].J Anxiety Disord,2012,26(1):189-196.
[19] Taylor S,Asmundson G.Treating health anxiety:a cognitive-behavioral approach[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2004.
[20] Baumgartner SE,Hartmann T.The role of health anxiety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J].CyberpsycholBehav Soc Netw,2011,14(10):613-618.
[21] Buhr K,Dugas MJ.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J].Behav Res Ther,2002,40(8):931-945.
[22] Fergus TA.Cyberchondria and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examining when individuals experience health anxiety in response to Internet searches for medical information[J]. CyberpsycholBehav Soc Netw,2013,16(10):735-739.
[23] Carleton RN.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construct in the context of anxiety disorders: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J].Expert Rev Neurother,2012,12(8):937-947.
[24] Sakai R,Nestoriuc Y,Nolido NV,et al.The prevalence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hypochondriasis[J].J Clin Psychiatry,2010,71(1):41-47.
[25] MacLeod C,Mathews A.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approaches to anxiety [J].Annu Rev Clin Psychol,2012,8:189-217.
[26] Li T,Feng F.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research paradigms,characteristics and modification [J].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3,21(12):2196-2203.(in Chinese)
李涛,冯菲.社交焦虑解释偏差:研究范式、特征及矫正 [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12):2196-2203.
[27] Joachims T,Granka L,Pan B,et al.Accurately interpreting clickthrough data as implicit feedback.In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annualinternational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C].ACM,2005:154-161.
[28] Wang XY.Research on ranking algorithm and spam detection techniques of search engine[D].Ji' nan:Shandong University,2010.(in Chinese)
王向阳.搜索引擎排名算法及作弊检测技术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29] Szewczyk - Bieda MJ, Oliver TB."Primum non nocere" ——first,do no harm [J].BrJ Radiol,2012,85(1014):838-840.
[30] Visser S,Bouman TK.The treatment of hypochondriasis:exposure plus response prevention vs cognitive therapy [J].Behav Res Ther,2001,39(4):423-442.
[31] Barsky AJ,Ahern DK.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hypochondriasi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JAMA,2004,291(12):1464-1470.
[32] Hedman E,Andersson E,Andersson G,et al.Mediators in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severe health anxiety[J].PLoS One,2013,8(10):e77752.
[33] Yang ZH,Wang JP.Short-term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in generalized anxiety individuals [J].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1, 19(5):694-698. (in Chinese)
杨智辉,王建平.广泛性焦虑个体的短期团体认知行为干预[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5):694-698.
[34] Beard C.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for anxiety: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J].Expert Rev Neurother,2011,11(2):299-311.
[35] Peng YN.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ing and health anxiety in outpatient[D].Dalian: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2012. (in Chinese)
彭彦妮.网络健康信息与门诊患者健康焦虑关系研究[D].大连:大连医科大学,2012.
[36]王有国.“网络疑病症”害人不浅 [J].健康,2012,11:18-19.
[37] Yu CY, ShiHJ, ZhangPY, et al.Correlations of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via internet and health risk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J].Chinese Journalof School Health,2009,30(6):482-484.(in Chinese)
余春艳,史慧静,张丕业,等.青少年网络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及其与健康危险行为的相关性 [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6):482-484.
[38] Liu Y.Empirical research on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individual health behaviors[D].Wuha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in Chinese)
刘瑛.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 [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39] Zhang YQ,Yuan YG.The research status of health anxiety[J]. Medicine &Philosophy,2013,34(7):71-74.(in Chinese)
张钰群,袁勇贵.健康焦虑的研究现状[J].医学与哲学,2013,34(7):7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