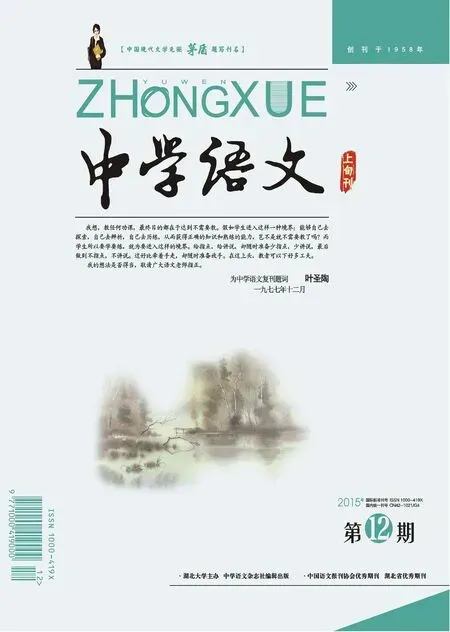审美想象在《诗经》中的建构性作用
熊婉君
审美想象在《诗经》中的建构性作用
熊婉君
审美想象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心理因素,在文学鉴赏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诗词鉴赏中,鉴赏者通过审美冲动,由诗文自发产生审美想象,加之自身的审美经验与审美情趣,构建起内心的审美图景,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获得情感上的陶冶,达到审美欲望,最终完成审美活动。
诗是美的化身。《诗经》作为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它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成为后世诗歌发展的蓝本。《颜氏家训·文章篇》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言:“别裁伪体亲《风》《雅》”,道出历代诗人对《诗经》的追摹和标榜。可见,自古以来《诗经》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是极高的。因而,对《诗经》的审美与鉴赏对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培养审美情趣具有积极的意义。《文心雕龙》中说:“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敝,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歌抒发人的心志,涵养人的性情,就连道德修养极高的孔子也将《诗经》作为陶冶性情、培养道德的最好教材。并且,根据《诗经》诗、乐、舞为一体的艺术特色和它字字玑珠、反复叠沓的创作手法,审美想象的建构性作用在《诗经》审美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言志,歌咏言。”“人秉七情,感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类的七情六欲原本在心,当通过语言文字吐露之时内心的思想得到升华,从感性到理性,由漫想到文字,由此便生成了艺术创作。《诗经》中的诗大多从劳动中产生,是古人最真实的情感表达,不同于其他经书,纪实性强是《诗经》的一大特色。现如今,《诗经》除了是一部艺术造诣极高的诗总集,也是学者们用来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等的有力根据。
《诗经》由采诗人采集而来,并经过挑选,对于艺术水平高的、能反映当时社会风俗与文化的诗歌就编制成乐曲,再赋上舞蹈供人们咏唱、欣赏。极强的音乐感和节奏感是《诗经》不同于其他诗歌的独有特色。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首诗。
其一: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是《诗经·国风·周南》中描写人民劳动生活的一首周南地方民歌。全篇生动地描画了周南妇女结伴采撷芣苢,充满了欢歌笑语的劳动场面。林从龙在鉴赏此诗时称其“是一首明快而优美的劳动之歌”,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的确,“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思想充分体现在此诗中,并且这首民歌也很好的体现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特色。
通观此诗,短短六句行歌以自然朴素、简单明了、反复叠沓的创作手法将妇女采集芣苢的欢乐景象描绘得惟妙惟肖。初读只觉得平常,甚至平淡无奇。六句行歌除了六个动词不同之外,并无其他变化,语言简单,韵律也单一,似乎除了妇女采摘芣苢这一事实外并无更多内涵可供发掘和玩味。然而,如果我们能用审美想象来构建一幅妇女采芣苢的欢乐景象,其中的审美情趣便跃然纸上。
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涵咏此诗,想象自己穿越到了三千年以前,在弥漫着草本香气的芣苢园中,到处飘飞着歌声,妇女们长衣素褂,裙袂翩翩……盛夏灿烂的阳光将女子的头发染成金黄,漫天的葱绿绵延起伏,延伸到山谷深处。此时,她们无暇顾及自己长裙上的蓝花是否沾染上了泥土的芬芳;她们乌黑的秀发是否被风吹坏了模样;她们纤纤手指是否被芣苢尖密的外衣亲吻了血痕;她们笑着唱着,手持衣襟,大把地捋着芣苢放进自己的篮中,满山荡漾着歌声与笑声。平原绣野、风和日丽,狗尾似的芣苢摇暖了阳光,摇碎了风,也摇乱了采撷人的步伐。仿佛自己也身在其中,俯身拾起遗落的芣苢放回她们的篮里,明媚的笑荡漾开来。
通过想象的审美构建,结合引领全诗的六个动词,我们可以做深层的理解与欣赏。全诗用赋的手法平铺直叙地为我们再现了古人劳作的情景,真挚热烈。诗的每一章开头直接咏唱采芣苢,层层叠进,和着音律反复歌唱,唱出了诗中人物内心劳作的喜悦,再现了采芣苢
的欢闹场面。可以说,三章诗中的六个动词准确而形象地直叙了采撷人的动作、劳作的顺序。先是大家伙儿高唱着“采之”来到芣苢园中;接着咏唱“有之”,是发现芣苢已成熟的兴高采烈,然后唱到“掇之”“捋之”,先拾捡起掉在地上的芣苢,再来采撷茎上成簇的芣苢;最后歌咏“袺之”“襭之”,用衣服盛满采摘的芣苢,洋溢着兴奋与欢快。全诗极具律动的音乐美,读来琅琅上口,再加上简单直白的歌词,任谁都可以和着唱个两嗓子。歌声交相呼应,令采芣苢的火热、喜悦之情更富有感染力。
审美想象让我们看到了这首诗平淡背后热情似火的一幕。试想,如果单单是诵读此诗,审美也仅是拘谨于这六个动词的不同意思,而不作任何联想与想象,此诗的意蕴是无法被完全鉴赏和体味到的。
芣苢是一种草本植物,果实可以入药,俗称车前子,可以治妇女不孕之症。闻一多先生在品读《芣苢》时说:“芣苢是一种植物,也是一种品性。”这是对诗中内容意义的更深层的认识,妇女采芣苢、咏芣苢映射出古人喜多子的传统风俗与文化。对此,我们亦可以做合理的揣测与适当的联想。
其二:
褰裳
子恵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恵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爱情诗出自于《诗经·国风·郑风》,相比于《诗经》中的其他情诗,它的诗风与众不同,别具一格。诗中女子的率真、爽朗和颇具反叛的个性带给人一种不同的感受,特别是当它出现在千年前的诗集当中的时候。此诗中的女子个性张扬,敢爱敢恨。全诗仅寥寥数句,便将女子对倾爱之人的思念刻画得入木三分。俗语说:“爱之切,恨之深。”仅涵咏此诗,我们就能感受到女子等不到爱人时内心的焦虑不安与对相恋之人的娇嗔之态。
但仅是如此,我们似乎并不能真切而深刻的体味到这名女子矛盾、无措、炽热而焦急的内心情感。此时,我们需要审美想象来构建出一个图景来填补诗文中的空白。比如这名女子为什么等不到自己心爱的人,难道是这名男子故意爽约,抑或是他被何事所困,因而不能如期而至?又如,这名女子与恋爱之人何时相约,又约在何时相见?她又是如何焦急地等待着爱人?……这种种疑问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通过审美想象,再结合自身的审美体验和生活经验,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并体味到这首诗想要表达出的意蕴和情感。
假如这一切发生在万物复苏、春意萌动的初春,一弯渐渐冰释的春水踏着轻盈的步履淌过山谷、深林,经过女子的膝边。这位少女痴痴地望着这潺潺的河水和河岸对面遥遥的青山、小径,她期望着一个身影前来,那是她日日思念的恋人。可是等啊等,她的恋人并没有出现。河水依旧欢快地向前流淌着,河岸边的花丛依然在风中摇着娇艳的身姿,仰着头对着太阳微笑。随着时间的流逝,少女的心情越来越不能平静,她在岸边来回地踱步,她等着、想着;想着、等着……
《褰裳》同其他民歌一样,运用反复叠章的形式,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表情达意,绘声描状。全诗用赋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少女怀春图。两句“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将女子情波激荡,无法抑制的热烈而纯洁的恋爱之心、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两个“狂”字,前一个形容男子之狂,后一个形容男子失约的行为之狂,更加强化了女子内心的爱之深、思之切以及女子那一股不甘屈软的倔强性格。
格式塔学派认为审美是力的作用模式,当艺术样式、外部事物、组织活动和人的知觉在力的作用模式上达到结构上的统一之时,就可能激起审美经验。在审美活动中,当审美想象与文学内容达到形式与内容上的高度统一时,审美体验便产生了。潘纪平老师的《语文审美教育概论》一书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感情活动与飞驰的想象在诗歌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想象,感情无所依托,便成为空洞的感叹和鸣叫。”因此,在《诗经》的审美中,审美想象是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审美想象本身就是《诗经》审美的主体活动。
宗白华在《美从何处寻?》一文中有《流云》一诗曰:
啊,诗从何处寻?
从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从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从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诗人从微风细雨、落花流水和碧空孤星中找寻美,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审美想象这匹飞驰的骏马。骑上这匹骏马,建构起奇妙的想象之旅,任思绪徜徉飞翔在这千年的诗韵古风之中,感受当时那风、那雨、那花、那碧空与孤星!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