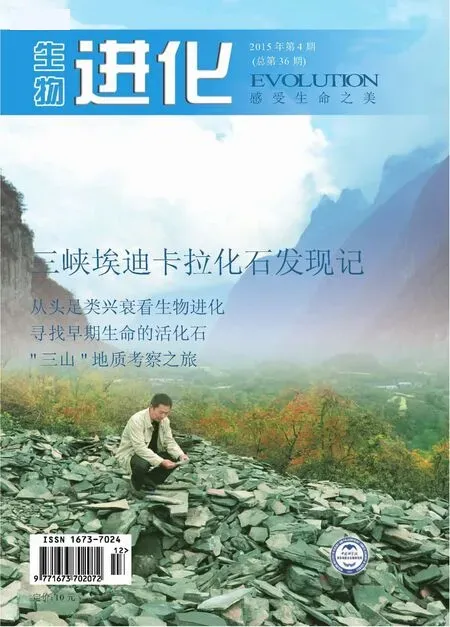寻找早期生命的活化石
肖湘
寻找早期生命的活化石
肖湘
"潜水器请求下潜"(IV-5唐嘉陵,当日不承担下水任务的主潜航员,潜器准备),
"同意下潜"(Ⅲ-2叶聪,潜器总负责人),
"收到"(总指挥于洪军),
"橡皮艇已回收至甲板"(Ⅲ-1陈存本,船长),
"收到"(总指挥于洪军)。
随着总指挥最后的口令,2015年1月11日清晨,中国大洋第35航次第二航段第8次下潜开始,这也是蛟龙号编号94次下潜。本潜次地点龙旂热液区,计划下潜深度2300-2880米,各就各位为时间当地上午时间7点,计划抛载上浮时间为当地下午时间3: 30,计划水中时间10小时。
蛟龙号要探访的目标是西南印度洋超慢速扩张洋脊深海热液区。常言道: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大约在深海2000-4000米以下,还存在着不依赖于阳光的生态系统。海底热液系统广泛分布于全球的洋中脊板块扩张中心,含有各种还原性气体、保持着较高的化学及温度梯度,类似于早期地球原始环境。海水经裂缝渗入洋壳深部,在与岩浆接触后发生水岩反应,溶解地壳内的多种金属,再从洋底喷出的烟雾状的喷发物冷凝、氧化而成的金属硫化物,高温硫化物看起来浓烟滚滚,被形象地称为"黑烟囱"。更为奇妙的是烟囱体的微生物多样性很高,特别是古菌,其多样性超过其他异质环境,这也是其与生命起源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海底热液环境生命起源学说自上世纪80年代末被提出以来,还得到很多其他证据支持:"进化树"的根部大多是嗜超高温微生物,其演化速度较慢;海底热液系统确存在非生物成因的甲酸和乙酸等简单有机物,甚至FeS/NiS能够催化将CO2和CO还原产生氨基酸,并进一步产生肽链;无生物酶参与的由FeS介导的逆三羧酸循环过程的发现,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化学自养模型。作为深部生物圈窗口的现代热液生态系统,既没有经历地球表面大规模地质历史事件如"雪球"低温事件的影响,也没有经历过一个明显逐步降温的过程,避免了早期的持家基因(组)的突变、丢失,因此在该环境中生存的微生物可能保存了与早期生命相似的基因组结构,成为代表早期生命的"活化石"。但如何到达深海获取热液烟囱体既是科学更是技术难题。
笔者第一次了解深海热液区是2001年回到国内开始从事深海微生物研究的初期。当时我们既没有可以培养深海微生物的实验室——深海环境模拟培养系统,也没有能到深海原位精确取样潜器,一切工作都是从零开始,获得一个热液烟囱成为梦想。记得2007年参加联合国会议时,笔者专门抽出会间宝贵的时间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了从Juan De Fuca洋脊获取的大型热液烟囱体,留下了深刻印象。2008年,笔者作为航段首席带领大洋1号科考船在西南印度洋热液区利用电视抓斗获取了一个死烟囱体,其难度就像在一个晃动的5层楼顶用一个绳系的镊子在硬币上抓取一个芝麻,当时的喜悦之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再后来,笔者参加了美国Atlantis-26航次,在东太平洋海隆获取了多个烟囱体。稍感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新Alvin号载人潜水器技术上不能满足下潜要求,临时改为Jason号无人缆控潜器,所以笔者始终无法到水下亲身感受被置放在今天低温、氧化的海水中"高温、厌氧的生命摇篮"。
走进潜舱之前,我又一次打量了今天的坐骑——蛟龙。他长、宽、高分别是8.2米、3.0米与3.4米,空重不超过22吨,最大荷载是240公斤,巡航每小时1海里,最大工作设计深度为7000米。本潜次是主潜航员傅文韬,这是他的第41次下潜,也是第三次热液区下潜,左舷是首次下潜的女潜航学员赵晟娅,右舷科学家位置坐的就是第二次下潜的笔者,也是第一次到热液区。不知道热液区居民是否欢迎我们这些好奇者。

笔者乘蛟龙号回到母船向阳红9号
潜器下潜的速度大约为每分钟40米,我们到水下大约需要70分钟,这是一段相对轻松的过程,在完成必要的设备检查和联络后,我们打开行李包,开始吃备航人员准备的食物,为后面的工作储备能量,毕竟从下潜的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在控制饮食量和饮水。要知道在直径2.1米的球形舱中方便并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在工作开始之前,我又仔细把本潜次的主要任务回忆一遍:1、测深侧扫,获得热液区的微地形地貌;2、选择合适的低温热液喷口区,测定喷口温度、采集流体,进行原位大体积海水过滤;3、在上述喷口采集烟囱体样品,标志物和各种原位设备;4、海底高清摄像和拍照,环境参数测量,确定大型生物种类/数量;5、适量采集岩石,生物样本;6、培训潜航员和生理监测。除新人以外,这个潜次最大的挑战在于新的设备,我们及合作伙伴研制的深海大体积过滤水系统。在深潜界业内有一句话,任何一个新的设备下海都是噩梦,但一代代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是勇敢向前。虽然我们的过滤系统按要求进行了3500米的陆地打压试验,也在南海进行过试用,下潜前团队伙伴在甲板上通宵测试,但在其极限深度2880米使用(有一个安全系数)1小时,还是一件有挑战性的事情。系统能否有效触发?过滤泵能否有效工作?要知道在水下的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更何况对潜器本身的安全影响. .....还有我们能否顺利的找到热液口并分布温度探头?两次测深侧扫能否顺利完成?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也慢慢进入工作状态。
9:18分,2857离底50米,高度计显示为零,只能通过避碰声呐看。这让我一下紧张起来,热液区地形复杂,加上喷发的黑烟,没有高度计几乎寸步难行。过一会傅文韬告诉我们虚惊一场,因为离底高度超过50米高度计自动显示为零。9.25分,2825米发现marine snow(直译为海雪)明显增多,marine snow是有机物未完全降解产物,在灯光下如同雪花一样,但一般的过滤却无法捕获,marine snow增多也是附近存在热液系统的一个标志。9:38,2727米,转向,赵晟娅打开仪器,测第一条线。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也屏住呼吸,因为一旦中途死机或者潜器走得不直,高度差在40-80米范围之外,就会导致前功尽弃。9: 53分终于完成测试到达400米外第二个点。开门大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下潜会十分顺利呢?
10:39分,2760米水深,发现活的热液喷口,热液一般温度较高,甚至可达400℃以上,pH较低,在2-4左右,其中溶有许多过渡金属元素,如Fe(II),Mn(II)等。从黑烟囱喷出的热液还有大量岩浆活动形成的CO2(4-215 mm/kg)、H2S(3-110 mm/kg)、H2(0.1-50 mm/kg)并混有生物及非生物来源的不同浓度的CH4(0.05-4.5 mm/kg)。烟囱内部与外部冰冷的海水(2℃)之间形成巨大的温差。热液中溶解的还原态气体和金属是整个热液生物群落的能量来源。
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低温热液渗漏区,所谓低温渗漏,在本地区往往是在大的烟囱体的根部或者柱体周围少量热液渗漏形成的生物聚集区域,通常在10℃左右。从舷窗看出去,是一片黄色的世界,大量的藤壶就在舷窗外,就在我的手边,因为水流的波动,看起来比鲜花更生动。由于水深对光线的影响,与到水表面的褐色不一样,含金属的烟囱体看起来显淡蓝色,更增添了神秘感。一条1米5长的大鱼,直勾勾的在舷窗前盯着我们,我想它应该是这个世界的长老。整个渗漏生物区面积大约50平方米,分4-5层,每层大约1个桌面大小,甚至还有部分生物层层倒挂在突出的崖壁下面。后来的统计共发现巨型底栖生物6个门: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环节动物、刺胞动物、棘皮动物和脊椎动物。其中软体动物丰度最高,为优势类群之一。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我所见过最大的热液生物聚居区,这个小生态系统是依赖于共生的自养微生物获得有机物质和能量。我们设计的大功率采水泵可以直接紧贴在大型生物的体表过滤微生物与大型生物幼体,并直接将RNA固定下来,反应当时(微)生物的状态。10:59,机械手触发启动开关后,水泵启动,取水管口绑缚着我们的低温探头以及溶解氧探头,忠实记录着取样点的环境参数。1小时后,取水完成,我们利用机械手抓去了藤壶、贻贝、螺等大型生物,随后又用温度探头检测了其他几个发现的流体。随后我们开始寻找高温热液喷口。
寻找高温热液喷口是一场真正的冒险之旅。本地区的烟囱柱可以到达20米以上高度,烟囱口温度达到400℃以上热液可对视窗直接造成威胁,而喷口区往往崖壁陡峭,能够供潜器停靠的平台很少。而所谓的平台也可以看成薄皮的小火炕,蹭破点皮就可能成了新的烟囱。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不少深潜器在热液喷口工作后回到水面被熏黑的部分。实际上身临其境,你会发现各种黄色的悬浮物颗粒和/或黑烟可以让你的视距为零,此时无论是直接碰撞或者被热液灸烤,后果都不堪设想。我们万分小心,潜航员驾驶着蛟龙从水流上方顺流接近喷口,滚滚浓烟就在我们正舷窗靠左边1米处,非常壮观。用我们携带的高温探头,进行了20分钟的温度测量,随后从喷口处掰掉几块烟囱体我们搁置在取样筐中小心盖好带回来,这些从喷口烟囱壁上分离的高温微生物就是我们探寻的活化石,记录了早期生命的历史。
现存的化石记录多来自于寒武纪之后,而此前30亿年,生命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以典型深海热液区超嗜热古菌为模板,结合现代生物信息与遗传操作技术,从其核心代谢途径出发,就可以找出其生存所需的边界条件,进而通过遗传密码推断出早期地球适合于这些古老生命生存的大致环境。破解早期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奥秘。
工作很紧张,时间过得飞快,到15:13,2710米,第六个点,第二次测深侧扫开始,通过在热液区东西两边两次南北向测深侧扫结果的叠加,我们才能获得较为精确的喷口区地形地貌。这项工作进行的也很顺利,但我们希望更往南面多走一点点,直到水面传来抛载的指令,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海底,时间是15:30。
上浮的过程中传来了母船的关心,按例现场指挥部虽然一直焦急等待但为不打扰我们现场决策一般不主动询问。我们依例进行了各项检查,向水面报告潜器、人员状况正常,又简短地总结了主要的科学发现和成果,等待着我们的是水面兄弟姐妹的笑脸,我也期待着这些宝贵的样本能早点回到实验室,帮助我们揭示早期生命与地球环境的奥秘。
西南印度洋热液区,我们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