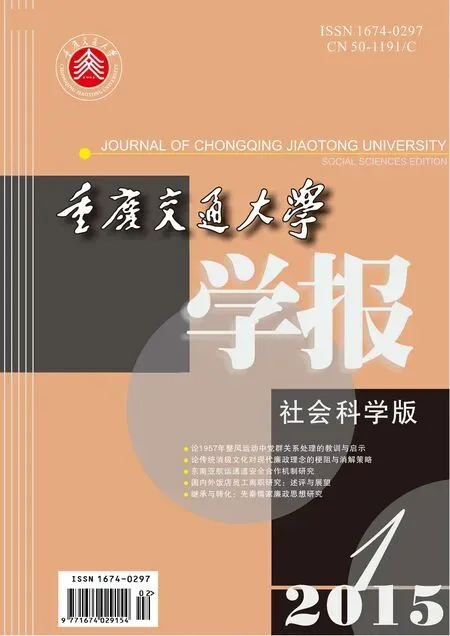《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动物意象解析
——基于图形—背景的理论视角
唐汉谷, 李金妹
(湖北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动物意象解析
——基于图形—背景的理论视角
唐汉谷, 李金妹
(湖北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流行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心理学的图形—背景理论不仅可用于对语言的解读,也可用于对文学作品进行认知解读。基于图形—背景理论视角,对《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的动物意象进行解析,阐释小说叙事的匠心所在。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 图形—背景; 动物意象; 认知解读
《哈利·波特》(HarryPotter)是英国女作家罗琳创作的魔幻文学系列小说,小说通过英雄的炼成,弘扬了人性中的爱与真善美。系列小说自出版以来获奖无数,被翻译成74种语言,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创下销售奇迹。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带给我们一种强烈阅读体验的同时,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该系列小说的研究。自2002年第一本研究论文集《哈利·波特与象牙塔:透视一种文学现象》出版[1],从各个角度切入研究哈利系列小说的著作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哈利·波特的研究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如翟弘媛从译介视角对小说进行了研究[2],高原媛从文化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3],任少云从叙事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4]。本文以小说中灵动的动物意象为切入点,以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为基础,对系列小说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的动物意象进行解析,以探讨动物意象在建构文本结构、推动情节发展、表达小说主旨方面的功能。
一、图形—背景理论
客观的现实世界与人类的认知世界之间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Talmy首先将这一认知心理学原则引入语言学研究中,论述了“图形—背景(F-G)”在语言中的若干体现情况[5]。这一研究思路与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完全吻合:人们通过对外界环境或具体事件直接体验和感知认识,建立了图形—背景认知方式,并可以此来认识世界,建构语言,理解语义。体验认知上的突显将决定语言表达上的突显。Langacker基于F-G建立了两种不同的突显关系:(1)侧显—基体(Profile-Base)。一个词语的“基体”就是它在相关的认知域中所涉及的范围,是意义形成和理解的基础。与其相对的是“侧显”,是指基体内被最大突显的一部分,成为基体内的焦点。(2)射体—界标(Trajector-Landmark)。在每一个关系性述义中,各个被突显的参与者是不对称的,其中一个叫做“射体”,它是最突显的参与者,表示了关系述义中被聚焦的一个实体;另一个为“界标”,表示了关系述义中其他被次要突显的实体,为射体的定位提供参照点[6-7]。
语言表达上的突显必将体现在语篇内容中,认知文体学利用图形—背景理论对语法现象和语篇内容进行了分析。在认知文体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知诗学,更进一步在文学语境中运用人们基本的认知能力,从阅读、阐释、审美和评价等多方面对文学文本进行理解,包括文学语言和作者的意图[8]。从认知诗学角度出发,图形—背景理论中的图形有如下特征:比背景部分更为详细、集中、鲜明;位于背景的顶部、前方,或大于背景;相对于静态的背景,图形具有移动性;在时间或空间上先于背景;是背景的一部分,因显露出来成为图形。这些特点体现于视域中,同时也适用于文本分析[9-10]。
二、图形—背景理论对《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动物意象的解析
纵观整部哈利小说系列,其中有着丰富的动物意象。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中的四个学院分别以狮子、蛇、鹰、獾为标志。此外,有着浴火重生的凤凰,勤劳忠贞的信使猫头鹰,还有许多麻瓜们所不知道的神奇生物——马人、夜骐、独角兽、瑞典短鼻龙、鹰头马身有翼兽、人头狮身龙尾兽等。
动物意象在第三部小说《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以下简称为《囚徒》)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囚徒》描写了主人公哈利·波特在魔法学校第三年的经历,在整个系列小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哈利的教父布莱克、黑魔法防御术教师卢平、小矮星彼得等人物的出现,为后面几部小说的情节埋下了伏笔,推动着后面的故事发展;另一方面,以上人物的出现引起了对哈利父母相关往事的回顾,整个系列故事的线索变得明朗,《囚徒》中的几个动物意象——鼠、狗、猫是本书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是仅次于几个主人公的重要形象[11]。
(一)鼠——虚弱、可怜的形象
书中的鼠在前18章都是以罗恩的宠物斑斑的形象出现的,给人一种瘦弱无用、担惊受怕、可怜无辜的印象。到了第19章,哈利、罗恩、赫敏三人与卢平、布莱克、斯内普之间的冲突对峙,才揭开了鼠的真面目,揭露了造成哈利父母之死的真凶,洗刷了布莱克的冤屈。
鼠意象第一次出现在罗恩寄给哈利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中:“他看到韦斯莱家九个人站在金字塔前,都在使劲向他招手。韦斯莱太太身材小而胖,秃顶的韦斯莱先生却很高大,他们的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罗恩正站在这张照片的中间,又高又瘦,他的宠物小耗子站在他肩上,他的手臂搂着他的妹妹金妮。”
根据上文提到的“射体—界标”理论,这一段话突显的是韦斯莱一家人,着重突显罗恩,而对作为宠物的老鼠一带而过。罗恩为射体,处于照片这个背景最突出的位置,鼠为界标,处于照片这个背景中次要突出的位置,为射体的定位提供参照点。这样的布局使读者的关注点集中在罗恩身上,忽视了老鼠。正是在此出现的老鼠包含着极其重要的信息,它是导致布莱克在阿兹卡班苦守12年而此时冒险越狱的真正原因。后文中的内容让读者误以为布莱克是为了哈利而越狱,直到最后揭开真相,读者才醒悟过来,才会记起在此处出现的被作者埋下伏笔又刻意隐藏的线索。
之后对鼠意象的描述强调了鼠虚弱、残缺(少了一根脚趾,秃毛)、愁眉苦脸(第4章)、皮包骨、濒死(第11章)。作者运用修辞性的语言描述,描写了鼠的上述特点,使这些特点作为图像突显于作为背景的常规语言之上,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读者产生和哈利一样的心理,认为是猫杀死了鼠,直到真相揭开,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心里为之一振。
(二)狗——不详、死亡的形象
狗意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3章。哈利深夜独自走在新月街,感到恐惧不安,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监视他。“哈利清楚地看到:一个很大的、有着发微光大眼睛的什么东西的庞大轮廓。”接着哈利向后退去,摔到了街沟里,几乎被巨大的骑士公车轧死。 这里没有对狗的直接描述,而是在深夜的街道这一背景下,突显了发着微光的大眼睛的图像。根据 “侧显—基体”理论,“发着微光的大眼睛”就是与“狗”这个基体相对应的侧显。通过对发着微光大眼睛的突显,加深了读者对狗这个意象代表着不详与死亡的体会,使读者与哈利有了相同的心理感受。
狗意象第二次出现在《死亡预兆》这本书的封面上:“封面上有一条狗,差不多有熊那么大,两眼发光。这条狗看上去出奇的眼熟。”结合店员说的话,“哦,我要是你,我可不看这样的书。你看了这本书,就会看到死亡的预兆无处不在,这本书会吓死人的。”于是“狗”的图像跃然“封面”这一背景之上,加深了不祥的恐怖心理感受。接着狗意象作为第三次“不祥”的启示出现在格兰芬多对赫奇帕奇的魁地奇球赛中。“又一道闪电照亮了看台:一条满身粗毛的巨大黑狗的侧影,这侧影在天际映得清清楚楚,它待在看台最高层的一排空座位上。”接着,地面上出现了至少100个摄魂怪,哈利从离地至少50英尺的高空坠落。 满身粗毛的巨大黑狗侧影作为图像突显于被闪电照亮的看台背景上,在读者眼前形成了一幅恐怖悬疑的画面。
结合占卜课教师特里劳妮教授装神弄鬼的死亡预言,上面“狗”意象的三次出现给小说情节渲染了一层哥特式的阴森悬疑气氛。直到最后谜底揭开,读者才回味过来狗在这些地方出现的真正原因。
(三)猫——动物本性、可疑的形象
猫意象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哈利、罗恩和赫敏出现于对角巷的神奇生物店时。“一个姜黄色的巨大东西从最上面的笼子里跳了下来,对着罗恩的宠物鼠呼噜呼噜地怒叫着。”小说在之后的描述里,几次写到猫试图捉住老鼠的情景。“大猫轻松地从篮子里跳出来,跳到罗恩的腿上;罗恩口袋里的宠物鼠颤抖起来。”“猫仍然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罗恩,然后,它一声不吭地来了个突然袭击。这时,猫的四只爪子已经牢牢地抓住书包,开始凶恶地撕咬起来。它紧抓不放,满嘴冒沫。宠物鼠冲到一个五斗橱下边去了。大猫猛然停住,低低地蹲着,开始用前爪狂怒地伸到五斗橱下面去掏。”
对猫抓老鼠的生动描写使一只猫的动态图像呈现在读者眼前。一方面,作者希望抓住读者对猫的注意力,把猫作为图像放在不同的背景之中:神奇生物商店、通往霍格沃茨的火车、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另一方面,为了制造悬念,作者巧妙地利用了“猫”“鼠”在人类认知中形成的概念,让读者认为猫抓老鼠是理所当然的,而看不到猫抓老鼠的真正动机。在谜底揭开之后,读者不得不佩服作者叙事手法的高超。
在魁地奇决赛的前夜,哈利看见猫和狗在一起的情景:“有一个动物在银色的草坪上徘徊。现在它正在禁林边缘潜行,是只猫!他认出了那瓶刷似的尾巴。难道只是那只猫吗? 哈利肯定他看到树影里还有别的东西。一会儿,它出现了:一条巨大粗野的黑狗,偷偷地在草坪上穿行,猫在它旁边小步快走”。基于前面的情节,猫一直试图吃掉可怜的老鼠,而此刻它又和代表死亡的黑狗在一起。在月光下的草坪这个广袤的背景下,两只可疑的动物图像出现在一起,带给读者一幅悬疑的图画,使读者和哈利一样,都对第二天的比赛感到既期待又不安,急于想知道答案,而答案只有等到情节发展到高潮才能显现。
(四)动物形象的反转
故事情节在前面对三种动物意象的描述上达到了高潮。赫敏在海格家的牛奶罐里发现了老鼠,读者和赫敏感到了一样的惊奇:原来老鼠并没有死。在第17章(本章标题即为:猫、鼠和狗)里,三种动物和三个主人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通过打人柳这个秘密出口到达尖叫棚屋之后,真相被层层揭开。
罗恩想要保护老鼠,但老鼠拼命要逃脱;黑狗进入尖叫棚屋后现身为逃犯布莱克,原来布莱克是一个没有注册的阿尼马吉(能够变身为动物的巫师);猫为了不让哈利等人伤害布莱克,舍身保护。“那耗子在疯狂挣扎。它显然是吓坏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从罗恩手里挣脱。”“那耗子出现了,绝望地猛烈摇动着。罗恩不得不去抓那条长而秃的尾巴,以防它逃走。”
类似的描写把老鼠怯懦、绝望、拼命求生的图像立体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随着真相的展开,读者和三个主人公一样,才明白老鼠之前的濒死状态不是因为猫,而是惧怕布莱克的复仇。一直以来的凶手、逃犯原来不是布莱克,而是之前表现得可怜无辜的老鼠。随着布莱克与卢平之间对往事一幕幕的追忆,老鼠的形象由之前的虚弱可怜突转为贪利忘义、狡猾邪恶。前后强烈的反差带给读者心理上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原因就是对鼠意象一幕幕突显,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的思维走向,最后再来一个突转,使人产生惊奇之感。
“那猫也来加入了战斗,两只前爪都深深陷进了哈利的手臂,并对着哈利的魔杖冲过去。”“那只猫从哈利面前飞跑过去,跳到布莱克的胸膛上,蹲在那里不走。它那张丑陋的脸转向哈利,用那双黄色的大眼睛看着他。”
在了解了真相之后,读者再来回味类似的描写,才发现猫原来是为了帮助蒙受冤屈的布莱克,一直试图抓住杀了哈利父母的罪魁祸首,在哈利等人不了解真相试图杀死布莱克的时候还舍命保护。于是猫的形象反转为勇敢无畏、机智正义的具有灵性的神奇生物。读者对猫的喜爱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除了引人入胜的情节,作者的叙事技巧也是该系列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上对动物意象的分析,高度体现了作者预设伏笔的技巧与作品整体结构的连贯统一。通过图形—背景的不断转换,三种动物意象在读者认知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深了读者对鼠形象的嫌恶、对狗形象的敬佩、对猫形象的喜爱,这三种形象正体现了作品对人性假恶丑的抨击,对爱与真善美的赞扬。
三、结语
图形—背景理论是认知诗学重要的心理学基础,本文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视角,对哈利系列小说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中的三个重要动物意象——猫、狗、鼠进行了认知解读,分析了作者是怎样运用图形背景的转换来安排叙事,引导读者的认知走向,增添作品的悬疑气氛,以达到读者心理上的震撼。哈利·波特系列并非横空出世的文学奇迹,它借助于幻想又植根于现实,冷酷荒诞的现实世界和天马行空的魔法世界交替更迭。图形—背景理论印证了罗琳独具匠心的叙事手段与整体布局技巧,这正是哈利系列小说风靡的原因之一。
[1] Whited Lana A.The Ivory Tower and Harry Potter: Perspectives on a Literary Phenomenon[M].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2.
[2] 翟弘媛.从《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看文学翻译的异化与归化[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
[3] 高原媛.《哈利·波特》的文化原型[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4] 任少云.《哈利·波特》的叙事空间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5] 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6]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7] 李金妹,李社教.论《古巷道》的文体风格——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视角[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1):129-132.
[8] Stockwell P.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2002.
[9] 杨颖.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哈利波特》认知解读[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1):74-77.
[10] 姜淑芹.哈利·波特研究综述[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0(1):82-87.
[11] 罗琳.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M].郑须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张 璠)
Analysis of the Animal Images ofHarryPotterandthePrisonerofAzkabanBased on “Figure-Ground” Theory
TANG Hangu, LI Jinmei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3, China)
The spread and prevalence of Harry Porter novels in the world has formed a kind of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produced from the psychology can not only be use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but also be used for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figure -ground” theory, the animal images ofHarryPotterandthePrisonerofAzkabanare analyzed and the narrative craftsmanship of the novel is illustrated.
HarryPotterandthePrisonerofAzkaban; figure-ground; animal image;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2014-04-19
湖北省教育厅项目“认知诗学视角下的文学模式研究”(2012B212);湖北理工学院大学生创新项目“哈利波特中语言表达解析”(12cx12)
唐汉谷(1984-),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理工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高等学校外语教学与管理。
I106.4
A
1674-0297(2015)01-008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