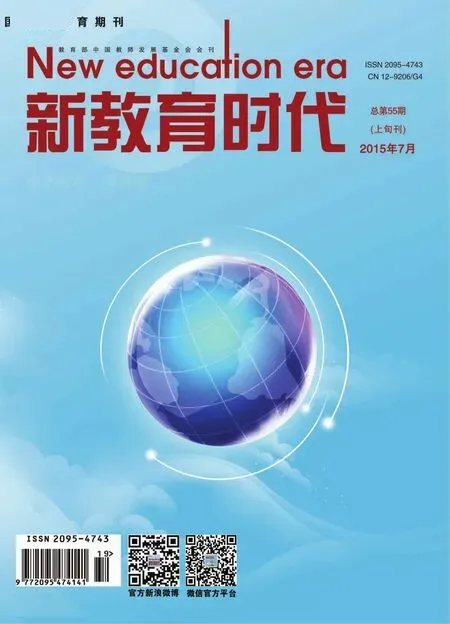《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对女性主义主流论述的提问
韩振江 张译丹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大连 116024)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对女性主义主流论述的提问
韩振江 张译丹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大连 116024)
本文主要对《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一书中三个具有开创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既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异性恋结构的由来以及性别操演论,文章最后说明了巴特勒如何在审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戏仿"政治理论。
朱迪思·巴特勒 女性主义 性别颠覆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研究融合了众多领域的精华,在学界发出她个人独特的声音。在其成名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发表之后,其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随后,她又发表了《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消解性别——欲望的主体》两本著作,以展现她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回应学界一些质疑的声音。提到巴特勒,我们一定要说到“酷儿理论”,她是此理论的开山鼻祖。“酷儿”既英文“queer”的音译,原是对同性恋的贬称,该理论认为人的性倾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甚至,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这理论向两分的异性恋霸权挑战,使边缘群体凝聚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要理解《性别麻烦》的要义,要先明白贯穿全书的一种系谱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从当前特定的问题出发,在它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的范围内找到它的抵达点和有用性。简单来说,就是关注事物的表层,不关注深层,不关注起源。巴特勒以这种方法在书中对传统女性主义研究的主流著作和观点进行了细致的重读,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
《性别麻烦》从形而上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实践三个层面上,分别对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原初同性情欲禁忌以及抑郁异性恋结构和性别操演论进行了探讨,下面我将按照作者的行文逻辑对其观点进行梳理。
一、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
巴特勒首先质疑了结构女性主义身份政治,为从后结构主义的权利框架重新设想女性主义政治做铺垫。
她对“妇女”这一概念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传统女性主义将“妇女”作为研究主体,为这个主体追求政治上的再现,而这种再现要求语言在某种规范之下运作,这规范恰恰就是现有的父系律法,巴特勒认为这种被规范的再现本身可能已经扭曲了主体想表达的真实。
巴特勒对“妇女”代表的终极主体也存有怀疑。“妇女”,究竟代表了一种怎样的范畴,谁规定了这样的范畴,是否先规定了一种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才是“妇女”,那标准从何而来,被现行父系律法压迫的就是“妇女”么?如果是这样,女性主义的主体就沦为某种政治体系的话语建构了,这是一种自砸阵脚的分析。用巴特勒的话说,就是“把‘妇女’再现为女性主义‘主体’的语言与政治之司法结构,是某种特定形式的政治在线的结果,女性主义主体成了那个原本应该是推动其解放的政治体系的一个话语建构。”
传统的女性主义的主体被认为有一种跨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基础,这种基础认为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有某种单一的形式,这种被压迫的普遍形式在不同的具体文化语境里很难被理解。如果一定要规定具有某种标准的是“妇女”,那么为了能够保证囊括它所保护的主体的,这个标准一定有所松动;而如果想使标准严丝合缝,那么这个范围就有多重的排拒,这与原来的,以追求普遍性来囊括数量众多的主体是矛盾的。我们看到,这种对一致的稳定的主体的追求,是一种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与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所要求的“被压迫”,只有在异性恋矩阵里才会存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不再一味否定“妇女”的时候,这个主体的再现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不展示她的被压迫,我们又无法界定这个主体。传统女性主义所保护和再现的主体,从一开始就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追求对这个“性别化”了的主体的解放是没有意义的。
接着,巴特勒转而研究传统女性主义普遍关注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问题。人们原来将对妇女不同形式的压迫归因为性别化,这些研究者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开来,将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归于文化,以这种方式来反驳所谓的生理命定论,借以打破以性别为基础划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阶层。巴特勒说“不管生理性别在生物学中是如何地不可撼动,社会性别却是由文化建构的,因此社会性别并不应该和生理性别存在什么因果关系,也不像生理性别那样单一固定。这就允许了社会性别的多元性。”我们可以说,性别是身体获得的社会意义,是社会的、文化的产物。然而不同地区的文化区分相当大,我们不能说某个社会性别是以某种方式,从某个身体性别发展而来的,社会性别应该因为文化的多元具有多元的可能性。由此,我们看到,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也就是说,男人,不一定从男性身体里衍生,女人,不一定从女性身体里衍生,社会性别也不应该只有男性和女性两种,而应该有更多地可能。为什么社会性别像镜子一般影射了生理性别,出现了和生理性别对应的二元化形式呢?是什么使人们无法忽视这种二元性?这种思维定式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们对生理性别的认识也受到了这种二元性的主宰?如果是这样,那生理性别的自然性就应该受到冲击。如果生理性别也是被建构的,那也就应该像社会性别一样是多元可变的。是什么力量在生理性别的基础上衍生了社会性别,又使人们认为生理性别是自然的,从而保护了生理性别,保证了生理性别的稳定性呢,这种力量究竟为什么服务呢?
我们发现,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的研究总是在此遇到困境,因为它无法打破普遍性、二元性的牢笼,巴特勒分析以往的女性主义研究,指出它们的这种局限。
波伏娃说过:“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的,而其实是变成的”。然而我们应该追问,一个人的社会性别是否像波伏娃所说的那样,是可以选择的,可以受意识控制的么?所谓的性别建构可以理解为一种选择么?如果是这样,一个女人不一定从女性身体发展而来。既然女人是变成的,那为何成为女人的总是女性身体?为什么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男人成为女人呢?“身体是一种情境”,意思是说身体是被动的媒介,是受文化隽刻的。如此说来根本没有什么生理性别,生理性别其实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并没有一个先于文化就存在的身体。巴特勒认为,她的说法仍然有一种将身体和精神区分的二元性,也就是承认人身体的精神部分是被性别化了的,但仍然认为生理性别的二元性是自然的,这使波伏娃的理论具有局限性。
伊利格瑞认为,女性是男权话语的一个虚构,因此是不在场的,是不可言说的。这种虚构使男性中心得到承认,认为女性的被命名是有意的,且这种命名遮蔽了女性的位置。这表面上消解了两性间的区分,但是我们不禁质问,最初的时候如何区分哪些人应该被命名为女性呢,是否是根据某种原则,那么这原则从何而来呢,还是以生理性别为区分的么,可我们已经讨论过,生理性别也就是社会性别。
讨论完性别身份的虚构性之后,巴特勒开始讨论性别化的另外一个维度,欲望。
在她看来,维蒂格所说的解决女性困境的方法——恢复受欲望律法压抑之前的多元变态欲望以及伊利格瑞设想的建立以女性身体形体学为基础的话语体系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些试图颠覆现有欲望论的方法都犯了同样一毛病,就是重复了他们想要推翻的现有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以伊利格瑞的想法为例,她想建立的话语体系是以女性为基础的,但仍然是二元的,不过是把现有的体系倒置了而已,并没有什么突破。传统的研究者认为,异性恋框架如此的稳固是异性恋霸权的作用,所以试图建立一种在现在的霸权话语之前的支点,来重建正确的欲望的体系,而这正中异性恋霸权的下怀,这使异性恋霸权本来企图隐藏的逻辑不受监视,因为新建立的秩序似乎越过了异性恋霸权,但实际上只是对这种霸权的重新书写。
巴特勒首先质疑了妇女这个范畴,认为女性主义问题的症结在于追求一个稳定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被性别化了的,然后巴特勒拆解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之间的因果联系,认为不存在自然的生理性别,因而社会性别也不是由生理性别社会化而来的,所谓“正确”的“异性恋”也是受到二元的异性恋霸权的产物。
二、原初同性情欲禁忌与它所造成的异性恋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用氏族联结的例子引出了对亲属关系理论与乱伦禁制的讨论新娘作为一个礼物,巩固了两个氏族的内部联结。此时,女性的作用是通过男性身份的不在场,来反映男性身份。父系传承通过对女性仪式性的排除和引进来获得稳固。宗族背负不同的姓氏,在同一的男性文化身份里寻求特殊化。然而,是什么样的文化将女性放到了一种交换物品的位置上呢。列维认为,父系氏族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对同性社群的欲望,对同性的欲望的基础上的,这是一种被压抑,被鄙视的欲望,因此这种男人之间的欲望,男人之间的结盟被转接到了通过异性恋制度对女性的分配上。
巴特勒认为,列维没有说明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刻,同性情欲是被鄙视和禁忌的,因此这样的说法欠缺一个基础。但是,这联结的例子似乎说明了乱伦之所以成为禁忌是因为它无益于男性霸权的巩固,列维把乱伦归为一种想象,但是没有解释为何乱伦异性恋恋情被认为是前话语的。
拉康认为性别化的存有是通过语言的意指行为而产生的,什么是存有,是在父系律法的基础上被判定的。男性拥有某种力量,女性是体现这种力量的场域,男性需要女性,这个他者的肯定,才能确定其自身。男性追求一种不证自明的独立性,然而这个过程需要女性去反应和证明;女性反应男性独立自主权利的要求,但是同时又因为其本身的存在削弱了她所追求的那个功能,因此,所以,这样的互惠模式被称为一种带着喜剧意味的失败尝试,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异性恋尝试,也是可笑的。由此,拉康指出,主宰女性的,是一种“伪装”的心理机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女性的一些特点,是女性的伪装,在此之下,应该有女性的本质和欲望需求。伪装是女性的假面,假面支配认同,被拒绝的爱得以解决。拉康对假面的探讨跟女同性恋相关。他认为,女同性恋来自一种失望,她们理想化的倾向,使她们对爱的追求更强烈,牺牲了欲望。但是他是否考虑到,依照这个逻辑,同样地,异性恋,是否同样地是从受挫的同性恋而来呢?那么我们现在所建立了的异性恋结构是否是来自同性禁忌造成的受挫,这是否说明了同性情欲禁忌是先在的?我们现在建立的异性恋结构是否是因为受挫的同性恋的伪装?里维埃尔也提出,女性同性恋伪装,带上假面,维持男性认同,为的是追求一种平起平坐的竞争关系,并以此逃避霸权的惩罚。值得注意的而是,拉康、里维埃尔都认为女同性恋有一种去情欲化的取向,巴特勒把这归因为对欲望的男性化和异性恋化的想象,因此所有脱离常规的女性欲望,都被认为是追求一种男性化认同,这种合并某种程度上使异性恋霸权更稳固了。
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来描述性别认同的形成过程。弗洛伊德指出,人在失去她所爱的人的经验中,会把那个失去的他者合并到自身的结构里,接受这个他者,延续他者的存在。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都面临爱人的丧失。只是这个拒绝他们的爱人,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母亲。如果这种丧失发生在异性恋禁忌里,既女孩爱上父亲或男孩爱上母亲,那被否定的是爱的客体,而非爱的形式,因此欲望从这个客体转移到其他客体上,没有对客体的内化。但是在禁忌的同性恋里,爱的客体和欲望形式二者都被否定了,因此这种抑郁被内化,拥有了失去的那个人的特质。这是弗洛伊德对异性恋结构的解释,在巴特勒看来,弗洛伊德原本指出人最初是有双性情欲的,这本来有颠覆的潜能,但是他从一开始,他就把异性恋看做开启俄狄浦斯情结的关键,他个人的倾向影响了他理论的激进。性别身份实际上是因禁忌而被否认的爱的客体经过合并形成的身份认同。而那些丧失的被合并的客体,直观地化于身体上或身体内,使性别看起来像是一种事实存在,这就是巴特勒所说的直译的幻想。
在这一部分,巴特勒转向了精神分析领域,追问欲望和性别的构建为何彼此具有一致性,她审视了列维-斯特拉斯、精神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理论中有关乱伦禁忌和性别获得的理论,运用对压抑假说的批判,以及权力运作的框架来分析这些叙事,指出其中隐含的异性恋假定,也提出了同性情欲禁忌是先于异性乱伦禁忌的先在禁忌。
三、性别操演论
对身体的幻想建构进行探究可能由精神分析学开启,之后福柯丰富了身体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巴特勒援此了她自己的政治构想。身体政治不是巴特勒独创的,传统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已经有这方面的探索,但法国女性主义身体政治的特征是本质主义,这与巴特勒反本质主义,并追求的建立在生产性权力框架的身体政治立场有很大差异。
要说明性别操演论我们需要引入巴特勒自己提及的一个例子——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在法的门前》。小说讲述了一个乡下人想求见传说中的法,至死也没有如愿的故事。看门人是法的守护者,也是特权阶级中一个卑微的存在,这样一个小人物却可以无限延长处于弱势的乡下人觐见法的时间。被统治者一旦知道了法的真面目是服务特权阶级,那么统治阶级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最后,乡下人倾尽生命也没见到法,而法的权威正是通过对乡下人对解释法律的真正意义的惧怕和渴望才得以建立的。巴特勒认为,我们对性别也有如乡下人对法一般的期待,既认为性别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等待我们揭示其意义,正是种期待孕育了我们所期待的现象本身。我们以为性别是种内在特质,这种特质是我们期待的并通过身体行为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性别本体,我们所认为的性别自身的内在性质,其实是通过社会规范不断作用于我们身体上的重复和操演的结果。先有重复性别规范的行为,才逐渐形成稳定的性别。这这些重复性的行为受制于话语规范和实践,正是这些话语对身体性别持续的风格化,使得性别获得了暂时性的稳固。所以,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本质的性别了,性别身份只是形成于持续的操演行动中。
巴特勒指出,“颠覆身份的可能性只存在于重复的实践”,因为“必须成为某个特定性别的指令必然产生挫败:呈现多元性的各种不一致的设定,超越并违抗了它们所由以产生的指令”。巴特勒在一些男同志和女同志的“戏仿”的性别实践上看到身份的增衍以及抵抗的可能性。据此,巴特勒提出了一种以“戏仿”(parody)为形式的政治设想。巴特勒之所以选择“操演”这个词描述性别形成的过程,是因为操演过程被性别律法隐藏,不易被察觉,而“表演”却带有主观的精神,好像我们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性别一样。性别操演是性别认识论上的转向:性别是一种时间性的框架,操演行为是永远的在进行之中的现在进行式,是不可完结的,人们的一生也不应该只具有一种性别。总之,性别颠覆政治提倡人们自由地在不同性别之间转换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真正自由的,不被性别束缚的主体就真正产生了。
[1][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2][法]西蒙·德·波伏娃著、李强选译.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3]宋素凤.《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后结构主义思潮下的激进性别政治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10(1).
[4]都岚岚.论朱迪斯?巴特勒性别理论的动态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2010(11).
[5]何维华.性别的假象与颠覆:从朱迪斯?巴特勒的角度看[J].现代妇女,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