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分析
奂平清 何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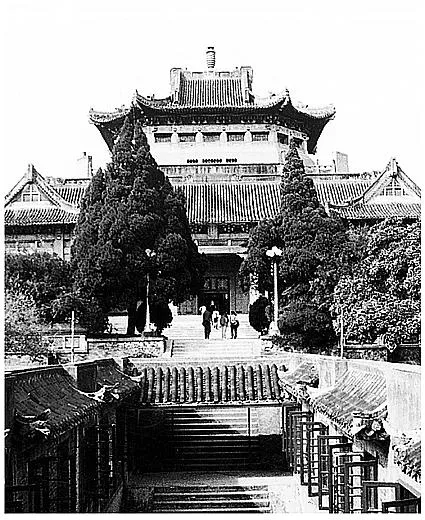
中国农民职业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分析
摘要:农民的职业化意味着农民从“小农”向“职业农民”的转变,实现农民职业化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CGSS2010调查数据构建的中国农民职业化水平指数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农民职业化水平还较低,农民职业化依然任重道远。城乡二元结构、现行土地制度和农民素质是农民职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当前,实施以推动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为根本任务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创新土地流转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构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体系,是提升我国农民职业化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农民; 职业化; 城乡二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
中国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45%*国家统计局(2015),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685799.html.、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31%*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总就业人口为76977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4171万人。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的国家,实现农民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在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农民”(farmers)更多是指一种职业,而在中国,“农民”(peasants)仍然具有明显的传统性特征。因此,由传统农民(peasants,即“小农”)向现代农民(farmers,即职业农民)转变,即农民的职业化,是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近年来也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措施。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分析当前中国农民职业化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探讨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的途径。
一、 农民职业化的涵义、意义及影响因素
农民现代化是农民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的过程,主要包括农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其中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是最基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农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包括土地的科学利用、农业先进科技的应用、经营方式的调整等内容。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传统农民的生产目的在于满足生活基本需要,因而竞争意识较弱,农业经营的规模有限,生产市场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对传统生产经验的信赖和依赖导致传统农民抗拒使用先进科技,土地的利用也不尽合理。农民职业化,可以看作是农民现代化的主要方面。从已有的研究看,关于农民职业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职业化的内涵、影响因素和相应对策等方面
(一) 农民职业化的内涵
农民职业化是一个过程概念,描述的是传统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的动态过程。人类学家沃尔夫曾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动机为标准,将农民区分为传统农民(peasants)和职业农民(farmers)。传统农民以维持生计为生产目标,而职业农民将农业生产作为一项产业来经营,并尽可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Eric R.Wolf,1966:2)。这一区分也揭示出二者的最大差别: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而职业农民更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英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艾利思(2006:116)将农民划分为追求利润型、风险规避型和劳苦规避型等类型,显然,职业农民是追求利润型农民。从国外的相关研究来看,追求利润被看作是职业农民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发达国家较早经历过农民职业化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在此过程中农民所发生的转变。Patrick Svensson(2006:390)在研究19世纪的瑞典农业发展状况时发现,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主动参与圈地运动,进入信用交易市场和教育系统,并且发生土地流转行为。Tony Lynch(2001:125-126)等根据澳大利亚的农业状况,认为农民在成为一个“职业人”(professional body)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转变之一是接受经济知识和农业生态知识的培训。由此可见,农民的职业化是农民市场参与程度加深、知识文化水平提高、经营能力加强的过程。
中国农民大多数仍处于兼业状态,一般以“新型农民”这一概念来指代那些在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和经营水平上高于普通农民的农业生产者。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新型农民”概念,并从素质方面将其定义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概念。有学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除具有一般农民的特征外,还充分进入市场、追求报酬最大化,具有高度稳定性(以务农作为终身职业),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并且农业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朱启臻,2013)。与传统农民不同,“新型职业农民”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标,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和经营水平。
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根据职业农民的特征与内涵,我们将职业农民定义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具有较高专业素质、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从业人员。农民的职业化也就是指农民生产目转变、素质提升、经营自主性增强的过程。
(二) 农民职业化的意义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普遍都经历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职业化、农民职业素质提高、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民支持的过程。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被迫或自觉地在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之间摇摆徘徊,农业面临严峻的“谁来做农民”的问题与困境。
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依然保持着小农经营的特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小农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严重制约着农业、农民的现代化,乃至国家的整体现代化,形成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诸多困境。例如,由于有限的土地规模不能保证家庭应有的收入水平,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下降,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大部分农民的选择,经营农业的人员主要以年龄大、缺乏外出技能的农民为主,无疑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建设;由于农民从农业经营中所获得的收入较低,对相关农业服务的购买能力也就较低,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投入也缺乏积极性;小农户很难抵御农业风险,尤其是在信息不对条件下,大市场的风险使得农产品贱也伤农、贵也伤农的循环成为常态;分散的小农户在监管缺乏的条件下,为追求农业经营的市场利润,对化肥、农药、抗生素、激素等“农业技术”的滥用,也加剧了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社会治理困境。此外,中国的农业补贴无论是在规模数量还是类型方面都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户籍“农民”人口众多,这些补贴分散到众多的农民头上,而不是真正的“务农”者头上,因此国家的农业补贴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难以有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小农经营停滞的问题,费孝通也开始探索规模农业和使“亦工亦农”的农民专业化等解决途径。他指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体制下,农民大部分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亦工亦农”的问题成为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急需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的问题”,因为“亦工亦农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过渡的方式,到工业化向深层次发展,工农势必分家,各自成为专业,农业也就实现了现代化”(费孝通,1994)。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邓小平在关于农业发展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2004:1310-1311)。这是因为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新型城镇化、土地流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战略与政策,也正是为了克服小农经营的困境、促进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三) 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有不少研究对于制约中国农民职业化的因素进行了探讨。有分析认为,限制农民职业化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在体制上,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流动,导致农民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无法接触外界资源,发展缓慢;二是在效益上,农业生产收益低,破坏了职业农民赖以形成的利益动因;三是在制度上,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依然不健全,农民能够获得的土地有限,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四是在个人素质上,农民文化知识、技术水平低,经营技巧缺乏,限制了自身农业经营水平(郝丽霞,委玉奇,2009)。有人以实证调查为基础,分析培育职业农民、解决农民职业化问题的对策。如米松华等(2014)在浙江、湖南、四川和安徽进行的新型职业农民调查,单武雄(2014)在湖南石门县进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情况调查,吴易雄(2014)在湖南株洲、湘乡、平江进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情况调查等。
二、 中国农民职业化现状
笔者尝试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等机构完成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为依据,测量和评估中国农民职业化的实际水平,并分析影响农民职业化水平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调查面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有效样本量11785个。本文关注农民的职业化状况,因此以“务农”为职业的受访者作为分析对象,即“工作经历及状况”为“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和“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的样本,剔除部分缺失值后,共有2007个职业为“务农”的有效样本。除注明外,本文所有分析数据均来自该调查数据。
(一) 操作化与测量指标
笔者对职业农民的操作性定义是:以务农为主要职业,文化水平高,能够运用农业科技,懂得市场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的从业人员。依据这一定义,本文将全职务农的程度、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市场经营水平、规模经营水平等方面作为测量农民职业化水平的变量。其中“全职务农的程度”通过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测量,以CGSS2010问卷中“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及“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收入”来计算;“文化程度”通过问卷中“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测量;“技术水平”通过“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情况”(即应用农业科学技术的频率)测量;“市场经营水平”通过“在农业生产中是否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种植或养殖结构”及“除自己消费外,处理农产品的首选方式”(即市场行为与意识)测量;“规模经营水平”通过“家庭目前土地的使用情况”(具体为自耕地面积)测量。由此构建出一个农民职业化水平测量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农民职业化水平测量指标体系
(二) 农民职业化现状分析
农民收入的组成状况可以反映农民获得收入的方式。表2数据显示,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在80%以上有81.5%,说明“目前务农”的被访者大多数是全职务农的,只有小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兼业情况。

表2 农业占总收入比重分布状况
从文化程度来看,表3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务农者”(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部分农民的文化程度仅为小学或初中水平,有1/4的农民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高中及以上水平的仅占5.5%。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农业的市场化与规模化经营均要求农民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而目前中国农民的文化程度尚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表3 农民的文化程度
传统农民一般依据经验进行农业生产。表4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科技的频率依然较低,40.6%的农民只是偶尔使用农业科技,而从来不用农业科技的比例为34.5%,经常使用的仅为约25%。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也主要表现为对农药、化肥和某些良种(如转基因作物)的高度依赖。

表4 农民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的频率
在商品化过程中,农民在确保农产品能满足自给自足需求的前提下,一般会将剩余产品在市场上销售。表5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1.6%的农民会将剩余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这表明市场交易已成为中国农民较为普遍的行为。不过调查也表明,由于农民土地经营面积小等原因,有22.6%的农民除了自给之外并没有多余的农产品。

表5 农民处理剩余农产品的方式
尽管农民存在较为普遍的市场交易行为,但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市场意识依然相对较低。近45%的农民“从来不会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自己的农业生产结构”,仅18.5%的农民会“经常根据市场行情进行调整”(见表6)。结合表5和表6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大多数农民会向市场出售自己的剩余农产品,但多数农民很少会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农业生产,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并不把追求市场利润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目的,而是首先要满足自家的生活需求。这也表明,中国农民的市场化经营程度依然较低。

表6 农民市场意识状况
小规模生产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依然较小。CGSS2010调查数据显示,“务农”者平均每户占有耕地8亩。其中自耕地在0-5亩农户占到50.5%,在10-20亩的占13.8%,自耕地在20亩以上的仅有6.6%*本文分析对象是以“务农”为职业的人员,故这里统计得出的数据反映的是农业从业者的耕地占有量。。

表7 农民自耕地*CGSS2010分别调查了受访者家中的田地、山林和牧场、水面和滩涂及其他土地类型的使用情况,包括从集体承包、转出、转入、自己耕种和闲置的面积,这里“自耕地”是指是农民自己耕种的田地面积。占有状况
从纵向历史比较来看,我国农民规模化经营水平有所提升。根据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至1996年底)显示,我国农业从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为4.6亩;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至2006年末)显示,我国农业从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已增至5.2亩*人均耕地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1996年中国农业从业人口为42441万人,耕地面积为13003.92万公顷;2006年农业从业人口为34874万人,耕地面积为12177.59万公顷。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但若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我国农业规模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如2011年时美国人均耕地面积9.9亩,农业人口*美国没有实施户籍管理制度,不存在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之分,因此其“农业人口”实质是指农业从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则高达495亩;而人多地少的日本,也通过农业合作组织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2009年,耕地面积75-150亩的组织占16%,150-300亩的占27.9%,300-600亩的占18%(陶爱祥,2012:27-30)。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农民的规模化经营仍处于较低水平。
(三) 中国农民职业化水平指数
这里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为基础,建立由以下五个方面的指标(各指标的得分都赋值和换算成0-20分的分值区间)组成的中国农民职业化水平评估指数:
a.全职务农程度。通过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测量,根据表2的内容,从“0%”到“100%”分别赋值和换算为0,3.33,6.66,10,13.33,16.66,20分。
b.文化程度。根据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到“本科及以上”分别赋值为0,4,8,12,16,20分。
c.农业技术水平。通过农民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情况来测量,对“从来不用”、“偶尔用”和“经常用”分别赋值0,10和20分。
d.市场经营水平。通过农民处理剩余农产品的方式(市场行为)及农民市场意识来测量。市场行为方面,“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赋值为20分,“出售给国家机构”赋值为10分,其他行为统一赋值为0分;市场意识方面,“经常根据市场行情调整生产行为”的得分为20分,“偶尔调整”的得分为10分,“从来不会调整”的得分为0分;市场经营水平取值为市场行为和市场意识的平均值。
e.规模经营水平。通过农民自耕田地的面积来测量,根据表4的内容,从“无自耕地”到“60亩以上”分别赋值和换算为0,3.33,6.66,10,13.33,16.66,20分。
在各指标的权重方面,根据库兹涅茨原理,在现代社会中,相对于非农业产品来看,农业产品的需求和消费弹性低*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102-103页。,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因此也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将以农业收入占比来测量的“全职务农程度”指标在农民职业化水平指数中的权重设定为10%。此外,将“文化程度”的权重设定为15%,“农业技术水平”、“市场经营水平”和“规模经营水平”三项都为25%。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中国农民职业化水平指数:S=a*0.1+b*0.15+c*0.25+d*0.25+e*0.25。

表8 农民职业化水平指数分布状况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农民职业化指数平均得分为9.03分。从指数的分布状况看,22.76%的农民职业化指数在8-10分之间,19.37%的农民职业化指数在10-12分,15.18%的职业化指数在6-8分。职业化指数在16分以上的农民仅占1.07%(见表8)。这表明中国农民职业化的培育和提升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三、 影响农民职业化水平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职业选择上,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从事非农工作;在市场经营和市场意识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民在生产时不再仅满足于自给自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此外,国家近年来也在逐步为农民的规模化经营创造相应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在我国许多地区,职业农民与现代农业开始成长,出现了一批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形式,其人员已经成为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不过,前述经验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民的职业化水平并不高,职业化步伐也并不快。因此,对于制约农民职业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还需要深入分析。
(一) 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职业化的制约
在以户籍制度等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城乡差距大,农村劳动力大多长期在城乡之间钟摆式流动,导致农村、农业因发展主体缺乏或不确定而陷入困境。因此,通过城镇化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大力转移农业人口,扩大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农民职业化的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农民工体制,大量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和非正式就业者,但依然保持“农民”身份。这种状况与费孝通所描述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民与城市间的关系很相似:城市吸引农村人口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其代价是家庭的割裂;同时城市对来自农村的劳工并没有保障,每个工人都得自己想办法,因此他们将乡间的土地作为有口饭吃的最后保障和退路。这样,城市里的劳工每个人背后都拖着一根与其家乡相连的“尾巴”——对家人的感情和责任以及土地。对城市而言,这样的“尾巴”使其难以向工业化发展(费孝通,1948)。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阶段所限,城市对劳动力和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而当前中国农民工的状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农村发展困境,则主要是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制约。也就是说,当前城市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吸纳能力已经足够强大,但体制性的排斥使农民工及其家庭难以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样,农民工的部分家人依然在农村,土地依然被其视为“退路”和保障。因此,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有明确的制度化保障之前,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种“社会保障”的。要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也就不容易顺利推行和实现了。
“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分析指出,用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把农民限制在农村的做法,束缚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农民富不起来,农村也难以现代化。因此必须要跳出农村、农业领域,进行战略性的社会结构调整,让相当多的农民转变为二、三产业职工和城市居民,改变我国“工业化国家+农民社会”的现状(陆学艺,2000)。
(二) 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民职业化的制约
从现实实践来看,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积极功效已经逐步弱化,当前已日益暴露出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主要劳动力的离土离乡对农业安全等方面形成极大的威胁,当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靠内卷化式的劳动力投入,而更多是依靠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来维持;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家庭缺乏应用现代科技、采用现代管理的能力和条件,也缺乏内在动力,更缺乏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开发性投入的能力和动力,即使是来自政府等方面的外部开发性援助项目,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往往也不高;由于小农家庭从农业中获益相对有限,因此针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即使是免费的,对农民也往往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小规模农业经营也使得个体农户很难应对大市场风险,也极大地制约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农民的职业化无疑依然是难题。
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杜润生分析指出,承包制之前的根本问题在于集体经济对于农民的束缚以及绝对平均主义。包产到户是符合中国当时人多地少、工商业机会少、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一国情的(杜润生,2005:154)。当前和未来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不是土地公有还是私有,不是家庭经营还是集体经营,关键在于经营规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人口转移的加速,土地规模将会扩大,实现多形式的联合,既告别过去自发的、孤立的小农经济,也将有别于那种限制农民自由发展的集体经济(杜润生,2005:134)。
在农业人口众多、为了保证社会稳定的国情条件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就需要通过相关配套政策促进土地流转,突破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民职业化的制度障碍。
(三) 农民文化素质对农民职业化的制约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最终得以农民为发展主体。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来承担。然而,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差距条件下,农民文化程度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都被城市所吸纳,即使是最近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也依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将那些素质较高、有转移条件的农民流动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这无疑会继续加剧农村人口素质的下降。

表9 务农者的年龄分布状况
从CGSS2010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务农者的年龄总体偏大,务农者中,35岁以下的仅占11%,45岁以上的则占到近64%(见表9)。从文化程度来看,尽管我国农村中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已由2000年时的11.55%降至2010年的7.2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但调查数据显示,务农者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到近95%,其中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高达25.4%(见表3)。在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和农业职业教育的比例都极低。
四、 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的路径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实现农民的职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指标。在当前社会转型加速期,我们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也要根据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国情,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农民职业化之路。
(一) 农民职业化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在促进农民的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有着值得借鉴的措施与经验。这里对美国、法国的做法与经验加以简要介绍。
美国作为世界上农民职业化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方面采取了众多积极有效的措施。总结起来,这些措施可以归纳为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现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工业,使得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工业化初期的63%降至目前的2%(洪仁彪,张忠明,2013),为促进农民职业化创设前提条件;二是重视农民教育培训,一方面在社会上开展多样的职业农民培训活动,另一方面为农业专业在校生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支持;三是提供政策性支持,如通过实施特色农作物(Specialty Crop)计划、开展食物本地化运动(Local Food)、鼓励发展有机农业等措施(李国祥,2013),支持职业农民在各农业领域的发展;四是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提供农业补贴与专项贷款,满足职业农民的资金需求。
法国与中国类似,也是一个有着很强小农经济传统的国家(许平,2011:100)。但在二战以后,为促使土地转让、扩大农场规模和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密的问题,法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鼓励措施,成功地把“小农”改造成现代职业农民。例如,政府设立“调整农业结构行动基金”,资助转变职业的农民,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对青年农民的安置和培训给予资助,停止向务农的老农发放终身年金,以促进农场劳动力的年轻化;政府赋予中型农场土地优先购买权,以促使小农户向非农部门转移;对改变职业的农民予以资助和专门的培训,由“全国治理农场结构中心”提供培训的路费和生活费,以使移居者更容易找到他们力所能及、有合适报酬的职业,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地区的生活;对于继续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除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外,还需要取得合格证书才能经营农业,这种教育与资格审查相统一的制度使得法国农民的职业素质有了保证。此外,法国农业部门还通过财政优惠、成立各类农业组织等方式帮助农民实现机械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王章辉,黄珂可,1999:213-216;杜朝晖,2006)。
(二) 促进中国农民职业化主要途径
中国的农民职业化虽然依然面临农民人口众多等因素的制约,在当前也面临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机遇。因此,加快推进以农民工及其家庭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创新土地流转为途径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步伐,建立健全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必将加快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一,实施以推动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为根本任务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技术进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决定因素,而这些因素的成长对城市化存在着很高的依赖性。城市化的合理推进,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郭剑雄,2003)。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转移劳动力是实现农民职业化的前提条件。推动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村小农家庭经营困境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必须要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减少和消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对农民的排斥。新型城镇化的“新”,核心在于一是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促进农民市民化,力求为农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以土地和城市规模为本;二是城镇化要建设城乡双赢互利的新型城乡关系,而不是城市这样那样剥夺农村。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城市规模扩张的做法,要以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和就业为核心,合理规划城市规模,积极主动有序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进和完善能让城乡居民都能安居乐业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现代职业体系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郑杭生,奂平清,2014:148-150)。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除了户籍制度改革,还要切实解决转移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转移农民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还要对其提供持续的支持,帮助其适应和融入城市的工作与生活,解除其退出土地或农村的后顾之忧。
第二,创新土地流转,推动现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基本经营制度的条件下,需要通过相关配套政策,创新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机制。对于不愿务农的传统农民,要建立流出机制,借鉴发达国家对其提供非农创业的资助与保障政策,鼓励其退出土地的经营权乃至承包权,消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和农民身份对土地规模、集约经营的限制;对于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并有能力的农民,要建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进入机制和职业化培训资助制度。要积极探索和发挥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在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中的作用。
第三,构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体系和农民资格认证制度。农业的现代化需要有文化、懂现代农业科技、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需要通过系统的职业教育培训来培养。我国以往的农民培训,更多的是针对小农户经营方式的零散的单项技术培训,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职业化的要求。在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农民职业教育长期受到忽略,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极不完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保障教育培训经费。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为了确保宝贵的农业资源能让高素质的农民经营,一般都采取严格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考试制度和农民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我国也需要放眼未来,探索建立农民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这既有助于当前农民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及效果的监督评估,也有助于从制度上促进和保障农民的职业素质,推进农民专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2004).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杜朝晖(2006).法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启示.宏观经济管理,5.
[3]杜润生(2005).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
[4]费孝通(1946).内地农村 农田的经营和所有.载费孝通(2009).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5]费孝通(1948).城乡联系的又一面.载费孝通(2009).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6]费孝通(1994).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载费孝通(2009).费孝通全集(第1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7]费孝通(1998).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4.
[8]弗兰克·艾利思(2006).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郭剑雄(2003).城市化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经济问题,11.
[10] 郝丽霞、委玉奇(2009).农民职业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农村经济,12.
[11] 洪仁彪、张忠明(2013).农民职业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5.
[12] 李国祥(2013).美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及启示.农业经济问题,5.
[13] 陆学艺(2000).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5.
[14]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5] 米松华、黄祖辉、朱奇彪(2014).新型职业农民:现状特征、成长路径与政策需求——基于浙江、湖南、四川和安徽的调查.农村经济,8.
[16] 单武雄(2014).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基于湖南省石门县50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职业技术教育,16.
[17] 陶爱祥(2012).中外农业规模化经营比较研究.世界农业,12.
[18] 王章辉、黄珂可主编( 1999).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 吴易雄(2014).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困境与突破——基于湖南株洲、湘乡、平江三县市的调查.职业技术教育,28.
[20] 许平(2001).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1] 郑杭生、奂平清(2014).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基本理论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2] 朱启臻(2013).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23] Eric R.Wolf(1966).Peasants.New Jersey:Prentice Hall.
[24] Patrick Svensson(2006).Peasant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weden.SocialScienceHistory,3,390.
[25] Tony Lynch,Bert Jenkins,Annette Kilarr(2001).The Professional Farmer.AustralianJournalofSocialIssues,2,125-126.
■作者地址: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何钧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责任编辑:桂莉
◆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hinese Peasa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0)
HuanPingq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eJunli(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Professionalization of peasants indicates that “peasants” have been transformed to “farmers” and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farmers.The professional level index of Chinese farmers that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CGSS2010 shows that the farmers’ professional level of China is still very low.The main restricting factors include the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the current land system and farmers’ quality.At present,we should promote farmers’ professional level by implementing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o reduce agriculture surplus population,innovating the way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and building a farmer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Key words:peasants; professionalizatio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new-type urbaniz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6CSH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SH002)
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4.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