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姐服务
张雄

蓝蓝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5号楼的街坊们都知道不拉窗帘的301是个办公室,他们也认识蓝蓝是这里的头。下班啦?上班啦?他们总笑眯眯招呼她。没人问起她这里的业务,蓝蓝觉得他们是知道的,“有时候姐妹们过来玩,她们的浓妆和衣服其实能看出来。”
按照头天的约定,我大约在上午11点钟到达先锋公寓——天津信爱女性家园的办公室设在东丽区的一处民宅里。蓝蓝正站在小黑板前给4个女下属讲解常见妇科病症状。她喜欢双手下压,那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在释放她的掌控欲。蓝蓝认真而急切的讲解给学员带来了压力,那些趿着猩红棉布拖鞋的下属们时不时挠头表达她们的焦虑,因为几小时后她们将要把刚学到的内容传达给另一拨人。一种莫可名状的紧张感在教学双方来回传递中加剧。好在蓝蓝板书时不常卡个壳,趁她匆忙寻找别字替代的间隙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工作的迫切感驱使着这个37岁的女人以一种不由分说的气概生活着,这与这个城市慢条斯理的节奏不太吻合,员工们也在被她拖着走。午餐叫外卖时蓝蓝点了四两素锅贴,曾在饭店打工的经历让她不信任外卖肉的品质。6分钟后她已经吃完,端着水杯跷起二郎腿斜倚在椅子上,向员工布置下午的外展任务。每吩咐完一个,她便冲人点点头表强调:你们听明白了?
外展(Out reaching Social Work)是蓝蓝挂在嘴边的术语,在这里指社会工作者为流动女性中的女性性工作者提供的支持服务。我有点担心一个男人混在一群女性工作者的外展队伍里是否违和——她们是不是会因此而警觉,蓝蓝的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她摆摆手,那神情告诉我这不是问题,“你就说是我们志愿者好了。”
“但你不要问她们一些奇怪的问题,”她好像想起什么,扭头甩过来这么一句,语气有几分严厉。“比如问她们为什么干这行——这问题很低级。”
我赶紧向她保证现场我什么都不会问,只看看就可以了。
司机座位上高高扎起马尾的L是信爱的新成员,她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载我们去外展目的地。我坐在副驾,为打发沉默,搭话问起她的上一份职业。L没接茬,也许她没听到,她跟后座的蓝蓝确认了一下是否在前方路口直行。后来蓝蓝告诉我,L是家庭主妇,丈夫常年在外地工作,她也做过一些“那方面的兼职”。
信爱的几个员工都有过性工作经历,包括蓝蓝。现在她们是一个民间组织,服务内容是为外来打工女性提供健康咨询,重点服务性工作者。这个团队的背景似乎与她们的目标天然契合,但蓝蓝最近的难题是如何搞定下属。团队里没有人上过大学,但她们干的活却很像一个导师带领的研究生团队:计划书,立项,调研,写报告,参加国际会议。蓝蓝说,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她们或许是餐厅服务员、家政员工,或者保姆。一个NGO组织需要的案头工作要求实际上已远超出她们的能力,蓝蓝用她的学习能力弥补了这一点,现在她可以写项目计划书,可以弄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甚至能跟外国女权主义者辩论“赋权”,但其他人做不到。蓝蓝偷偷在家喝酒哭过好几回,同事的工作能力和态度都不能让她满意。她必须一次次按捺住自己的急性子,等待她们的作业。结果往往是令人失望的,于是干脆推倒自己重新来过。
但能力建设的需求是双向的。有次她在泰国出差,打了一个小时的国际长途教同事如何使用Excel。她没想到网络视频。
没有办法,她说,你不能指望一份工资只有两三千元的工作能招来人才。
我问她:“对她们而言这只是份工作,但对你是事业,对吗?”她很满意这个总结,在后来访谈时流利地重复了这句话,就像她从来就是这样想的。
或许强大的吸纳能力让这个东北女人在不到5年时间里从洗浴中心小姐摇身变成一个NGO的领导者,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她的野心。她承认自己理解力比较好。这也会表现为一种优越感,在我采访她的7个多小时里,她大约5次提到其他人的“笨”或“蠢”。在说俏皮话或争执时她会略带轻蔑地发出东北人的翘舌音,这让她的攻击性有所暴露,也多少有点让人畏惧。但同时她又有种热情的爽朗,它与客气和教养无关,那是一种能让陌生人迅速靠近的率真。这个女人像个谜团,让我感到困惑的不仅是她何以进入性工作者行列,又全身而退,我更为感兴趣的是她通过自我教育完成城市化乃至精英化,以及她如何找寻自我的历程。
她每晚都要敷面膜,这让她保持了成熟后的活力与光泽。眼影和眉毛也描画得简约而到位,相比之下她的荷叶裙摆黑色连衣裙显得有些保守——她并不喜欢黑但说这是“最适合她的”。如果非要说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她看人的眼神是直直的,或许是某种魅惑,盯久了会让人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是某种禀赋还是职业训练的结果,与他人交流时她常露出这种神情。
聪明而倒霉的优秀生总是具备相似的起点。她成长在吉林农村,从小成绩拔尖,7岁父母离异,读到初一自己放弃学业出外打工。她不忍看母亲为全家日夜操劳。她喜欢钱,确切说是喜欢支配金钱的感觉。还在上学时她自己捡破烂、上山采柳条挣来的零花钱让她感到满足。打工使她成为家中顶梁柱,她卖冰棍、卖水果、卖早点,后来在饭店刷碗,切菜。厨师的工资是切菜工的两倍,她也想做厨师,并成功将饭店厨师变为自己的首任男友。但厨师男友嫌弃她不足1米6的身高,以及她给老家寄钱的习惯,在分手前她终究没能学会这门手艺。
她蠢蠢欲动,精力充沛,但挣钱之外她对未来并无计划。第二段恋情结束时她已身怀六甲,她决定生下孩子。22岁的未婚妈妈蓝蓝即将成为河北沧州一家工厂的女工。火车上遇到的歌厅妈咪,劝蓝蓝去天津跟她干。她拒绝了妈咪,在工厂呆了半年后她又拨通了妈咪的电话。“我做事喜欢留一手。”她说。
“不是我脸皮厚,我不怕。”她提醒我在农村老家,她在打工几年后已经从一个优秀、能干、懂事、谁娶上烧高香的姑娘变成一个被人戳脊梁骨的未婚妈妈。“都已经那样了,你怕能怎么办?”
歌厅的公关小姐并不提供性服务,但立身之技是要么会唱,要么能喝。蓝蓝不会唱歌,只能被客人灌酒。她见歌厅旁边的洗浴中心,按摩师傅一天下来也一百多,跟她挣的一样。她觉得这比歌厅小姐强,无非出力气,却不用喝酒。她是打小干惯农活的姑娘,出点力算什么呢。便跑去跟人师傅学按摩。
那是她记忆里开心的3年,她觉得自己在凭力气赚钱。10年前日入百元收入不算少,但她发现有个在北京洗浴中心的朋友能挣10倍,她也想多挣。在沈阳租房时母亲来看她,母亲说这楼房真好,冬天不用烧炕也暖和。她想给母亲在城里买个楼房。
“入行有心理障碍吗?”
“没,一点都没有。”她说,“好多人问这个问题——有没有思想斗争,怎么说服自己的。那些大学教授们总问。我真的需要钱,我知道缺钱的痛苦,我女儿上户口上学都要花钱,我不能让我孩子缺钱。我入这行没有什么斗争,每个人心里是有衡量取舍的。这不是走投无路,而是在我能选择的前提下,最好的选择。”
2014年,蓝蓝的团队用一年时间,通过访谈37位女性工作者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探索70年代生进城女工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结论写道:
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之所以从事性工作,并非是自己个人的因素主导所致,原生家庭的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社会对贫困的歧视,生存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性别歧视等等,这一切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才让她们选择了性工作。
朋友把蓝蓝介绍到北京的一家“中档的”洗浴中心。新工作让她感到愉悦,她发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实:在她告别两任男友并生下一个孩子后依然对男性生殖器感到陌生。洗浴中心的培训和工作让她第一次完整看清男人的身体,以及第一次高潮体验。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她注意到我的惊讶,“我们受过培训,整个过程中你就要表现得很投入,假作真时真亦假,在那里大家是纯粹的性关系,我们也是人。”
这份工作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她的天性。我们聊起性爱观,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性与爱可以完全分离的主张,我则认为很难分那么清。
“你还是没想清楚。”她以一种孤独的得道者口吻迅速终结了这个话题。
洗浴中心门口时常有宝马车光顾。那些老板们体面绅士,她觉得他们的言谈举止也并不讨人厌。我问她每天需要接待多少人,她笑笑说自己以质取胜而非次数。把客人服务得满意了,就会加各种服务,运气好的时候——比如有人请客,他们不看账单也不在乎加钟,一单生意能赚到两三千。
我问在那里什么会影响到赚钱,“技巧、耐性和态度。”有时夜里两三点钟来人,也得站成一排挤出笑脸供人挑选。惟一不爽是,不能拒绝客人。“我性格很直,但绝对能收住。”她说,“我的目的很明确——反正就这几十分钟,我憋住了,走了再骂你,好几百块钱呢。”
她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值班时跟姐妹们坐在一条极细的长凳上,挺胸抬头。趁经理不在,她就溜到旁边的一个小仓库蜷着眯会儿。听见脚步声赶紧起来,以免被经理看到扣钱。那3年里她过得紧张。最难捱的是半夜三四点钟的生意,从床上薅起来,困得睁不开眼,也得挤出笑脸接受挑选。“选我吧,选我吧,”她用笑容和眼神挑逗来客。她仍然希望被点到,虽然她很困。她永远是个努力的人。生意不仅仅意味着钱,也能证明实力和地位。
“我加钟很厉害,”她说,经常有客人完事后加钟,再加一个钟。她嘴甜,会哄人开心,即便现在有些发福,也不难看出她在一个女人最好年纪时的妩媚清爽。“如果我能挑选客人,或者管理不那么让人紧张,那真是个好工作。”
“赚钱有目标吗?”
“有,存够20万吧。这很容易,没多久就到了,继续干。”蓝蓝说,天天看着存款的数字往上涨,“特别开心。”只是她依然舍不得花钱吃喝,她往家寄的钱也并未显著增加,她害怕家人知道。她给家里的说法是“按摩师”。姐姐曾到天津探望她,看她在洗浴中心,有板有眼地给客人捏脚捶背。
车在路上开了半个小时,绕了点弯路后停到路边马路牙子上。我们兵分两路,蓝蓝带着L和我进了沙柳路,这是一处回收垃圾的城中村,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蓝蓝瞅瞅道路两边,径直推开一家门口挂着“足疗”字牌的小屋的玻璃门。屋子很旧,没有暖气。磨得光滑的水泥地面上有些坑洼,但屋子收拾得整洁利索。一个长发女人偎在被子里,电视里放着警匪剧《案发现场》。旁边摆着一盒宫炎康颗粒。
蓝蓝推门的熟练程度让我以为这是她的老熟人。一进屋她就坐到她的床沿上,并吩咐我们俩照做。后来她说如果你站着就表明你分分钟要离开。不,她们不仅仅是来发安全套和宣传单的,她们要好好聊聊,当然得坐下来。
被子里的女人坐起身来,似乎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有些茫然。我才发觉她们并不认识。“我身体挺好的,没嘛事。”女人怯怯一笑,婉拒了陌生人的好意,“我就按摩,不做别的服务。”她的双颊露出类似高原红的颜色,她表示过几天会回甘肃,在老家她有两个孩子。

在一个大型货车停车场附近,一些发廊的性工作者在等客
“你知道公益么?”蓝蓝问她,就是不收费的服务。
“不太清楚。”
“知道汶川地震吗?”蓝蓝提示她,就是不要钱的帮忙。“我们想帮助你,就身体上的事,检查要去正规医院,不能去小医院。或者以后也可以到我们这里做检查。”
“对,我都看了。以前你们的人好像也来过。”
“那你说你不认识字。”蓝蓝轻轻捏了下女人的大腿,嗔怪道。
“有些字不认识,朋友念给我听的。”
“为啥没上学?”
“上学不方便。”
从我的两位同行者的表情来看,一个出生于1986年的女孩竟然没有上学着实让她们有些惊讶。蓝蓝的双手松弛地握在腰间,一条腿搭在床沿上,这种略带强势的亲近姿态在十几分钟后似乎收到了效果。女人坦承她有时瘙痒,还有其他一些小问题。
门外马路对过,拾荒者大声喊着话,用力将分类好的破烂装上车。砰砰的玻璃瓶子摩擦、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和男人的吆喝搅在一起。
临走前,蓝蓝跟女人互加了微信,并重申了她的组织的宗旨,“以后要痒弄不清楚了,打电话告诉我们,”她说,“给你省钱。”
这条街上几乎每家都是这样的按摩屋,床是这些简陋足疗屋里共同的最大家具。蓝蓝一次次熟悉地坐上去,放松地伸开腿搭在床沿,就像搭在她东北老家的炕头那样自然。她说要跟对方保持45度角,侧点身,大约一臂距离。这样的距离和角度是最好的,蓝蓝说,你一伸手就能碰到她,有时候身体的碰触比你说一些话更有效果,特别是对方身体有异味或者患上梅毒,这时你紧紧握住她的手,让她知道你跟她站在一起。
蓝蓝喜欢身体接触的交流。后来在NGO负责人开会时,我惊讶于这些三四十岁的男女们竟如孩童般互相挑逗身体,堪称肆无忌惮。蓝蓝说,他们都是同性恋,她很喜欢跟他们这样放肆地逗乐。
这条街大约有几十个类似的“足疗店”,巷子深处的几户年纪大的已经是蓝蓝的老熟人。在过去4年里,她跟她们建立起一种老姐妹的关系。你能从她们的眼睛里看出来,她们想念她。她们抓住蓝蓝的手,问她是不是升官了好久没来。
“最近出国了吗?”她们问蓝蓝。
“5月份去了瑞士,有钱,比美国还好。我要是会英语就黑那儿不回来了。”她时常把一些英文单词挂在嘴边,但她说自己的英语都是开会时跟人学的。比如在华盛顿游行时她高喊的口号:Sex work is work!她把work发成了worker,也通。
“国外这行生意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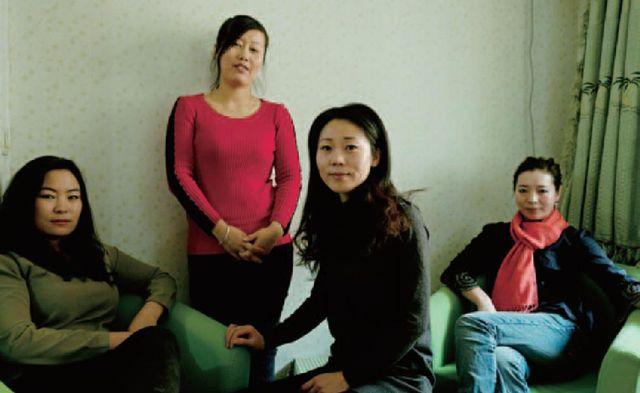
蓝蓝(左一)和她的同事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站街的一次也就三四百块钱,人家国外都得划线。”
“挣那点钱还去干啥啊。”
“到那的都年轻的,你还得找人钱呢!”蓝蓝挤兑她们,“人家那儿没民工呀!”
有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位头发染黄、低胸、穿着黄毛衣的中年女人听到动静过来串门,“求你了别打扮得那么洋气!”蓝蓝向她打招呼并介绍我,“这是我们的志愿者,来做研究的。”
“做研究好啊,你也给咱呼吁呼吁,让他们别再抓小姐了行吗?”女人毫无防备地看着我。那是一种年长者无能为力、让人心生怜悯的眼神。她大约是我在这条街上见到年纪最大的小姐,但她有一种别样的明亮,一种超越油盐酱醋的精气神。后来蓝蓝说,她叫A,估计已经快60岁了。A挣的钱多数寄回老家,养活她那三十多岁的儿子一家。A的女房东感慨说:这个地方不用长得好,能躺下就能挣着钱!
A把蓝蓝拉进自己屋里,低声告诉她自己最近做了缩阴手术,“客人反映特别好,一天能多干两个活儿”。她们又聊起养老保险的问题。A最近买了款商业保险,只管大病医疗,每年要交一万多。“太贵了!”蓝蓝说,她建议A上老家找个能帮着补缴社保的公司,这样到60周岁后就可以拿到政府发的养老金。
很长一段时间,她们认为她就是“发安全套的”。她开始研究她们关心的问题,健康、保险、养老。混熟后她甚至教她们如何让客人“出得更快”,以及把安全套藏在嘴里,在给不愿用套的客人做口活时悄悄戴上。“我要让她们知道我们是行内人,跟我们说话不必有忌讳。这些都是职业技能,她们学会了保护自己的筹码就更大一些。”
让她头疼的是依然有姐妹不愿用套。并非防治艾滋宣传不到位,而是警察在打击卖淫嫖娼时常拿安全套作为证据。“除非警察抓住了嫖客和小姐现金交易的现场,才可以判定嫖娼成立。但这很难。”蓝蓝说,法律没有认定两个陌生人发生关系违法,那么即便警察冲入两个赤身男女所在的室内,也不可认定两人违法。
她把律师请到办公室,给小姐们讲这些。但她们依然被抓走,警察从垃圾篓翻出安全套,嫖客们低头认罪,连同被他们指证的小姐们一起被强制收容。她很愧疚,去收容所探望,她不敢看姐妹们被剪短头发的模样,她们告诉她这里连上厕所都要受到限制。
“培训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实操作不这样。懂了吗?法律只是条款,现实里行不通。”她的控诉好像是自嘲,“她们没偷没抢,干嘛受那么大罪,不就是凭着自己身体挣点钱吗?”她说从未庆幸自己早已离开这个行业没被抓。“我曾经都想过,如果我被抓了,就上里面作死把收容教育制度取消!”她看着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表示领悟到这种想法的喜剧效果,“我真的受不了这种状态。”
我们正坐在一家蓝蓝熟人的店里,一个二十来岁穿牛仔外套的年轻人忽然出现在玻璃门前,他的右手搭在把手上,准备推门进来,又看了看坐在里面的我们,转身走了。显然,我们耽误人家生意了。
太阳下山前,另外一路的两个人跟我们在L的车里会合。她们表示此次外展效果不佳,她们没勇气打破寒暄之后的沉默,安全套也没有发完。“我好累,”蓝蓝重重靠倒在后排座位上,没有立即点评下属们的表现,“笑了一下午,这儿都是酸的。”她指指颧骨。
第二天早上9点钟在北京有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订火车票时蓝蓝说订个晚点的,“我知道他们这种会,一上来肯定是领导致辞什么的,可以多睡会儿。”我们终于差点迟到,打车到火车站时距离开车还剩15分钟,我跟着她一路狂奔,取票、安检、进站。她不顾一切地插队,几乎要推开所有挡在面前的人。她像一道黑影闪过各种关口,我被远远抛在后面。要知道她脚底下是双至少8厘米的高跟长靴。我会一直记得那高跟在天津站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来的那阵急促有力的哒哒声。
我们在开车前6分钟坐到座位上。“每次都这样,我都习惯了。这种时候是顾不得风度的。”她说自己有次去华盛顿开会,没带平底鞋,走得累了索性脱掉高跟鞋,光脚大步踏在华盛顿的大街上,“没素质就没素质吧!”
半小时后我们到了北京南站,我们决定搭乘地铁前往会场。大概赶上了早高峰的尾巴,我问挤着臭烘烘的地铁去开联合国的会是什么感受,她笑起来。“其实我最早对联合国期望很高,但后来熟了就知道也就那么回事。永远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蓝蓝第一次跟NGO开会时还没离开洗浴中心。有天上班她遇到在酒店门口发放安全套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来二去跟人混熟,对方邀请她去办公室玩。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办公室工作”:每人一台电脑,打打字,有人在玩游戏,朝九晚五,每月两千多块钱。噢,这就是办公室生活,她想有一天要是离开洗浴中心,挣点工资做这个,我也满足啊。后来爱知行带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开会。会议上某学者关于性工作者与艾滋病防治的发言让她感到愤怒。
“你讲得不对。”她站起来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里面干过我怎么不知道。”
全场哗然。
后来她随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人去海南做培训,她的身份是同伴教员。在海口附近热带雨林的小别墅里,北京来宾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县长秘书长对我们点头哈腰地敬酒,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我知道别墅和酒菜都是可以买来的,但那种感觉——好!不!一!样!啊!”她一字一顿地向我强调她的喜悦,“长这么大从没被这样过,我就见过村长。”回京后她跟洗浴中心的朋友分享这段经历,朋友说她傻:去海南机票才几个钱,耽误三天能赚出多少个机票钱呐。
“她们不懂。”她总结道。
这是个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援助问题的会议。与会者跟蓝蓝一样,是各类NGO的负责人,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很多人一张口说话其他人便开始点头,这表明他们也很熟悉彼此的观点。每个人的发言都如此流利,各种名词的变换组合,你很难辨识发言者的表情背后是何种情感。
“我觉得这个会并没有太多信息增量,因为没有观点的交锋与碰撞,所谓会议就变成自说自话。不识趣的、爱吵架的都已经被弄走了。”蓝蓝说。但我好奇蓝蓝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会。她说有3个目的:1,听有用的点;2,认识人,扩大知名度;3,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一些词语组合”。
更重要的是,会议主办方会有项目资源,“你不来就不带你玩啦。”
文山会海是蓝蓝最大的敌人,发言稿和PPT总让她焦虑得不能入眠,但这也让她完整习得了一种至少看起来理性、逻辑的表达方式。在小组讨论时,她的发言并不多,但你知道她能很自如地表达她的立场。如何让小姐避免处罚?她一直在问这个,但没人能回答她。主持人点名让她做小组讨论的总结汇报人,这说明她在这个圈子里已受到充分认可。她是个合格而讨人喜欢的与会者,别人发言时她还能拿起桃红色的小米手机给天津的下属们分派任务,她的总结汇报表明她没有漏掉重点。要么是这个只上到初中一年级的女人背后下了不为人知的功夫,要么就是这种制式化的会议特别能锻炼人。
午餐时一位年轻的圆脸姑娘递来名片,看来她是圈子里的新人。“我一直好奇,”她交叉双腿略微忐忑地立在蓝蓝跟前,“警察会占小姐的便宜吗?”
“你觉得呢?”
姑娘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你觉得有的话那就有呗,”蓝蓝以一种含糊而高深莫测的口吻答道,“很多时候她们是希望被占便宜的,她们觉得这样就可以不被收容了。”
过了两天,另一个性工作者的研究工作坊也邀请了蓝蓝,但我被挡在门外,一位与会者认为记者对NGO是危险的。蓝蓝对这次会并不很满意,她希望呼吁警察不要把安全套作为抓嫖证据,因为它影响艾滋病的预防。而其他人认为应抨击警察在对性工作者执法中的违法问题,这在她看来过于激进,她不想冲得太猛。“在中国社会,一个NGO你能长远发展,必须有策略,你不能锋芒毕露。你把容易的和难的混在一起,那容易的也不见得能达到。”
在涉及官方的问题上她是保守派,或者说她在坚持自己的实用主义。她避免跟官方发生冲突,也做过违心的事。机构成立初期,官方迟迟没有给他们项目。后来信爱终于得到一个检测的项目后,蓝蓝让丈夫从机场免税店买来6瓶剑南春酒,送给有关负责人。“这点东西人家根本瞧不上,但送礼起码可以表示我不会跟你对抗。”
一盘大菜里摆盘的那朵萝卜花
蓝蓝下定决心离开洗浴中心是在2007年,此时她的小姐身份和敢说敢言在公益圈内已小有名气,各种名目的会议都愿意邀请她来参加。“我就像一盘大菜里摆在盘子边上的那朵萝卜花,”她说,“但萝卜花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能浪费机会,要一次次给别人增加对我的印象。”
当她跟与会的几个帅哥眉来眼去时,爱知行的人把她拉到一边:这几位都是艾滋携带者,你跟他们在一起要戴套。
她知道艾滋病,在她想象中艾滋病人应该是头长疮脚底淌脓那种样子。原来真正的艾滋病人却啥也看不出来。她想起接待过那么多客人,有不少是没戴套的。
她立即去宣武医院做了梅毒和艾滋的化验。在等待结果的那个星期里,她像只霜打的茄子心神不宁地杵在候选小姐队伍里。她发出的抗拒信号也收到了效果,没有客人点她。
在洗浴中心的两年多时间里,她的存款已经达到近五十万。她默默地做着打算:如果结果是阳性,先给母亲在城里买个房子,然后去海边旅游。她喜欢百合,那么她的墓地应该摆满鲜花。
结果是“阴性”。她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是时候离开了。她觉得自己比那些防艾组织的人聪明,那么就更有资格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游戏。故事到这里似乎应指向一个有志女青年弃暗投明顺理成章,但命运并没有安排她进到某个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她回到天津,找到几个按摩的姐妹帮着做兼职,宣传防艾知识。但在那两年里,除了从其他组织拿来的一些安全套外她几乎一事无成,她不知道如何写计划书,那么就没有项目,就没有经费。她开始准备后路,默默捺下性子啃了整整一年的书本,又找人办了个假高中毕业证明,她考下了导游资格证。她向我强调这个证书的通过率是十分之一。蓝蓝想着手里的安全套发完那天,就去当导游,她从来不会坐以待毙。2010年5月的一天,她正带着游客在中央电视塔下的一个水族馆游览——那时她每周能赚到“数千元”,忽然接到电话,一位开会时认识的台湾教授帮她撰写的计划书,成功申请到香港乐施会的一笔资金。这是信爱的第一个项目,她立即决定放弃导游事业。作为项目负责人,她也给惟一的正式员工即自己设定了工资标准:月薪2400元。
她每年还去审核她的导游证,这样可以省去景点的门票钱,只是她总是忘带。如今她的导游朋友们已经作为领队带团出国,她则往返于各种国际会议。母亲早已住进她买的楼房,只是她仍然不知如何跟村人讲述让她骄傲的女儿的职业,“做妇女工作的,跟妇联差不多。”
我们在信爱的办公室聊着天,我注意到几天来结婚钻戒一直戴在她的左右无名指上。她说结婚后就没再摘下来。6点钟蓝蓝的丈夫准时出现在楼下,他开车过来接她回家。那是她还在天津做按摩时认识的东北老乡。从北京回到天津后蓝蓝找到他,两人2010年结婚。她没有告诉男人自己的过往,他也从未问起。她常跟男人说随便找小姐她不会管。男人说他才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