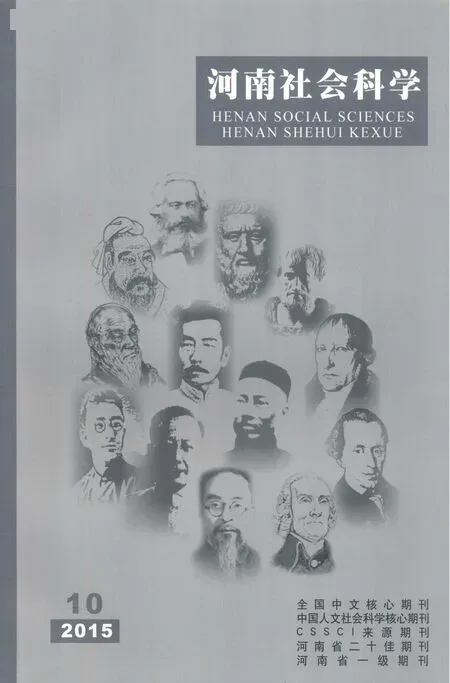社会的可计算性与人的自由
刘力永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
伽利略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世界是一本以数学语言写成的书。如今这本书的内容越来越繁杂,其中社会的可计算性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存在的根基,甚至人的外在长相可以用“颜值”来量化,内在情感能够用数据加以分析,社会生活逐渐变成一种依据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过程。关于这种改变,黄仁宇曾经使用“数目字管理”的概念来标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现代社会的一切可以加加减减,都可以在数字上进行处理。社会可计算性的效果,正如卢卡奇所分析的,人们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所做的那样[1]。对于社会可计算性的研究,在今天的时代有着特殊的韵味。原因在于,如何摆脱以可计算性为核心的“第二自然”加之于人的“虚无感”“无力感”和“宿命感”,在实践上探索一条通向生活世界的自由之路,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计量、计算与社会的嬗变
计量、计算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公元前3000年,信息记录在印度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计量和记录一起促成了数据的诞生,它们构成了社会的可计算性最早的基础。然而早期文明的计量方法不太适合计算。阿拉伯数字从12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直到16世纪晚期才被广泛采用。最终让阿拉伯数字广为采用的是复式记账法的出现。复式记账法是一种高级的数据记录方法,它的使用奠定了阿拉伯数字此后不可取代的地位。建立在使用阿拉伯数字基础上的算术也因此赋予了数据新的意义,因为它现在不但可以被记录还可以被分析和再利用。到了19世纪,电流、气压、温度、声频之类的自然现象也得到了测量和记录。
通过把模拟数据转换成0和1表示的二进码制,计算机成为新的计量、计算工具。计算机的发展使得数字测量和存储设备更加先进,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可计算性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文本实现了数字化,接着图像、视频和音乐等内容也实现了数字化。伴随着智能手机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对个人的生活行为进行数据处理也变得更加容易。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经历和情感逐渐被转化为数据。数据化代表着人类认识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将世界看作是信息而不是原子,看作可以理解的数据的海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审视现实的视角。[2]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说道,把各种各样的现实转化为数据,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也许是新奇而有趣的,但在不久的将来,这将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如同吃饭睡觉一样[2]。
社会的可计算性的最突出特征就是量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原则,对量的强调取代了对质的要求。在乔治·里茨尔看来,麦当劳的模式是社会可计算性的典型代表,这种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全部社会生活。麦当劳强调产品的量而不是质,金色拱门的标志在夸耀着由麦当劳快餐店所售出的数以十亿计的汉堡包。同时,麦当劳强调提供餐饮的速度,它一度曾力求在50秒之内做到供给一份汉堡包、雪果和法式炸薯条。对于量的强调还体现在对于精确性的要求,它要求对快餐生产的每一个要素都要加以测度,确保每一个原坯麦当劳汉堡包的重量是1.6盎司,不多也不少。10个汉堡包所含的肉的重量正好是一磅。烹制前的汉堡包测度的直径恰好是3.875英寸;圆面包正好是3.5英寸直径。麦当劳快餐店发明了“脂肪测量器”,以便确保其常规的汉堡包肉馅的脂肪不超过19%[3]。
社会的可计算性中所蕴含的对于速度、规模和精确性的强调,已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篮球比赛的变化,球迷想从篮球比赛得到的与从麦当劳快餐店得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亦即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数量。越是快速、比分越高的比赛越是可以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利润。24秒计时制的确立就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投篮机会,使篮球比赛的投篮节奏更快。再如,政治的可计算性,政治家特别在意民意测验的排名,民意测验影响着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的性质,政治家关心排名甚至超过了对政策实质的关心。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休闲旅游,特别是团队旅游的组织方式。团队旅游强调观光景点的数量而不是旅游的质量。当旅游者观光旅游之后,他们炫耀最多的是所看的景点、所拍的照片、所录的视频的数量。然而旅游者走遍全国看到更多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东西而很少有什么差异,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也日渐变成了事实[3]。最让人感慨的例子是科学管理。泰勒的科学管理力图将与工作有关的每一样东西均转化为可以量化的因素。科学管理不是依据工人“从实际工作所获得的经验”,而是力求形成关于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所能完成多少工作的精确尺度。凡能还原为数目的每一件事情都经由数学公式来加以分析。为了使工作量增加四倍,泰勒对最具生产力的工人亦即一流的人员的操作加以研究。他把他们的工作分解成基本的要素,然后用计时表把每一工作步骤加以计时,精确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秒[3]。在泰勒制的科学管理中,人的特性直接地被抽象化为数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人也因此彻底地和自然物体没有什么区别,成为可以任意分解和组合的客观对象。
二、社会可计算性的因和果
社会的可计算性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显著的、主导性的特征,根源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即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形式。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商品之间普遍交换的基础在于其中凝结了抽象的人类劳动。所谓抽象的人类劳动,就是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4]。马克思接着说,这种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不过商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对人来说,劳动时间不仅是他出卖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客体形式,同时作为主体的生存形式,人因此被简化为抽象的数量符号。
卢卡奇揭示了社会的可计算性形成的客观根源,它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支配作用有着内在的联系。劳动可以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到越来越精确的测量,这一点对于社会结构的演进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劳动过程从手工业协作、手工工场发展到机器工业阶段,合理化不断加剧,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多地被清除。一方面,劳动过程逐渐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合理计算的基础,起初它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整个人格相分离,成为可以计算的客体和合理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1]。社会的可计算性或者社会的合理化导致客体和主体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客体两个方面因此都失去了各自的完整性。
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社会的可计算性成为一种吞噬一切的力量,在这股汹涌的潮流中亦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社会的可计算性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第一,生活的同质化和差异化之间的对立。在前文分析的麦当劳的案例中,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矛盾。麦当劳强调数量而不是质量,它制造出数量的幻觉,把生产过程和服务过程还原为数字,其结果就是消除差异,在全世界不断造成同质化。这种缩小差异的倾向体现在快餐模式向各种民族食品的扩张方面。事实上人们很难在一家民族快餐连锁店中找到真正别有风味的食物。这里的食物都被合理化和调和化以便能为实际上所有就餐者所接受。具有悖论意义的是,虽然快餐店向许许多多的人做出许诺在那里可以体验民族食品,实际上人们在那里吃到的食物却已经失去了许多特色[3]。
第二,空间的占有和生存之间的对立。《货币哲学》的作者齐美尔认为,现代城市是为了计算金钱的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在多维看来,购物中心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是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空间,它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快乐消费的错觉。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共同体,在这里,贫穷是缺席的,社会分化与古怪反常的现象也被抹去了。购物中心被打造为一个纯净的环境,是消费者逃避现实的保护装置:购物成了戏剧,成了生活方式,消费者可以陶醉在令人迷惑的超级空间中,以至于让购物中心用一种“地方感”取消了“一种历史感”。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一种可以无所顾忌地开心花销的对地点与时间的幻想[5]。不言而喻,购物已成为市场经济掌控城市空间的中介。这样一种影响可以从数量上获得证明。例如17%的美国劳动力受雇于零售业,而商场的数量则超出基督教堂、犹太教堂和各类寺院数量的3.6倍。而在英国,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8.7倍。更有意思的事实是,购物本身已成为一种调节市场变化需求的社会变化的晴雨表,最终,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别无可为,只有购物[5]。空间成为用来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消费者知道这些限制,但却乐于接受它们。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是主动并有意识地与之合谋的,他们为放弃理论上应有的自由做好了准备,以便去体验消费主义不得不提供的有限的自由和欢愉。消费空间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把购物当作自由来体验,正如佐京所指出的:我们感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舞台,我们在上面演练选择的自由、自我激励的自由,并同时逃避市场经济的归化。购物一方面提供自由,而另一方面又夺去自由:“购物就是消费我们自己的生命,可是却很少能给我们带来满足。销售的商品越来越多但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们真正想要的。”[5]斯蒂芬·迈尔斯认为,空间的商品化改变了人们对存在的认知,社会生活大概只与占有有关,而不是为了生存,围绕在我们周边的形象持续提醒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唯一合法的生存方式只能从消费开始[5]。城市的空间变成了一个盛大的消费的对象,它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精确的计算使消费得以有效地最大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它们的独特性。各个地方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制造了昙花一现的唯一性、差异和本地化[5]。因此在面对生存空间转化为消费空间的情况下,城市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其本真性就是一个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第三,社会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对立。可计算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但是也产生了明显的不合理性。为了种植符合麦当劳统一标准的土豆,过度使用了化学肥料和农药,土壤、水因此受到了污染。此外,在麦当劳的餐厅里,顾客排队购买,制作食品的工人们在装配线上工作,他们似乎成为装配线的一个组成部分,顾客和工人仿佛都陷入了麦当劳化的铁笼之中。当麦当劳化主导社会越来越多的部门时,人们将日益无法“逃避”这一铁笼的控制。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案例充分地体现了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间的尖锐对立。尽管投产前测试表明,福特斑马牌汽车燃油系统在车尾受到碰撞时容易破裂,但由于价格昂贵的生产斑马车的装配线机械已经安装完毕,福特决定照样投产而不作任何改变。福特的决策依据的是一种定量的比较。公司估计上述缺陷会导致180人死亡和大约同样数目的人员受伤,对他们所赔付的价值为每人20万美元。于是,福特公司得出的结论是,用于死亡的总成本比用于修正该项缺陷所需成本平均到每辆车上是少了11美元[3]。虽然从利润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较是有意义的,但从牺牲人命和以低成本高利润的名义致使人的肢体伤残则是一种完全没有理性的决策。这种冷酷的计算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不能不说这是对人类理性的一种辛辣的讽刺。
三、数据拜物教与自由的可能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社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今天“庞大的商品堆积”已经转换为“庞大的数据堆积”了。过去不可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数量化外衣。我们越来越依赖数据,似乎成了数据的奴隶。社会的可计算性因此表现出了拜物教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从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演化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数据拜物教。关于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指出,就商品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种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4]。劳动产品成了商品之后,变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于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换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4]。对于人来说,拜物教意味着,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不是他们控制这一活动,而是他们受这一活动的控制。
商品拜物教所导致的非人化或自由的丧失,数字世界也未能幸免。人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被转化为数理量值,并用数学的方法加以建构、描述和公式化,于是人本身与桌子、铁锤、机器、数字没有了根本区别。在这个系统之中,人才是现实的,在这个系统之外,其他特性是多余的、非现实的。这个数字化的世界表现出与自然世界同样的规律,竟使人无法觉察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人的社会活动造成的结果。当代人越发无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缺乏完整性、能动性的存在,自由显得如此稀缺而更加令人向往。难怪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感叹,大数据预测可以为我们打造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社会,但是却否定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能力[2]。
思考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它批评世界的数理化的趋势,主张回到前现代世界中,以求恢复人的本真存在,重新获得存在的自由和完整。海德格尔的态度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他对整个世界的数理化充满忧虑,认为这个世界已被连根拔起,“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赎”。他希望回到本真世界,人与世界像农民与大地、铁匠和锻造之间一样,流露着亲密的情意。卢卡奇以辩证的方式,精彩地描述了现代人在自然和文明之间挣扎的这种命运:他越是占有文化和文明,他就越不可能是人。人的内心就越是充满回归自然,重新成为自然的倾向和渴望[1]。社会的物化与个体对自然、自由的向往相反相成,这正是浪漫主义拥有广泛影响的内在缘由,例如今天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旅游的热衷。捷克哲学家科西克认为,浪漫主义者否定了科学的进步作用,使人道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特有问题的研究焕发出新潜能的,恰恰是现代技术、控制论、物理学和生物学。它重新提出了人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变更了创造性活动与非创造性活动之间的界限[6]。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则肯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影响,认为人类最伟大之处是运算法和硅片也无法揭示的东西,因为数据也无法捕捉到这些。如果所有人都诉诸数据,都利用工具,那时人类的无法预测性即直觉、冒险精神、意外和错误等,反倒可能发挥重大作用[2]。
卢卡奇指出,近代以来,数学成为认识的理想工具,借助于数学的工具性力量,所有的现象都可以成为精确计算的对象,进而能够探求各种现象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使用各种数学的、理性的范畴来解释各种现象,数理方法成为哲学、把世界作为总体认识的指导方法和标准,成为把握现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卢卡奇进一步分析,这种方式的后果就是,现实越是彻底地合理化,它的每一个现象越是能更多地被织进这些规律体系和被把握,预测现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应地,主体的态度将变成纯直观的,只是被动地接受适应这些规律。主体对这一过程采取纯观察员、纯实验员的态度[1]。在哲学史上,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命题归根结底是这种直观态度的反映,即所谓的现象和自在之物、必然和自由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二元对立。于是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悖反特性:要么采取决定论的态度,完全服从客观规律,放弃主体的自由意志;要么采取唯意志论的态度,不顾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把自由当作是一场刺激的冒险或者爽快的为所欲为,最终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种“虚构的自由”。
要想克服这种直观的态度,卢卡奇指出,只有当哲学通过对问题的完全另外一种提法才是可能的[1]。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实现了从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到主体客体辩证统一的范式转换。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7]。总而言之,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忽视了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之意义和价值。美学家席勒说过,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有在成为美学的时候,才能不被扼杀。其实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只有实践才能够克服主体的分裂、客体的僵硬和不可理解。只有在实践的视野中,物的外衣下人与人的关系,数量化的外衣下质的活的内核,才得以呈现出来。马克思通过提出实践的观点,把哲学对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引向了历史的、现实的领域,找到了如何回答人的存在意义问题的真正钥匙。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在恩格斯看来,以实验和工业为主要形式的实践不但可以驳斥以不可知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观念,而且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了解客观实际和内在规律,进而实现控制和利用它们,重新获得主体的自由。或许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总有那么一天,在实践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将摒弃数据拜物教的束缚,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使冰冷的数字世界复归于合乎人性的生活世界。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M].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英]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M].孙民乐,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6][捷]科西克.具体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