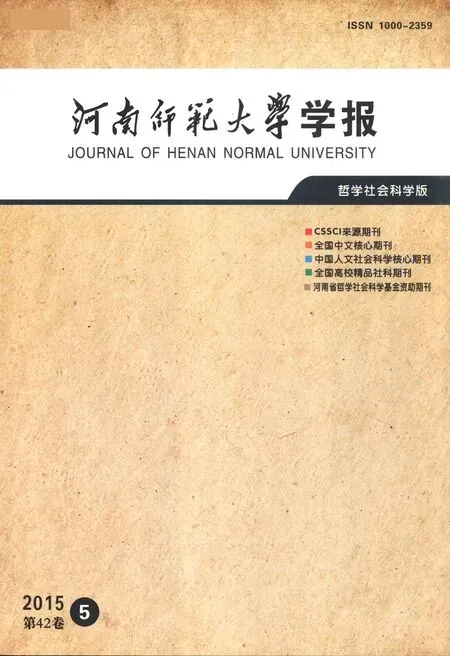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
岳 杰 勇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
岳 杰 勇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作为在总体性层面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特色的一个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之所在,其目标在于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是彰显教育之本质意蕴、满足人类生活需要、推进社会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等的根本要求。鉴于当前的条件和状况,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应切实做到:更新教育理念,拓展教育领域;拓展教育空间,提高资源利用;优化教育载体,注重空间再造;开展教育活动,强化价值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公共人;公共化转型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问题目前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显学。就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此论题的探究正如火如荼,尤以对其重要性、必然性与紧迫性等方面探讨为甚;然而,对作为现代转型之总体趋势的公共化问题却鲜有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从公共性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的基本规定
要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问题,必须首先厘清公共、公共化以及政治教育公共化等基本概念问题,阐明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
西方近代以来,在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神权和皇权等超验想象予以解构并颠覆的基础上,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借由先进生产方式和激进政治运动推翻了近代封建专制制度之理性主义狂妄,市民社会应运而生。在市民社会中,与“私人”“私人性”等西方现代政治学概念相对立意义上的“公共”以及“公共性”概念相继产生。
我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中,没有“公共”这一概念。与西方“公共”概念最为相近的,是“天下为公”之“公”的概念。尽管“天下为公”意指“天下为天下人”,从而与西方的“公共”概念语意近于重合,但二者并非完全同义。主要在于,中国的“公”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的共有和共享,而西方的“公共”概念不仅限于此,而且更注重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一种和谐、互助、交往等关系。事实上,正是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导致了诸多歧义和滥用。对此,著名政治学者章清断言,西方“公共”概念和中国有关“公”的说辞之间的差异,是将西方公共领域概念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引起诸多歧义的原因之所在[1]。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是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概念,意取与“私人”相对之意。基于这一概念,公共性主要是在近代乃至当代民主化社会中所拓展出的涵括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多重公共领域所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在其首要的意义上,即在标识事物所属形式的意义上,“公共性”是一个与“私人性”相对的概念。其中“私人性”标识着资源、财富、空间、生活专属于特定社会个体或群体的性质,其拥有者意味着享有对这些事物或事务具有排他性的占有、使用、处分以及决断等权利。与之相对,“公共性”则意味着共同体中的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社会空间以及社会生活不具有专属性质,强调所有个体对社会事物或事务的共有、共在与共享。同时,“公共性”还具有标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与“集体性”相对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集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一种虚假共同体,人在集体中没有个体权利和自由,一切都服从集体的意志和利益;集体中所有的关系都是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个体之间不具有外在于集体中介的私人关系。因而,说某一个物品或设施是“集体的”,往往意味着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对它都不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具有“公共性”事物的存在,不仅蕴含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的存在,而且还涉及共同体中所有个体在对这些事物的共有、共在与共享所存在的自由、和谐的交往关系,意味着其中任何人能够在充分地表达和自由地行动中对共同体和他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谓公共化,是指是通过特定的实践或机制,使原本属于私人或隶属集体的事物或事务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公共化具有多重维度和含义,但在本文中主要涉及从私人领域或集体领域转变为公共领域的公共化。这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是指一个社会个体借由言行展现自我、相互之间通过交往实现交流与协作的领域。可见,公共领域不仅包括一个由公共建筑或者公共场所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固定边界的实体空间,一种社会公众能够在其间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而且还涵括一个主观空间,一个能够附以诸多外在属性并借以区别于客观的实体空间的范畴,意即人们在其中通过相互交往、相聚、相连及相离构建而成的、对其生存而言所不可或缺的关系域和意义域[2]。
可见,公共生活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方面。因而,公共生活所由产生的公共化,构成公共化的关键环节。在生活的层面上,公共生活主要是由公共生活公共化而来的。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做的社会形态划分,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处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3]。在这一阶段中,人依赖于共同体,人们所过的是共同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颇有见地地指出,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社会生活已基本实现了从传统的共同生活向当今日趋展开的公共生活的转化和演变[4]。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政治国家尚未从群体社会中分化出来之前,人类还不具备公共生活的现实形态乃至于主观理念据以产生的实践基础,因而社会生活只能而必然是共同生活。例如,在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中,公民的生活就是一种群体性的或集体性的共同生活。之所以是共同生活而不是公共生活,是因为在此时的社会形态中,城邦并不是为所有成员所共享和共有,而是专属于为数不多的公民,除此之外的奴隶和女人则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可见,城邦的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不平等,从而不具有公共性。
在西方近代,公共生活领域所由产生的公共化首先是人们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起的。与之相对应,原始形态的公共生活也是人们利益考量的产物,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构建起来的共同体,尤其表现为经济共同体。其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共同体日益扩展,最终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涵括政治、文化等所有社会维度的共同体,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生活由此而生。从社会分化的视角看,这一过程尤为明显。在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长期以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统状况得以改变,随之社会生活便有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分野与对立。作为一个客观规律,这一社会发展规律无疑也适用于中国社会,其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变迁进程与西方社会有着极大的相似度:在延绵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公共交往还是公共生活都处于低水平的不发达状态,社会生活表现为集体生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巩固,公共生活日趋形成,集体领域最终公共化为公共领域。
随着公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影响日渐波及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论题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生的公共化。在这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教育的基本目标、核心内容、实施方法和实现路径,还是教学的载体、方式以及资源与环境,无一不显现出公共性特征,进而在其总体性层面上呈现出公共化特色和趋势。其目标主要在于培养出社会主义公共人。所谓社会主义公共人,就是指具有公共性品质的、能够称其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这里,公共性品质的核心在于公共精神,一种主要由公共情感、公共情怀、公共理性、公共观念以及为公共利益而敢于奋斗乃至牺牲的集体精神等共同构成的崇高精神。公共性品质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友善合群,关注公共生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关注并关心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对国家和社会建设有所贡献[2]。
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公共设施与环境的利用状况、公共文化空间参与建设与公共传播的主要方式、公共交流空间日常参与的广度与频度、公共事件或模拟事件的公众参与度、以公益活动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服务的开展状况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发生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中的这些问题,都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从而在后续的教育过程中有的放矢地予以修正和改进。同时,通过这种教育,受教育者还能够对自身素质进行自我提升,对内在品格进行自我建构,从而完成公共品质的陶冶和塑型,在政治、法律以及道德等方面实现社会化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适应性。
应当看到,将培养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公共人所必备的公共性品质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的目标和目的,并不是肯认并坚持西方语境下的激进社会角色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理论[2]。在某种意义上,二者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中的“公共”,所推崇的是知识分子的高度专业化,所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政治倾向的中立化和客观化,并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和担当精神。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所着力培养的公共性品格,却尤其重视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所忽视的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就此而言,政治教育的公共化意味着拉塞尔·雅各比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消逝”[5]4。
二、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出现与日渐成熟,与私人领域相伴而生的公共领域逐渐兴起。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作为社会公共化之重要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有着极其重大的必要性。
其一,是教育之本质意蕴彰显的根本要求。长期以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认定争论不休。他们纷纷从自己的视角或立场出发,坚持并坚守着自己的观点。其中强调“教育性”的居多,而另有一些学者则重视其“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这些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很少有人否定其公共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大众的事业,是一项社会工程。然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育,所注重的是对用以处理私人关系的个体德性的培养,注重个人的内在精神的修炼和内在品格的完善;在个人与长者、集体、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人对后者的尊重、贡献和服从。可见,这种教育是一种私德教育和奴性教育,所强调的是以上曾论及的在与“公共性”相对立意义上的集体性。这种教育,倾向于仅仅满足于增强主体对社会的消极适应性,所培养出的是萎缩型人格。尽管口头上鼓励社会个体要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由于公共性品质的缺乏,何以能堪此重任?尽管我们早已推行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但鉴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旧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并没有完全禁绝。若不通过公共化改造来改变其残余,要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其二,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随着集体生活向公共生活的转化,人们的生活领域分化出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互独立而又不可分割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私人领域主要涵括私有财产、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私有财产为个人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私人空间为保持个人的隐私与尊严而提供的一个稳固的隐蔽场所,私人生活为社会个体个性、习惯、私德等养成提供一个特异的生活氛围。然而,与私人领域相比,公共领域尤为不可或缺。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6]2。这就是说,每一个个体的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都必然将自己的个体生存奠基于与他人、与群体建立相互联系乃至合作关系之上。换言之,私人领域不仅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也是他们相互之间发生联系与合作进而建构社会共同生活的必要基础。由此观之,与私人生活相比,公共生活更应成为人的生活的基本形态。为了能够形成与他人及集体的良好关系,社会个体在共同生活中作出行动和判断时,“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6]167。这无疑就是要具有以上所述及的公共性品格。而人的公共性品格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长期的公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陶冶、塑造而成的。可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是形成公共型品格进而满足人的社会性的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根本要求。
其三,是推进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已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化为生人社会,私德教育不再完全适应。就其社会结构的构建形式而言,我国社会直至改革开放前,在实质上都是一种熟人基于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家庭,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规范是“非功利性”“非对等性”“出于规定或义务”的家庭伦理,正是由家庭和家庭理论构成了一个“信度较高而风险较低”的共同体[7]。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与深度还很有限,从而对人之公共性品质的要求不是太高,因而传统的德育对社会成员之私德的塑造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社会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日益分化,社会的开放性、交互性日渐提高,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仍拘泥于对私德的培养,就会致使公共领域和谐而有序所需要的公共品质与德性严重缺失。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实现一个公共化转型,推进从“小德育”向“大德育”的转轨,在培育私人领域所需私德的同时,着力于对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品质的培养。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已从集体生活转变为公共生活。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固然中国传统社会在特定的地域和时间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公共生活,但从总体而言,并未形成一个稳固的公共生活传统。有的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就出现过公共生活。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生活与其说是公共生活,毋宁说是集体生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种生活样式中,公共生活并没有现实且有效地发挥其所应有的创权、赋权与维权功能;相反,却在相当程度上沦为理查德·桑内特意义上的一种“形式的义务”[8];而且,这种社会的“公共性”是如此地强劲,以至于深度侵入广大社会公众的私人领地,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归于政治的领域。不难想象,在公共生活严重缺失的社会里,政治对集体生活的过度渗透和大肆入侵势必会使民众对与之外在样貌颇为相似的公共生活持有畏惧情绪和抵制态度。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众的公民意识日渐增强,公民社会应运而生。在公民社会中,要想有效消解集体的相对性并遏制其所引发的各种不良影响,尤其是阻止小团体主义的滋生与蔓延,进而确保集体免于向压制个体自治与发展之异己力量的蜕变,有效措施和可行路径不是片面而畸形地强化集体,而是着力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强化与构建。这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公共化,以培育出公民社会所需的公共性品格,包括公民意识和公民理性。
其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当我们深入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难发现散见于其中的对“公共”的偏爱与重视:其理论视界聚焦于“回到公共的生活世界”,其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改变世界’的公共实践哲学”,其哲学的唯物主义新质则在于“社会共同体价值本位的公共性理念”[9]64-219。当然,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公共生活、公共实践等,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人不过是一种“公共人”的不断生成;而这种人之所以被冠以“公共”之名,是因为他不仅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而且尤其是以公共价值为理想追求的[9]196。可见,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并不在于公共生活、公共实践本身,其人本立场在于“‘公共人’的终极关怀”[9]144。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正神合于马克思的理论追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而是社会主义教育目标实现的必然要求。
三、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鉴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采取种种措施推进这一进程。在笔者看来,主要应着力于如下几点。
(一)更新教育理念,拓展教育领域。思想是行动的基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首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主要是做到:将教育目标从授予知识转变到培养公共性品质;将教育方式从填鸭式转变到情感互动与思想交流;将教育场所从学校扩及整个社会。其中关键方面与核心环节在于对传统的教育空间进行重新角色定位。在传统上,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直承担着“主渠道”“主阵地”的角色。然而,在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受教育者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形成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化,家庭环境、社会风气、大众传媒等无一不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塑造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同时,在学校教育中,中小学由于面临着升学压力,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课程被列为副科而置于次要地位;高校面临着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技能性教育内容被置于重要地位,而思想政治教育又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可见,在当今这种社会氛围下,学校教育越来越不堪全部承担思想政治教育重任。因而,为了弥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不足与缺位,在强调学校教育的同时,应将教育领域扩展至整个社会,并在学校与社会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和科学的角色定位。其中学校教育主要承担起基础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着力于借由对学生公共生活的引导来培养其公共性品质。鉴于此,教育者在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时,不仅注重内容的政治性,而且还应注重其公共性;在教育的实施上,应变硬性灌输和说教为隐性观点表达和价值观引导。而社会之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应承担起传统上学校教育所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主渠道、主阵地角色,最终完成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教育目标。
(二)拓展教育空间,提高资源利用。教育空间是教育实施不可或缺的支撑与依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的首先意蕴应该而且必然是教育空间的公共化,这就是要实施教育空间拓展。在这里,教育空间拓展主要包括两种方式。其一是内涵式拓展,就是指通过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诸要素的充分利用来实现教育空间的拓展。这一方式要求打破传统意义上教育空间内的主元素——包括环境、资源和设施等——所有权、管辖权、使用权等限制,以最大限度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领域,丰富其资源类型和样式。比如,学校、社区以及社会上各种性质及类别的单位,应摒弃其惯常持有的单位所有制观念,将自己管理、掌握的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资源和设施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切实实现空间共用和资源共享。其二是外延式拓展,就是指通过政治思想元素的加入使一些原不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社会空间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比如,在城市中的一些广场、园林、公共艺术场馆等公共场所与设施,融入一些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念等元素。当然,这种融入应避免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化,因而不能强行介入或硬性插入,而应在设计、建造之初就将政治价值、生活理念以及文化偏好等巧妙、合理而自然地渗透于各种物质载体之中,使社会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充分挖掘出公共空间与设施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蕴含与思想潜力。
(三)优化教育载体,注重空间再造。公共文化空间是教育实施的载体。在当前情势下,大众传媒已充斥整个文化空间,在公共领域的构建中发挥着意见整合空间、社会化举措的孵化器、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器以及传播本义的复归[10]等重大作用,从而日益成为影响民众政治信仰与价值观念的主要因素,进而成为其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生成、塑造、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此,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就必须推进以大众媒体为主要主体的社会教育空间的公共化,其重点在于净化并优化网络空间。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再加上对其进行必要监督与管理的缺失,一些媒体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漠视了其所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甚至借由自己的话语霸权来纯粹地为经济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经济利益的崇拜者和追逐者。同时,一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将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抛在脑后,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在网络上为一些商品品牌做宣传;有的甚至为了赚取佣金而成为一些反动政治势力的代言人。这些存在于大众传媒领域的不良现象,无疑是将其领域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是自己的经济方面,是大众传媒公共化的巨大倒退。针对这些问题,宣传、教育、文化等相关管理、监督部门应通过颁布并实施管理条例、加大稽查与惩处力度等措施,来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监管。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部门的职责不仅限于管理和监督,而且还应承接起学校曾经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责,勇于并善于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充分利用公共文化空间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来实施教育。对具体的教育者而言,必须学会公共文化服务和大众传媒的种种手法与技巧,将自己所掌握的政治思想、观点与立场传授给受教育者,并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提升自己,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与能力。
(四)开展教育活动,强化价值引导。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公共交流、公共服务、公共参与等宏观公共领域的活动。通过公共交流,不仅有利于促进和谐、互动的公共教育空间的营造,而且还能够借由人际交流实现个人观点的公共化呈现;借由以公益性组织服务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活动,不仅可以实际地造福于他人和社会,而且还能够使民众在现实的实践中感悟出善行的真谛,进而养成关心他人、关注社会的良好利他行为习惯;透过公共参与,不仅有利于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一种集体的合力,而且还能够使参与者参悟自由与平等,形成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可见,上述活动的积极开展,不仅有助于丰富并填充人们的生活内容和实践维度,构筑他们的主观的精神空间和理念的价值世界,并为社会主义公共人所必备的公共性品质的形成营造氛围并创造条件;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公共生活方式,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进而将其塑造成关心并实际贡献于国家、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公共人。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微观公共领域,开展微观公共领域活动。一般而言,与关注宏观层面的宏观公共领域构成互补的,是着重关注微观层面的微观公共领域。这一领域聚焦于通过协作与合作解决问题、促进并提高创新和创造力、提升公民教育和公共参与、为弱势群体创造并提供表达管道与机会等[11]。可见,微观公共领域不仅是公民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的重要管道,而且尤其是公民自我教育的重要载体。就当前而言,在微观公共领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要为社会公众供给社团生活机会、传授用以公共舆论表达和传播的技术、营造公共讨论和协商的社会氛围和条件,从而不断提高民众社会参与能力。
[1]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M]//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93-194.
[2]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4]张康之,张乾友.从共同生活到公共生活[J].探索,2007(4).
[5]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晏辉,等.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5-37.
[8]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9]贾英建.公共性视域——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许剑.新闻媒体与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构建[J].新闻大学,2003(1).
[11]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中文版序6-7.
On the Public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UE Jie-yong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The public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ideology and politics, as a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pub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eneral terms,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hich aims at cultivating socialism public men. It is the fundament requirement of demonstrating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satisfying human beings’ living need, promot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rxism theory.In light of 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ublic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4 aspects must be achieved: updating our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extending the educational field; expanding the educational space and increasing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the sources;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al carrier and emphasizing the space reconstruction;launching the educational ev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value-guid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ocialism public man;public transformation
2015-02-1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KS006)
10.16366/j.cnki.1000-2359.2015.05.033
D64
A
1000-2359(2015)05-0162-06
岳杰勇(1974—),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意识形态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