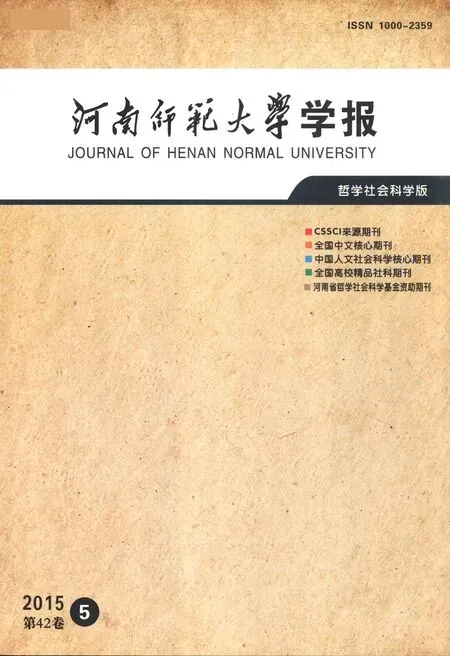教授治学的理论证成
罗红艳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争论在学术界一直是个议而未决的问题。以赵蒙成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教授治校。赵蒙成认为,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创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而教授治学仅指教授在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二者具有本质区别,不能将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混为一谈,更不能用教授治学取代教授治校。针对赵蒙成的观点,杨兴林指出,从内涵意蕴上来揣摩,“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的本质规定,从历史发展源流的角度考量,“教授治校”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现实中不宜机械照搬,教授治学才是符合教授内涵意蕴与大学治理历史趋向的科学选择。以两位专家为代表,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把教授治学理念纳入国家教育治理的官方政策文本之中,也宣示了在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争论中的国家态度。可是,纲领性文件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停息这一纷争,仍有学者撰文认为教授治学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回应教授参与大学管理诉求的一种权宜之计[1]。可见,政策话语要真正入耳入心,还需要从学理上予以证成。
一、教授治学的合理性证成:彰显了学术自由与大学秩序的辩证统一
究竟是应该主张教授治学,还是提倡教授治校,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与处理大学内部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则是关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与边界。
学术探索与知识创新是大学的神圣使命,自由则是学术获得与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本途径。从根本上看,所谓学术自由即意味着有效排除来自大学外部的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大学内部行政职能部门与管理人员的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干预或限制,从而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能够自由地进行。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分别在其创办的“阿加德米”学园和“吕克昂”学校大力倡导自由研究与讨论。中世纪欧洲大学更是在排除外部干预与控制、争取大学自治的基础上奠定了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洪堡筹建的柏林大学则成为学术自由原则的典型的实验场。蔡元培把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作为治理北大首当其冲要遵循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之一。
推行教授治学,保障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的学术权力的合理性恰恰源自于对学术自由价值的尊崇。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仅要传播知识,更要创新知识。正如博克所言,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而围绕着发展知识而形成的大学治理模式也必然以保护学术自由为逻辑起点与价值旨归。学术资源由行政人员掌控与分配,教授没有话语权;自上而下的集权化管理,基层缺乏活力;外行领导内行,学术规律无法彰显。诸如此类大学管理过程中的陈弊积病致使学术权力被边缘化,知识创新与发展受到限制,严重地戕害了大学学术自由,致使行政化现象成为大学之殇。越来越多的诟病与批判指向大学行政化均与大学管理有悖学术自由精神、大学教授学术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密切相关。大学教授自身掌握了最高深的专业知识,是所在学科与专业的权威,同时又肩负着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使命,他们对学术管理最具发言权。充分发挥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在大学管理中作用,推行教授治学则成为回归大学本质、彰显学术自由、实现大学知识发展追求的回应。
但是,自由又不是绝对的,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学术自由的限度来自对大学秩序的追求与维护。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目的性价值的话,大学秩序则具有工具性价值。没有大学秩序的存在,学术自由无法真正实现;同样没有学术自由的大学秩序,已经失去了灵魂与意义。因此学术自由与大学秩序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体现出了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Derrida)提出的一种式的“亦此亦彼”的“既是……又是……”式的“增补逻辑”[2]。即大学既要关注学术自由,又要追求大学秩序,力求两者的辩证统一。如果说大学治理中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的合理性来自对学术自由价值的弘扬的话,那么,对大学秩序的追求则构成了大学行政权力的理性基础。理想的大学不是要排除行政权力,而是要廓清行政权力的边界,恰当地行使行政权力,有效地发挥其在大学秩序维护中的作用,使之为学术权力的运用、学术自由的实现保驾护航。因此,行政权力的无限度扩张以致大学行政化以及行政权力遭遇放逐以致教授治校都是大学治理中的非理性状态,均无益于大学理想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保护学术自由,要尊重教授的学术权力,要推行教授治学;为了创设大学秩序,我们不能否定大学治理中的行政权力,从而主张教授治校。教授治学是在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保持恰当张力下民主治理理念与实践的体现。
二、教授治学的合法性证成:契合了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的制度精神
除了对教授治学所奉行的法则及功能是否符合学术自由、大学秩序等被民众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与大学精神予以理性审视之外,教授治学的合法性追问也是对教授治学予以理论证成的一个重要路向。马克斯·韦伯指出:“今天合法性最普遍的形式,便是对合法律性的信仰,也就是服从形式正确的以一般方式通过的成文规定。”[3]从这个意义上看,教授治学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对其进行合法律性考量,即审查教授治学理念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大学内部规范性文件的精神与规定。由于教授治学这一理念蕴含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道而治的民主治理原则,即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主要在学术性事务的治理中享有权力、以党委与校长为代表的行政团队享有行政事务的治理权,因此,对教授治学的合法律性分析自然也得从这两个方面切入。
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的学术权力从根本上来源于法律规范与规范性文件的权利赋予。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国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规定人民有著作与刊行等学术权利与自由,这可以被认为是有关学术权利最早的法律渊源,此后的宪法草案也均承续了这一规定。然而,国民政府193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却中断了这一传统。新中国建立之后,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再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等权利予以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47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上述宪法以及宪法性质的文件规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权利,这种公民权利在教育治理中则被推演为教师的民主管理权。比如,我国现行《教师法》相关法律条款规定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享有民主管理的权利,教师行使该项权利的主要组织机构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设立的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该机构,教师可以对学校的各种教育教学工作、行政管理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1995年出台的《教育法》再一次明确了教职工通过教代会等组织形式民主参与学校各项工作的管理与监督的权利。而教师的民主管理权在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在学术领域则集中体现为学术治理权。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对高校教师学术治理权的组织载体——学术委员会及其“治学”的功能与权限做了法律规定,即高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行使学术事项的“审议”和“评定”两项职能。但是该法并没有明确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与操作规程,致使行政人员充斥学术委员会的现象颇为普遍,普通教授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过低,最终使法律规范的实践效果十分有限。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标志着“教授治学”第一次进入国家纲领性文件的话语体系。而2014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则从组成规则、职责权限以及运行制度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从而使学术委员会的职能越来越广,普通教授群体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以致被媒体解读为“教授治学味越来越浓”。
从上述关于教授治学合法律性的考察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的学术权力是随着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逐步被赋予的;二是迄今为止,由于国家相关教育法规对教授学术权力的规定并不清晰、可操作,因此,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的有效行使还有待于相关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三是现有的法律法规文本只有对教授治学的权威表述,而看不到教授治校的法律主张,因此,教授治校至少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不具有合法性。事实上,与学术权力的法律基础较为薄弱相对,我国大学行政权力一直在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处于主导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1950年)、《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1953年)等系列文件的出台,教育部、高等教育部享有对全国高等教育事业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大学事务,事无巨细均由其直接管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则确定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作用。随着《高教六十条》(1961年)的颁布,我国构建起了日益典型完备的集权化高教管理政策范式。虽然经过“文革”为期十年的崩溃式管理政策震荡,但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家本位的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又迅即形成。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央政府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地位是有着坚实的法律基础与制度保障的。就大学内部领导体制而言,我国高校先后经历了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以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多种领导体制的变迁与选择。1989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得以最终确定,并一直延续至今。大学党委与行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在大学内部的基层代表,是其高等教育政策与意志的执行者。1998年《高等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大学党委在公办大学中的领导作用,也明确了大学校长在教学、科研以及其他行政工作中的负责人地位,并进一步廓清了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的行使必须面对与尊重党委领导、校长负责这一法律事实。教授治校的主张一方面因为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法律规定背道而驰而不具有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其由于忽视了大学治理中行政权力在获得与维护大学秩序上的重要价值而不具有现实理性。
三、教授治学的合目的性证成:回应了大学学术发展理想与使命的价值诉求
判断作为大学治理理念的教授治学是否科学的、理性的、先进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反映了大学治理活动的客观规律,是否有利于大学理想与使命的最大程度实现。
大学在不同时代或者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想与使命。传统的古典大学以知识传承为目标,承担着人才培养的使命。默什埃姆指出:“在巴黎大学出现之前,在当时著名的帕多瓦和科隆大学里,并不传授当时的科学知识,而巴黎大学的诞生,不单在教师和学生数量方面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大学机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教学内容囊括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和科学,正是在此意义上,巴黎大学首先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4]纽曼更是认为:“大学就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5]威廉·冯·洪堡把科学研究引入其创办的柏林大学中,从而改变了大学单一功能的主张。在洪堡看来,大学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是学术机构的顶峰。洪堡认为:大学“应唯科学是重”、把创造知识、探究科学作为核心使命,人才培养则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1963年克拉克·克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著名的“大学的功用”的演讲时认为大学已经走出了专注于教学、科研的象牙塔,开始成为社会的服务站。科尔认为:“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提供服务。今天,知识是为每个人服务的。”[6]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威斯康星大学则明确地把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第三功用。从纽曼普遍知识的传授到洪堡的唯科研是重,再到科尔的社会服务站,大学开始承载着越来越多的使命与责任。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教学、科研、服务等功能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即都可以涵盖在大学“学术发展”的理想之内。因此,“学术发展”是统辖诸功能的大学理想,是大学所有活动与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大学目的之所在。
现代社会大学学术发展目的的达成需要把握两类活动的规律:一类是学术性活动的规律,一类是为学术性活动的规律。学术性活动是以高深知识的传播、发现与应用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知识专门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专业与专业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越来越厚。这就使得外行人在高深知识面前失去了话语权,即便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很难对彼此之间的专业活动做出评价。由于教授们掌握了高深知识运作的规律,他们理应在教学、科研与转化等学术领域中享有自主权。我国长期以来高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致使行政人员队伍过于庞大、权力不断越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十分严重,学术活动不遵循学术规律的现象较为明显。行政人员用行政思维处理学术事务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的学术发展,使得大学不像大学,学场沦为官场。教授治学主张把学术性事务的管理与决策的权力还原给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这好比是让医生享有治疗活动中的把脉权、诊断权与处方权一样,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教授的权力也应有一个限度,因为大学活动除了学术性活动之外,还有诸如后勤、基建、财务等非学术性的活动以及学术领域中带有行政性质的管理性活动。这些活动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但都是为学术服务的活动,可以称之为为学术性活动。在现代社会,大学为学术性活动越来越繁杂,因此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为学术性活动需要打破专业与学科之间的壁垒,在松散结构中建立起价值关联,因此需要管理者有统筹协调的能力与价值中立的态度;为学术性活动服从的主要不是高深知识的规律,而是管理活动的规律,因此需要丰富的治理经验与管理艺术。为学术性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决定了教授不可能“治校”,而只能“治学”。因为毕竟教授们的“主业”在学术,而不在管理,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聚焦于管理活动;专业的限制决定了他们更多的是忠诚于学科,而不是学校;经验的不足,思维的定势往往又可能造成管理中的失误与低效。而教授的这些劣势又恰恰是行政人员的擅长。一言以蔽之,把学术性活动的管理与决策的权力交给教授群体;把为学术性活动交给行政人员,各行其道、各展其长、分权而设,才能真正把握不同性质活动的不同运作规律,最终达到促进学术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大学的理想与使命。
总之,为了化解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之间的话语纷争,夯实教授治学的理论逻辑,需要摆脱对具体观点与论断的过分纠缠,跳出争论,以消解争论,确立更为整体、宏观的讨论路径。而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则是对教授治学理念予以证成的三个理论向度。合理性旨在通过追问教授治学本身的正义性以剖析其践行的必要性问题;合法性解决的是教授治学在现实制度框架与政策语境中是否具备可行性特征的问题;合目的性则从更加宏阔的视野来观照教授治学是否有利于以及最大程度有利于组织愿景的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探索教授治学理论逻辑的可能的框架与标准。
[1]王长乐.“教授治学”到底是什么意思[J].民主与科学,2011(14).
[2]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8.
[3]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8.
[4]王晓华.纽曼的大学目的观与功能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1).
[5]John Henry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Defined and Illustrated[M].London:Routledge/Thoemmes Press and Kinokuniya Company Ltd.,1994:10.
[6]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