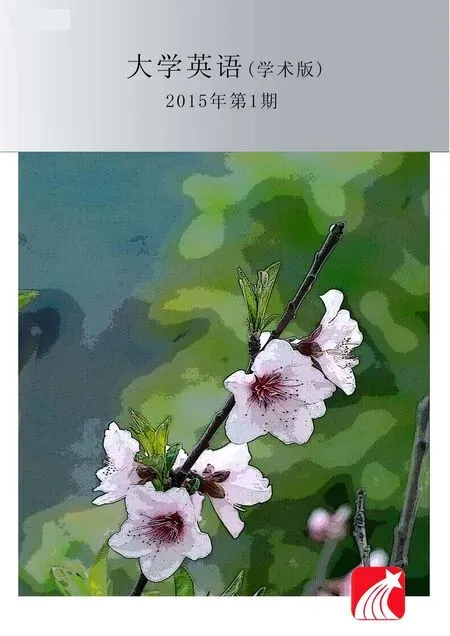从创伤角度剖析《嘉莉妹妹》中嘉莉的成长和独立
梁 霜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从创伤角度剖析《嘉莉妹妹》中嘉莉的成长和独立
梁 霜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嘉莉妹妹》是西奥多·德莱塞的代表作,主要描述美国梦的实现。嘉莉是个美丽聪慧的农村姑娘,一跃成为当红明星,跻身上流社会。本文尝试从创伤角度分析嘉莉成长的原因,并探讨嘉莉在获得物质充裕的生活的同时如何在精神层面找到出路。
美国梦;成长;物质;精神
西奥多·德莱塞,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被誉为是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巨头。《嘉莉妹妹》是其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通过农村姑娘嘉莉到芝加哥谋生而成为当红演员的故事,揭露了以金钱为中心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冷酷与无情,抨击了所谓的“美国梦”的实现并不能给追梦人带来真正的幸福。
弗洛伊德思想是创伤理论的原创点和源头活水(陶家俊:117)。提及创伤,我们就会想到战争,洪水,地震, 火灾及空难等等,其实心理创伤远远不只是这些强大的事件。还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长期经历到的忽视、情绪虐待、躯体虐待或者暴力,都会促进心理创伤的形成,可能心理创伤的印记和伤痛更为持久。弗洛伊德不关注创伤事件本身, 而是强调创伤性记忆。事实上,外在创伤结束后,内在创伤或许会走得更远。荣格认为, 对创伤经历的正常的心理反应是从受伤的场景中退缩, 如果退缩是不可能的, 那么自我的一部分就必然退缩。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的共同地方是, 他们都强调内在心理创伤的影响大于外在创伤, 他们都强调无意识幻想在处理创伤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作用(赵冬梅:93)。本文尝试分析嘉莉通过遭受创伤后,凭借自身的天赋,外加得到命运的垂青,一步步走出家庭,最终走向彻底的独立。
一、 经济上的创伤使得嘉莉最终取得经济的独立
小说发生在1889年,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市场繁荣,整个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无数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汗水、辛劳发家致富,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一幕幕“美国梦”的实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跃跃欲试,前仆后继。嘉莉就是追梦者的一个典型。她是个来自农村的贫困姑娘,坐上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时,身上除了些随身行李就只有四块钱。小心翼翼地怀揣着自己的“美国梦”,带着种种美好的幻想与期望,嘉莉放弃了家乡的便利条件,到繁华的大都市闯荡。小说一开始除了嘉莉,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就是推销员杜洛埃。整本小说我们不难看出,嘉莉不仅仅注重个人的仪表打扮,也很留意别人的外貌服饰。借着嘉莉的眼睛,一个衣着新潮花哨,光鲜亮丽,庸俗浮夸,注意修饰的杜洛埃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不仅是嘉莉所结识的第一个人,也是嘉莉所向往的一种成功,还是嘉莉对于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美好奢华生活的初次印象。杜洛埃是芝加哥繁华时髦生活的一道折射,一个缩影,一种反映。他衣食无忧,往返于各种闪亮的聚会,周旋于各种女人之间,百般讨好接近女性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并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这样一个深谙世事的猎艳者,表面上羡煞旁人,实则庸俗空虚,注定得不到真正美好的爱情,也不配拥有。作者细致的刻画杜洛埃的着装,与嘉莉的穷酸外表形成鲜活的对比,第一次嘉莉深刻感受到经济上的差距带来的自卑与伤痛。
初到芝加哥的嘉莉,被富丽堂皇的展物、喧闹的人群和华丽的大厦吸引,幻想着能过上比以前幸福的生活。可是姐姐敏妮经济上的窘迫,对丈夫汉生的顺从妥协以及汉生的不近人情浇灭了嘉莉的一腔热情。现实与梦想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敏妮每天忙于生计,无暇享乐,汉生则只顾嘉莉是否找到工作,能否如期上交住宿费,这些都让嘉莉颇感失落沮丧。她必须外出寻找工作,经历几番艰辛,终于找到一份每周工资四块半的工作。她对于享乐的向往极为强烈,却没有金钱没有时间寻找欢乐,尽情享受。那些衣着华丽的女孩根本看不起她,从她们面前走过,嘉莉感到羞愧,心里很不是滋味。又一次经济上的差距,给嘉莉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因病,嘉莉失去了这份工作。敏妮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加上长久受丈夫的支配,他们都对嘉莉表现出了极大的冷漠。她必须二次求职,但却处处碰壁,无依无靠。充满寒酸和屈辱的环境,破坏了她原先的梦想。这时,杜洛埃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度,在嘉莉眼里,杜洛埃代表了巨大的成功,是拯救她的骑士,是文雅的绅士,她甚至认为鞋厂粗俗轻浮的男人不能与他相比。“她恐怕周围的男工会跟她开这种玩笑—这些男工与杜洛埃相比似乎野蛮可笑”(德莱塞:29)。在这一次面对经济上的威胁时,她选择委身于杜洛埃,把自己的物质愿望寄托于男性。嘉莉不爱杜洛埃,却可以依靠他实现自己的物质欲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赢得社会地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核心就是创伤的思想和行为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陶家俊:117)。杜洛埃并非真的爱嘉莉,这样一个花花公子,只是享受这追逐猎物的快感和自豪。人都是软弱的,无法战胜欲望的引诱,只能受欲望的驱使前进。嘉莉不是没有过摇摆不定,她在与杜洛埃同居后也常常扪心自问,但是比起传统道德行为标准,她的天平不自觉地倾向了物质一方。贫穷带来的痛苦和威胁帮她完成了这道选择题。
渐渐地,嘉莉看清杜洛埃的轻率和粗俗,并深知不能娶自己,可又不能离他而去,因为结局只能是自己落得没有安身之地,寒酸落魄。这时,一个更好的选择出现了。“赫斯渥的来到让她看到了一个比杜洛埃更强的人。每个女人都会赏识他献出的殷勤。他不拘束,也不放肆。他的魔力是体贴入微。他训练有素,能在常到他酒店来的那些上等人中间博得好感”(德莱塞:71)。这样一个温文尔雅、富贵显赫的赫斯渥能给嘉莉带来一种比现在更舒适、更高档的生活。对于地位和物质的欲望的膨胀,很快,嘉莉坠入情网。于是,赫斯渥携带公款带着嘉莉私奔到纽约。来到纽约,赫斯渥的事业屡屡受挫,一蹶不振,从此,自暴自弃,悲观消沉,他们的生活又面临困境。他们没有可观的收入,每顿饭都要精打细算,不断的搬家,买不起考究潮流的衣服、光彩夺目的首饰,也不能出入富丽堂皇的高档餐厅,看不了热闹非凡的戏剧。尤其在衣着华丽气派的万斯太太身边,嘉莉更是觉得自己不值一提。嘉莉是个物质欲望和攀比心理都极其强烈的人,她肯定不满于生活现状,她要过高级的生活,她不愿重新回到原先的那个穷困潦倒、饥寒交迫、微不足道的漂泊的人那儿。面对再一次的经济重创,赫斯渥颓废萎靡,一点点沉沦,嘉莉终于决定不再靠男性来生活,而是勇于再次求职,争取独立生活。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加上嘉莉也确实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她终于登上舞台,成为红极一时、众星捧月的演员。名利双收的嘉莉最终跻身上流社会,摆脱了对于男性的依附,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实现了经济的独立。但是被掌声、鲜花、赞美包围的嘉莉,却深感空虚孤独,只能睡在摇椅里低声浅唱,重新定义幸福的含义。
一次次经历经济上的困境,在嘉莉心里留下深刻的创伤。她害怕贫穷的生活,甚至对于贫困的人群她都能感同身受。“她老是在为从她身边匆匆走过的那些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精神沮丧的男人而伤感。每天晚上从她窗口匆忙走过的衣衫破旧,从西区某些商店赶回家去的姑娘也会引起她内心的同情,当她们走过时,她总是站在那儿,咬着嘴唇,摇着小小的脑袋发呆。她想他们一无所有。没钱没衣真是太惨了。穿着旧衣服的人让她目不忍睹”(德莱塞:106)。她深知贫穷意味着什么,她畏惧回到曾经的生活,所以为了不再受到贫穷的威胁,她决定走入社会,改变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经济的走投无路和心里的创伤在嘉莉取得经济独立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正是这么一次又一次生计困窘,才使得嘉莉打破了依靠男性生活的传统思想,勇敢地走出家庭,发现自己的才能,敢于冒险挑战,终于能够自食其力。不得不说,经济的贫困给嘉莉带来伤痛的同时,也为她的成长与独立起了积极作用。
二、 情感上的创伤使得嘉莉最终开始追求精神的食粮
(一) 亲人的冷漠无情
一踏上这片灯红酒绿、喧嚣热闹的土地,见到姐姐敏妮,嘉莉没有感到踏实安全,兴奋激动,而是感到现实的冷酷扑面而来。敏妮和汉生每天起早操劳,勤勤恳恳,可是生活却依旧入不敷出,一家三口始终没有过上幸福的日子。姐姐房间的景象深刻地冲击了嘉莉希望通过努力能干实现梦想的观念,也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人民的辛酸、压抑、沉闷的生活显露无疑。同时作者也揭露了资产阶级对于下层人民的压榨和剥削,以及在这样一种冷酷无情、世态炎凉的环境下人的异化。汉生沉默寡言,思想古板,老实本分,斤斤计较,生活枯燥泛味,甚至是一种病态。敏妮是传统女性的代表,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长期处于丈夫的支配和控制下,精打细算每一笔钱,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由于长期奔波生计加上艰辛的婚姻生活让她早就放弃享受娱乐的念头。嘉莉在辛劳一天回家,得不到可口的晚餐,体贴的安慰,温暖的同情,换来的却是亲人对她的“算计”和非分之想。面对不近人情的亲人,嘉莉深感心灰意冷。雪上加霜的是,嘉莉因病丢了工作,敏妮和汉生感到她是个累赘,是个包袱,于是冷眉冷眼,漠不关心。亲人自私丑陋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所谓的亲情、善意、关怀在金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下层人民就是一株弱草,手无寸铁,面对捉襟见肘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成为金钱的奴隶,被动地受金钱的驾驭。
(二) 两度沦为情妇
嘉莉深深地感受到了亲情的冷漠,万念俱灰,做了杜洛埃的情妇。杜洛埃贪恋嘉莉的年轻美貌,把嘉莉作为自己的一个迷人的战利品,一种卑鄙的炫耀,一种美妙的胜利(邹艳菁:114)。“他喜欢追求女人,使她们倾倒于他的风度之下,并不因为他是个冷血的、黑心肠的恶棍,而是因为他天生的欲望,促使他以此为最高的快乐。他爱虚荣,爱夸耀,他像头脑糊涂的女孩一般迷惑于美丽的服装”(德莱塞:47)。虽然嘉莉把杜洛埃看做自己物质欲望和享乐的实现者,她也承受着道德的束缚和良心的拷问。其实,嘉莉也把他看成一个情感依靠,一个精神归宿,毕竟作为一个来芝加哥漂泊的单薄的女性,在遭受亲人的抛弃后,她也渴望能够安定下来,渴望一个温馨的家庭,所以她希望与他尽快结婚。这也充分反映了嘉莉所持有的传统女性依靠男性生活的思想。逐渐地相处,嘉莉看清了杜洛埃并不想与她结婚。亲情的冷淡漠然,已经在嘉莉心中留下了一道创伤,而从杜洛埃身上所获得也仅仅是物质、金钱、享乐,没有一丝一毫的真情实意。她不爱杜洛埃,杜洛埃也不爱她。杜洛埃迷恋嘉莉的美貌,把嘉莉留在身边作为炫耀自己魅力的资本,但他不愿意受到法律的约束只对一个人忠心耿耿。嘉莉害怕再面对贫苦和孤独,也不能离开杜洛埃。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没有真心,没有温馨,只是不同欲望的结合,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又给嘉莉抹下一道伤痕。正是由于杜洛埃把嘉莉当成炫耀个人魅力的资本,所以才介绍赫斯渥与嘉莉相识。赫斯渥风度翩翩,沉着自信,有地位有权势,很快虏获嘉莉的芳心。不难看出,赫斯渥也是个感情经验丰富,善于逢场作戏、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赫斯渥的婚姻生活不幸福,太太工于心计,儿子女儿一味地追求名利,但是他总体的生活还算稳定—显赫的地位,丰厚的财产,蒸蒸日上的事业。他“此时此刻只是玩乐,并没有什么责任感”(德莱塞:97),把与嘉莉的关系当做生活的乐趣而已。隐瞒自己已有妻室的事实,他想要的就是把嘉莉“抢”到自己身边(邹艳菁:114)。对于嘉莉而言,赫斯渥不仅是引领她离开杜洛埃的一条出路,而且赫斯渥成为嘉莉新的感情寄托。嘉莉历经亲情和爱情的创伤,她渴望的就是一个稳定温馨的家庭,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一份笃定的深厚的矢志不渝的异性的爱。赫斯渥对嘉莉情真意切地示爱,让嘉莉兴奋不已。赫斯渥对嘉莉的欲望与日俱增,而面对嘉莉一次次关于结婚的所施加的压力,以及他和太太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他决定抛下一切带嘉莉私奔。嘉莉满怀希望与赫斯渥结婚。随着生活的每况愈下,赫斯渥却固步自封,随遇而安。雪上加霜的是,嘉莉得知赫斯渥并没有娶她。嘉莉悲痛欲绝,又一次沦为情妇,又一次经历被情感蒙骗。嘉莉对依附男性彻底失去信心,开始摆脱家庭束缚,独立生活,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穷愁潦倒、饥寒交迫的赫斯渥沦为流浪人,最终选择自杀,为自己曾经一度羡煞旁人、荣华富贵后来凄苦无助的人生画上悲惨的句号。
(三) 追求精神提升
亲情的冷漠无情,两度做别人的情妇并且得不到真爱,嘉莉在情感上遭受严重的创伤。重逢杜洛埃,杜洛埃想和嘉莉破镜重圆,却被嘉莉断然拒绝。嘉莉不仅经济独立,有自己的地位和声名,而且她看到了杜洛埃丑陋虚伪、内心空洞的一面。朝三暮四、轻浮放荡的杜洛埃给嘉莉内心带来的创伤更为长久,再面临感情她只会选择退缩。同样,被赫斯渥诱骗私奔却作为情妇也对嘉莉影响深刻。“一旦他们所代表的一切,所象征的一切对她已经没有诱惑力时,她自然不再信任他们。即使赫斯渥重新回到风度翩翩的体魄中去,即使他又有了如同以前光辉的事业,嘉莉现在也决然不会动心。因为,她已经知道,他的世界,如同她本人现在的境遇一样,并无幸福可言”(德莱塞:395)。
众星捧月的嘉莉享受着极其丰富的物质世界,却感到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艾姆斯在小说中扮演嘉莉人生导师的角色。艾姆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思想有见解,与目光短浅的嘉莉相形见绌。第一次见艾姆斯是万斯太太带嘉莉去豪华气派的餐厅吃饭。金碧辉煌的餐厅里,他们见识了有钱的美国人一掷千金,过着奢侈糜烂、铺张浪费的生活。嘉莉满心羡慕,艾姆斯却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么挥霍金钱是可耻的,对于发财致富他也是不屑一提。他“决不愿意成为这种富人,一个人的幸福并非建筑于这类东西上”(德莱塞:246)。他有长远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他清醒的认识到幸福不建立在富贵上面,而是应该追求精神上的进步和提升。他的观点也如一扇门,让嘉莉看到更为广阔更为精彩的世界。嘉莉出名后,艾姆斯见到她除了给予肯定和表扬,也提出中肯和指导性的建议(林晓青:95)。他让嘉莉充分发挥个人的优势和才能,鼓励她去演正剧。她接受艾姆斯的引导和推荐,读起来世界名著。她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肤浅愚蠢,她努力充实自己,提高精神境界。“她是一个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善于感觉而不善于思考,因而进入迷谷之中的人。尽管幻想经常破灭,她依然期待着梦想中的幸福会变成现实。艾姆斯曾经给她指明更高一层的境界,但还要继续上升、上升”(德莱塞:395)。不得不说,情感上的创伤也是嘉莉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使她在实现物质目标后,又在找寻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探求精神的更高层次。
虽然结尾时嘉莉迷茫困惑,但是她仍然向往着,憧憬着,努力着。我们也期待一个全新的嘉莉。嘉莉追寻美国梦的过程也是她蜕变为一个新女性的过程。
林晓青(2013). 从女性成长角度看德莱塞的《嘉莉妹妹》 [J]. 名作欣赏(8)。
陶家俊(2011). 创伤 [J]. 外国文学(4)。
西奥多·德莱塞(1995). 《嘉莉妹妹》 [M]. 王艳燕, 胡莺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赵冬梅(2009).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 [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6)。
邹艳菁(2013). 《嘉莉妹妹》中的爱情观 [J]. 名作欣赏(9)。
2014-11-22
梁霜(1991-),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