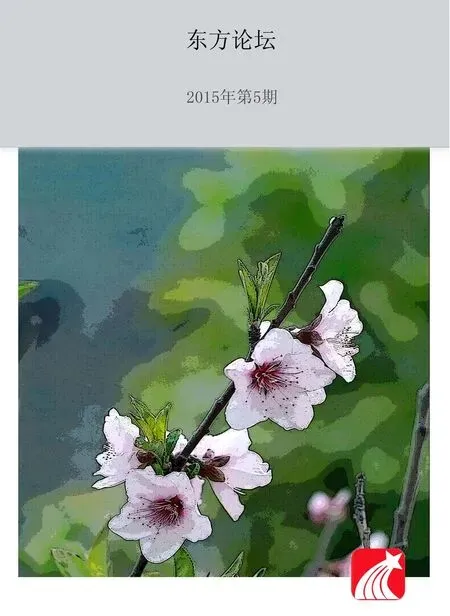困境与突围:生活哲学之依归
摘 要:新世纪山东新锐作家的乡村叙事打破新时期乡土题材作品相对单一的主旋律创作模式,逐渐走入了一个多元化开放格局。主要体现在启蒙话语的延续、从政治乡土到文化乡土的书写转型,以及一系列行不由径的乡土先锋文本的出现。新锐作家们对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乡村生活和农民命运、基层干部处境、观念变迁等诸多问题予以关注。在叙事领域的拓展和表现技巧的大胆革新层面都突破了山东乡土文学原有的叙事格局。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5-0064-06
回顾20世纪山东文学,最辉煌的时期当属八十年代,李存葆、张炜、王润滋、矫健、尤凤伟、李贯通、左建明等作品奠定了文学鲁军在新时期文坛的领先地位。但九十年的山东文学创作整体态势不尽如人意,学者吴义勤曾尖锐地指出:“90年代的山东文学大概只能在全国居于中游的位置,进入了一个衰退的过程中,……山东青年作家处于被压抑和遮蔽的状态中,这严重影响了他们走向全国的速度” [1]。新世纪文学已走过整整13个年头,山东文学、尤其是山东青年作家的发展现状如何?本文以山东新锐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为例来做一梳理,因为乡土题材始终是山东文学的创作重镇。新世纪山东乡土文学创作逐渐打破了政治性话语为主的单一写作模式,实行了现实主义的开放,呈现出一种多元开放格局。
一、启蒙乡土
山东新锐作家群体的王方晨、刘玉栋、张继、李辉、凌可新、刘照如、闵凡利、滕锦平等都是创作活跃、成绩斐然的乡土文学作家。在人文精神式微的当下,他们仍恪守一个作家对社会的文化守望职责,表现出应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启蒙话语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所揭示的全部内涵就在于使中国的文学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它要挣脱的是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桎桔,这个历史性的重任尚远远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主要落在致力于乡土小说的作家身上。” [2]新锐乡土作家继承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派”到张炜、刘玉堂、尤凤伟、李贯通等新时期“鲁军”乡土题材小说所标举的人文主义旗帜和启蒙话语,书写了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土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心理变迁,字里行间流露出冷峻的批判意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
有“山野间的先锋”之称的王方晨认为:文学上所谓先锋的意义,应是一种先于大众的智慧的觉醒。王方晨小说中展示的乡村图景既不是寻根文学笔下的藏污纳垢之处,也绝非京派作家笔下的桃园净土,他从不掩饰乡土世界的丑陋,撕破它、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方思改变,是他的创作动机。“塔镇”世界的“村长系列”是王方晨创作标
收稿日期: 2015-04-27
作者简介: 卢军(1970- ),女,山东莱芜人,文学博士,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志之一。他生动传神地塑造了王光乐(《乡村火焰》)、老万(《乡村案件》)、乔尚七(《说着玩儿的》《村长的原则》)、“大花脸”(《跑吧,兔子》《兔子回来了》)、江福兴(《塔镇的塔》)、刁金豆(《麻烦你跟我走一趟》)、王连举(《樱桃园》)等诸多村长形象。这些故事各异、形形色色的村长们是国家权威的底层代言人,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村民对其只有俯首称臣。一旦有人试图反抗,他们都会给予沉重打击。
毫不手软地惩治“异端”是村长们维护权威的首要工作。小说《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入木三分地描写了村长刁金豆作为一个乡村土皇帝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威。他对不肯对其臣服的村民范思德恨之入骨,睡梦里都在大叫“拉出去毙了!”最终刁金豆借助镇派出所武所长之力铲除了这个异己分子。小说《跑吧,兔子》《兔子回来了》中的凤祺老汉曾公开表露对村长的不满,村长对此耿耿于怀,决定杀鸡儆猴。适逢凤祺老汉在麦地里干活时不知被谁误当作兔子打了一枪,这偶然的事件让村长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机会,他无中生有地冤枉村民来继,“来继,是你开的枪吧?”并逼来继向凤祺老汉当面认罪。来继只有违心地承认了这桩冤案。小说《说着玩儿的》中村民刘树礼因为说了一句牢骚话“统统枪毙”,招来村长乔尚七的不满,认为是公然挑战村长的威严,要狠狠“收拾”他一下。村长发动全村人大搞群众斗争,整得刘树礼百口莫辩,只好一死了之。当民兵连长禇金盛惊慌失措地向村长报告刘树礼自杀的消息时,乔尚七不以为然地到现场查看。因绳子突然松脱,吊在门框上的刘树礼沉重地跌在了地上。乔尚七对地上的刘树礼冷冷、不慌不忙地看了一眼就回家了。可见民众生命在其心中如草芥蝼蚁一样一钱不值。小说《乡村火焰》中阴险狡诈村长王光乐听说有人要到镇政府告他,为了震慑村民,便自编自演了一场戏,纵火烧了自家的柴垛,而塔镇村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纷纷向村长殷勤慰问以表忠心。唯有村民王贵锋在村长的柴垛失火后没有去“慰问”,村长遂诬陷无辜的王贵锋为纵火犯,塔镇派出所不问青红皂白抓走了王贵锋。这些村长的共性是专横霸道、不可一世。他们与会计、派出所所长、合同制民警、工商所干部等共同组成了一个权力团体,共同欺凌压榨村民的利益和尊严。
与强势的村长系列相对应的是软弱无助的懦弱的村民系列。来继(《无助的豆苗》《跑吧,兔子》《兔子回来了》)、刘树礼(《说着玩儿的》)、刘福采(《村长的原则》)、王贵锋(《乡村火焰》)都具有典型意义。在相对封闭的乡村世界里,他们首先懦弱地臣服于村长的权威,逆来顺受,丧失了个体的尊严。面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正的事件,从无反抗的勇气。其次他们又都是权力秩序的自觉维护者,任何反抗者都被视为异端,面临集体舆论的围剿。在《麻烦你跟我走一趟》《说着玩儿的》等小说中,村民们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路线,共同对付范思德、刘树礼等异端。看热闹、散布谣言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方式,反映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贫瘠。王方晨称自己“关注的是生活中所有处于非自然状态的‘人’。……因为生活的非自然状态,我们感受到了诸多的恐怖、颠倒、苦恼、梦魇、缠碍” [3]。他笔下的村长系列和村民系列人物都是非自然状态的被异化的人。
闵凡利的短篇小说《张山的面子》,描述了村民张山对“面子”的看重和为了挣得“面子”而做的荒唐行为。张山早知老婆跟村长黄运河有染,但因惧怕村长的权威,更碍于自己的面子,佯装不知情。但万没料到此事被不谙世事的儿子在学校里说了出来,很快传遍全村,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张山再装聋作哑,面子上说过不去。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张山计划在大街上当众大骂村长一顿,但又怕村长报复,所以先请村长的客,希望村长能暗中配合,不料村长也为了自己的面子毅然回绝了张山的办法。张山破釜沉舟去强奸村长的老婆扳回面子,虽然没有得逞,还因强奸未遂罪被关押,但却得到了张村人另眼相看,因为挣回了“面子”。小说借“面子”问题批判了今天农民身上依然残存的国民劣根性。
张继的中篇小说《人样》中,村民朱七的老婆刘英被村长李木骚扰,朱七感到很气愤,发誓要报复。刘英则更关心家里承包的菜园子能否继续包下去,认为只要村长答应他们家继续承包菜园子,自己吃点亏也无所谓。当村长真的让他们继续承包菜园子之后,朱七不仅不再气愤了,反而觉得村长人还不错。可见,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沉积千年的畏惧盲从权威、奴性与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依然根深蒂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艰巨复杂性。
在由专权的村长与惧权、媚权的村民组合而成的乡村政治景观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件随处可见。作家们沉重的笔锋直指当下中国乡村秩序。但他们在展示乡村苦难的同时也从未放弃对人性善的发掘,小说结尾处常有如同鲁迅《药》中代表希望的小尾巴,诚如王方晨所言:“我有不忍之心。我相信光明是存在的,即我不为,它仍在” [4]。新锐乡土作家们始终坚守道德立场,呼唤着正义与良知。
二、文化乡土
与上述从政治角度切入,书写中国乡村权力场的作品不同,张继、滕锦平、刘玉栋、刘照如等青年作家的乡村叙事超越了传统的启蒙主义立场,转而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乡土社会,在他们的笔下,“乡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联系着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从而具有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联系着人性的细微变化从而具有文化意义,表现乡村生活状态的变迁和沉重苦楚的人性变异” [5]。
张继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创作了《杀羊》《优秀青年王渔》《集资》《黄坡秋景》《一个乡长的来信》等优秀乡土小说,他擅长用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观照乡土政治,笔下鲜见王方晨“塔镇乡长”那样营私弄权的基层干部,篇章结构也很少以农民与干部之间的紧张对立冲突为表现重心,而是呈现了四平、黄大发、刘春明等乡村基层干部既要应付上级各种检查、完成大大小小的任务,还要兼顾村民的实际利益的“夹缝人”的尴尬艰难处境,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基层干部的理解与同情。
张未民在《对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提出“新世纪文学是一种生活的文学” [6],20世纪80年代启蒙文学的宏大叙事话语中被忽略的日常生活场景、生活趣味成为新世纪文学表现的中心。张继新世纪的小说《村长的耳朵》《人样》等可归为“生活的文学”之列。小说叙述重心皆为鲁南乡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的人和事。《村长的耳朵》中徐村村长王大敢醉酒之后一只耳朵被狗咬掉了,村民们始而不信,及至从王大敢八岁的儿子小满那得到证实后,或假意关心,或幸灾乐祸……白脸文书传来最新消息,说村长从医院包扎后去找陈庄专治狗伤的老中医陈麻子,陈麻子说关键是要用吃村长耳朵的那条狗配药做药引子,村长的耳朵才能长出来。于是,全村五十三条狗被集合起来进行测试,寻找元凶,几经折腾也没找到。忧心忡忡的小满语出惊人地问了一句:“我爹没有耳朵还能不能当村长?”这句话把文书白脸的私心点燃,暗地里对媳妇说:“他的耳朵如果是为抗洪救灾掉的还差不多,为了喝酒,门也没有了,乡长不会让他再干”,因最有可能扶正的就是白脸,夫妻二人遂沉浸在当村长的亢奋的期盼中。没想到小满发现庆祥家的狗有很大嫌疑,追问之下胆小怕事的庆祥供认不讳,让文书把狗牵走,天亮后送去做药引子。小满不肯回家睡觉,执意在文书家拴狗的院子里站岗,“我看着这条狗,别让它跑了,他要一跑我爹就当不上村长了。白脸和玉芝都打了个寒颤。这一夜白脸和玉芝都没有睡着觉,下半夜白脸真产生了将庆祥这条狗丢到水井里的念头,但出去一看,小满还很精神地在狗身边坐着,就没敢,装作撒泡尿,回了”。农村中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毫无诗意可言,但真实地揭示了当下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涌入城市,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里的身份问题已不容忽视。张继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是一部富有当下意义的力作,深刻地探究了农民进城谋生后的身份问题。村民贵祥的二亩好地被村长李木卖掉了,而且事先没给他“透透气”,这事关系到生计和面子双重问题,忿忿不平的贵祥在妻子和乡邻怂恿下,放出口风要告状,本想让村长服个软给个台阶下就了事,但村长压根没把老实怯弱的贵祥放在眼里。贵祥遂进城告状,否则在村里就太没有面子了。进城之后的贵祥在与城里人的不断比较中,感到自惭形秽。告状不成功又羞于回乡的贵祥只好留在城里打工,后来还做起了生意,有了立足之地。贵祥和老婆徐钦娥的城里人的衣着打扮、举止做派,使他们在村里的地位发生了巨变。“从城里回来,贵祥不再是贵祥,因而村长李木也不再是原来的李木了。”腊月二十八,贵祥回村,提了酒去村长李木家。举动自然随意,此时的贵祥与村长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村长面前,贵祥一扫先前的拘谨敬畏感,变得能说会道起来,还吹起了牛,引得村长羡慕,说贵祥一年挣的,赶得上十几个村长一年挣的。村长请他吃饭,贵祥给了他面子。当贵祥回城时,村长求他把女儿带走,他没有答应,封闭的乡村权力体系坍塌了。正因如此,尽管贵祥觉得城里虽好,但不属于他。不时有“没有了地我心里怎么有点不踏实呢?”的感叹,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城市。小说结尾处邻居小胡跟贵祥夫妇一起奔向城市的举动预示着城市化进程的势不可挡。《去城里受苦吧!》和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展示了当代乡村的变革,讲述了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思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什么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等问题,表现了作者对当今社会转型期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的关注和忧虑之情。不同的是《秦腔》笔触凝重悲凉,《去城里受苦吧!》则颇有轻喜剧风味,有读赵树理评述体小说的顺畅感,但幽默风格下蕴含着引人深思的诸多社会热点问题。
胶东作家滕锦平也擅长从文化角度观照当代乡村生活。其长篇小说《烟花镇》中的烟花镇展示了当代农村、尤其是小城镇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变迁。小说以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两条情节线索来描写烟花镇镇长黄有法的生存状态。政治生涯以黄有法和副书记郑霖的明争暗斗为主线,黄有法对官场的潜规则了然于胸,还有即将离任高就的书记周志明的大力扶植,本应稳操胜券,但他的消极避让,使本处于弱势地位的郑霖后来居上,在野心勃勃的郑霖的强势进攻下,黄有法最终落败。周志明调走后,郑霖做了镇长,大权独揽,而黄有法则变成了有名无实的代理书记。厌倦了官场中尔虞我诈争斗的黄有法,辞去公职去作“梵蒂冈”游乐船的经理。“梵蒂冈”提供女色、赌博等服务,与在拉丁语中意为“先知之地”的宗教圣地“梵蒂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颇具反讽意味。但在商业经营中黄有法也没有体会到丝毫乐趣。小说的心理描写尤为成功。冷静细致地展示了一个身处全民焦虑时代的乡镇干部的精神追求及孤寂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基层干部,黄有法常常自审反思人生,这使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烦躁不安是他情绪的常态,既不能象老婆麦儿那样兴兴头头地过世俗生活,又不能象政客郑霖那样八面玲珑地行走于官场,在融入俗世和精神自由之间游离不定,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小说以“梵蒂冈”出了一场事故,黄有法受到牵连被拘捕告终,人生无常的命运感油然而生。另外,在大学生村官、硕士村官越来越多的中国基层社会,在官场生态、世俗生活与理想追求之间寻求平衡、进行抉择是许多基层干部要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烟花镇》是具有先锋意识的佳作。
三、先锋乡土
提起二十世纪山东文学,乡土题材、写实手法、道德理性精神、厚重朴实风格等俨然成了山东文学的代名词。吴义勤曾批评山东文学的保守:“山东作家毫不犹豫地排斥和拒绝着文学上的一些新潮或先锋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的山东文学似乎永远只是一种追赶的文学,一种落伍的文学,这尤其表现在形式层面上。” [1]房伟指出:“具体而言,要实现山东文学的现代转型,就要避免四个误区,即乡土文学误区、现实主义误区、传统文化误区和道德主义误区。” [7]好像山东作家与现代派的手法无缘。新世纪伊始,山东新锐作家们开始“离经叛道”,在传统的乡土文学领域大胆变革文本形式,为中国当代乡土写作提供新的叙事经验。
刘玉栋是不断开拓着乡土文学表现手法的青年作家。短篇小说《幸福的一天》荣登“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小说描写的是菜贩子马全的人生轨迹。他每天开着机动三轮车到城里卖菜,乏味辛苦的生活令他厌倦却也无可奈何。冬天的一个凌晨马全像以往一样开着机动三轮车进城,不慎栽到了马路下的水沟里。许久之后马全醒了过来,突然对自己的生活有诸多不满:“多少年了,天天披星戴月,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吵吵闹闹,为了一分钱,也能争个脸红脖子粗。从一大早,把满满的一车菜推进那个黑洞洞的菜市场,到傍晚时,再推着空车从里面走出来。这么多年,说句夸张的话,连太阳都看不见,当然,更感受不到那暖烘烘的阳光了。”于是,马全决定要好好只为自己活上一天,他从沟里爬出来,扔下三轮车和满车的菜去了城里,要享受一天城里的生活。他打了出租车到城里最有名的凤都楼吃早点、到天河池去洗浴、从头到脚换了新衣服之后又去美发厅理发,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当马全心满意足轻飘飘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院子里热闹非凡,“大人们进进出出,表情严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马全心里一急,便从屋脊上跳下来。他的身子还是那么轻,落地时,连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马全往屋里一瞅,心便抖了一下。果然出事了,他看到老婆和儿子正跪在地上哭,他们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很伤心。在他们面前,是一张门板,上面似乎躺着一个人,但被黑布子盖着,他看不清楚。他走进屋来。老婆和儿子只管低着头哭,根本就没看到他。马全觉得奇怪。他在门板前站了会儿,便蹲下身子。他伸出手,轻轻的揭开黑布。让他吃惊的是,黑布下面躺着的是自己。他看到躺在门板上的自己,也是干干净净的,头发剪了,胡子刮了,穿的衣服竟然跟自己身上穿的一模一样”。马全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已不在人世,家人都在为他哭丧。《幸福的一天》与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一样,都采用超现实的魔幻荒诞手法讲述了一个绝望的故事。菜贩子马全与《第七天》中的杨飞等人都是与世无争的小人物,却饱尝生活的艰辛,唯有在彼岸世界的乌托邦之地才能实现卑微的人生理想。小说对底层社会辛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
近年来,青年作家范玮创作了数篇具有浓厚先锋色彩的试验小说,这是他有意为之的,“文学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沿着别人走过的旅途,走至终点,永远不会和大师会师,而变成了朝拜之旅。循规蹈矩意味着原地踏步,行不由径,屡险出格是试验小说无限可能性的不二法则” [8](P300)。现代主义大师博尔赫斯对他的实验小说影响显著。范玮的小说《鸡毛信》《东野湖》《桃镇之行》《孟村的比赛》《乡村催眠师》都以构建叙事迷宫、营造非现实梦境为表现重心,充满了形式主义的游戏精神。《乡村催眠师》中桃镇的小林医生会使用神奇的催眠术,能让患者不知不觉进入梦境后把心底的秘密和盘托出。桃花坞的少年四甲给小林医生讲述了六奶奶的传奇故事:在战乱年代,富家小姐六奶奶与当兵的六爷爷私订终身,“六奶奶来到桃花坞,一等就是一辈子,六爷爷一直没有回来”。据说有103岁高龄的六奶奶驻颜有术,始终保持容颜不老。四甲的讲述引起了小林医生的强烈好奇心。一场大雪后,小林医生去桃花坞寻访六奶奶,路上遇到了一个向桃镇方向走去的女人。阴差阳错的是,与小林医生擦肩而过的女人就是六奶奶,她是到桃镇找小林医生的。六奶奶把小林医生的同事杨时误认为小林,杨时给六奶奶实施催眠术后告诉她:当年六爷爷告诉她的地址不是桃镇的桃花坞,而是一百里之外的桃花坞。得知自己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等待了一辈子后,精神崩溃的六奶奶冻死在回桃花坞的路上。得知此事的小林医生不辞而别,从此在桃镇失踪。《桃镇之行》继续用魔幻的手法讲述六奶奶的故事。小说采用并行文本的结构,记述了“我”来到了桃镇之后听到的不同版本的关于六奶奶的新故事,有当年和六爷爷一道出去当兵的铁匠父亲的叙述,有村长的叙述,各种叙述交织在一起,制造了新混乱,使文本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让读者不断在叙事中迷路。在先锋的形式外衣下,范玮致力于探索人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
纯文学创作的坚守者刘照如也致力于对各种文本建构方式进行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起,刘照如就写作了《幸存者》《目击者》《失踪者》等具有“元叙事”意味的先锋小说。与范玮一样,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被刘照如奉为圭臬,叙事迷宫、时间的不确定性、结局的多向可能在刘照如小说中随处可见。他一方面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他在虚构故事,同时他又常引用了一些县志、史料,把读者带进故事中,让读者有种身临其境同时又不辨真假的亦真亦幻的感觉。《竹器》即是最好的例文:“我要说的故事发生在两百多年以前。根据我的家乡山东省定陶县的地方史志资料对一场洪灾的记载,可以推断出故事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清朝乾隆39年的春天。那一年的春天风大,干旱,漫长,预示着夏天到来的洪水。我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万福河的上游一带。” “我”的祖上刘权是长春、柳林一带最出名的篾匠,他利用业余时间,精心挑选质地最好的篾子编制了一只河蚌模样的针线盒,还在竹蚌的口翼处嵌了一圈细小的咖啡色的珍珠,生动可爱。刘权鼓足勇气把这件特别的竹器送给长春镇的一位姑娘,但回答他的是“长春姑娘”低声的哭泣,放在她胸前的竹蚌也掉到了地上。没待刘权进一步表达,“长春姑娘”就被家里一个苍老的男人的大声叫嚷吓回了家,紧接着那一年的洪水就到来了,“长春姑娘”和长春镇一起消失了。故事讲到此处,作者用镶嵌式文本的方式穿插了几则关于“长春女子”的民间传说故事,特别详细地讲述了《白娥树》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叫赵明成的商人带领着一支骡队去南方贩大米,路过定陶县长春镇时,在水井边遇上一个叫白娥的美丽女子,一见倾心。相约回来时在井边相见。赵明成在南方经历了战乱后再次回到长春镇,没有看到白娥身影,只看到井边有一棵浓荫蔽日的百年垂柳。向镇子里的人打听,但是没有人见过白娥,因为白娥的故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白娥姑娘天天坐在水井边,等待一个赶骡队的人,据说那人去南方贩大米,回来时就会娶走她。但是她等啊等,牵骡子的人却没有回来。后来白娥的嫂子逼她嫁人,白娥就吊死在井边的柳树上。“只是有一点,我刚刚讲述的这个故事和洪水没有关系”。这几则故事的共同点是都与“我”祖上刘权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但都隐藏着宿命的观点。接下来作者才继续讲述中断很久的《竹器》的故事:一个老篾匠担着挑子走村串乡卖竹器,路过一个叫大王庄的村子,在村头的水井边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做针线,老太太的针线筐里放着一个河蚌模样的小小竹器,它的口翼处嵌着一圈细小的咖啡色的珍珠。老篾匠认出了那是祖上的手艺,问老太太有没有听说过被一个被洪水冲走了叫长春的镇子,老太太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老篾匠又问老太太竹蚌的来历,老太太道出了竹器是城里的一个年轻人送给她的小孙女的礼物。故事到此嘎然而止。小说充满哲思意味,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对存在的荒诞、对命运的不可知的独特认识和思考。
当然,上述先锋小说试验有牺牲普通读者的可能,但诚如文学大师沈从文所说:“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陋,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在沈从文看来,“具有‘永生意义’的作品是不需普通读者来证实的!” [9]刘玉栋、刘照如、范玮等人正是用不断的先锋小说试验实证心中那个永生的文学之梦。
综观新世纪十余年来的山东乡土文学写作,经历了从以重大题材为重心到取材日常生活的转变,展示了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普通农民、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命运起伏;表现领域更加广阔,扩展到“农民进城”后传统农民形象的嬗变、外来知识分子型基层干部进驻乡间给乡村政权带来的变化以及他们的人生困惑、在城市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传统乡村文化的萎缩等诸多层面;在艺术手法上,新锐作家们对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的文学技巧大胆借鉴,进行叙事的多样化探索,丰富了乡土文学的表现技巧。但他们没有在“叙述游戏”中迷失自我,先锋的形式下蕴含的是对现代人的存在境况的深层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