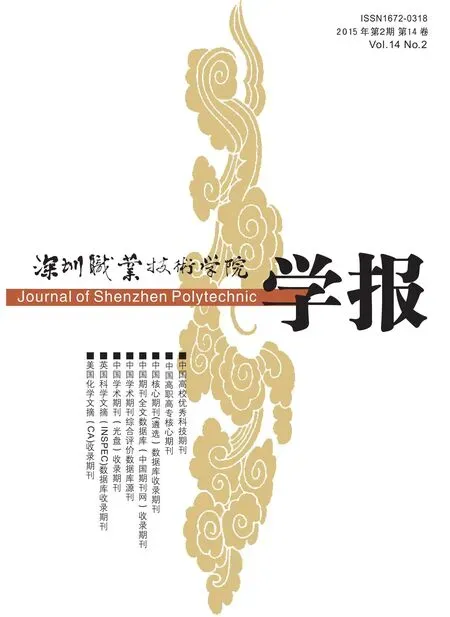论清末民初历史语境中的国家主义
曾 科
(深圳博物馆,广东 深圳 518026)
论清末民初历史语境中的国家主义
曾 科
(深圳博物馆,广东 深圳 518026)
国家主义属于西方政治学的范畴,它传入近代中国时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变异。在清末民初民族救亡的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被视作一种由民族危机所激发出来的抵抗性机制,其“合群”的功能被放大。在革命与立宪的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内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思想方案。中、西国家主义这种相即而又相离的历史现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汇的复杂形态。
国家主义;民族救亡;革命与立宪;民族主义
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思想文化开启了新一轮碰撞与交流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方的国家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引人注目的思想流派之一。然而,当国家主义传入中国时,它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突变。换言之,中国近代的国家主义尽管源于西方,并与之有着某些相似的思想因子,但它不是对西方国家主义的简单移植,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语境对西方国家主义进行了改造和形塑。本文将细致考察国家主义在清末民初历史语境中是如何被理解和消化的。
1 民族救亡语境中的国家主义
一般来说,国家主义属于政治学的概念,是与自由主义相互对立的思想范畴,两者对于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存有不同的知见:国家主义“强调推崇国家理性,认为国家有独自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形式”;自由主义“主张的是有限但却有效的政府,以及严格遵守宪法进行统治的宪政。个人自由与权利要受到更多的尊重与保护,国家的权力则被制度化的机制所束缚”[1]。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家主义的学理主要包括国家目的论和国家主权论,其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1)国家具有伦理性,本身就是目的。(2)国家主权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个体应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权威。
需要指出,国家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它往往溢出政治学的范围而泛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与16至19世纪英、法、德、意等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西方近代政治的世俗化与民族化进程。国家主义的原旨本是强调国家本位,追求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具有正义性与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国家主义逐渐蜕变为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开始鼓吹所谓‘民族优越论’,尊本民族为‘优等民族’,贬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为本国的扩张政策和发动对外战争臆造借口。所以,国家主义至19世纪末发展到极端,已彻底质变为反理性的绝对主义思潮,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则是其实践形态”[2]。
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任务,而要求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正是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因此,国家主义在近代中国民族救亡的历史语境中找到了非常深厚的土壤。从词源上看,“国家主义”一词最初出现在汉语文献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而这个时间段正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急剧深化的时期。1894—1895年,日本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攫取了中国台湾等大片领土及二亿两白银的军费赔偿,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它还刺激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胃口,后者继而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掀起了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潮。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即社会就像生物体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严复在《〈原富〉按语》中进一步指出,组成社会的细胞就是个人,只有每一个人的素质提高了,才有国家的强大,“今夫国者非他,合亿兆之民以为之也。国何以富合亿兆之财以为之也。国何以强合亿兆之力以为之也”[3]。1897年,严复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中文《天演论》,首次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不仅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适用于自然界,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告诫国人,处于强国争胜的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小国家要想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就必须要发愤图强,使自己成为强国,舍此绝无二途。这种观点适应了甲午战争后中国人迫切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思想需求,因而在舆论报章上广为流传。正如胡适所说:“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4]
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清末思想界往往基于人群竞争的角度来理解和认知人类社会兴衰存亡的规律以及中国的现实处境。清末知识分子在使用“国家主义”一词时,往往透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知框架,将国家主义视为人群竞争的利器。较早使用“国家主义”一词,并为它作出定义的知识分子是邓实。1903年,邓实撰在《论国家主义》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者,一国人皆知爱其国,即一国所以生存于世界上之要素也”。在邓实看来,国际社会的竞争异常残酷,“夫同处一球之中,划一土而号之曰国,国与国相对于是,而有国际竞争焉。有国际竞争,则一兴一灭,一盛一衰,此必然之势也”,西方国家致胜的秘诀就是人人皆知爱国。为避免淘汰出局的惨剧,中国“舍实行其国家主义何以也”[5]。
1907年,《东方杂志》转载了一篇《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的文章。该文指出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种族之竞争日烈,龙骧虎视者,莫不磨牙吮血,奋其帝国侵略主义,而以夺人之地,争人之城,竞互市之利权,拓殖民之政策,其所以得优胜之地位者,无他,爱国爱群,同心同力故也”。国家主义正是达成“同心同力”的重要途径,“惟有国家主义盛行,则上下一心,遐迩一体,国人皆互相团结,壮其合群之魄力,发其爱国之精神,然后众志成城,急公仇而缓私仇,先国事而后家事,其国未有不盛其种,未有不昌者也。故欲致和平之幸福,为伟大之国民,必自尊重国家主义始。”[6]
显然,邓实等人所理解的国家主义,是一种激发国民爱国心与凝聚力的动力机制。清末思想界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积弱不振、屡遭欺凌的根源就在于国人缺乏国家观念,不知爱国,“于国家之事、公众之业,可谓痛痒不相关,冷视已极矣。睹民生之多艰,而不知救;任外力之来袭,而不知屏”[7]。1900年,麦孟华在《国民公义》中批评四万万国人“各谋其身,各顾其私”,以致“无一人能知国家之主义,无一人能任国民之公事,宁他日之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为异族之驱缚鞭笞,而必不肯于存亡呼吸之间,少缓其私、少用其力,以赴国民之急”[8]。梁启超发出“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的感叹,指出“部民”与“国民”的重要差异是“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家者也”[9]。当前各国之间的竞争是举国一心、全民一致的国民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故夫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则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二心焉。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过其时而可以息也,今则时时为其性命财产而争,终古无已时”,然而中国人绝无国家观念,“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事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此涣散之国人,“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其将何以堪之?”[10]1906 年10月,《云南杂志》创刊号指出,“夫国民者,富于国家观念,与国家为一体之民也”,但是举国范围内称得上国民“恐悬千分之一以求,而犹恐不及格也”[11]。
为挽救民族危亡,清末知识分子主张将传统的“臣民”塑造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国民的核心特质是富有国家观念,即梁启超所谓的“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梁启超后来接受了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将国家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有机体:“伯氏乃更下国民之界说为二:一曰:国民者,人格也。据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曰:国民者,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而此体也,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家即有国民,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异名也。”[12]梁启超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比喻作身体与器官的关系:“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以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13]这种以国家为最高认同对象的、整体式的国民观在清末思想界非常盛行。麦孟华在《清议报》发表《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认为“国家者,成于国民之公同心;而国家者,即为国民之公同体也。是以欧美政治家之公言,无政权之人民不能与以国民之称,而谓之曰:无国民者,无国家(No Nation,No State);而国民之情感与国家无关系者,亦不能与以国民之称,而谓之曰:无国家者,无国民(No State,No Nation)。国民者,与国家本为一物,异名同实,要不能离为二也”[14]。不仅如此,国家还是国民道德理想的基础和来源。梁启超认为“天下之盛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真爱国者,国事以外,举无足以介其心,故舍国事,无嗜好;舍国事,无希望;舍国事,无忧患;舍国事,无忿;舍国事,无争竞;舍国事,无欢欣”[15]。1903年,《游学译编》发表的《社会教育》强调说:“吾所谓伦理主义,但有绝对之国家主义,而其他诸事皆供吾主义之牺牲;吾所谓道德,但有绝对之国民之道德,而其他诸事皆为吾主义之糠秠。国家者,……有绝对之完全圆满之主体,有绝对之完全圆满之发达。惟国家为绝对体,故民族之构造之也、崇奉之也,有绝对之恋慕、有绝对之服从。”[16]1905年,《二十世纪之支那》出版宣言开宗明义地说:“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17]
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与同时期更为流行的“民族主义”一词几乎传达着相同的含义。1901年,梁启超对“民族主义”解释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8]民族主义也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法宝:“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19]1903年,竞盦在《政体进化论》中强调说:“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先有统一人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者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于吾国之性质之主义焉,无它,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20]
国家主义移植近代中国伊始,便被视作一种由民族危机所激发出的紧急动员机制,它要求全部国人的全部力量急速向最高主体——国家——凝聚和靠拢,缔造一个与国民合二为一、足以应对西方冲击的国家组织。这个强健有力的国家组织宛若霍布斯笔下的巨灵利维坦。鼓吹社会之整合,在西方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本不占重要地位,然而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后,却透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知框架,突出了“合群”的功能。这是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后产生的第一个理论突变。
2 革命与立宪语境中的国家主义
随着清末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特别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后,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逐渐被严格地、有意识地区分开来。
民族主义是革命党关于民族建国的构想,其基本内容是鼓吹排满,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狱中答《新闻报》记者时激进地表示:“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21]后来在《哀焚书》中,章太炎更加明确地指出“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22]。1906年4月,汪精卫在《民报》第2号发表《民族的国民》,强调“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23]。1907年5月,柳亚子在《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国家,自立自治,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24]。
显然,革命派所理解的“民族”,是通过共同的血缘、体貌、地域、语言、文化等原生性基质聚集而成的群体,大致上接近于“种族”或“族群”(ethnic group)。相应地,革命派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更贴切地说是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它主张将不具有同一族群特质(如血缘、语言、文化)的人群排除于国家范围之外,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和攻击性。毫无疑问,这种民族主义的建国方案是与推翻满清政府统治、光复汉族政权的政治诉求相一致的。刘师培强调说“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25],对满族采取排斥的态度。陶成章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因此他在编写《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时采取了“叙事以汉人为主,其他诸族之与汉族,有关系者附入焉”[26]的体例。
革命派强调族群同质性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主张由一个民族单独来建立和组成一个国家,不赞成多个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国家。1903年,《游学译编》发表的《民族主义之教育》指出“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着,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着”[27]。《浙江潮》发表的《铁血主义之教育》,将培育国人的种族观念视为建国的前提条件,认为“无种族思想者,不可以立国。若是乎我同胞欲有国民资格,当先有种族思想”[28]。《游学译编》发表的《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也强调“欲以国家思想造国民者,不可不以种族思想造国民;以种族思想造国民者,不可不悬民族建国主义以为国民趋赴之目的”[29]。1905年,马叙伦在《政学通义》中指出“国之远本在种族,近本在政教;其必种姓同一,其固久。……固辨乎民兽而秩乎种姓,建国之大例”[30]。蒋方震也认为族群的同质性问题不容含糊,“种不能统一,则不能成国,则此种亡;国不能统一,则不复成国,则国亡,而种随之。故曰:民族主义者,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者”[31]。林獬在《国民意见书》中反对多个民族共同组成一个国家,认为“大凡一个国度,总是由同种族的人民组织成功的。一个国度里头,若有两种混合,这就不能够称他为完全的国度了”[32]。邓实将中国历历史上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思想传统视为中国立国的“正气”:“夫神州旧学,其至粹者曰道德;道德之粹,其至适用于今者曰正气。正气者,天地之精,日月之灵,而神州五千年所以立国之魂也。自古以来,夷狄乱华,中原涂炭,国破家亡,何代蔑有?而忠臣义士,节妇烈夫,杀身成仁,至死不悔,为风雨之鸡声,为岁寒之松柏,卒以留正朔于空山,起神州之陆沉者,何莫非一息之正气有以维系之哉?”[33]
与革命派鼓吹民族主义不同,立宪派宣传的是国家主义,基本内容是主张调和满汉矛盾,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立宪派重要人物梁启超早在1903年时,就主张国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个大的国群。不过他当时用的名词是“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者也。”当排满革命思潮高涨后,“民族主义”几乎成了排满革命的同义词,梁启超正式用“国家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民族国家思想,并有意识地将它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1906年,梁启超在与革命党《民报》的论战文章中写道:“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34]梁启超还特别说明了放弃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重要原因:“吾认民族主义为国家成立、维持之不必要,故排斥种族革命论。吾以为若从国家之成立维持一问题着想,则民族主义赘疣已耳。”[35]
在立宪派的报章文字中,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处于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1907年,一份鼓吹“统合满汉蒙回藏”、“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大同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报第5号发表的一篇《中国政体变迁论》指出,根据英国学者甄克斯关于人类群体进化的学说,人类组织形态的进化可分为“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三个阶段;“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多个民族共建一个国家”的国家主义思想则是国家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之本为宗法者,则于民族主义内而忽搀以国家主义,不可谓非社会之进化;在社会之已进于国家者,则于国家主义内而又搀以民族主义,却适以成其社会之退化”。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逐渐步入军国社会阶段,因此按照社会进化的原理,中国应该采取国家主义,摈弃民族主义[36]。《大同报》第2号发表的《中国之排外与排内》强调说,宗法社会“只知保守己之种类,而排斥他种族,且不知并吞他种族以扩张其国家”,军国社会则反是,“其主义在兼容并包,以张大其国家。异族之来也,不排斥之而收容之,岂惟其既来而始收容之?即其未来处于国外之异种人民,且将用手段以牢笼之,用兵力以兼并之,种族虽不纯而国势固张大无比矣”[37]。在立宪派看来,革命派所鼓吹的民族主义适足以酿成国家的分裂。若汉人持民族主义来排满,满人持民族主义来排汉,“不问能达其目的与否,就使达其目的,则国土必使缩小,人民必使缩少,……又必使各族分立,各自成国”[38]。中国处于列强环伺的艰难处境,“救国之政策必以国家为本位,谋全国民之幸福”,而不能以某一民族为本位,“凡我全体国民,亦岂能专谋其本族之利可以生存者?中国此后各种民族又安有自削其手足排斥他族,能以一族立国者?”[39]
在陈述了反对单一民族建国的理由之后,立宪派接下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血缘、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国内各民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07年,《大同报》第4号发表的《民选议院请愿书》主张通过颁布宪法、开设国会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使满汉蒙回藏各族人民处于同一之地位,担负同一之职务,权利义务一切平均,种族猜疑,自然融化”[40]。《大同报》第5号发表的《蒙回藏与国会问题》提出“合中国地盘上所有之人民为一完美之宪法,造一大军国制度,消灭其民族的思想,而确立国家之基础,所谓国民的是也,完成秩序的结合是也”[41]。试图通过颁布宪法、开设国会等近代新式政治建制,将汉、满、蒙、回、藏纳入同一个政治架构中,进而塑造成为政治上高度同质化的“国民”,所谓“满蒙回苗藏与汉人为种族则异,而为国民则同”[42],这是立宪派国家整合思想的基本思路。国家整合与立宪改革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1907年,蒋智由在《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一文中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43]。1906年,《新民丛报》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指出:“今世立宪各国,无不包孕各种之民族,以结合于一国家之下,而不闻发生种族问题,……则以国家之利害为本位,而不以种族之利害为本位。……况近世各国所谓帝国主义者勃兴,民族主义已为前世纪之遗物,今持分裂的民族主义以与各国之帝国主义相竞,几何而不为其帝国主义所蚕食也?”[44]
由此可见,立宪派主张组成国家的主体应是“国民”,而不是革命派所鼓吹的“民族”。梁启超认为“民族”与“国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族民’或‘民族’(德文为Nation,英译作people)者,系一文化、历史与社会之名词,其所赖以存立的基础,在于血统、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根基性的联结纽带’;而‘国民’(德文作Volk,英译为nation),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乃构成一个国家的实体与主体,其得以形成,必赖一有意识的政治作为与一套明确的法制结构,俾人人得以参与其间,共建一国”[45]。虽然革命派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终于推翻了满清政府,然而民国建立后却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并制定约法、开设国会,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立宪派“国家主义”的方案。民初各政党大多将“国家主义”写入自己的政纲,如统一党主张“融合民族齐一文化”,统一共和党主张“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国民党主张“实行种族同化”,共和党主张“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进步党主张“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46]。因此,在清末革命与立宪的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内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思想方案。这是西方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后的第二次理论突变。
3 余 论
国家主义传入近代中国之际,它所遇到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理论上的突变,然其基本特质还是得到了保留。前已论及,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政治学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准确地把握了这条理解国家主义的主线。上引邓实《论国家主义》一文,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作者称之为“平民主义”)视为对立的两个学说系统:“十八世纪之末法儒卢骚出倡平民主义,其主义盛行于十九世纪。十九世纪之末,德儒伯伦知理出倡国家主义,其主义盛行于二十世纪。故昔也重个人而轻国家,以谓国家由人民结契而成立者也。人亡则国隳,故不惜牺牲国家之利益以为人民,今也重国家而轻个人,以为人民恃国家保护力而生存者也。国墟则人奴,故不惜牺牲人民之利益以为国家。”并认为“国内之竞争,个人与个人战,则宜用平民旧主义;国外之竞争,国与国战,则宜用国家新主义。今日者,大地之上战云六七横蔽,五洲之方面为国与国战之时代,则平民主义代谢,而国家主义方飞跃之秋也。”实际上,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的说法,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就已出现。是文对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伯伦知理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有如下评说:“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47]
因此,中国近代的国家主义尽管在源头上起于西方的国家主义,并与之有着某种相近的思想基因,但同时又受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制约,从而形成了某些异于西方国家主义的特点。中、西国家主义这种相即而又相离的历史现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汇的复杂形态。
[1] 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6.
[2] 王发臣.近代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研究[J].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16.
[3] 严复.严复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917.
[4] 胡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0.
[5] 邓实.论国家主义[J].政学文编,1903(1):17.
[6] 佚名.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J].东方杂志,1907(8):20.
[7] 梁启超.论功名心[J].新民丛报,1903(37):29.
[8] 麦孟华.国民公义[J].清议报,1900(48):1.
[9] 梁启超.新民说四·论国家思想[J].新民丛报,1902 (4):3.
[10]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J].清议报,1899(30):4.
[11] 墨之魂.地方自治之精神论[J].云南杂志,1906(1):1.
[12]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J].新民丛报,1903(38):8.
[13] 梁启超.新民说一·叙论[J].新民丛报,1902(1):1.
[14] 伤心人.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J].清议报,1900 (67):9.
[15] 中国之新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J].新民丛报 1902 (6):12.
[16] 全民.社会教育[J].游学译编.1903(11):2.
[17] 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J].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1):2.
[18]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J].清议报,1901 (94):8.
[19] 梁启超.新民说二·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J].新民丛报,1902(1):2.
[20] 竞盦.政体进化论[C].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545.
[21]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C].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233.
[22] 章太炎.訄书·哀焚书第五十八[C].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155.
[23]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C].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100.
[24] 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C].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0:814.
[25] 申叔.论留学生之非叛逆[J].苏报,1903(1):1.
[26] 陶成章.中国民族消长史[C].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12.
[27] 佚名.民族主义之教育[J].游学译编,1903(10):19.
[28] 霖苍.铁血主义之教育[J].浙江潮,1903(10):23.
[29] 佚名.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J].游学译编,1903 (11):28.
[30] 马叙伦.政学通义[J].国粹学报,1905(9):17.
[31] 蒋方震.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1903(1):1.
[32] 林獬.国民意见书[C].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0:892.
[33] 邓实.正气集序[J].国粹学报,1906(13):22.
[34] 梁启超.杂答某报[J].新民丛报,1906(86):18.
[35]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论[J].新民丛报,1906(79):21.
[36] 文元.中国政体变迁论[J].大同报,1907(5):12.
[37] 佚名.中国之排外与排内[J].大同报,1907(2):15.
[38] 恒钧.中国之前途[J].大同报,1907(1):19.
[39] 隆福.现政府与革命党之比较[J].大同报,1907(5):13.
[40] 佚名.民选议院请愿书[J].大同报,1907(4):5.
[41] 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J].大同报,1907(5):1.
[42] 直觉.国民主义[J].牖报,1907(4):4.
[43] 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J].政论,1907 (1):1.
[44] 兴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J].新民丛报,1906(92):12.
[45]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28):21.
[4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26.
[47]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J].新民丛报,1902 (1):2.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ENG Ke
(Shenzhen Museum,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6, China)
As a term in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ism was introduced to modern China, a historical contex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st. The transplantation of nationalism into China resulted in certain theoretical chang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ism was regarded as a defence mechanism in national crisis, with a magnified power of “Unit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revolu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nationalism advocated national unity and state sovereignty. The intermingl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western world somehow reveals how complex the interaction of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gking can be.
nationalism; national salvation; revolu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 nationalism
D693.7
A
1672-0318(2015)02-0035-07
10.13899/j.cnki.szptxb.2015.02.007
2014-10-01
曾科(1985-),男,湖南常德人,历史学博士,深圳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改革开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