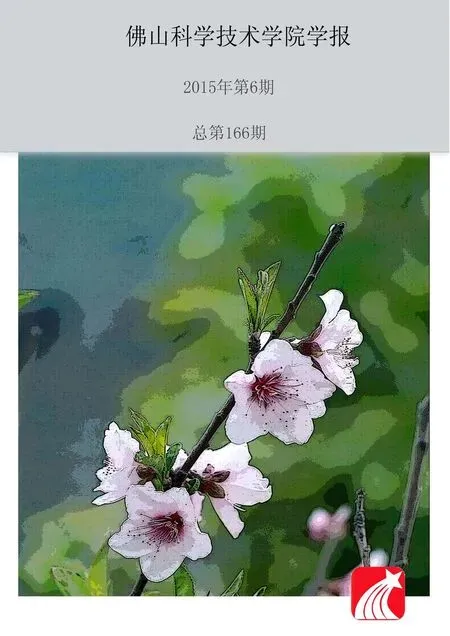道路与瑶族村寨的文化变迁
——以广东连南南岗和油岭瑶寨为例
朱卿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道路与瑶族村寨的文化变迁
——以广东连南南岗和油岭瑶寨为例
朱卿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近年来,对道路的研究不断深入,甚至催生了“路学”(Roadology)。道路不仅是地理景观,还是一个复杂的象征系统,承载着多重功能。以在广东连南南岗和油岭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对道路的记忆、围绕道路的互动、道路的经济学、道路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道路在民族文化变迁的初期扮演者先锋的作用,而到了变迁的后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纽带的作用。
道路;瑶寨;文化变迁
引言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510鲁迅先生所言,生动地形容了道路从无到有的“进化史”。“地理景观首先指的是不同时期地球形态的集合。地理景观不仅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地理景观就像文化一样,是这些因素的集中体现。”[2]19道路作为一种重要的地理景观,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而延展,是一个自然人化的过程。道路是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直观呈现出来的地理景观,同时又是一个多主体交互形成的、复杂的动态空间,对于道路的研究甚至催生了“路学”(Roadology)。周永明以汉藏公路为例,旨在从公路的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四个方面展开建构一个全新的“路学”研究框架。[3]14对于道路的人类学研究也是近些年新兴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除了周永明对“路学”的积极倡导之外,如朱凌飞《修路事件与村寨过程——对玉狮场道路的人类学研究》[4]69-78、赵旭东、周恩宇《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型塑》[5]100-110、宋婧《“大通道”与“小城镇”——对甘庄道路的人类学研究》[6]等从修路事件、族群关系、文化变迁等角度开展了人类学个案的研究。
随着技术的突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全天候公路、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互联网等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应用,因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形成的时空阻隔被迅速压缩。在不断扩张的交通网络上,其中又以全天候的公路的延展最为迅速,其触角最为密集,延伸的最远,影响也就最大。恰如前文所言,公路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存在,从其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等方面被赋予了诸多属性,构成一个复杂的象征和互动体系。同时,公路修建之前的小路(如乡间土路、田间小路、上山小道等)的属性和意义随之也发生了改变,呈现出了与大路相应的象征和表达的系统。
一、景观与记忆:路的大与小
南岗和油岭位于广东省西北部的排瑶村寨,属于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地处海拔700-800多米的丘陵山腰上,为从隋唐以来陆续从湖南等地迁来粤北地区定居的瑶族形成的村落,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南岗村距离县城约26公里,目前有开通一条从县城到南岗千年瑶寨旅游区的盘山公路,可以供大型客车通行,该公路是由省政府拨款400万元,县政府出资300万元修建(包括修复古排的费用),并于2003年前建成通车,主要是为了南岗排旅游景观,发展民族经济之举。油岭村距离县城约18公里,目前也有一条从县城到油岭老寨的公路,由于油岭老寨位于海拔较高的山顶上,目前开通的公路(广东青年志愿者路)是由是共青团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开展扶贫攻坚战,由多方筹资60多万元修建,公路全长5.5公里,落差840米,于2000年10月建成通车,大部分呈之字型上升,上下山最多能走中型客车。
由于瑶寨中房子为依山势而建,到两个寨子的公路都止于寨门前的小块平地上,在寨门这里形成了大路(公路,主要供机动车行使)和小路(石板路、田间小路等,主要供人、畜等行走)的分野,公路犹如人体的动脉,而在寨门的背后道路并没有消失,而是像人体毛细血管般的小路,到各户门前,到田地,到山上。寨门犹如门槛一样具有过渡的意味,从一个性质的空间进入另一个性质的空间的过程,进入寨门意味着从外部世界进入社区,寨门也将道路分割为公共的空间和社区的内部空间。同时,大路主要是指车路,能够保证机动车辆的通行,大路是有尽头的,而小路则是可以四处延展的,大路抵达的范围是有限的,大路的成本是远高于小路的,大路是远非当地的社区所能够实现的,通常为外部力量(一般为政府)实现的,修路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说大路构成一种通达,那么小路则可以构成一种景观,甚至意味着一种冒险的经验,当地居民和游客对小路的情感上出现了一种不同情感向度。游客通常来源于城市,习惯了大路和发达的交通体系,小路(如曲曲折折的石板路)则成了摆脱日常的一种另类的体验。而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大路更多意味着一种交通的便利,而小路则被赋予更多的情感内涵,而这种情感是不同于大路的,小路在其童年记忆被多种情愫所缠绕,一方面意味着很多童年趣味,另一方面又饱含着艰辛的感受,如在笔者访谈对象中,接受采访的村民就表达出,小时候走小路到县城要走四五个小时,甚至耽误了母亲病情的治疗。因此,路的大小不仅是民众眼中物质景观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成了民众对文化变迁记忆的重要载体。
二、山上与山下:围绕道路的互动
瑶族作为比较典型的山地民族,以连南为例,瑶族分布于占全县面积88%的山区,有“百里瑶山”之称。南岗和油岭两个瑶寨也不例外,虽然不像通常的山地民族那样较为频繁的迁徙,而是较早地从事定居生活,但其定居地也主要在山腰、山顶等地区。在瑶寨内部,从寨脚到寨顶由石板路铺成,将村寨的房屋联结在一起,同时向山上的盘王庙和田地联结在一起。在山寨之外的山路主要为所谓“人走得多了而形成的路”,直至2000年之后才陆续修通公路,在国家的公路等级序列中显然属于乡村公路。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中原王朝将权力不能达到的地方看作不文明的“蛮荒之地”,也即“化外”,而这显然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后果。山地的居住环境和道路的路的不通或是阻隔,最大程度保持了其自给自足的状态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一种自我隔离和保护的机制。而随着1949年之后民族政策的调整,为彰显新国家的形象先后实施了民族识别、制定民族政策等国家行为,尤其民族自治地方政策的提出,诸多涉及民族地区的行为被赋予了“民族”、“扶贫”等标记。一句“要致富,先修路”又深入人心,道路自然而然也具有了这些标标记,无论是南岗修路时为了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还是油岭为了打响扶贫攻坚战而修通的青年志愿者路也都具有这样的特性。然而,这也仅是道路的属性的一部分,笔者更关注的是道路的修通之后引起的变化。
道路意味着一种联通,意味着流动。道路的修通,首先逐渐打破的是因道路不便带来的阻隔,同时也意味着人和物具有了更强的流动性,进而压缩了瑶寨与外部世界的时空距离感,而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又促成了这一过程的加速实现。因交通工具的使用,大与小的差异也再次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是否能通行汽车成为重要的标准。在笔者前往两地的过程中,笔者看到在公路上来往的客车和运货的卡车,还有出行便捷的摩托车等机动车辆。道路的开通和机动车辆的使用带来最直接的变化,便是从村寨到县城的便捷性和时间的压缩。笔者在南岗采访一位年龄在20岁的年轻人时,他说,在他小时候的印象中,也就是在没有修建硬化的道路之前,主要为山路,进一次县城约要5个小时左右,而且主要为步行,半年也就到县城五六次,而且他也就走过一次,而且是小时候,那会儿大人会背着,后来骑单车也要很久,再后来是骑摩托车。在大路修通之后,现在一般有需要就可以来县城,通常可以做到一个月来往于县城五六次,可以坐客车或是面包车,车费也就六七块钱。当然公路的修通带来的变化不止这些,建国初期就有村民陆续搬到山下较为方便的地方,而路的修通加速了这个过程,同时改变了寨子的建筑格局,从原来的依山势而建而变为沿着交通线而修建。
通过访谈了解到,由于旅游开发,南岗老寨中则只留下20多户80来人常住,而油岭共有244户700多人生活在老寨中,然而很多搬到新寨中居民还在老寨中保留着房屋得和田地的产权,或是因为家里有老人生活在老寨中,因而部分居民也因交通的便利过起了“双城”生活。以南岗为例,现在瑶胞主要是居住在山下的新寨,只有十几户居住在老寨中,而老寨又是旅游景区,这些在景区从事各种工作的多数瑶胞也过起了“双城生活”,居住和工作构成了不同的区隔,而这种区隔的联结便是道路,一条回到老寨,感受老寨,感受传统的之路,同时又是一条工作和谋生之路,一条“赚钱”之路,实现的历史与现实的共时勾连。山下的新寨的房屋也是沿着道路两侧进行布局,这也不同于山寨上依着山势进行布局,由一种组团式的分布转换成了一种线性的分布格局,道路带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勾连和变化。
道路的修通,推动了从山上到山下的过渡,同时由山下到山上的空间边界的控制逐渐消失,山上不再是所谓的“化外之地”,同时也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的地融入更大的社区之中,便再也不是当地居民完全占据沟通的主动性了。虽然当地的公路处于国家公路等系序列中的乡村公路一级,但是其所联结的是通向外部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以笔者为例,家乡在河北,上学在云南,而最终能到达南岗和油岭则有赖于发达的道路网络,至少个体的进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在笔者在南岗和油岭的两位访谈对象,都有到外出打工的经历。交通、通讯等“消除距离技术”发展,尤其是道路的变化改变了个体的时间体验,呈现出一种时间被压缩的感觉,在个体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一个人的活动范围、“生命厚度”被拉伸,由一种简单的日常的农业生活逐步被裹挟到工业社会之中,成为巨大社会结构中一个“螺丝钉”。同时,道路也增强了其瑶胞的流动性,以及城乡之间互动的频率,由个体进入县城的频率带来的是城乡居民之间多种方式的互动。
在个体生命体验得到了极大地拓展和丰富的同时,原有的“桃花源”式的生活状态也注定要被终结。道路的开通不仅意味着是一条出去的路,同时也是一条进入之路,形成的是一条进出的双线结构。以瑶寨为例,道路的开通意味着旅游开发者和旅游者的成规模的进入,同时原来的村民也走出原来的村寨,被“重新”纳入到公众的视野之中来。同时,也预示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的迅速扩张,道路的延伸成为了那些曾经过着完全或基本上完全与外界隔离的群体慢慢地向现代化的外界靠拢过程中看得见的线索。道路修通的过程加速了这个社群不断向着外界靠拢的过程,包括衣食住行等诸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而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和外部进入的人员和商品正是他们向外部世界靠拢的重要途径之一,透过瑶寨中村民的服饰穿着便可窥知一二。
对于社会发展,道路在提高通达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地区的自治性,国家治理制度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其中最显现的一项便是教育,在民国时期,“当时瑶区也有几所简易小学,但时断时续;另有少数私塾,每间私塾学童多则10多人,少则三五人,均由先生公(宗教活动主持者)授课,日授《瑶经》一二小时而已,瑶区文盲率达99.5%以上。”[7]8而现在的状况或许也并没有十分大的改变,以油岭为例,目前老寨只有一个到三年级的小学,且只有两位老师,而较完整的小学则在油岭新寨。在访谈过程中,好多村民都表达了为了孩子上学才搬到新寨的想法,学校的布局则又以区域内的中心和交通为依据。即便在现在,我们也会时常听到大山里的孩子为了上学走好几里的山路,因而当地家长为了孩子教育而搬到新寨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教育恰恰是接受国家文化大传统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三、上山与下山:道路的经济学
道路带来了生计方式的多元兼容,随着道路的开通,农村和城镇之间进行沟通的频繁,从而使得当地的居民不再把自己与田地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如客货运输、旅游商品的经营等越发增加。由于公路具有公共性质和全天候性的特点,公路上所行驶的车辆并不能由当地村民所决定,然而其实现对道路的“占有”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道路构成一个流动的社会公共空间。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田埂和公共道路,就是交通用途而言,像水路一样,不是任何人的特有财产。任何人不得阻拦公共道路或田埂上行走的任何其他人。但是道路和田埂也用来种菜。这种道路和田埂的使用权,是对此有特殊权利的家所专有的。因为公共道路要通过各家门前的空地,这空地是用来堆放稻草、安放缫丝机和粪缸、安排饭桌、晾衣服的地方,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每一家都有把道路作为这些用途的特权。”[8]156因此,道路的公共性质及其具有的特殊使用权,也就成了多主体互动的集中显现之处。
在笔者访谈过程中发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南岗千年瑶寨景区内的石板路不仅成为一种景观,还具有了商业“开发”的价值,就笔者观察而言,各式摊位布满了石板路的两旁,恰如费孝通所言村民对于自家房屋前的道路具有特殊的使用权,而这种使用权又与作为旅游开发主体的旅游开发公司要求公共道路整洁、不允许随便摆摊的要求是相冲突的。同时,这种特殊使用权也有其局限性,不能超越自家的门前道路的范畴,据访谈对象讲,在村寨中出现过由于山上村民到山下摆摊而出现冲突的现象。在油岭,在从新寨到老寨的道路上,立着一块大意为“油岭老寨还未被开发,路况复杂,请谨慎驾驶”之类的警告语,诚然在这里并没有设置路障,阻止其他非本地车辆驶向油岭老寨进行观光,但是通常这样一个警示便给不熟悉路况的外地司机一个“下马威”,而这恰恰成了当地居民获取利益的一个有效途径,即通过收费搭载乘客往返于油岭老寨和新寨之间,从而实现了对这段路的“特殊使用权”。
四、先锋与纽带:道路在变迁中作用的探讨
从山上走到山下,从山下走进城市,沿着道路塑造了一个人的生命史。道路上的足迹构成了一个人的活动空间和生命阅历,更是带出了一个生命轨迹。而道路的命运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小路的命运,正在落入鲁迅先生所言的对立面,在过去的时间里形成的小路走的人越发少了,小路也就随着时间流逝也就慢慢消失,掩映在荒草丛中,或许只是成了故事中的点缀。作为大路的公路成为大传统进入的载体和通道,从一种边缘状态融入到国家文化系统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同时,小传统的又不断继续着自我生产和保护。道路的修建是一种国家意志,不是某个个人的想法,是以国家的规划和财政收入推动的一个过程,道路的延伸的方向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家的意图。于个人而言,道路也意味着一种延伸。在这种过程中,小路和大路便构成了一种对比,小路是对大路的一种不驯服,是通过另一种方式的实现,但是实现方式是有差异的。有时候小路代表一种便捷的、私人的、非官方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规避和遁逃的意味。而大路代表的是另一种便捷,集体享有的,但它是官方的,一种公共的,甚至是受监视的。但无论是大路或者小路都是一种通达的方式,有其各自的表达需要。
经济一体化的需求催生了道路的延伸,随之而来的人流和物流则构成了催化剂,催化了民族文化的变迁,又因为是少数民族,这种融合就带来了民族主义的疑惑,于是有些人就想保住这些所谓“民族文化”,但是瑶胞也有现代化的需求表达,走出山区,享有现代化带来的便捷舒适的生活,而道路恰是这些诸多表达的焦点。在笔者看来,道路在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初期更多地是起一个先锋的作用,而到后期民族文化融合得更加深之后,其作用更多地是起到一种纽带的作用,所谓的“弹持”的文化现象就出现了,这时文化又会做出相应的新的自我调整,从而来适应新的社会状态。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的生产、使用与消费[J].文化纵横,2013(3).
[4]朱凌飞.修路事件与村寨过程——对玉狮场道路的人类学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3).
[5]赵旭东,周恩宇.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型塑[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6]宋婧.“大通道”与小城镇——对甘庄道路的人类学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4.
[7]连南瑶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连南瑶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戢斗勇jidouyong@qq.com)
The Road and Cultural Change of Yao Village——taking the Yao village of Nangang and Youling in Liann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UQing
(School ofthe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China)
In recent years,the research on the road has been developed and the term of“Roadology”emerges. The road i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landscape,but also a complex symbol system,carrying multiple functions.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the Yao village of Nangang and Youling in Liannan of Guangdong province,the paper analyzes the 4 aspects:the memory of the road,the interaction around the road,road’s economics,and the role of road in cultural changes.The paper insists that in the early cultural changes of ethnic groups the road plays a role of pioneer,but in the later,the road works as a bond.
road;Yao village;culture change
K892.25
A
1008-018X(2015)06-0038-05
2015-08-22
朱卿(1990-),男,河北卢龙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