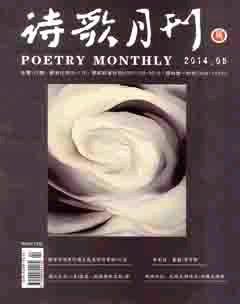新诗与自然
高春林
自然,即诗。这不是单纯的溢美之词,重要的是一种呼应关系。很难说,哪个诗人,他的词不与自然发生关系。我们的时代不再是一个田园诗的时代,机械、技术、楼柱,在高强度灯光下,城市复制着城市,文明颠覆着文明,破碎之处也即词语疼痛之处。我在诗中写到“弯道上,王维和明月都不见了。”“我也想做王维不做杜甫,但是行吗?”自然在转移。一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都市镜像在揭开它的魔术花脸……。我的高速路途,我的人造彩虹桥,我的词语亲戚,都在城市和矿区的外延中烙上了现实的拓印。自然是什么?自然,一直在那里存在着,那是一个国度,由一小片一小片卑微的风景构成,不为我们的语言所动摇——自然不是艺术——在现实和超验的世界之间,诗作为一种象征,在赋予自然这个物象以某种意义。亚里士多德说,比起历史的真实,诗更为真实,诗提供意义的真实。我也可以说,相对于现实的可信,自然更为可信,它至少远离了现实的废墟让世界有了蓬勃的一面。我不想提起过多的厄运、片面、专断和灾难性的际遇,那多半发生在人类之中的社会漩涡。词就像灵魂,在寻找着它的根,寻找着未来。自然,在这时给它带来了一个出口,带来了一面可以参照或后视的镜子。
这个出口不是逃逸。王家新有一句诗:“一个在深夜写作的人,/他必须在大雪充满世界之前/找到他的词根。”这就是意义所在。我在我的林间空地上走动,我可以自由地呼吸。当然,这不是说诗歌仅仅停留在自然之上,毕竟生活还有另外的出口。这里强调的是,自然中的诗意,是任何生活和出口都不能替代的。自然作为一个师者,始终在对我讲话,赐予我水性的词,让我发现并说出。为此,我有时会抛弃后现代的猪仔不去喂养,宁愿在山林里寻找自己的河流。在这里,有一种背对破碎、面向自然的姿势——前边越是美好,越想把身后破碎的处境抛远。这让我对自然有了更深的情感——不仅是我,很多诗人都不能置身其外。就连曼德尔施塔姆谈到“词分享着面包和肉体的命运:苦难”时,也先谈到自然。他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新的自然、灵魂的自然那温柔的存在中得以延续。在这没有人的精神的王国中,每棵树都将是女神,每一现象都将谈起自己的变形。”
2
我曾经参加一个“鸿爪寻踪”之旅
沿着漫长而久远的路途寻找苏东坡的足迹。因“流寓”生活,苏轼走过太多的地方,而今那些旧貌风霜在飘摇中有许多已荡然不存了,但是诗歌的影子依稀还在他生活的那个自然场景中唤醒着某些记忆,构成一个地方的诗歌地理。当再次站在我生活的小城
苏东坡归焉的那片林地时,我重获无限的亲切感。我在想,苏东坡作为一个“流寓诗人”,他从政治中心流放到了远方,退隐到了山水自然之中,即便是在那个年代,他的诗,在重构生命的同时也在对抗世界。作为诗人的苏轼完成了他的精神拯救之路。现在,庆幸的是:我作为苏轼的守林人,在这里住了十年、二十年,这让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亲近着一种精神、亲近着自然。我那一个系列的《自然书》的诗或许是这种词与物的关系的明证?我姑且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拯救,看作是对现实的对抗。是的,对抗。
当然,必须说到这种内在的对抗关系。自然中的诗意一直都在无形地对抗着现实,这并不是我一厢情愿的诉求。这是诗歌的个性,是我们的词在现实和自然之间的一种挑衅。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词有着一种不自觉的宿命感,另一方面又要打破这个局限,在当下的状态中开疆拓土,找到它的光亮。自然,对于诗人来说或许是万物之像的幻化,是一个依托的山体。我特别羡慕俄国另一位作家米·普里什文。能够带着倾听乌兽之语、草虫之音的异能,翻阅《大自然的日历》,他说,“歌德错了”,人能创造的是无个性的机械,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有个性地变化着。“数百万年以前,我们失去了像白鸥一样美丽的翅膀,”在他眼里,鱼的畅游、会飞的种子飘落各处,都是我们人类先前丧失的本领,人和自然存在同一血统。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以亲人般关注的力量来恢复这种关系”。这是一个真诚的诗人,以敬畏之心还原着词语的品质。而现代生活的一个隐忧是,现代性在破坏着自然的诗意。譬如鲍曼说的:“只要现代性(即永久的、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成瘾性的现代化)还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现代性的全球霸权终将自食恶果。”那废弃的生命所带给人类生存空间的问题上升到一种毁灭性的恐慌。或许这是另一层面,社会学家的话题。但我们的词语似乎绕不开这个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灾难性话题。词的力量,在于寻找着,而且持续抗拒,直到一种光亮到来。
3
我们都在寻找着这样的光亮。我的诗歌中《自然书》部分倾注了很多自然的情愫,比如我走过的湖泊、河谷,或者宿在山崖的某一个星空之夜。在我的诗中,这不仅是我倾听世界的一种方式,更是情感的一个站点、诗的后视镜的一个反观点。在这里,我不再是一个蒙着面具的人,我是一个恣意的人,无拘无束的人,脱离了社会状态拘限的人。我相信,这是诗歌的一个路程,也是自然带来的的一种境界。这个路程,是从世界返回的路,反之也可以说成通往世界的路。最终通向的是一个黎明——当走出现实的废墟之后,当诗的光亮开始照向内心之时,期盼已久的明澈之境到来了。
”我清晰地读着贝壳,草叶,星辰/在天空的大路上我的对抗无用了……”埃利蒂斯有着更精到的理解。他的自然中的“对抗无用论”是那种一切归真的心,是实现了的拯救,是赞美式的逍遥。他曾说:“自然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在当今技术的时代,自然已屈居第二。如今的年轻人对自然无动于衷,认为它是一种平板、冷漠的东西。而我认为,人们无论从哪一种途径去寻求真理,最终都责无旁贷地回归自然。”对于我们的写作来说,词与物在彼此寻找着。自然,和自然中的树木、河流、乌兽还在幻化成物象,和世界、和我们的内心发生着关系。这是一种合理的逻辑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有着陶渊明的《闲情赋》、宋玉的《神女赋》的写作传统,也是合理的,而且我相信,这种传统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社会形态下的琐碎中,我们内心的反抗在增加,而我们的空间在挤压中,寻找精神的出口就成了一个人——不,是一群人的意志。这个使命,就交给了词以及承载这些词的物象,这是拯救的过程。走过了这个路途,是澄明的逍遥之境,还是借用苏东坡的一句话:“余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自然有太多的内涵。别向诗歌要求太多。它们之间一直在呼应,在互为角色,在唤醒与被唤醒,它们彼此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