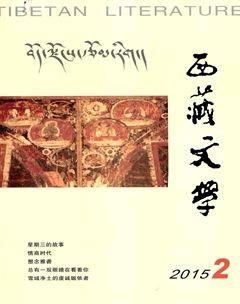雪域净土的虔诚皈依者
汪璐
楔子
2013年8月,拉萨最美的季节。
古老的琉璃桥不再是进出拉萨的要道,一个年轻的《唐卡学术邀请展》悄然在此举行。区内外知名画家云集,他们或精研于唐卡,或仰慕于唐卡,或只是来感受一下这浓厚的艺术氛围。
人声嘈杂中,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瘦高老者忽然大步向前与人丛中另一位中等个子、面容清癯的老人紧紧相拥,温暖的微笑掩不住各自的激动……前者是著名国画家、73岁的余友心,后者是誉满藏区的嘎玛嘎赤派唐卡最杰出的传人、国内外公认的世界级画家嘎玛德勒先生,此刻嘎玛德勒已经是82岁高龄。
跨过三十年的时空,两位老人都从人生盛年走到了各自艺术的巅峰,成为一代艺术大师!时光仿佛在那一刻穿越,艺术交汇的光芒感动激励着无数画坛后辈。
岁月历练艺德,令其熠熠生辉。一个“果”的蒂结总伴随着许多的“因”的机缘,且视为这篇文章的楔子吧。
抉择
1978年,余友心为所在单位立了件不小的功劳,作为奖励,不惑之年的他获得单位特许,赴西藏采风。
西藏,在仓央嘉措的诗歌里,余友心是感受过、沉醉过的,他很热爱先圣那些飘渺多情的句子,也自诩为仓央嘉措的粉丝。可是仓央嘉措毕竟是活佛的身份,在他笔下,即使描写凡尘也笼罩着几分偈语的味道。所以终究,余友心还是渴望自己能够脚踏实地的去解读西藏。
之前,他曾鼓励自己在美院附中执教时教过的学生韩书力到西藏施展抱负:“那里人少事情多,你去了会找到很多可做的事!”
初次进藏的时间定格在1980年。余友心因为有个学生可以“投靠”,所以并不担忧。当时韩书力正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藏分会秘书长。
后来半年的时间里,师徒两走遍了扎什伦布寺、白居寺、萨迦寺、夏鲁寺等后藏著名的寺院,这些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壁画,饱足了他们的眼福。同时他们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百姓,体验了后藏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这一番行程也为这对师徒之前的十多年和往后的三十多年做了最好的链接,成为西藏画坛的一段传奇佳话。
返回北京不久,余友心的单位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也加快了体制革新,并希望调他到王府井大街的北京画店任职。
当时的北京改革发展充满机遇,也是国内最早开放美术界的地方,北京画店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涉外画店之一,此议一出,业内的朋友们哗然:这可是与美元打交道的工作啊!
就在各种羡慕的眼光纷纷投来之际,余友心却选择了果断辞别,导致他的朋友百思不解地抛下一句:“这家伙有病!”
和以往的采风不同,这次经历他却再没能忘记。为了追寻西藏质朴、本真的艺术,他干脆让自己成为了雪域净土一名虔诚的皈依者……这样的结果他未曾预料,却感觉这才是自己冥冥之中一直想要的。
从那之后,他再没打算离开,理由简单且厚重:西藏可以让他以身相许、寄托终身!这种情分甚至超越了爱情和亲情,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
西藏,接纳了这名虔诚皈依者的相许……
“西大荒”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号称“西大荒”的西藏文联院内,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藏文化小气候,弥漫着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浸染其中的余友心得以和西藏各类文化人物广泛接触。
文联大院坐落在拉萨西郊一处茂密的树丛里,当时那里有一片清风摇曳的芦苇荡增加着院中空气的湿度,有一口压水井供大家洗衣做饭。人们开荒种菜、自力更生,蔬菜不够时还在院中挖可吃的野菜,谁家做了好吃的也相互招呼……那份生活是简单纯净、安宁和谐的,大家却在各自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充满了生命力,似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塑造着不一样的自我。
从1983年到1988年的五六年时间里,余友心就在这个“闹中取静”的大院里工作生活。优美的环境和人文关怀舒展着他的身心、笔墨……那样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很少去回忆,因为从来都清晰无比。
那时的西藏文学艺术界有一批激情燃烧的作者,热烈追寻着义无反顾的理想,特别是青年人在创作手法上的探索精神在国内掀起了不小的影响……《西藏文学》编辑部人很少,作为美术编辑,余友心常常要兼一些文编的工作和理论写作。大量翻阅他们的文稿,不仅开阔了视野,还全方位地了解了西藏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余友心受益良多,至今想来也为那时的编辑身份自豪。
接触这样一些繁杂的工作,让余友心的文化思考和文字表达能力都获得了极大提高——
扎西达娃的第一篇成名作《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发表时,余友心为其配画了插图;
做《西藏古典文学专号》时,余友心请人翻译了仓央嘉措老师桑杰嘉措的文章《金穗》,这篇文章写出了寻找仓央嘉措、把他培养成活佛的历程。为了顺利通过这篇当时有些“敏感”的文章,余友心亲自撰写编者按,为研究仓央嘉措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这样的事余友心做了不少,也挖掘了不少好作者、好文章。
“对文学,本编辑也是有眼光的、有水平的!我成就了不少人的代表作。”这是余友心美术之外最乐于自夸的功绩之一。一些彼时的青年人,因为余友心帮着出点子、几易其稿而有了后来的名家名作……
那一程人生无疑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高光亮点。
这些积累有如一次透彻的洗礼,为余友心后来在美术方面的探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支撑。
藏 漂
八十年代初期,西藏,作为一种地理和文化的存在,开始成为内地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西藏现代美术当时还势单力薄,画家都很年轻,而且多数是兼职的,还没能形成扎根藏文化的现代艺术观念,更没有成熟的创作队伍,但有一批以藏族青年为主体、包容了一群内地来藏美术青年的现代艺术朝圣群落,他们踏上了漫长的文化苦旅,各自做着个性鲜明的实验性创作研习——这就是后来西藏现代美术群体崛起的萌芽。
在余友心看来,所谓“藏漂”主要是指一种生存状态,有如天上飘过的云朵,在蓝天映衬下,展示一程轻柔潇洒的人生,虽然平凡却也自在畅快。
有人把这种不约而同的聚集,与当年的革命青年奔赴圣地延安相比较。
特别是85年从北京兴起的美术新潮,很快风靡全国,也被简称为85新潮。与文革美术相比,85新潮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
这种突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的一个产物。那些人看大量的文艺书籍、画册,跟着西方流派走,用了20多年时间把西方所有的艺术门类都走了一遍。
余友心和一帮年轻人的奋斗目标是逆向而行,他们不管西方人干什么,他们选择去了解藏民族在干什么、藏族民间艺术在干什么、宗教艺术在干什么……他们把创作扎根在这样一个藏文化的土壤上,再把学到的现代艺术创作能力与之结合起来,于是创造出一个新的、西藏艺术的当代形式——布面重彩。
这是一群人的功劳,更多的是一群年轻的藏族画家。这一创造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很高评价。
当时四十岁出头的余友心,相比之下在这个群落中算长辈。
作为自己在西藏的定位,余友心用了一个词汇——藏漂,接着补充道:“一个资深老藏漂!”
资深,绝不只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智慧。
余友心那时是冷静的,他觉得自己毕竟已是人过中年,见识的东西比别人更多。通过比较和认真思考,他选择了与几位友人结伴,深入到最原生态的藏民族民间生活中去,到传统美术的文化土壤里寻求精神食粮。
用自己的心去感受身在其中的藏族生活、雪域美景、历史文化,用自己的情感作画,力求开创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画风——这是他唯一的执念。
当他们看到那些尘封千百年的寺庙壁画时,忘记了沿途的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只剩下激荡心胸的诚敬和惊喜;他们陶醉于随处可见的、各式各样的民间美术现象时,就会与那些朴实的农牧民作者一样,心花怒放。
“他们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艺术大师!”
余友心觉得自己并不孤单,甚至庆幸西藏有韩书力、阿扎、美朗多吉、嘎德等一代又一代志趣相投、心怀大志的艺术家与他结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文化身份证
对于选择留下来,余友心细化为两个原因:之一,他认识和钟爱的西藏是他心灵中的西藏,不是那种与外部世界迅速趋同的表象,西藏的民族生活、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都给了他最好的学习机会,学习和创作激情都缘于对西藏的迷恋。他虽然岁数大了,自以为还是一个白髮学童,总说自己的学业刚刚开始。
之二,年轻时他学习工作都在北京,但现在那里的文化内涵淡化了,生活在淘金梦里人会浮躁,更有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弊病,吸引他的东西太少了。
基于以上两点,他不打算回去,他爱西藏,也赖定了这里。
眼睁睁看着大多数在藏内地画家最后都重回内地发展,余友心认为这与拉萨的艺术市场还不健全有关——生存问题使许多“藏漂”画家又漂向内地。而他觉得自己有特殊性:“我生命的主要时段从中年到老年是在这里度过的,落叶归根的普遍性对我这个特例不适用。”
余友心说自己人在西藏时心平气和,离开久了就会心神不宁,甚至生病,“回来就不治而愈了!”他摊开两手,作出无可奈何的得意状。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做出判断。
比如85新潮开始,西藏出去的一批年轻画家,十几年之后又都做了“海归”,大多数还客居北京,他们的身份是外国人,内心深处仍深藏着西藏情结,时刻怀念着西藏。
“由此可见西藏对人的心灵塑造多么深刻!”余友心认为在西藏就该研究和发扬西藏艺术的优秀传统。只有更深入地去探讨西藏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然后把它和现代文化对接起来,才能获得和“洋东西”平起平坐的文化身份。
如老先生所言,西藏艺术的规模不大,但可以在调整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大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人,我们追求的艺术理想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证。”这是余友心一直强调的观点。他也为此承担着西藏当代艺术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童 心
一位在拉萨打拼20多年的商人转行从事文化产业,但寻遍拉萨却很是失望,认为西藏好的国画家太少,直至看见了余友心的画,那水墨渲染的天空,灵动遒劲的牦牛让商人激动的彻夜难眠,大呼:“这才是大师!这就是我心里国画所能表达出的西藏最美好的样子!”
这大概就是余友心先生说到的审美共鸣。
作家马丽华谈到余有心的绘画时,曾说:以我外行人眼光看来是挺好看,挺灿烂,反映了余友心豪迈的艺术风格,充分展示了他内在生命力的充沛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大众欣赏水平。
余友心的画不是那种莫测高深的,也不是生涩难懂的,他觉得自己是用一种精神的追求去表现作品,不是从某种功利目的出发。“我作画不为别的,首先是为自己的心灵,‘乘物以游心,在创作中追寻梦境。”
几十年浸泡在西藏神奇的自然、人文的玉液琼浆中,余友心创作激情涌动,始终处在高度兴奋状态,每当作品中出现梦幻空灵的艺术效果时,就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醉意涌上心头,他便乘兴品味诸如神妙、奥妙、玄妙、微妙等种种妙趣横生……
过了三十多年,他果真修炼成了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难怪那般满足!
“只要你有一种真诚,你肯定会找到出路。实际上它就在那里,只是我们容易交臂而失、视而不见,或者被当下的各种诱惑搅乱了心灵,就六神无主了。”言及此处,他忍不住又得意的强调了一句:“像我这样的状态,不为世俗诱惑所动,心怀喜悦坦然面对人生,是不太容易做到的!”说完自己先笑了,那份笑容能让任何乱麻豁然开朗。
——我发现他喜欢表扬自己,一表扬就心情大好地笑出声来。这大概也是他保持年轻态的原因吧?
余友心对新事物很有好奇心,他没让自己在数码时代落后,上网、聊Q、电子信箱,他一样不落。他说最近刚在网上系统地看了关于整个西方从六十年代到现在的现代艺术思潮,都有些什么样的观念,都有些什么样的流派,都有些什么样的思路,其哲学基础是什么等等,都是他关注的范围,也都梳理得清清楚楚……
“我第一次知道了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怎样的理念,它是针对西方当代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晚期,社会变革带来的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用马克思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去解剖,提出了很多新的观念。这种批判性是马克思思想武器最核心的部分。欧美盛行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就反映了上述的社会矛盾。”他的这番话令人耳目一新,不由得佩服他这股学习的劲头。
从零开始
早年著有西藏艺术三卷集中的《绘画卷》、《民间艺术卷》,前年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举办了个人画展,去年出版了个人画册——余友心认为这几个跨步算是对自己过去三十多年在藏艺术历程做出的系统总结。
下一步?下一步是学齐白石的“衰年变法”,从零开始再创新画风!余友心心气儿很高。
“一切创新都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我正在筹划新的学程和科目,着眼点还是藏文化这个大系统,从原生态的藏族‘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要素出发,进一步深入了解其‘生活方式、‘信仰方式、‘思维方式,以期贴近其‘情感方式,感触其审美心理。”这一大串“方式”让我窥见了他前方那条隐秘的路,既实在又虚无。
“我的目标不仅是学会与此相关的系统知识,更要达到感性冲动、理性冲动方面都与这个艺术的民族共振共鸣。这样,就具备创新的基本条件了,然后借助创作‘逍遥游,去造访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从中汲取灵感潜心作画,再办一个面貌全新的画展。然后继续我的‘雪域寻梦之旅。”此刻的他像个太极高手,把一切揉捏在掌中,刚柔并济地玩得很自在,还不忘远方有梦,梦里花开!
余友心的脑子似乎永远处在激情当中,他的思维太跳跃了,有些想法总让你应接不暇,让你无法相信他已过古稀之年!
上世纪80年代有个外国人要买余友心的画,他却顽皮地问人家:你不认识我,我也没啥名气,干嘛要买我的画?外国人则很认真的回答:我走遍全世界,关注各地各种风格的绘画作品,而你的画法和风格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独一无二!
外国人的表述简单而有说服力,同时也提示了一个道理:艺术作品终究要面向社会,审美共鸣要靠心灵沟通而不是炒作。
画家的硬道理就是画独一无二的好画!这也是余友心多年实践得出的感悟。
小规模文艺复兴
余友心曾多次与几位藏族中青年画家一道走出去办展,当时西藏画家的作品已经独具风采,令外面的观众耳目一新。他们经过提炼,画心中的佛;画西藏的自然风光;画藏民族的风俗民情……这样从内容上、从艺术角度上、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是全面创新的。
那十多个画家虽然都代表西藏,但又是独特的,没有重复。在继承的基础上,他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韩书力,巴玛扎西,晋美赤列、嘎德、边巴、拉次、德珍、次朗等画家个性非常鲜明,使西藏的绘画即使呈现在世界舞台上也很有冲击力。
对西藏美术,西方人也经历了从不理解到理解。他们原来想象西藏是非常封闭的,除了宗教艺术没有现代艺术。余友心则骄傲地说:你们西方的文艺复兴从神本走向人本,用了几百年,我们的艺术走下神坛只用了30年!西藏历史进程晚,但我们完成的速度快,这才有了西藏当代艺术!西藏要走向现代,也需要文艺复兴。
而过往那一段,在余友心看来,正是一个小规模的文艺复兴。
“我们往传统里走,然后创造了现代艺术。”这一段艺术探寻的经历永远也磨灭不了,它对余友心来讲太深刻了。
西方世界还给了大家一个令人欣慰的反应:他们从作品中感受到了西藏作者内心的宁静。
可见,那时的作者在创作心理上是强势的!虽然西藏的经济落后,但在余友心看来,西藏的文化艺术早已“脱贫致富”了。
这些年余友心都是一边创作、一边进行理论思考,并时常参加国内外展览。他认为西藏美术已经成年了,需要总结、理清楚。
“西藏美术这30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深入研究西藏传统艺术开始,然后潜心创作、着力创新,最后的成果是一批批土生土长的西藏中青年画家走出去,登上世界当代艺术的舞台去展示西藏当代美术的成功,得到国内外的认可,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他说想把产生这一艺术成就的西藏文化沃土、文化生态放到一个世界平台上去让大家认识,因为那些东西是最根本、最宝贵的,不能丢了。
闲暇时余友心会骑着自行车在拉萨的大街小巷穿行,“这是我比较积极的生存方式,不是在耗时间,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就得想办法长寿,保持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充沛的体力,把我在西藏的时光资源浓缩、用好,力争再勤奋工作30年!”看他开心又充满信心的笑着,仿佛未来30年光阴已在他的掌控之中。
因 果
佛说,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因缘的巧合,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余友心对这句偈语尤其有感受。
说到因果。自然要说到佛教的第一神山——岗仁波齐。它被佛教信徒比作宇宙中心“须弥山”,数以亿计的信徒奉它为世界的中心。
2014年六月底,余友心为了回报佛的眷顾,为了修一次因果,也踏上了转山之路,去朝拜这座信仰之山,众神之殿。
他和朋友先去了沿途不同的地方采风。
由于长时间清心寡欲的生活,和朋友一同起居几日,反倒令他饮食不习惯。刚行至山脚,就闹起了敏感似的呕吐。
恰好此刻,大家开始转山了,他也开始一路上呕吐。转山用了两天多,他连一滴水都存不住,朋友担心,他会不会死在这里?
余友心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他安慰朋友,“佛在考验我,让我把一生的苦水都吐出来了。”
他们一起五个人,他是年纪最大的。但他还有一个榜样,一个在半路上遇到的83岁的藏族老阿妈,这位老阿妈独自背着行李转山。
我才75岁!余友心想,我怎么也不能输给一个更老的老人吧?孩子气让他用尽全力开始追赶。
老阿妈在前面引路,余友心获得了转山时学习的榜样。
就这样,余友心完全自己独步,凭着一股执着劲儿翻过了最高的海拔5700米处,坚持转完了全程。
返回时,朋友关照着他,每到一站都赶紧把他放到医院抢救,效果却不甚明显,这样不温不火地治疗了几天后,余友心急了,直接动手把吸管拔掉,并嚷嚷:我要吃饭!
从喝下第一碗稀饭他没再吐,他就相信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佛要我活着!他这样认定。
因果,也让他想起了当初进藏的那个不大不小关于“烟瘾”的病。
上个世纪末,余友心去印度朝圣,自备了十多条红塔山。
坐汽车先去尼泊尔时,他在曲水扔了个烟头,汽车走了二百多公里他却一根烟也没有抽,这简直是个奇迹,于是朋友干脆帮忙把十几条红塔山都送了人。没想到这一坚持就十六年了。那个缘分突然降临,印度之行给了他新生!
无意间达成了当初戒烟的愿望,这也算一种因果吧?
尾 声
生命不止、学习不止是余友心得以不断进步的根由。他告诉我,为了更好地了解藏文化,就得听懂藏语,看懂藏文,为此,他报了藏语夜校,随身带着一支专写藏文字的钢笔,还准备聘请一个老师在家为他上课……看来,他已在为未来三十年的征程做准备了。
采访余先生,让我明白:在西藏,你找到这片土地、找到理解这个民族的切入点,你就会有做不完的事情。
因为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想要在浮燥不安的环境中避免迷失自我,创作、写作都是最好的个人行为,它能使你葆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