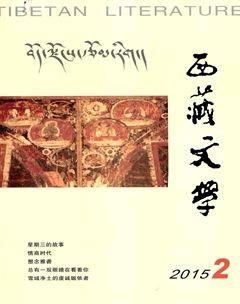生态视域中的藏族文化与西藏当代文学
普布昌居
摘 要:西藏因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自然地貌和世俗生活,始终与大自然和其他生灵保持着原始的亲近,也因此拥有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信息。以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审视西藏文学创作,可以发现生态意识体现在各种题材的创作文本中。
关键词:生态;藏族文化;西藏文学
当前,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现代化在带给我们物质丰裕的同时也引发出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生态危机(自然生态危机,人文生态危机)因其存在的普遍性尤其引人关注,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保护意识。基于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文学领域的生态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理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外兴起,很快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家也积极响应,以生态文学标注的文本创作与研究正日渐形成了一股热潮。
以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审视西藏当代文学创作,不难看出生态意识体现在各种题材的创作文本中。需要说明的是,西藏文学文本中与时代最新创作潮流的这种呼应,并非简单跟风,因为生态理念之于藏族文化、西藏文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她是构成藏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藏族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学中都表现得十分鲜明而且深刻。
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神山圣湖的顶礼膜拜深入人心,对大自然以及所有的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在藏族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中处处都能看见这样的记录。藏族史诗《格萨尔》伴随着藏族文化一同生长和发展,它不仅是一部反映古代藏族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随意翻开《格萨尔》的章节,藏族先民与自然万物相互依靠,以期“共生”的生态意识随处可见。在《霍岭大战》一节中,辛巴梅乳孜唱道:“狂妄大胆的渔夫,你们心中可清楚?霍尔大川大河水,全属霍尔流本土。水中鱼儿无其数,跟霍尔人共生息。其中三条金眼鱼,是霍尔三王的寄魂鱼。我们霍尔山沟里,禁止人们来打猎,我们霍尔河水中,禁止人们来捕鱼。谁若打猎捕鱼类,依法严惩不放生!”道破了人与生灵之间命运的息息相关,其思想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表达了藏族先民对一切生灵的珍视。这种传统的理念到现在依旧影响着藏族人的思想与情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陆川导演执导的《可可西里》为例,可可西里的人们保护藏羚羊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行为,同样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的环保层面,体现了藏民族“以整个生态系统为本”的生态理念,彰显了所有的生命同样尊贵,人应该像尊重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尊重其它的生命的崇高生命观。
仰仗着民族传统文化中生态意识悠久、深厚的文化背景,早在当代生态文学写作还未被命名之前,西藏当代文学承袭着从口头到书面几乎从未断流过的藏族古老的生态传统,在文学文本中表现出了鲜明的生态意识。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婚礼歌·藏族民间长歌》中这样歌咏牧民眼中的骏马:“马头像纯金的宝瓶一样,愿金宝瓶盛满吉祥。马眼像天上的启明星一样,愿启明星闪耀吉样。马牙像三十颗贝壳一样,愿三十颗贝壳带来吉祥。马舌像锦缎的彩旗一样,愿锦缎的彩旗招引吉样。马髻像蓝宝石的玉环一样,愿蓝色的玉环圈来吉祥。马尾像透明的丝线一样,愿透明的丝线扬起吉样。”诗人对马的歌咏,道出了,马在藏族牧人心中的地位——它绝不是不会说话的牲畜,而是值得尊敬与珍视的宝贝。
藏族文化珍视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理念影响着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上世纪70年代进藏,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的散文家马丽华在行走于青藏高原山山水水的日子里,对高原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的亲身见闻,让她的心灵得到了涤荡。在倾情书写高原绚丽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的独特关系中建立起了她自己的生态观点。学者张晓琴将其总结为:“自然的形成有它自身的原因和规律,它是我们人类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去改变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人类自己。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不要把自己树立为自然界的暴虐之王,不要随意地戕伐自然,否则,自然会反过来惩罚人类。”她完成的三部长篇纪实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不仅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西藏热,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当代散文摹写人类原生态的新阶段。”①
而与藏族传统生态文化有着血亲关系的本土作家,在文学写作中传达出来的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更是深植于人的内心,无需理论的支持,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世代相传。朗顿·罗布次仁的散文《山》这样写道:“在每个藏族人的心中,山是活的,就像是家里的一个长辈,梦中的一位恋人,心中的一个偶像。怀着这种复杂的情感,对山的迷恋、狂热、崇拜渐渐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植根在骨髓里。山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形,而岿然屹立在人心中的只有一个魂——山魂。”在藏族文化中,高山大河从来都不是孤独而僵硬的自然存在,而是温暖而可敬的,比如像念青唐古拉山和纳木错、冈底斯山与玛旁雍错湖,不仅是巨大威力的超自然存在,也是有情有爱的恩爱夫妻。藏民族对山没有渴望征服的欲望,也没有征服后的高高在上,攀登更多的喜悦在于与自然的亲近,这种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暖色场景。
在这个暖色场景中不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有人与动物的亲密相处。收录在白玛娜珍的散文集《西藏的月光》中的《我的藏獒与藏狮》中这样描写家里饲养的小狗:“嘎玛是条棕红色的土狗,身体矮胖又长,嗖地窜过草丛时,像只红狐。”“藏语里星星叫‘嘎玛,给它取这名,除了它那双灵动的眼睛,还因这些年它带给我星星一般数不清的快乐。”一段时间里,嘎玛常常离家出走,在“我”四处寻找中找到被铁链拴住的嘎玛,才知道它爱上了住在不远处胖女人家的小母狗。我赞赏它的举动,认为“追求爱情是它的权力,与其苟且一生,不如铤而走险。”白玛玉珍的《姨妈的善良生平》中写到:“姨妈”对家里的几头大藏獒“天热了会时不时为它们换冷水喂;天冷了还要把食物烧热了喂给它们;刮风时不停地在狗的近旁洒水,怕沙粒吹进它们的眼睛。”在西藏有这样的传说,狗将自己得到的青稞种子给了人,人们才有了食物,狗在藏族人心目中是人类的恩人。所以藏族善待狗,既非看门的家伙,也非金贵的宠物,而是家庭中的一员。
不只是与人有恩的狗,在藏族的文化中所有的生灵都是珍贵的。白玛娜珍在《百灵鸟、我们的爱》一文中写到,在“我家”院子里筑巢的一对百灵鸟,成为“我”和儿子旦那的朋友,日日关照。“小百灵鸟出生后,母亲提出留下一对小百灵鸟给她,儿子旦那使劲儿摇头,拿走它们的孩子,鸟爸爸和鸟妈妈会伤心的。”而“我”在佛前为所有的生灵祷告,因为“连一个目不识丁的百姓也懂得生物是相互依存的,它、它们不好,我和大家也不好”。母子俩都在用行动阐释一个道理:人不是世界的主宰或者中心,人只是自然的一分子。
在诠释传统文化生态理念在帮助藏族作家建立起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建立起与其它生命体的亲密关系上所产生的影响时,作家白玛娜珍如是说:在西藏“当你在街上跌倒,或是老人在医院排队,都会得到热心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帮助和仁爱。而一只狗、一只小鸟在藏地都能够获得临终救度。还有很多比如供“苏”,是专门点燃香柏,加入糌粑、白糖、酥油、等以食物的精气和愿想慰籍饿鬼、幽灵等。出家人更是在每天早晨自己滴水未尽前要给饿鬼道和幽灵奉上七滴水作为水供;走路时也不会大幅度甩手,担心惊扰存在于空气中的无限存在着的灵识;还有在水里撒甘露丸,在水里印六字真言等,关照水里一切生物、微生物......这些数不胜数的仪式和民俗,表面看天真烂漫,实则展现了藏民族的慈悲情怀和众生平等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文化人群中,博大的爱的智慧和爱的力量,令我充满了写作激情。”②正是对万物有灵,前世今生的信仰,藏族传统文化自然地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把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联系起来,将此刻与未来联系起来,从而建构起了人与其它物种、生灵之间友好、亲密的关系。
如果说,和平解放之初的西藏文学表达出的生态观是对传统文化的承袭,那么还应该看到新时期以来西藏作家在创作文本中传达出的深刻而鲜明的生态理念除了有对传统文化的承袭,还源于实实在在的时代忧患。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逐步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洪流在创造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与冲撞,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在经济变革的时代大潮面前精神滑坡,价值失衡。重物质,而“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③的价值观所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影响深远。学者王喜绒在《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这样描述:“如果说自然生态危机使人类正在丧失可以栖息的物质家园,那么普遍的精神危机有使人类正在丧失可以安息灵魂的精神家园。”生态危机作为世界性问题迫使文化研究者重新审视现代文化与价值标准,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的呼唤也就成为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自觉。西藏虽然地处边境,但新时期以来具有多元文化成长背景的西藏作家没有局限于自己生活的狭小区域,立足全球化的视野,积极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表达了自己的生态理想及其价值判断。
早在90年代西藏作家郭阿利在小说《走进草原的二种方式》中就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对高原牧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的破坏,以及对由此引发的生存环境危机的忧虑。白玛娜珍在博文《听风十三年》描写了城市化进程中,拉萨近郊娘热村十三年来自然环境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记录下了变迁中的时代阵痛,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则通过一位格萨尔艺人的经历,表达了作家对西藏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发现与理性思考。主人公亚尔杰是一位藏北的牧民,当他还是色尖草原上的13岁的放牧娃时就被格萨尔的大将丹玛选为宣讲格萨尔战绩的神授艺人,并将厚厚的经文放置进亚尔杰的体内。神授的力量让亚尔杰这个只字不识的放牧娃可以用最华美的辞藻讲述格萨尔的事迹,几天几夜,滔滔不绝;神授的力量使他赢得草原上牧民们的尊敬和爱戴,无论他走到哪里,进献的美食和姑娘们羡慕的目光就到达哪里。皓月当空的夜晚,宁静、开阔的草原,人们围坐在篝火的四周,眼里充满了热情与景仰,聆听着格萨尔的故事。与自然、与神的亲密接触,使每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绽放出灵性的光芒。然而,世界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现代化的触角不可避免地探进了这个隐秘的世界,改变着亚尔杰和他的草原以及草原上的牧人的生活。当亚尔杰离开草原,坐进研究院苍白的办公室,面对机械的录音机宣讲格萨尔的事迹时,当他把宣讲格萨尔和工资待遇这些世俗的利益对等起来的时候,神授的力量距离他越来越远,同时远去的还有闲适、安稳、充满灵性的灵魂状态。而往日那些最忠实的聆听者早在致富的忙碌中忘却了格萨尔的事迹曾带给他们的心灵感动。古朴的民间信仰就这样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逐渐退出了生活的舞台,而外来的现代性又没能真正融入高原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的茫然,心灵的茫然,让人的精神失却了寄居地。小说结尾,亚尔杰只身离开研究所,深入曾经巧遇丹玛的色尖草原,希望找回神授的力量,召回曾有的心灵状态。
就如英国著名生态文学家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中面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生态危机,深刻思考“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一样,西藏作家也和内地作家一样也通过自己的文本探寻着现代化背景下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失落的轨迹,思考化解危机的方法与观念。
必须指出,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规律都告诉我们,全球化和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一个民族放弃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退回到传统社会的老路,那么,这个苟且偷安的民族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④是原地驻守还是向前发展已毋庸置疑,在发展中人类采取和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观及其体现的社会发现目标模式才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因为这不仅对社会的经济、政治、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社会的文化教育、思想道德、人文环境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学抒写的藏族生态文化与大自然和其他生灵保持着原始的亲近,积极倡导社会成员之间的友善、和谐的处世经验与思想模式弥足珍贵,它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可以为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次仁罗布的小说《阿米日嘎》为例,小说将故事的发展放置于商业主义的背景中,燃堆村村民围绕贡布买回的优质奶牛“阿米日嘎”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纠葛,村民的羡慕、嫉妒、恨;贡布只顾自己发家致富的自私自利让原有的睦邻友好反目成仇,乡村原有的宁静与和谐被打破。而“阿米日嘎”的意外死亡让冲突步步升级。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小说中贡布的母亲,这位藏族老妇人在围绕“阿米日嘎”的矛盾冲突中,坚守着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善、爱、慈悲、宽容的做人信条,始终用友善、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极力反对贡布为致富与村民为敌的自私做法。小说发展到高潮阶段,“阿米日嘎”意外死亡,贡布财物两空,失魂落魄,深受传统文化心灵滋养的村民们,内心深处的善与宽容被激发出来,大家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带头买死牛的肉,帮助贡布减少经济上的损失。在宽恕、责任与爱的光耀下,放下利益纠纷的人们让古老的村庄又呈现出美好与祥和,在商业化浪潮蜂拥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加显得珍贵,它也成为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健全心灵世界,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参考。
现代化是全社会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但在前行时,我们也需要经常审视走过的路,在倒掉洗脚水时,留下孩子。在高擎现代文明的火炬时,不忘坚守传统文化中那些最可贵的。就如黄轶在《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生态文学“社会发展观批判”主题辨析》一文中所说:“人类历史常常不是线性发展的,我们必须殷殷回首,以捡拾不该遗落的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生存经验,使前行之路少一些误区。”⑤因此可以说,当代西藏作家在创作中积极挖掘并呈现藏族传统文化中亲近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共生的生态观念,融合现代意识,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得与失,真诚表达对生态自然、健康心灵的呼唤与赞美,表现自己的思考与立场的态度与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难发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工业文明浪潮蜂拥的新语境下,这些浸润着充盈的生态理念的藏族文化是可以给饱受现代性冲击的自然与人的心灵以慰藉与启发,藏族文化与西藏文学依旧具有对这个世界价值输出的能力。
(该文为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背景下当代西藏文化的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013ZJRW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汉语言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张晓琴.《高原生态的发现者——论马丽华散文的文化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②白玛娜珍.《听风十三年》白玛娜珍的博客,访问路径:http://blog.sina.com.cn/s/blog_
6a0395390101chch.html
③[法]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J].见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3辑.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2年版。
④马国川.《文贯中:往事何曾付云烟》.《经济观察报》[N].2007年10月1日-8日第47版。
⑤黄轶.《生命神性的演绎——论新世纪迟子建、阿来乡土书写的异同》[J].《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参考书目:
1、王喜绒.《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北京.2009年8月.
2、次仁罗布.《界》[M].第一版.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2011年12月。
3、白玛娜珍.《西藏的月光》[M].第一版.重庆出版社.重庆.2011年12月。
4、西藏文学从书编委会编.《西藏行吟——西藏诗歌散文选》[M].第一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2007年6月。
5、张晓琴.《生态文学的文化建构意义》[N].光明日报.2009年4月06日
6、黄轶.?《“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生态文学“社会发展观批判”主题辨析?”》[J].
7、刘雨林.《论西藏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增刊。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