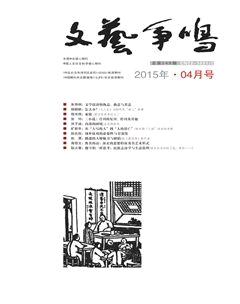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及其意义
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这部小说是路遥作品首次在我国大型文学刊物上的亮相,并于1981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的发表,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心。随后,他才有中篇小说《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问世。考察这部小说的发表过程,对于研究路遥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
新时期之初,担任《延河》文学杂志编辑的青年作家路遥,还只能在编辑之余,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拨乱反正,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得到极大的鼓励,这对于心性刚强的路遥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路遥一边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
1978年,就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时,路遥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为题材、以“文革”前夕担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为原型(1),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篇小说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发泄情绪的路子,而着力塑造某山区小县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为制止两派的武斗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我牺牲。它是路遥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题材,一则路遥有在“文革”武斗时的亲身经历和生死体验,写起来得心应手(2);二则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而他的这部作品的“着眼点就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3)。
就路遥创作该小说的时间来看,正是“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伤痕文学”同新时期“拨乱反正”及“平反昭雪”社会现象,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关系。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以及话剧《于无声处》等,均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表现出了一种潜藏于社会底层的民间变革性诉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反响。而路遥在创作上有明显的“异向思维”能力,经过自我生活的积淀与思索,为读者塑造了一位拥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县委书记的形象。该小说从表象上来看,与当时的文学主流相异,没有顺大流,没有跟风。路遥所塑造的主人公马延雄是位为了人民利益而甘愿舍身的英雄,具有基督精神与佛的精神,在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中有一定的典型性。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创作手法上,深受法国作家雨果长篇小说《九三年》的影响。《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文,以及郭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这三个中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描绘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一七九三年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场面。小说的结尾是矛盾的最高潮:朗德纳克因良心发现,返回大火焚烧中的城堡救出三个孩子;郭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所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则在郭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杀……熟悉西方文学名著的路遥,在《惊心动魄的一幕》创作上对《九三年》有着明显的借鉴:一是把人物放置在“文革”武斗这个大的时代场景中进行塑造;二是在故事的不断演进中,着力塑造在“红指” “红总”与农民三方的尖锐冲突中、勇于自我牺牲的县委书记马延雄形象,故事也是在矛盾的最高潮结束。马延雄身上既有为群众利益而献身的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4),也暗合了《九三年》中传达出的人道主义光芒。
路遥下定决心创作这部与当时文坛潮流有些不甚合拍的中篇,是一招剑走偏锋的险棋。很多年后,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晓雷回忆:“我看过去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既震惊这部小说的真实感和我的朋友闪射出来的令我羡慕甚至嫉妒的才华,又震惊于这部小说主题和思想的超前。那时我的思想还深陷在‘文化大革命后的长期喧嚣形成的藩篱中,而如今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讨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怎能不让我感到惊恐呢?但我的真诚认可了这作品的真诚,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我的支持。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乎叫作《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而且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5)不仅晓雷看到这部小说时叫好,《延河》副主编董墨也有同感,路遥拿出这本小说的初稿让他看后,他认为:“这个中篇小说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作家着眼点的不同。”(6)
当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否定,而路遥以“主题先行”的方式,进行“文革”反思,这不能不说具有思维的前瞻性。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之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文学编辑们能否完全领会路遥的创作意图,这也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寄出后,路遥的心也就随之悬了起来。这部中篇先是《延河》副主编、路遥恩师贺抒玉推荐至某大型文学刊物主编,不久被退了回来;又寄给一家刊物,二次被退回(7)。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在“周游列国”后,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遥都在等待发表的焦虑与煎熬中度日如年。而那时的陕西作家却一路高歌,莫伸的《窗口》与贾平凹的《满月儿》在197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忠实的《信任》和京夫的《手杖》又分获1979年与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陕西已有四位作者在全国获奖,而路遥却出师不顺。
这样,路遥的创作一直在中篇与短篇之间犹豫,他甚至重新拣起短篇,先后写出了《在新生活面前》(《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夏》(《延河》)杂志1979年第10期)《青松与小红花》(《雨花》1980年第7期)。《匆匆过客》(《山花》1980年第4期)。《卖猪》(《鸭绿江》1980年第9期)等,这些短篇小说仅仅是发表与增加数量而已。
当《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时,路遥甚至有点绝望,最后他将稿子通过朋友转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结果稿子仍没有通过,原因仍是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路遥怎么办?路遥写信告诉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如果《当代》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寄回,一烧了之。
二
1980年春天,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久,《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改,可不可以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要看到所期望的结果(8)。《当代》是新时期我国文学杂志的“四大名旦”之一,有“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特色,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整体大气、厚重,能在《当代》上发表小说是每个作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1980年5月1日那天,路遥激动地给《当代》编辑刘茵写了一封长信,诚恳而详细地阐释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动因、思路乃至写作中的苦恼。这封信件,是目前路遥本人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系统的创作阐释。他甚至明确地告诉《当代》编辑:“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同时,路遥在此信中还提出:“这篇作品最好以中篇小说发表为好。因为这不是写一个具体的真事,我是把我了解的许多作品构思的要求虚构的;这不像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样的长篇报告。基本按历史事件和真实写成,并不虚构。另外,因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区(注:每字下均有点号)的生活,如按报告文学发,多事的人必然会从作品里寻找生活中的真实的原型,这样怕惹麻烦。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最好能按中篇小说发”;他还提出,“另外,能不能让我改一下校样?因为5月份初发稿,大动不可能的(我也不准备大动)。如有可能,我想在校样上改一改个别不妥处的地方。”(9)
路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这封书信中有清晰展示。这封书信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当代》杂志当初想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发表此小说,这说明路遥这部小说写得太真实了,以至于编辑产生“误判”,认为这是一部“报告文学”,路遥不得不费力解释。
《惊心动魄的一幕》能在《当代》上刊发,这将是路遥创作的重大收获。就在1980年5月1日,路遥又情不自禁地给朋友谷溪写信,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好长时间了,不知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说《当代》已决定用,五月初发稿,在《当代》第三期上。这部中篇《当代》编辑部给予很高评价,秦兆阳同志(《当代》主编)给予了热情肯定……中篇小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10) 路遥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连续使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 “莫大的荣誉” “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这些极致性的词语,来表达他当时的兴奋心情。这说明路遥在文学突围时期,文学前辈秦兆阳与《当代》其他编辑的充分肯定,对他提升文学创作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年5月初,路遥应邀到《当代》编辑部修改小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后,在责任编辑刘茵的陪同下,去北京市北池子秦兆阳住所见到了那位德高望重的《当代》主编。秦兆阳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生,他的青春年华是在战争中度过;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1956年,他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起很大反响。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1980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也就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上任不久后就看到的作品。路遥的确是幸运的,他的命运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结果,路遥在秦兆阳与孟伟哉、刘茵等人的指导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二十来天,作品不光比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而且在故事结构上有所调整(11)。路遥当时无限感慨地对刘茵说:“改稿比写稿还难。”(12)
路遥1980年5月24日给好友谷溪的信中谈到这个情况:“我于5月初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那个中篇小说已20来天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比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现在6万多,估计在《当代》第三期发(6月发稿,9月出刊)。此稿秦兆阳同志很重视,用稿通知是他亲自给我写的,来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在家里约见了我,给了许多鼓励……”(13)
三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头条刊发,秦兆阳专门题写标题。在秦兆阳的力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还一连获了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1979年—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样,路遥成为新时期陕西作家中第一位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家。路遥好友、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著名诗人闻频,见证了路遥得知获奖消息的情景:“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一大早我在办公室写东西,他从前院急促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高兴地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把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路遥这种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我只见过这一次。这是他《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全国获奖,也是他第一次获奖。后来的几次获奖,包括茅盾文学奖,他再没激动过。”(14)
1982年3月25日,秦兆阳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再次谈到当初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第一印象:“初读原稿时,我只是惊喜: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文字风格又是那么朴实” “所以路遥同志,你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他也客观地分析了这部中篇小说未被评论界关注的原因:“它甚至于跟许多人所经历、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之情和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联系不起来。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15)《当代》编辑部与秦兆阳独具慧眼赏识了这部小说,并成就了路遥。这样,路遥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知名作家行列。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路遥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说是从这部中篇小说开始的,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显露的。从此,路遥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至少有这样几重意义:一是极大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二是他跻身全国著名作家行列,为全国文坛所关注;三是也改变了他在陕西文学界坐冷板凳的际遇。在1981年的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获奖座谈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郑重向路遥约稿,才有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出炉(16)。此后,“农裔城籍”的路遥找寻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优质文学表达区位。
当然,并不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一篇十分成功的作品。1985年元月,路遥在接受采访中坦诚地谈到它的局限:“这个作品比较粗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艺术准备不充分,很大程度上是靠对生活的熟悉和激情来完成的,因此,许多地方留有斧凿的痕迹……”(17)
1991年,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直言不讳地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这样写道:“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18)这进一步证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之于路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本文为“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3SXTS01)”成果。]
注释:
(1)1980年5月1日,路遥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件中称:“这篇作品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生活,其中的许多情节都是那时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致刘茵》,见《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70页。
(2)1980年5月1日,路遥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件中称:“在1966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暴烈的时候,包括我们县委书记在内的许许多多陕北老干部,为了群众的利益,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这是老区干部最辉煌的品质),许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都是带着迷惑不解的心情死在最初的风暴之中。”《致刘茵》,见《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71页。
(3)(9)路遥:《致刘茵》,《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72页,第573-574页。
(4)1980年5月1日,路遥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件中称:“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关于那段生活,三言两语简直说不清楚,有机会我向您详细讲述。现在只好告诉您一些一般的情况:我当时和我所有同龄人一样(十五六岁),怀着天真而又庄严的感情参加了这场可怕的革命。”《致刘茵》,见《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70页。
(5)晓雷:《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见李建主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6)(8)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见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7)贺抒玉:《短暂辉煌的一生》,见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10)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11) 刘茵老师2013年9月新发现一封路遥1980年5月30日写给《当代》编辑孟伟哉的信件,此信是路遥在结束北京改稿返回延安后写给孟伟哉的信件,主要说明修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具体情况,未刊,但颇有研究价值。信中称:“您和刘茵同志谈过意见后,我又把稿件整理了一遍。我想了一下,觉得农民场面结束后,是应该很快跳到礼堂门口的。您的意见是对的。因此我把以后的那两节(现已合成一节)调整到农民场面的前面去了;农民场面一节重写了一遍。现在已经从农民场面的结束直接过渡到了礼堂门口上。至于您提出删去的那些内容,我用这种办法保留了下来。主要考虑到:一、如果没这个内容,马延雄回城的理由、必要性以及他对这个行动的思想动机将给读者交代不清楚,会留下一些漏洞(主要通过马延雄和柳秉奎的谈话说清楚这些)。二、这些都是马延雄和柳秉奎两个重要人物的细节描写,尤其是马延雄雨中挣扎一节。整个文章密度大一些,好不容易有这么个空子抒情性地描写了一下。现在这样处理,您提出的意见解决了,也保留了那一节。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对,请您再看,如不行,我再改。”
(12)2013年9月28日晚,正在路遥家乡延川县进行文化考察的刘茵亲口对笔者讲述当年情景,说路遥改稿后感慨地说:“改稿比写稿还难。”见笔者访问记录。
(13)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14)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见刘仲平主编:《路遥纪念集》,内部刊印,第41页。
(15)见马一夫、厚夫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6)王维玲《岁月传真——我与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17)老戈《路遥谈创作》,山东省文联《文学评论家》1985年第2期。
(1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责任编辑:王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