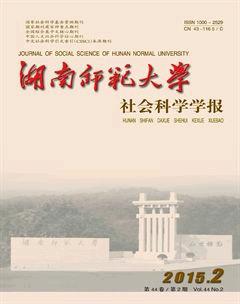赵翼诗论的唯新倾向及与性灵派的离合
李秋霞 蒋寅
摘 要:学界一向将创新精神视为赵翼诗学的核心内容和独特价值,并当然地被放在性灵派的理论框架中加以阐释,而并未追问其理论出发点。从赵翼对才名的焦虑和对文学价值的悲观态度入手,说明赵翼诗论的唯新倾向出于超越前人的渴望,其背后的动力乃是“影响的焦虑”。赵翼论诗虽同样以自抒性灵为要旨,却只不过视为创新的手段,而不像袁枚那样以之为目的。随着年至耄耋,老境寂寥,他对诗歌的观念有所变化,逐渐由求“新”转向求“工”,甚至放弃了与前人争新的意识。这无意中呼应了诗坛正涌动的自我表现极端化、绝对化的思潮,成为嘉、道诗学中绝对自我表现观念的先声。
关键词:赵翼;诗论;唯新;性灵派
作者简介:李秋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7)
蒋 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赵翼历来是乾隆朝诗论家中较受关注的一位,因为他的史学甚至比他的诗歌创作更出名,就不要说诗论了。有关赵翼诗学的研究,其创新精神一直为学界所注目,朱东润先生称“此种精神,实为吾国文学史中所仅见”{1};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也着重论述了赵翼的创新理论,认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创新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来对待,而且把创新作为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标准”{2}。后来的研究者,如王建生讨论了实际批评,而未涉及其诗学主张{3}。而周明仪将赵翼论诗主张概括为诗本性情,不拘格调;以才运学,才学并济;诗贵创新,忌荣古虐今{4}。近年不断有学者对赵翼的诗论展开多向度的研究,赵翼与同时代批评家的异同也受到关注{5},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赵翼诗学的认识。不过,我也注意到,学界对赵翼诗学的主导倾向及与袁枚性灵诗学的关系,看法还比较笼统和宽泛,未能揭示赵翼与袁枚诗学的真正差异所在,同时也未注意到赵翼平生论诗观念的转变,这都为本文的探讨留下了进一步展开的余地。
一、唯新的焦虑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武进人。初官军机中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进士,三十七年(1772)由贵州兵备道辞归,讲学著书,享耄寿而终。赵翼因幼赋异禀,对才名的渴望尤为急切,曾有诗云:“少年意气慕千秋,拟作人间第一流。”{6}然而青春年少的抱负,历经宦海沉浮,只留下“从军无奇功,作吏无奇绩。始知天下事,不能任其责”的落寞感觉,最终在理想的幻灭中萌生恬退之思:“不能立勋业,及早奉身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7}像袁枚一样早早地退归林下后,赵翼所有的人生期求都转向文章学术。同时诗中也经常流露出一种不甘和无奈:“士有名世才,出手爆雷电。远夷争购诗,达官求识面。必待史策传,其传已有限”,“千人万人中,有我七尺身。千年万年中,有我数十春。白首自照镜,塌然暗伤神”{8}。到晚年,赵翼所有的生活乐趣和希望,更全然寄托于文学。相比乾隆中初归田时撰著的《陔余丛考》和嘉庆元年(1796)编成的《廿二史札记》,嘉庆六年(1801)七十五岁所撰《唐宋以来十家诗话》,显然是他晚年倾注心力的大著作,绝不同于《随园诗话》那种浮光掠影、道听途说的信笔闲谈,而此时他对诗歌的观念也与早年有所不同。
赵翼虽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并称,但他与袁、蒋两人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首先以学者立身处世,自青年时代就对学术抱有很大的志向。《瓯北集》开篇之作《古诗二十首》其三论经学曾说:“俗儒识拘墟,硁硁守故纸。或言古制非,攻者辄蜂起。岂知穷变通,圣人固云尔。是古而非今,一步不可履。”{9}诗成于乾隆十一年(1746),作者年方二十,而一股突破故常、走自己道路的创变之志已勃然于胸中。在《补邹衍》其一中,他又写道:“人情每厌故,数见辄不鲜。天亦似好新,寒暑辄互迁。春来桃李艳,冬来冰霜兼。其实总陈迹,如文袭旧篇。惟其四时嬗,一候一改观。遂使人耳目,常换景色妍。”{10}这虽是借邹衍谈天的题目,讲自然运化之理,但人情厌旧、天意好新之旨岂不正是王渔洋论诗所说的“物情厌故,笔意喜生”么?{11}寒暑互迁如文袭旧篇、无非陈迹的说法,流露出对文学生命的一种终极的悲观态度:没有常新的美景,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变化本身是不变的,物候因这变化给人带来新的景象。循此理反观文学,也同样是惟有变化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虽说不上是什么深刻过人的见解,但已决定了青年赵翼的道路,他未来的史学和诗学都将朝着这唯新主义的方向前进。
然而,作为生于唐宋之后、面临古典文学末世情境的清代才人,更经受举业对才华、精力的磨耗,要想超越古人,谈何容易!他早年的写作洋溢着不拘一格的豪迈之情,“乃知卓荦人,胸次固不羁。吟咏出兴会,万物供驱驰”{12}。入仕后辗转中外,簿书鞅掌,笔墨应酬,明知“诗非苦心作不成,佳处又非苦心造”,“偶于无意为诗处,得一两句自然好”,但现实却是“如何一管秋兎毫,立课分程日起草,腕脱抄胥不停笔,口授堂吏各成稿。此是供役官文书,就中赏心固自少”{13}。这不能不让深谙“言情篇什贵隽永,岂比宿逋可催讨”的诗人,三省自己写作的命运。乾隆五十七年(1792),一组题目很长的七律《有以明人诗文集二百余种来售余所知者乃不及十之二三深自愧闻见之陋而文人仰屋著书不数百年终归湮没古今来如此者何限既悼昔人亦行自叹也感成四律》道尽物伤其类的悲慨:“不知曾费几敲推,无限精灵付劫灰。传不传真皆有命,想非想岂尽无才?”{14}又有《连日翻阅前人诗戏作效子才体》云:
古来好诗本有数,可奈前人都占去。想他怕我生同时,先出世来抢佳句。并驱已落第二层,突过难寻更高处。恨不劫灰悉烧却,让我独以一家著。有人掩口笑我旁,世间美好无尽藏。古人宁遂无余地,代有作者任取将。{15}
诙谐的语言终究难以掩饰“影响的焦虑”和创新的渴求,如果说“恨不劫灰悉烧却”代表着焦虑的自我,那么“代有作者任取将”就是对创新充满期待的自我。这正是赵翼创作人格的两面,前者是现实的自我,后者是理想的自我。65岁的赵翼犹然雄心勃勃,饶有与古人争长之志;但到耄耋之年,“归田已历三十年,著书未满二百卷”,便不得不正视那个现实的自我了。《呼匠刷印所著诗文戏作》由是自哂道:“恨不借祖龙火,烧尽好诗独剩我;恨不借黄虎刀,杀尽才士让我豪。笑问此心赧不赧,要显我长幸人短。果能置身万仞冈,何山敢与争低昂?乃欲临深作高蹇,固知所挟本浅浅。”{16}究竟有无创新的能力和成功,是踌躇满志还是茫然失落?只怕他自己也不清楚。
当然,凭赵翼的才学禀赋,是足以与前人争胜的。友人序赵翼诗集,无不对其才华赞叹不已。王鸣盛称“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于天者高,又佐以学问,故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见其促,繁言之不见其碎,浅言之不见其轻浮,深言之不见其郁闷”{17}。袁枚则说“耘菘之于诗,目之所寓,即书矣。心之所之,即录矣。笔舌之所到,即奋矣”{18},显然引为性灵同调。但平心而论,赵翼诗比袁、蒋两家路子要窄,惟以议论犀利见长,好辩驳{19}。袁枚甚至视此为扬长避短,以掩饰不长于古文的弱点:“古文家多论古以抒己见,瓯北乃移其法于韵语,便觉斩新开辟,此正其狡狯处。然立论精确,自是不磨。”{20}这种种不同的看法最终造成赵翼评价的戏剧性变化:生前才名震耀一世,身后却颇招贬议。就连推崇“瓯北才气直在随园之上”的崇拜者,也不能不承认其诗歌写作存在明显的缺陷:“贪多务得,结少含蓄,一憾也;鸣谦太过,未能免俗,二憾也;好用俚语,格不谨严,三憾也。”{21}朱庭珍更是恶其“诙谐戏谑,俚俗鄙恶”,直斥为“风雅之蠹,六义之罪魁”{22}。参观正负两方面的评价,大致可知赵翼诗歌的得失。但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我更关注的是赵翼诗学的理论倾向和得失。
二、与性灵诗论的离合
赵翼平生论诗宗旨,概见于《书怀》“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一联{23},袁枚引他为同调是很自然的。比起蒋士铨来,他明显与袁枚的诗学趣味更加接近,也更能互相欣赏和分庭抗礼(蒋士铨与袁枚晤对明显落下风)。晚年两人在扬州相见,赵翼有《子才过访草堂见示近年游天台雁荡黄山匡庐罗浮诸诗流连竟夕喜赋》四章纪事,其三云:“我最爱君诗,君亦爱我句。他人岂不赏,不著痛痒处。惟此两老翁,交融水投乳。”又形容两人论诗的较量是“徐夫人匕首,不待血如注。赏奇意也消,中病手无措”。其四历数从前文人相轻之例,坦言“茫茫大宇宙,听人各千秋。盖棺论自定,睽睽有万眸”,最后结以“君才驭飚轮,我力破浪舟。一代诗人内,要自两蛟虬”{24},大有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气概。
尽管如此,两人论诗仍有枘凿不合之处。除了研究者指出的思想观念的差异之外{25},其诗歌趣味也有细微的不同。比如两人都喜欢白居易、陆游,于本朝独推查慎行为巨擘,但评价的着眼点却不相一致。以查慎行而言,袁枚较欣赏其白描,说“查他山先生诗,以白描擅长,将诗比画,其宋之李伯时乎!”{26}又称他“是白描高手,一片性灵,痛洗阮亭敷衍之病”{27};而赵翼却认为“初白好议论,而专用白描,则宜短节促调,以遒紧见工,乃古诗动千百言,而无典故驱驾,便似单薄”{28},又说“初白诗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觉寒俭,一遇使典处,即清切深厚,词意兼工”,显见得两人对查慎行白描功夫的评价颇有出入。总体看来,赵翼对前代诗歌的接受范围更广,钱钟书先生称“《瓯北诗话》中论李、杜、昌黎、遗山、青丘诸家,皆能洞见异量之美”{29},实能道着赵翼的长处和特点。此外,赵翼对待诗歌技法的态度也与袁枚不同。周春阅二十五年七易其稿成《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一书,自负“此事成绝学”,自信其说甚精。赵翼题诗称“允作杜功臣,艺苑更绳尺。《音签》《韵府》外,另树一帜赤”{30};可袁枚却诋諆其说,周春在《耄余诗话》曾提及{31}。说到底,正像赵翼《偶阅小仓山房诗再题》所意识到的:“老我自知输一着,只因不敢恃聪明。”{32}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诗学,都是有底线的。有底线即有顾忌,而袁枚没有。他不及袁枚处在此,胜过袁枚处也在此。
赵翼论诗虽以自抒性灵为要旨,但并不像袁枚那样以性灵为目的。性灵在他只不过是企求创新的手段,背后的动力是超越前人的渴望。所以,赵翼诗学最核心的观念即是由影响的焦虑所激发的创新意识。门人李保泰深知这一点,序老师的诗集,着力阐发一个“新”字:“天地之运,积而不穷。风气之新,推而日出。试以《三百篇》律汉魏,则汉魏异矣;又以汉魏、六朝律唐宋作者,则唐宋又异矣。日月终古。光景常新,新之一言,亦文章气运之不得不然者也。”{33}友人张舟跋《瓯北诗钞》,也盛赞“奇思壮采,惊心动魄,无一意不创,无一语不新,信古来未辟之诗境也!”{34}我们知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历来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但自从明代格调派的复古模拟之风盛行,求同于古人反倒更像是传统习尚,而求异于古人成了诗学的新动向,其表征就是以叶燮为代表的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思潮。到清代中叶,“新”已在不同层面、不同意义上被反复强调。前辈诗人如卫既齐说:“体制惟旧,情性惟新。”{35}后辈诗家如延君寿说:“诗无新意,读之不能发人性灵。”{36}但这些批评家似乎没有意识到,任何创新都在使前人相形见旧之余,带来新的影响焦虑,产生新的压抑,从而激发新的改写。这是一个永无结局的竞争。杜牧翻前人旧案作《题乌江亭》,到宋代又被王安石《乌江亭》再度翻案:“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赵翼却虑及这一层,在他看来,翻案甚至不是什么值得肯定的求新手段,说:“诗家欲变故为新,只为词华最忌陈。杜牧好翻前代案,岂如自出句惊人?”{37}但问题是,自出新句又能怎么样?每一篇新作、每一次创新,都只是焦虑的暂时缓释,表现空间的缩小更给后人带来新的焦虑,而且随着时代推延,这种焦虑到明清之际已越来越沉重,终于形成观念化的表述。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失去写作的优先权,给后来诗人的写作带来强烈的焦虑,他称之为“影响的焦虑”。中国古代的批评家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胡应麟说“大概杜(甫)有三难: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38},其中“极盛难继”正是“影响的焦虑”产生的根源。这与其说是杜甫的焦虑,还不如说是盛唐之后所有诗人的焦虑。毛奇龄《西河诗话》揭示中唐元、白诗风创变的动因,即说:“盖其时丁开、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侻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中略)不过舍密就疏,舍方就圆,舍官样而就家常。”{39}“怯于旧法”正是面对前辈巨大遗产而不甘被其范围的焦虑。赵翼对韩愈诗风的变革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40}下及宋代,则像王安石说的,“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41},以至于诗学宋调的蒋士铨也不得不感慨:“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42}对前人的同情中,又何尝不饱含着同病相怜的自叹呢!
从根本上说,赵翼认为自然本与人相待而交发其蕴,因此人的创造必日新无已。这就是《园中即事》所说的“天地有至文,花鸟与山水。当其生机妙,巧画弗能拟。亦必有解人,乃不虚此美”。既然“化工日眼前,触处无非是”{43},那么诗文也必日新月异,像陆游的创作那样“直罄造物无尽藏,不许天公稍自秘”{44}。但他由此不仅未激发起创造的自由和豪迈感,反而无奈地体认了艺术生命的短促及其悲剧性。因为“诗文无尽境,新者辄成旧”{45},在自然的无尽藏和创造的无尽境面前,个别作品的“新”终究是短暂而有限的。这样一种悲观意识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那组著名的《论诗》中达到了顶峰: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46}
惟其如此,“新”变得愈益需要追求,就像当今时尚更替的速度加快、周期缩短以后,人们不是放弃追逐时尚,而是制造更多的时尚。在袁枚颠覆所有文学经典的可模仿性之后,赵翼进一步对经典的永恒价值做了否定性的判决。仍是那组《论诗》,其二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47}乍看一派前无古人、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细味之也夹杂一丝悲观无奈的弦外之音。置身于生生不息的自然运化中,没有人能够永葆艺术生命常青,顶多只能引领一时的风骚。这听起来颇有点时尚理论的味道,的确,赵翼诗学的核心理念便是唯新,而唯新正是时尚的本质属性。我们在《瓯北诗话》中看到的赵翼,是清楚地将“新”放在首要位置的。如卷五论苏东坡,提到元好问《论诗绝句》“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颇不以为然:“此言似是而实非也。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48}严格地说,以新为尚也算预设了艺术目标,与性灵派的宗旨已有距离。不过,这终究不是赵翼诗学的理论归宿。享寿甚高且悠游林下多年的赵翼,晚年平心读书治学,不仅论学意气尽消,对诗歌的观念也有较大变化。
乾隆四十一年(1776),赵翼年五十,辞归里居已逾三载,有《杂题》九首。其九云:“有明李何辈,诗唐文必汉。中抹千余年,不许世人看。毋怪群起攻,加以妄庸讪。宋儒探六经,心源契一贯。亦扫千余年,注疏悉屏窜。《书》疑古文伪,诗斥小序乱。理虽可默通,事岂可悬断。竹垞西河生,所以又翻案。吾言则已赘,一编聊自玩。”{49}诗中对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和宋儒论学废弃注疏、独主心源的狭隘偏执作风,都作了批判,表明自己为文论学将立足于一个兼收博采、折中持平的立场。在赵翼讲学扬州期间“得晨夕过从,从容谈艺,与闻扬扢之旨”的门人李保泰,这样概括老师为诗之旨:“先生综括源流,默识神理,大指在自出新意,不斤斤于格调。”又述其论诗三言曰:“句中有意,句外有气,句后有味。”{50}这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赵翼65岁时的事,既主自出新意,又意、气、味并重,显出兼容综合的倾向。钱钟书先生说“瓯北晚年论诗,矜卓都尽”,“温然见道,慕古法先,非如随园、藏园、船山辈之予知自雄,老而更狂也”{51},也注意到赵翼晚年诗学的变化。那么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赵翼晚年朋辈凋零,诗中弥漫着浓重的寂寞感觉。七十四岁所作《遣寂》云:“少陵在成都,结交到朱老;东坡在海南,符秀才亦好。由来索居者,藉以慰枯槁。余性本落落,晚更少将迎。同辈已死尽,末契期后生。后生有才者,方自高其声。仰而不能俯,谁肯就老成?以兹绝裾屐,默作孤掌鸣。惜哉得佳句,无人共欣对。欲起古人看,古人已无在;欲俟后人赏,我又不及待。终朝块独处,嗒焉一长嘅。”{52}晚境体会到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寂寞,不禁使平生争名之心尽熄。翌年夏日所作《批阅唐宋诗感赋》云:“历朝诗帙重披寻,掩卷苍茫感不禁。千古真如飞鸟过,四时何限候虫吟。子云著述玄仍白,逸少胸怀后视今。赢得老夫长敛手,剩夸惜墨贵如金。”{53}此时的赵翼,阅历千古犹如一瞬,历史上所有的作家、著述都如过眼浮云,而诗史生生不息,各色诗人如鸟鸣春、虫吟秋一般应时而起,各写其诗。什么是经典?什么是成功?甚至“新”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诗家径路都开尽,只有求工稍动人。”{54}诗的问题只剩下好不好,别的全都不重要了。于是他对诗的艺术追求同袁枚一样,最终也归结于一个“工”字。嘉庆九年(1804)78岁所作《论诗》云: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出东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挂角,天马奔绝尘。其实论过高,后学未易遵。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古疏后渐密,不切者为陈。(中略)是知兴会超,亦贵肌理亲。吾试为转语,案翻老斫轮。作诗必此诗,乃是真诗人。{55}
这里由苏东坡诗论兴感,涉及严羽“羚羊挂角”、王渔洋“伫兴”、翁方纲“肌理”诸说,主旨落实于“切”。这正是袁枚推倒前人所有论说退守的底线,赵翼晚境竟然也归结于此。其论诗尚新的出发点虽不近于袁枚,但始离终合,最后仍与袁枚的性灵诗学同归一辙。
的确,直到生命的最后年头,赵翼的诗歌观念仍有微妙的变化。在他再三写作的《论诗》中,他虽仍嗤斥“拾残牙慧”,但更厌恶掉书袋(满地撒钱难入贯)和用意刻苦(汲泉垂绠漫钩深),而相信“祗应触景生情处,或有空中天籁音”{56}。到下世的前一年,又有《称诗》一首说:“称诗何必苦争新,无意为诗境乃真。”{57}在发挥前诗崇尚自然的前提下,他似乎放弃了“争新”的执念,《遣兴》也有“老境诗篇不斗新”的自白{58}。尽管平生最后一首《论诗》,仍以争新为前提否定了诗必汉唐的胶固{59},但我们终究能够感觉到他晚年唯新意念的动摇。这除了与万念俱灰的垂老心态相关外,还应该与诗传不传全凭运气的体认有关{60}。放弃争新意味着放弃独创性的追求,这在赵翼不过是晚境无聊之思,但无意中却呼应了诗坛正涌动的自我表现极端化、绝对化的思潮,成为新潮流的先声。考察嘉庆以后诗学中的绝对自我表现论{51},赵翼晚年对争新的扬弃,应该视为其理论渊源的一个分支。
注 释:
①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6页。
②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77页。相关研究还有张明曙《论赵翼的诗歌创新主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毕桂发《赵翼论诗的宏观视野和创新精神》,《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等多篇论文。
③王建生:《赵瓯北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
④周明仪:《赵瓯北诗及其诗学研究》,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87-97页。
⑤陇兴龙、王洁:《从〈江北诗话〉和〈瓯北诗话〉看洪亮吉和赵翼的诗学观之相似性》,《教育交流》2008年第10期;李永贤、吕会玲《赵翼、袁枚诗学观异同初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梁结玲《略论〈瓯北诗话〉论诗的先进性与保守性》,《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5期;吴兆路《赵翼诗学思想述论》,《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学位论文有李成玉《赵翼诗学思想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王继承《赵翼诗歌理论研究》,齐齐哈尔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李铮《赵翼性灵诗论探究》,宁夏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有关赵翼研究的概况,可参考吕会玲《赵翼研究综述》,《现代语文》2009年第4期。
⑥⑧{14}{15}{16}{24}{28}{32}{37}{40}{46}{47}{52}{53}{54}{55}{56}{57}{58}赵翼:《七十自述》其三十,《瓯北集》卷三十七,《赵翼全集》(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第572页,第652页,第654页,第883页,第551页,第141页,第1022页,第1105页,第1105页,第510页,第510页,第836页,第851页,第952页,第938页,第1055页,第1078页,第1097页。
⑦赵翼:《偶书》其二,《瓯北集》卷二十三,《赵翼全集》(第5册),第387页。
⑨赵翼:《瓯北集》卷一,《赵翼全集》(第5册),第1页。按:《瓯北诗钞》删“是古而非今,一步不可履”二句。
⑩{12}{23}{43}{44}{45}{48}{49}赵翼:《瓯北集》卷十一,《赵翼全集》(第5册),第168页,第3页,第418页,第388页,第446页,第413页,第53页,第396页。
{11}俞兆晟:《渔洋诗话》序,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3页。
{13}赵翼:《连日笔墨应酬书此一笑》,《瓯北集》卷十,《赵翼全集》(第5册),第157页。
{17}{18}{20}{33}{34}{50}赵翼:《瓯北诗钞》卷首,《赵翼全集》(第4册),第7页,第5页,第8页,第16页,第18页,第16页。
{19}祝德麟:《瓯北诗钞序》借客之口曰:“瓯北之诗,好论驳。”《赵翼全集》(第4册),第9页。
{21}赵莲城:《书瓯北集后》卷上,《豹隐堂集》,光绪间杏花村舍刊本。
{22}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66-2367页。
{25}有关这方面的比较,李永贤、吕会玲《赵翼、袁枚诗学观异同初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李铮《赵翼性灵诗论探究》(宁夏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都有较细致的论述。
{26}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27}袁枚:《答李少鹤》,《小仓山房尺牍》卷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册第208页。
{29}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补订本,第133页。
{30}赵翼:《题周松霭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瓯北集》卷三十九,《赵翼全集》(第6册),第768页。
{31}周春:《耄余诗话》卷二,国家图书馆藏葛继常钞本。
{35}卫既齐:《沈平远诗稿序》,《廉立堂文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36}延君寿:《老生常谈》,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43页。
{38}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91页。
{39}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七,《西河合集》,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
{4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陈辅之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0页。
{42}蒋士铨:《辨诗》,《忠雅堂诗集》卷十三,清嘉庆间刊本。
{50}赵翼:《瓯北诗钞》卷首,《赵翼全集》(第4册),第16页。
{51}钱钟书:《谈艺录》,第132页。
{59}赵翼:《瓯北集》卷五十三《论诗》:“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赵翼全集》(第6册),第1104页。
{60}赵翼:《瓯北集》卷五十二《佳句》:“诗从触处生,新者辄成故。多少不传人,岂尽无佳句?”《赵翼全集》(第6册),第1079页。
{61}关于嘉、道之际诗坛的绝对自我表现论,可参看蒋寅《乾嘉之际诗歌自我表现观念的极端化倾向——以张问陶的诗论为中心》,《复旦学报》2014年第1期。
The Innovation-Orientation in Zhao Yis Poetics and Its Separation
and Reunion with Xing Ling School
LI Qiu-xia,JIANG Yin
Abstract:Abstract: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was always be considered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special value of Zhao Yis poetics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s a result,his poetics was only being put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Xing Ling School and being explained along this line of thought. Its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was not being inquired yet.Starting from Zhao Yis anxiety for literary fame and Pess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terary value,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Innovation-orientation of Zhao Yis poetics was rooted in his eagerness for surmounting predecessors,and its driving force wa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lthough Zhao Yis poetics took Xing Ling as the keystone,he did not consider it as a aim like Yuan Mei. Instead, he saw it just as a tool. As he got older and lonelier,he changed his poetic concept. That is,he turned gradually to pursuing perfectness instead pursuing innovation. He even abandoned the idea of competing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poets. Unconsciously,Zhao Yi echoed the poetry circle in which the trend of thought was surging that self-expression was being putting to extreme and absolute .His change became the first signs of the absolute self-expression concept in the poetics of Jiaqing-Daoguang period.
Key words:Zhao Yi;poetics;innovation-oriented;Xing Ling school
(责任编校:文 建)